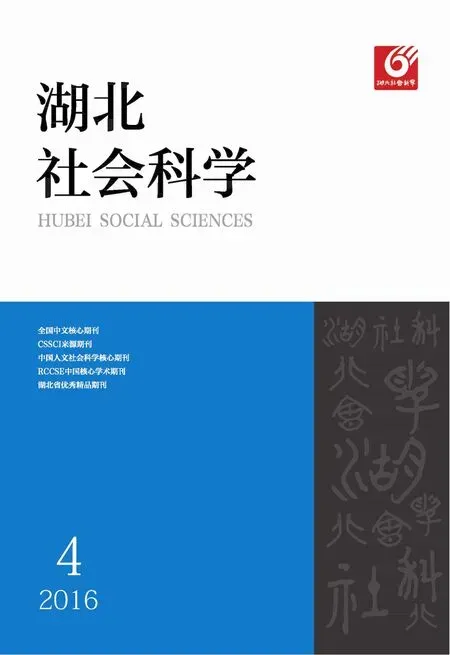“無可無不可”:淺析儒家的行道精神
劉春嬋(華南師范大學國際商學院,廣東 廣州 510631)
?
“無可無不可”:淺析儒家的行道精神
劉春嬋
(華南師范大學國際商學院,廣東 廣州 510631)
摘要:根據對《論語》、《孟子》中相關思想的詮釋,能夠理解儒家的“行道”精神。通過孔子的身體力行,“行道”精神開始注入儒家的傳統之中,孔子所說的“無可無不可”集中體現了這種“行道”的精神,孟子則直接繼承了這一精神,并予以完善和發展。由于孔、孟二人的努力,“行道”精神最終發展成為儒家思想的重要一面,從而在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中得以繼承與發揚,而“行道”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及其價值追求。
關鍵詞:孔子;孟子;儒家“行道”精神;“無可無不可”
一、從《烏托邦》中的比喻說起
“明智之士,或者說真正的哲學家,何以會逃避政治?”關于這一問題,柏拉圖的《理想國》曾經做了說明,而托馬斯·莫爾則在《烏托邦》一書中,借助于自己所假想的、游歷廣泛的哲人拉斐爾·希斯拉德之口,給出了進一步的解釋:“哲學家看見其他人沖到街上,在瓢潑大雨中被淋得渾身濕透。哲學家無法勸服他們進屋避雨,他知道,自己若是也走出去的話,只能同樣被淋濕,因此,他就自己待在屋子里,而且,由于對他人的愚蠢束手無策,也就只能用這樣的想法來安慰自己:‘好吧,不管怎樣,至少我自己還不錯。’”[1](p71)
如果僅從歷史的情境來分析,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中所說的這個比喻,對于儒學的兩位奠基者孔子和孟子來說,無疑也是十分恰當的。孔、孟二人所處的春秋戰國時期,正是一個“禮崩樂壞、處士橫議”的時代,因此,明智之士大概會選擇“獨善其身”,而不肖之輩恰足以汲汲營營。面對如此不堪的現實,儒學的兩位奠基者會做出什么樣的選擇呢?“獨善其身”,抑或是“汲汲營營”?對于這一問題的回答,一種不失為有益的“后見之明”為我們提供了幫助,正如歷史所告訴我們的,儒家的兩位奠基者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給出了完全不一樣的答案。事實上,孔、孟二人的選擇既不是躲進屋里,充當獨善其身的“自了漢”,也不是庸俗地融入現實,投身于追名逐利的大潮之中。憑借著一股堅定的“行道”精神和對理想、信念的執著追求,孔、孟二人為我們展現了另一種別具風采的人生道路。
通過對《論語》、《孟子》中相關思想的詮釋,本文試圖抓住“行道”精神在這兩部儒家經典著作中的呈現方式,從而更好地理解“行道”精神是如何被注入到儒學的傳統之中。文章從論述孔子的“行道”精神出發,緊接著考察了孟子對“行道”精神的繼承和完善,最后,本文簡要地分析了“行道”精神在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之間的傳承與影響,簡單地說,“行道”精神至少部分地塑造了傳統知識分子的人格及其價值追求。
二、“無可無不可”:孔子的“行道”精神
在《論語·微子》篇中,記錄了一段孔子對前賢的評論:“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其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根據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里的注釋:“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2](p186)所謂“逸民”,大概也就略等于我們今天所理解的隱士之類的人物,或者是柏拉圖、托馬斯·莫爾等人所說的“明智之士”、“哲學家”。因此,通過孔子對“逸民”的評價,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對于那種“待在屋子里”的避世方式,孔子本人實際上也是非常清楚的,并且,還有著很高的評價,孔子認為:“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論語·憲問)。然而,他卻進一步指出:“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那么,孔子所說的“無可無不可”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或者說,“無可無不可”何以異于伯夷、柳下惠等人的處世方式呢?
如果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就必須更好地理解孔子本人的人生追求,事實上,通過“無可無不可”這一表述,孔子想要說明的也恰恰是他自己的人生追求。在與其弟子的問答中,孔子對顏淵、子路等人宣稱,他的志向即在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冶長),孔子自信,“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論語·子路),因此,孔子最根本的關懷即在于“行道”。為了實現這樣的理想,孔子周游列國,一生皆在顛沛流離中度過。然而,當時的政治環境卻并沒有為他提供一個實現其理想、抱負的機會,直到在瓢潑大雨中被淋得渾身濕透之后,孔子也忍不住發出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論語·公冶長)的感嘆。
此外,在《論語》一書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孔子的行為經常會遭到當時的隱士之流的嘲弄。例如,石門的司門者說他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論語·憲問)、荷蓧丈人則譏諷其“四體不勤,五谷不分”(論語·微子),而長沮、桀溺更是直截了當地對子路說:“與其從辟人之士,不如從辟世之士”(論語·微子)。從《論語》中的相關記載來看,對于這些隱逸之流的評價,孔子基本上還是比較認可的,不過,他也為自己的行為做了辯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論語·微子),朱熹將其進一步解釋為“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2](p185)換句話說,恰恰是在這種“天下無道”的情況下,孔子才堅持要以其“道”易天下,欲將海潮音化作獅子吼,因此,朱熹的上述詮釋可謂是深得圣人之心。行文至此,孔子之所以不愿意“待在屋子里”的原因也就很明白了,簡單地說,孔子的一生即是以“行道”作為其使命的,因為“行道”之使命感的存在,促使他既不愿意也不可能會選擇“待在屋子里”。通過“無可無不可”,孔子所想要表達的,其實也就是這種“行道”的精神。
但我們也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行道”的使命感對于孔子來說,不僅僅意味著一種“入世”的積極努力,更為重要的是,“行道”還是一種極為豐富的精神資源,并為其種種行為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正是通過孔子的言傳身教,“行道”的精神開始被注入儒家的生命之中,從而幫助儒家找到了一種“可恃以批評政治社會、禮抗王侯”的精神憑藉,[3](p88)余英時先生曾經使用“哲學的突破”來概括孔子的這一貢獻,在我們看來,這種評價是十分恰當的。孔子認為,“士”應當以“道”為己任:“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里仁);“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論語·先進)。因此,孔子為儒家所注入的其實是一種全新的人生理想和價值追求。儒家的“行道”精神不僅體現為一種“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的關懷,更重要的是,“行道”精神還表現在對“道”的固守與堅持,這就使得原本即已存在的“儒”,[4](p149-152)開始展現出完全不同的精神風貌。
“行道”精神是孔子一生的價值皈依,此外,“行道”精神也是孔子在仕途中進退、取舍的判斷標準。正是由于感受到了自身所承擔的“行道”使命,所以縱然是公山弗擾、佛肸這樣的“亂臣賊子”相召,孔子亦“欲往”,“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此所謂“無不可”是也;同樣是因為對“行道”的堅持,所以“衛靈公問陳”,“(孔子)明日遂行”(論語·衛靈公)、“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論語·微子),此所謂“無可”是也。因此,從這種“無可無不可”中所折射出的,正是孔子為儒家所注入的那種“行道”精神。
在這一部分的最后,我們還想多花點筆墨,簡單地說明一下孔子所謂的“道”的內涵。既然孔子的一生是以“行道”為志業的,那么,孔子所欲行之“道”又是指什么呢?雖然孔子并沒有明確地對其進行說明,然而,通過對《論語》的閱讀和把握,這個問題其實也并不難回答。事實上,孔子所說的“道”無外乎仍是以“仁”和“禮”為其核心的,因此,“行道”也就是“行仁政、復禮樂”。根據《論語·顏淵》中的記載,孔子曾告之其最得意的弟子顏淵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當顏淵進一步“請問其目”的時候,孔子答之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通過這樣的一問一答,孔子所欲行之“道”,已然是不言而喻的了,由此,我們也可以更好地理解,顏淵之死何以會讓孔子“哭之慟”,并且宣稱這真是“天喪予!天喪予!”(論語·先進)。
三、“愿學孔子”:孟子對“行道”精神的繼承與完善
孔子為儒家所注入的這股“行道”精神,在孟子那里得到了很好的繼承。由于處在一個“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的時代,孟子不僅繼承,而且也進一步發展了孔子的基本理念,正如程頤所說的:“孟子有功于圣門,不可勝言。如仲尼只說一個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個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5](p1-58)僅以“行道”精神而論,孟子對孔子的繼承與發展也是十分明顯的。
與孔子一樣,孟子所處的時代也可稱得上“大雨傾盆”,而且,情況似乎更為嚴重,誠如顧炎武在《日知錄·周末風俗》中所指出的:“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6](p221)因此,在當時的情況之下,選擇什么樣的人生道路,對于孟子來說,同樣也是一個極為嚴峻的現實問題。孟子關于“圣”之類型的劃分,其實就是在孔子“逸民”之論的基礎上所做的進一步拓展,并且,還特別加入了“治亦進,亂亦進”的伊尹以及孔子本人,而孟子所說的“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孟子·公孫丑)也正是孔子所說的“無可無不可”的具體闡釋,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朱熹在其為《論語》所做的集注當中,也恰恰是用孟子的這句話來解釋“無可無不可”的。[2](p715)通過孟子的闡釋,孔子所說的“無可與不可”的內涵變得更加明確,所謂“無可無不可”,孔子強調的其實是要尋求“行道”的時機,亦即孟子所謂的“圣之時者”。通過不同人生選擇的比較,孟子指出:“乃所愿,則學孔子”(孟子·公孫丑上),這就清楚地向我們揭示出了孟子對孔子的繼承。
但問題在于,孟子到底從孔子那里繼承了什么?或者,用孟子自己的話來說,他本人“愿學孔子”的哪些方面?關于這個問題,研究孟子之學甚力的臺灣學人黃俊杰先生曾指出:“孟子想學的是孔子畢生為人處世那種建構在深刻的時間意識之上的與時俱進的精神。”[7](p187)但在我們看來,這種“建構在深刻的時間意識之上的與時俱進的精神”,具體而言,就是本文所論述的“行道”精神。事實上,孟子“后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于諸侯”(孟子·滕文公下),無非就是在尋覓一個行道的機會,正因為如此,即便是像滕、宋之類的小國,孟子也不愿意放棄其“行道”的努力,而對于曾經的東方霸主齊國和齊宣王,想要“援天下以道”(孟子·離婁上)的孟子,則更是寄予了相當高的期望,因此,當他由于種種原因而不得不離開齊國的時候,孟子“若有不豫色然”,他向自己的學生充虞感嘆道:“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孟子·公孫丑下)于斯可見,孟子“行道”之心的迫切。
除了積極地尋覓“行道”的機會之外,更加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孟子還真正地繼承了孔子“以道自任”的精神。由于生活在一個“諸侯放恣,處士橫議”的時代,當時的策士之流,如周霄、公孫衍、張儀以及惠施等人,皆曾出入于各國公侯的王庭,尤其是公孫衍、張儀之輩,更具有所謂的“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的威勢,然而,孟子卻很少與這些人交往,[8](p24)并且,他還曾嚴厲地斥責這種人不過是“以順為正”,乃“妾婦之道”,孟子認為,真正的“大丈夫”,應當“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正是因為承載著這種“行道”的使命,孟子堅持主張,“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孟子·公孫丑下)憑借著這一點,孟子得以在精神上禮抗王侯,即便是與梁、齊等大國的國君相處,也始終能夠不卑不亢。例如:孟子曾直言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孟子·梁惠王上);盡管齊宣王對其禮遇有加,“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鐘,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孟子·公孫丑下),然而,孟子卻堅決地予以拒絕。孟子的這種“進退必以其道”的處事方式,的確迥異于當時的公孫衍、張儀之流,但與孔子所說的“無可無不可”,卻是若合符節的。
與孔子不同的是,孟子實際上更為明確地說明了其所欲行之“道”,也就是他本人所一再宣稱的“王道政治”的理想,誠如黃俊杰先生指出的,“(孟子)所謂‘王道’,是指‘先王之道’,以德治為基礎,以民本為其依歸”,[7](p246-248)因此,我們認為,孟子所欲行之“道”仍然不離孔子所說的“仁”和“禮”等基本范疇,只不過,孟子更多地討論了一些制度設置的問題(如君臣關系、井田制度、五等爵制等等),但從根本上來講,孟子所欲行之“道”基本上仍是對孔子的繼承和發展。
四、“憂以天下,樂以天下”:“行道”精神的傳承與發揚
孔子開始將“行道”精神注入到儒學的傳統之中,孟子則進一步完善并發展了孔子的這一“行道”精神。由于孔、孟這兩位儒學奠基者的不懈努力,“行道”精神開始融入儒家傳統,成為儒學的基本特質之一,并在此后的儒家知識分子那里得到了繼承與發揚,北宋政治家范仲淹所說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集中地反映了儒家知識分子對這種“行道”精神的繼承與發揚。當然,由于政治環境的變化,儒家知識分子們的“行道”努力也逐漸呈現出多樣化的色彩:
首先,一部分儒家知識分子繼續走“上行”的路線,隨著君主制的確立,這種“上行”路線自然而然地將全部希望寄托在君主身上,亦即“格君心之非”、“得君行道”。例如:作為第二期儒學的展開,宋明理學通常被視作一種“義理”、“心性”之學,[9](p162)然而,理學家們卻并沒有躲進書齋里,與之相反,他們幾乎從未放棄過“得君行道”的努力。關于兩宋理學家們的不懈努力,余英時先生在《朱熹的歷史世界》中有過相關的描述,至今讀來,仍令人為之動
容。[10](p3-64)
其次,由于秦漢之后大一統局面的形成,儒家的“行道”理想更為經常地感受到來自于“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的皇權的壓力,因此,也有一部分儒家知識分子開始轉入“下行”的路線,而這種“下行”路線即試圖從民間社會中挖掘資源,所謂儒者之效,“在下位則美俗”(荀子·儒效),通過對一鄉、一里的改善,儒家知識分子們至少能夠在部分上實現其“行道”的理想,事實上,北宋的張載、“呂氏鄉約”的發起者呂大鈞、呂大臨等人均有過類似的思想或者嘗試。[11](p35)
最后,我們還想簡要地要討論一下牟復禮(F.W.Mote)、杜維明等人所說的“儒家隱逸主義”(Confucian Eremitism),[12](p60)這一類型的儒家知識分子的主要代表有元代的劉因、明末清初的顧炎武、王夫之和黃宗羲等人,事實上,儒學傳統中的“曾點精神”,以及在宋明理學的開山鼻祖周敦頤等人的身上,[1](p213-215)我們都或多或少地能夠看到這種“隱逸主義”的傾向。問題在于,這種“隱逸主義”是否與本文所論及的“行道”精神相沖突呢,二者之間雖然存在著一定的張力,但卻并不是互相矛盾的。這里的原因在于,劉因、顧炎武等人所處的政治環境,使得他們的“隱逸主義”看上去更像是一種無奈之舉,此外,“劉因并非完全沒有接受過官方委任”,[5](p59)而顧炎武、黃宗羲等人更是不忘關懷天下,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日知錄·正始),我們很難想象,一位真正的隱逸之士會有類似的主張。關于這一點,陸九淵所說的“儒者雖至于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于經世”,[13](p80)真可謂是一語中的。因此,在我們看來,“隱逸主義”并不否定“行道”精神在儒家知識分子之間的傳承。
綜合以上論述,我們認為,盡管在形式上仍然存在著差異,但孔、孟為儒學所注入的這股“行道”精神卻仍然得到了繼承與發揚,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行道”足以稱得上是儒學的典型特征之一,也是儒家知識分子們最為根本的價值理想與人生追求。
對于任何一代人來說,是否投身于政治或者說公共事業,都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那么,明智之士應該如何面對政治?關于這一問題的回答,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大致為我們提出了三種不同的選擇:一是道家所主張的“隱”;二是法家所主張的“仕”;三是本文所論述的儒家“行道”精神,亦即孔子所說的“無可無不可”。[13](p17)其中,道家傾向于潔身自好的“隱”與儒家懷抱著道德和政治理想而出仕經世的努力,都相應地得到了人們很高的評價,但由于道家式的“隱”通常顯得更為逍遙和自在,因此,也更容易引起知識分子們的認同(如前文所說的柏拉圖、托馬斯·莫爾)。然而,本文認為,能夠清楚地認識到自己對于這個世界的責任,既能夠有所擔當,又能堅守住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負,正如儒家所展現出來的這種“行道”精神,不僅自有其獨特的魅力,而且也應獲得人們更多的尊敬。事實上,“行道”精神在儒家知識分子之間的傳承與發揚,已經為我們充分地展現了其自身的活力,而對于今天的知識分子以及公務人員來說,這種“行道”精神也仍然沒有失去自身的意義,從而能給予我們一定的啟發。
參考文獻:
[1]杜維明.道·學·政:儒家公共知識分子的三個面向[M].錢文忠,盛勤,譯.北京:三聯書店,2013.
[2]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1.
[3]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章太炎.國故論衡[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5]王孝魚.二程集[M].北京:中華書局,2004.
[6]陳垣.日知錄校注[M].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
[7]黃俊杰.孟子[M].北京:三聯書店,2013.
[8]錢穆.先秦諸子系年[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9]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一卷)[M].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
[10]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
[11]錢穆.宋明理學概論[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12]Frederick W.Mote.Confucian Eremitism in the Yuan Period[C].in Wright A F.ed.,The Confucian Persua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0.
[13]鐘哲.陸九淵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0.
責任編輯高思新
作者簡介:劉春嬋(1980—),女,華南師范大學國際商學院講師,博士研究生。
基金項目: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先秦散文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15YJC710032)。
中圖分類號:B222
文章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477(2016)04-012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