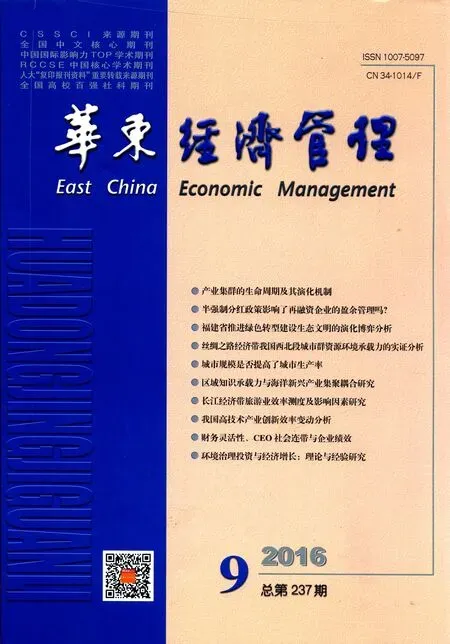社會媒介環境下高校輿情新變分析與危機應對
姚江龍,魏 捷
(1.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公共事務學院,安徽合肥230026;2.安徽農業大學辦公室,安徽合肥236000)
社會媒介環境下高校輿情新變分析與危機應對
姚江龍1,魏 捷2
(1.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公共事務學院,安徽合肥230026;2.安徽農業大學辦公室,安徽合肥236000)
做好高校輿情工作是高校危機管理的重要內容。快速發展的社會化媒介平臺,創設了全新的信息傳播與人際交往方式,使得高校輿情生成與演變呈現新的變化。面對社會轉型帶來的“變革式焦慮”,高校師生以社會化媒介平臺實施“自主性宣泄”,將個體訴求在“符號式表達”中予以“情緒化內聚”,并在“圈群式存在”中實施“交往式擴散”,推進個體意見和情緒不斷放大與升級,使得高校輿情在“流動式匯聚”中實現“群體性發力”,給高校危機管理帶來挑戰。鑒于以上新變,應對高校輿情危機,應當區分類型與層次,科學運用策略與方法,實施“分層式干預”與“微方式化解”,以確保高校穩定與發展。
社會化媒介;高校輿情;新變;危機應對
一、源起:“變革式焦慮”與“自主性宣泄”
一直以來,社會改革與教育改革協同推進、同向驅動,社會上各類流行傾向與思潮必然滲透并影響到高校師生身上。在大眾化發展中,高校與社會實現了深度融合,其與社會之間的“發展共同體”與“危機共同體”凸顯。大學生處于成長成熟的發展階段,其對自我個性釋放與未知領域渴求,表現出較強的探求欲望和行動傾向,是高校輿情的最大攪動者、施動者、受動者。與此同步,由于改革與轉型,讓他們時常面對不斷加大的學業、生活和就業壓力,進一步加大其焦慮感,甚至有個別人無法直面壓力,或逃離逃避,或沖動易動。復旦投毒案折射出大學生人際焦慮,不斷升溫的“放松專業、抓緊考證”現象透露出大學生就業焦慮。這些焦慮和緊張感,在個體中滋生,在群體中傳播,以潛輿情的形式存在,時刻牽引著危機事件的出現。
輿情在表達中形成,是意見和情緒的匯聚。社會化媒體讓每個個體從技術層面擁有了自主表達的渠道與話語存放的空間,被稱為“全民DIY”。這種自助化的草根媒介,為廣大大學生提出了可以擺脫議
程設置、自主釋放個性的理想場所。由于存在一定的“面具”效應[1],自媒體在傳播中所表達的更多是個體情感,而非對事實的理性認知,所以在各類自媒體平臺上,充斥著大量多元化的思潮、觀念、話語,其在解構、重構以及大話、戲謔中宣泄情感、化解焦慮。大學生們無須刻意注意自己“微世界”中的言行,憑借自我心中的自由、正義以及是非標準,以排山倒海之勢在虛擬空間傳遞蔓延自己的感受,雖排遣了內心的緊張感、焦慮感等不良情緒,同時也加大了輿情危機風險。
虛擬空間的大學生如同“脫韁的野馬”,奉行“我的地盤我做主”,以“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方式霸占社交媒體的話語空間,在“刷屏”中找尋“存在感”與“暢快感”。對各類社會現象或問題,大學生好沖突、好表達,輕信與從眾突出,對一些流言或傳言往往“大膽地假設”,急切地判斷和評價[2]。“狂歡”與“宣泄”是一種非制度化的政治表達,當下雖不常存在于現實的街角,但社交媒體為這一形式提供了空間重構與再生的歷史契機。蘭斯·班尼特(Lance Bennett)和亞歷山大·賽格博格(Alexandra Segerberg)認為,“社交媒體賦予個體以信息傳播、組織動員的力量,傳統的集體行動已轉變為個人化的聯結行動(connective action)”[3]。此外,少數人通過策略性“經營”社交媒體和掌握網絡話語權,便可將小眾觀點“制造”成社會主流意見,壓制社會觀點的多元化發展[4]。新媒體使抽象的“網友”變成具象的“朋友”,從“點贊”、“評論”到“轉發”,彼此之間的每一次互動都催生個體情緒的“感染式”擴散,進而加大輿情的“集群化”與“危機化”傾向,讓“上網”與“上街”在同一空間中演變。
二、呈現:“符號式表達”與“情緒化內聚”
不論媒介形式如何發展變化,個體必然以某種形態參與到各類網絡活動中。這一形態可能超越傳統時空的限制,帶來網絡社交環境下個體交往的“去身份化”與“無約束感”。物理缺席的個體,通過對自身表征的多媒體符號化實現了對網絡時空的在場[5]。在社交圈層成員之間頻繁“點贊”、評論轉發的過程中,個體具象、音容笑貌實現了符號式在場,缺席的是身體、在場的是情感、呈現的是符號。在場的情感與訴求符號,由于抽離了個體的限制屬性,沒有了社會的階層壓力場,其呈現形態及表達方式直接而大膽,甚至出現無底線宣泄、無理由索取。缺少“他人在場”,日常生活中被壓抑的“丑與惡”,會在這種無約束或低約束的狀態下不斷宣泄[6]。
除“去身份化”外,個體在言論表達中,根據傳播擴散的需要,往往將輿情核心要素、人物情節抽離并符號化、概念化、標簽化,賦予文學藝術及文化想象的功能或元素,形成社會諷刺和認知模型[7],從而超越單個輿情事件本身,在個體與個體、事件與事件、文化與文化中的相互關聯與牽扯中,指向社會與高校某些長期積壓的共性問題和現象。趙鼎新認為,“話語和符號性行為在集體行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8]。網絡上最具鼓動力的表達,需要在迎合網民情緒的基礎上訴諸修辭建構。在信息構建與表達設計中,大學生情緒表達顯示出新奇、大話與娛樂心理,將一些難以言狀的情緒轉化為形象、逼真的符號,借助“詞媒體”宣泄。雖無從查證“我爸是李剛”信息的真假,但其包含的情緒回應了網民的集體記憶和共同心理想象,足以保持其高位傳播擴散。微時代,表達的“快餐式”,語言信息的“微方式”與“碎片化”存在,適應了當下人們快節奏的生活方式,滿足了個體既想表達情感又想含蓄內斂的想法,受到廣泛追棒。所以,往往一個圖片、表情、短語甚至一個標點,都傳遞了交際主體的心跡與感受。這些符號形式簡單、形象生動、趣意盎然、傳遞方便,雖初次創作較難,但傳播與再創較易,且在再傳播與再創作中對交際雙方的共同聯想、共同相像實現了再激發,為符號意義注入了更為豐富的內涵與價值。
雖說“人機”替代了“人際”,“虛擬”融入了“現實”,“場域”重構了“場景”,但多變的符號之下依然是個體的真實訴求,這些訴求或為私利或為公益甚至為宣泄,既是輿情的表征,也是輿情的動因,更是個體主體性的呈現。充當個體之間黏合劑的是個體表達中借助符號而釋放的情緒。羅伯特·利珀(Robert Ward Leeper)把情緒定義為“一種具有動機和知覺的積極力量,它組織、維持和指導行為”。正如前文所分析的,不斷滲透的現代性社會風險,加大了高校師生特別是大學生的焦慮情緒。大學生活是人生的重要轉折點,成長進步需要過程,看清看透現象、合理控制情緒需要閱歷與積淀。而未來的不確定性、發展環境的突變性,物質訴求、精神滿足、情感追求等與個體期待以及付出成本之間的差距不斷加大,個體表達符號中情緒內聚性加大,輿情生成與異變的概率必然同步放大。
有研究表明,在面對問題與壓力時,大學生主要使用情緒應對策略來緩解壓力[9],且他們更多選擇網絡,而非現實中面對面的人際傾訴。情緒聯結著主體的思想與感情。大學階段是人生重要的成長階段,大學生個體往往具有豐富的情感與躁動的行為,對外界較易敏感且對個體較難控制。在社會化媒介中,所傳播信息是否吸附且吸附多少情緒,是被關注、轉發和評論的重要預測指標。有研究指出,輿情形成是主題訴求演化的結果,主題訴求之所以演化
在于其吸附了情緒和訴求,吸附力越大,演化進程就快,根據“吸附力指數=包容度×(敏感度+利益相關度)”[10]這一模型可得知,越是與大學生利益相關的,越容易引起關注;容易被關注的,就容易形成輿情;越易形成輿情的,就越快催生危機。于是常看到,大學生容易捕捉并關注與切身利益相關的消極情緒,并在傳播中放大,以形成輿論壓力推進問題解決。
三、特質:“圈群式存在”與“交往式擴散”
“圈群式存在”的特征,既體現個體關系結構形態的“圈群式”,也展現了個體信息及輿情傳遞的“圈群式”。人是群居性動物,在現實社會和網絡世界中,一直在一定的關系圈子中生活與交往。早期,這一“部落化”的生存方式是自然形成的。當下,社會化“自媒體”、“微媒體”共同組構了一個以“找組織”、“結圈子”為模擬形態的“半熟社會”[11]。在此關系結構中,信息傳播擴散以個體為“源點”或“節點”,每個個體都可能成為他者與外界聯系的中介,由此形成了基于新媒介技術的“再部落化”圈子[12]。這一圈子結構中,既有親朋好友式的“熟人”,也有一面之緣的“生人”。一面之緣的“生人”往往并不完全陌生,屬于“輕熟人”式的“弱關系聯系”。在與“熟人”與“生人”的溝通中,個體分層建立起自己的“小世界”,且借助他者與其他圈子形成“嵌套”,為信息及輿情擴散提供了渠道。
個體的關系結構形態決定了信息傳播的主要路徑。在傳統媒體時代,其信息是由點到面的大眾式傳播,但自媒體傳播方式是圈群化,信息通過交際圈群,以點對點或點對群的形式傳播[13]。當下大學生嫻熟使用各類新媒體技術,形成了以自我為中心的生活與交往習慣,更加劇其對這一關系結構的歸屬感和親近感,且都能夠根據自己喜好,以自我為中心,自發組織起不受現實規訓與壓制的自組織與交往圈群。所以,大學生輿情在生成發展與演進轉化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以輿情核心主體為圓心的輿情中心圈[14]。由主題輿情形成的圈群,在誘發事件的不斷發展中實施著變化與轉移。主題輿情群內外匯聚的大學生,在信息傳播與意見碰撞中,同步進行著轉向與遷移,既有進入中心圈,也有離開中心圈,形成“圈群式”存在結構及交流方式,加大了外圍圈與中心圈之間的轉換,同步增大了個體與輿情的主體活性以及升級極化的概率。
“圈群式”交往關系,推動“強關系聯系”向“弱關系聯系”轉變。馬克·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認為,“弱連接”雖然不如“強連接”那樣堅固,卻有著極快的、低成本和高效能的傳播效率。“輕交往”、“輕聯系”模式,沒有物理上的束縛與場所,沒有儀式上的開始與結束,沒有套路、沒有程式,自由進出、來去悄然,改變了傳統時空統一的交流方式,在現代性時空分離下形成新的交往模式,導致了人際關系的“脫域”。“脫離出來”的人際交往關系,人的真實個性缺失,實現了“虛擬群性”,即個體在虛擬環境下遭遇強制性的行為規范和思維規定,進而形成一種被動意義的去個性化和同質性[15],實現信息意見一致化,催使輿情快速形成。也因此時常看到,經由網絡的討論能迅速形成輿論。當大學生與新媒體環境結合后,這一現象更為突出。多數大學生習慣以激情代替理性、以不假思索代替深入探究,看似平等、寬松的對話、發帖與討論的背后,主導輿論、極化輿情已在一片點贊、評論中悄然形成,更多的個體在討論中實現了被動意義上“沉默”和“從眾”,形成澎湃熱情,推動出現“政策窗口”。
新媒體內具的“朋友圈”、“訂閱號”,提供了快速獲知信息的通道,同時主觀化、小圈子化的信息接收模式,不可避免地使大學生進入被創設的信息環境,導致看問題窄化、刻板與擬態,從而拉低了大學生用于理性思考的智慧。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指出:“當一個人需要對事件做出判斷,而又無法接觸到大量真實信息的時候,他總是很樂意將他個性化的情感傾向模式套用在對事件的理解上,形成了他所理解的有別于真實環境的虛擬環境。”[16]正如凱斯·桑斯坦(Cass R Sunstein)在《信息烏托邦》中所描述的那樣,“只注意自己選擇的東西和使自己愉悅的通訊領域,將自身桎梏于像蠶繭一般的繭房中”[17]。“圈群化”的生存與交往,以及由此帶來的信息接收,讓大學生沉迷于自己創設與喜愛的媒介與社交環境中,在“自我空間”中任意地宣泄與狂歡,如同進入了“信息繭房”。封閉環境下的孕育功能帶來的是爆炸式的擴散與危險。當敏感信息聯姻微媒體,再輔助以“圈群”與“繭房”,“極化”與“爆棚”的隱患必將就此種下。一旦封閉的空間被打破,“圈群”與“圈群”之間的互動加快,輿情必將從“繭房”破出,給危機管理帶來挑戰。
四、力量:“流動式匯聚”與“群體性發力”
“社會輿論的傳播呈現出波浪曲線,以起伏狀態向四周推進,使一定范圍的公眾漸漸卷入輿論波,在時空延續中展示出輿論連續高漲的狀態。”[18]如果把危機事件所形成的輿論,看成是對社會造成的沖擊且具有起伏波動和流動匯聚的“波浪”,那么輿情作為輿論形成的前期表征,其生成演變的軌跡必然呈現“流動式”。輿情與輿情的碰撞,形成輿論涌浪,并伴生相應的輿論內波,這些輿論波組合疊加相互作用,就可能發展成輿論波群,掀起輿論風暴[19]。根據
輿論波理論模型,輿情的流動式匯聚是由多點向一點靠攏、由外向內收縮,且呈現波浪成長式的翻涌和增長。輿情以運動集合式積少成多,形成浩大的匯流,匯流的過程,也是輿情自身生長的過程。
“輿情是在公開討論中形成,由公開表達得以實施。”[20]公開討論的過程,是輿情“流動式”匯聚的過程。一個敏感話題或事端產生后,一系列的當事人、圍觀者、同情者、旁觀人,都可能在觀察中評判、在關注中討論,或訴說或批判或支持或解讀或煽風,多樣化的討論給空間注入多元化的話語流,每個個體都可能成一個輿情波點,并推進其向波浪發展。“輿論領袖”者通過“轉發、加精、置頂、跟帖、評論”等方式,形成“滾動散發式”傳播,加速波群合攏。特別是在“符號式表達”與“圈群式存在”的雙重刺激下,符號化存在的輿情信息,借助“圈群”成幾何級數擴大。大學生個體同質化程度高,對話題的關注發問有很強的趨同性,具有快速組織起多方參與交流的時空環境以及支持條件,面對敏感話題,大學生往往關注趨一致、討論趨一致,甚至行為也趨一致。由于個體身份的統一性以及時空流動的便捷性,在同情同感的刺激下,吸引更為遠方的大學生群體參與討論,實現了輿情言論由遠及近、由小到大的流動性匯聚。
個體通過表達形成輿情輿論,借助輿論動員形成力量,進而推進相關問題解決,或加快某個領域的改革進程。這是輿情事件演變的一般性規律和正向性作用,也是廣大參與者所期待的結果。期間,推進輿情演變及事端解決進程的力量,是源于輿情輿論背后“圈群式”存在的個體,正是他們“符號式表達”以及“情緒化內聚”的匯聚與表征,形成了強大的動力系統,實現了“群體性發力”。“群體性發力”體現在輿情生成演變和輿論影響實現的全過程。借助社會化媒體平臺,人們實現了更方便地發表觀點、自由集合以及組織動員,進行著廣場式的全民圍觀與全員討論,而社會化媒體平臺上所提供的同步呈現與放大的技術環境,讓個體感受到了強烈的現場感。期間,大學生感受到了對個體力量控制的刺激、自我力量放大的過癮以及對社會影響的成就,進一步吸收更多的個體力量在社交平臺上匯聚、在群體中發力。
“微傳播”的“蝴蝶效應”放大了大學生的傳播能量,加速了輿情信息“核裂變”,拓展了個體“圈群”的空間,放大了集群與極化的可能。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在《烏合之眾》一書中認為,群體在集體意志下容易喪失自我意識,變得容易盲目、沖動、狂熱、輕信。“群體極化現象”一般在群體從眾與盲從中產生。社會化“微媒體”與“微社交”,形成信息的符號化與碎片式,個體對自我言論構建一般不多考慮事件真相,僅憑自身經驗和判斷,通過碎片式媒體報道,構建自我的認知與判斷,出現迅速“支持”或“反對”的簡單化站隊[21]。在自己預設的標準的指引下,對一些傳播、更新較快的消極或負面言論較快接受,并以此為參照,以同樣的不假思索實施同樣的不理性,“把自我想象為可以肆意對別人審判、指責的‘道德完人’,然后陷入審判的快感之中”[22],為“集體暴力”滋長提供溫床。
五、應對:“分層式干預”與“微方式化解”
輿情引導干預要立足于高校工作的全方面,著手于輿情生成的全過程。遵循輿情輿論演變規律,對不同時期大學生興奮點、敏感點進行歸類,分類處置、分層化解,避免“大題小做”或“小題大做”,走向兩個極端,或刺激輿情發展或錯失有效引導時機,尤其要避免形成誘發事件與大學生輿情的“雙向刺激”。區分輿情不同的推進動力,實施不同的引導干預。針對由個體推動的情況,采取“尋根溯源”介入,找出誘發信息源或爆料個體,通過分析解決個案來化解;對于由群體推動的輿情,分析群體生存的環境和推進的方式,采取“順藤摸瓜”介入,找出信息傳播網絡,并區分自然匯聚的群體還是組織形成的群體,有機結合“輿情規律”和“法律規定”予以化解。
分析把握基于移動互聯和自媒體平臺下的大學生人際交往行為及過程特征,針對個體表達的“符號式呈現”,深入關注符號背后個體“情緒化內聚”的程度以及可能蔓延的焦慮緊張等負面情緒,確保做到提前進入,以符號對符號化解,以感情對情緒疏導。加大對學業、生活困難群體的關注,以人文關懷和有效舉措撫平個體的緊張感。而在輿情應對中,應針對個體情感的不同呈現,有機采取“反向定調”、“詢問調侃”和“正面回應”等方式化解。“反向定調”采用,一般在輿情尚未完成匯聚的早期,對話題本身進行“反向定調”,提出質疑、提出矛盾,引發其他個體的自我思考。而“詢問調侃”,讓引導者化身為輿情漩渦中個體,以第三方個體的身份介入,以詢問深探底、以調侃微引導。“正面回應”也是一種積極有效的輿情應對方式,有時個體情緒持續匯聚以及“爆棚”的根本原因,在于及時有效的正面回應不足,加大了個體的剝奪感和緊張感,以至于突破“圈群”走向“串聯”。
主動設置并進入大學生廣泛喜愛的各類新媒體、自媒體“圈群”,針對不同“圈群”中個體的生存特點、表達方式以及動員模式,予以差異化干預。大學生是當下各類新媒體的原居民,是很多由新媒體誘發的輿情事件的信息爆料人或匯聚推進者。爆料人一般不固定,信息一旦爆料后推進者往往較為固定。爆料的不固定,加大了提前預判的難度,而推進
者的固定,又給了干預可遵循的指向性。不同的個體,其在“圈群”上的行為不一樣、表征也不一樣。對非固定爆料人的關注,要立足普遍意義上的關懷,要從高校工作的各方面化解負面情緒,同步實施“事件性”解決與“結構性”改革,減少敏感話題被爆料的可能。對固定的參與者,要能夠定點關注、精準引導,要善于將其轉化、培育為代言人,切忌打壓和封鎖。處于青春期的大學生,性格活躍、觀點易動,好從眾、易盲從。采用的“正鯰魚效應”,培養高素質“意見領袖”(opinion leader)[23],化解輿情、轉化輿情,能有效避免可能出現的輿情危機。
高校或高校師生在輿情事件中,既可能是裹挾者,也可能是參與者,但內部的管理完善是化解的重要舉措。除前述的分層干預外,還要針對高校輿情事件的本質特點,多采取“微方式”予以化解,這既符合高校教學育人的根本,也有利于大學生的心理成長。強調“人文關懷”,培養大學生“慎獨”精神,做到線上線下同步、現實虛擬一致。規章和規范是一種“硬約束”,也是高校正常運轉的保障,比這種“硬約束”更能調節大學生行為的是大學風氣的“軟約束”[24]。要注重發揮“軟約束”在輿情引導中的重要作用,通過“軟約束”規制出大學生群體普遍認可的價值體系與是非標準,讓規章規范的核心要義潛移默化地在大學生心中留下印記。“軟約束”要在文化建設與氛圍培育中形成,立足“微媒體”打造“微文化”,在“微”體系上集聚放大正能量、形成正導向。線上問題必須在現實中尋找根源,在現實中解決問題[25],方能有效避免同類事件頻繁爆發。定期研判內外發展形勢,做好體制缺陷與積壓矛盾的摸排,也是高校危機管理的常用方法。
[1]孫麗園.新媒體環境下高校學生群體性事件的預防和應對[J].思想教育研究,2011(4):97-99.
[2]夏雅敏.大學生網絡表達特征及引導對策[J].思想理論教育,2013(1):71-74.
[3]Lance Bennett W,Alexandra Segerberg.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ntentious Politics[M].Cambride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1-54.
[4]周凱,劉偉,凌惠.社交媒體“沉默螺旋”效應與青年人的政治參與——基于25位香港大學生的訪談研究[J].現代傳播,2016(5):143-148.
[5]蘇濤.缺席的在場:網絡社會運動的時空邏輯[J].當代傳播,2013(1):23-25.
[6]吳婷.基于角色引導的大學生網絡輿情治理與思政教育協同模式研究[J].高教探索,2014(6):181-185.
[7]曹勁松.網絡輿情的發展規律[J].新聞與寫作,2010(5):45-47.
[8]趙鼎新.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226-233.
[9]陳建文,王滔.大學生壓力事件、情緒反應及應對方式[J].高等教育研究,2012(2):87-94.
[10]姚福生,錢芳,蘇暢.大學生網絡輿情主題演化探究及其預警指標設計[J].學術論壇,2013(2):215-220.
[11]陶賦雯.“微媒體”視閾下高校輿情現狀窺探[J].東岳論叢,2014(12):186-190.
[12]劉碧珍.“再部落化”與微信敘事[J].當代傳播,2016(1):74-77.
[13]宋全成.論自媒體的特征:挑戰及其綜合管制問題[J].南京社會科學,2015(3):112-120.
[14]姚福生,錢芳,蘇暢.大學生網絡輿情主題演化探究及其預警指標設計[J].學術論壇,2013(2):215-220.
[15]任小燕.悖離與異化:工具理性視域下高校虛擬管理模式的價值反思[J].高教探索,2013(6):45-48.
[16]Va yrynen R.New directions in conflict theory:conflict resolution and conflict transformation[M].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1991:1-25.
[17]梁鋒.信息繭房[J].新聞前哨,2013(1):87.
[18]劉建明.社會輿論原理[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160.
[19]廖衛民,柯偉.網絡輿論波研究——基于波浪力學及杭州兩起輿論事件的理論思考[J].新聞記者,2010(4):12-17.
[20]林凌.新聞學概論[M].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11:36.
[21]鄧若伊,郭佳.網絡輿論萌芽階段的特征及規律分析[J].新聞界,2015(17):49-52.
[22]杜駿飛.網絡群體事件的類型辨析[J].國際新聞界,2009(7):76-80.
[23]Massim oF ranceschet,Antonio Costantini.The effect of Scholar Collaboration on Impact and Quality of Academic Papers[J].Journal of Informetrics,2010(4):540-553
[24]張偉.基于大學生輿情引導的高校學生工作價值研究[J].新疆社會科學,2015(4):16-20.
[25]張瑜.社會網絡視角下的網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探析[C]//楊振斌,吳潛濤.思想政治教育新探索(第2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148.
[責任編輯:歐世平]
An Analysis of the New Changes of University Public Opinion and the Response to the Crisis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Media
YAO Jiang-long1,WEI Jie2
(1.School of Public Affairs,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Hefei 230026,China;2.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fice,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Hefei 236000,China)
It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for crisis control of university to do a good job in university public opinion.Social media platforms developing rapidly create new way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making the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of university public opinion taking on new changes.Facing“reform-based worry”arising from social transformation,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universities make“independent vent”by social media platforms.They turn individual appeals into“emotional cohesion in“sign-based expression”and make“interaction-oriented spreading”in“group-based existence”,promoting continuous enlargement and upgrade of individual opinion and sentiment.As a result,university public opinio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group-based powerful”in“flow fusion”,bringing challenges to crisis control in universities.Considering new changes above,types and levels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when responding to university public opinion crisis.To ensure university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strategies and ways should be employed scientifically and“layered intervention”and“resolving in tiny ways”should be implemented。
social media;university public opinion;new changes;response to the crisis
G647;C912
A
1007-5097(2016)09-0180-05
2016-06-16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學一般課題(BIA110039)
姚江龍(1979-),男,安徽桐城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危機管理;魏捷(1954-),男,安徽阜陽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10.3969/j.issn.1007-5097.2016.09.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