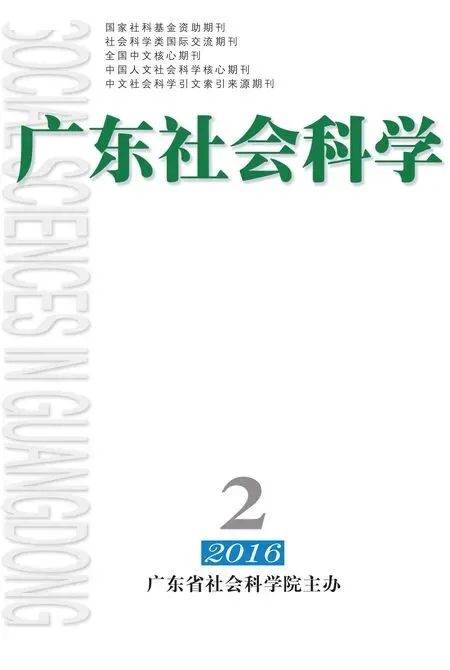日本對中國臺灣和東北地區移民的關聯性與差異性*
孟月明
?
日本對中國臺灣和東北地區移民的關聯性與差異性*
孟月明
[提 要]中國臺灣和東北地區是日本兩次侵華戰爭后分別占領的地區。為了長久統治并作為全面侵華的后方基地,日本分別對臺灣和東北地區實施了大規模的、有計劃的、官方主導的農業移民計劃。就時間順序而言,臺灣移民在前,是日本移民侵略的經驗和藍本,東北地區移民在后,但規模和數量以及對移民政策的重視程度都明顯加強。日本對兩地的移民侵略既有關聯性又有差異性,也是日本侵華步伐一步步加深的手段和結果。
[關鍵詞]日本移民 臺灣 東北地區
*本文系2014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近代以來日本對華移民侵略問題研究”(項目號14BZS109)的階段性成果
近代日本的對外侵略,以領土擴張和人口增殖為首要目標,而人口的移殖又勢必以軍事占領為前提條件。戰爭和移民在日本侵華過程始終互為表里,相輔相成。日本之所以重視移民,是因為他們認為移民政策更為隱蔽、巧妙,是“一箭雙雕”的“良策”。一方面,移民可解決了日本本土人口與土地的尖銳矛盾;另一方面,被移殖的日本人對所在殖民地人民還可以起到監督和同化作用,同時進行農業生產,協助掠奪當地資源。更為重要的是,一旦戰爭爆發,放下鋤頭扛起刺刀,移民可以成為最近距離的后備兵源。
日本對中國臺灣和東北地區都實施了政府主導下的移民侵略計劃,二者既有關聯性又有差異性。
一、日本對臺灣與東北移民的基本情況
1.日本對臺灣移民情況
1895年甲午戰后,清政府迫于日本的軍事壓力,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馬關條約》,將臺灣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割讓給日本。臺灣被占領后,日本上下一直主張推行移民政策。學界最具代表性的是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提出的“移民殖產論”,其基本觀點為:“臺灣地處熱帶,天然資源豐富,一定有大批日本內地人移住,因此應該規劃成一個‘新日本國’,對臺灣的統治應采取干涉方針,以臺灣之日本化為目的來實行一切處置。”①福澤諭吉甚至提出臺灣最好成為無人島,可供日本移住過剩人口,任由日本完全處置、開發,而不需考慮臺灣原有的風俗、民情及住民的需求,即使全數島民退出境外也在所不惜。據臺伊始,時任外相陸奧宗光也主張放逐臺灣島民。他認為日本占領臺灣的目的主要有兩點:“第一,把臺灣作為日本帝國往大陸及南洋群島發展的根據地;第二,開拓臺灣的富源,移殖日本工業,并壟斷通商利權。”②第三任臺灣總督乃木西典和民政局長曾根靜夫也曾經傾向于驅逐臺灣人民。但后來日本政府怕大量放逐臺灣人會引起島內紛亂,并且即便動用大量的兵力、人力和物力,也難以短時間內用日本人完全填充臺灣島。因此,日本政府最后并未采納完全驅逐臺灣人的主張。
不能完全驅逐臺灣人民,日本當局便試圖通過改變臺灣的人口比例,使臺灣人民逐漸被日本人同化,以達到永據臺灣之目的。臺灣總督府首任民政局長水野遵在的《臺灣行政一斑》中直言不諱地表述:“移住內地人之計,非獨為開發山地資源之必需,而且為使中國人種或原住民均能浸浴日本文化,應盡量移住多數我內地良民,讓彼我相互接近,逐漸改變其風俗習慣。”③《臺灣民報》曾有這樣的報道:“日本既然占領臺灣,便應該積極移入日本內地過剩人口從事拓殖。臺灣應成為容納大量日本人的‘日本帝國之一地方或一州’,為日本基地之延長,使日本人成為臺灣的主體,臺灣也成為新的日本社會。”④由此不難看出,日本殖民主義者認為,只有日本人口的大量進入,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對臺灣的占領,移民入殖是日本侵華的既定計劃和長遠之策。
在殖民統治臺灣的五十年中,日本對臺灣的農業移民側重點有所不同。因此,可將其劃分為五個時期,即:“1895年至1905年的放任時期;1906至1909年的前期私營農業移民時期;1909 至1917年的前期官營農業移民時期;1917至1930年的后期私營農業移民時期;1931至1945的后期官營農業移民時期。”⑤
為了鼓勵大量日本人口移民臺灣,日本采取積極的對臺移民政策。由臺灣總督府主辦的大規模官營移民,移民人數較多,依其職業又分為農業、礦業、漁業三種。礦業和漁業移民人數有限,經營時間也很短。因此,官營移民的重心是“農業移民”。在日本官方政策大力支持的背景下,也有日本農民自行組團到臺灣謀生,自由移民移住的地區多分布于臺灣的東、中、南部。
2.日本對中國東北的移民情況
1905年日俄戰爭后,日本便加緊對中國東北的侵略步伐,移民作為一項重要侵略手段被正式提上日程。1913年,由“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組織了“除隊兵”移民;1915年,關東都督福島安正在大連金州創建第一個移民試點村——“愛川村”。1928年4月,“南滿鐵道株式會社”成立專門的移民組織機構——“大連農事株式會社”。這是九一八事變前日本向中國東北地區移民的初始嘗試,雖然都未成功,但已初現日本殖民入侵之野心。
九一八事變后,雖然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執行不抵抗政策,但東北民眾和抗日武裝從未停止過對日本的抗爭。基于此,日本關東軍把最初的移民計劃定為“武裝移民”。1932年10月4日,開始第一次“武裝移民”,至1936年上半年,共進行了四次“武裝移民”,共約1800戶。1937年2月第五次移民處于從“武裝移民”向大規模農業移民的過渡期,改稱集團移民。此后,日本移民方針有了重大轉變,開始進入大規模的“國策移民”階段。
在強大的軍事占領前提下,日本殖民主義者認為大量移民侵略的時機已經成熟,于是開始對中國東北進行大肆移民侵略活動。1936年8月25日,“滿洲移民政策”被指定為日本“七大國策”之一,從1937年開始正式實施。作為日本“七大國策”之一的《二十年百萬戶移民計劃案》的主要內容為:投資預算18億元,20年向中國東北入殖百萬戶500萬人。“其百萬戶500萬人的計算方法按每戶農業移民的家庭人口為5人計算,計500萬人”。⑥“二十年百萬戶移民計劃”的國策化,標志著日本向中國東北移民侵略政策的最后確立和形成。
為掩蓋侵略本質,1939年2月起,日本把對中國東北大規模農業移民團改稱為“開拓團”。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后,日本勞動力的大量兵員化和軍需產業使用勞動力的急劇增加,使得勞動力的枯竭狀況日趨激化,加上對戰爭的自顧不暇,日本已經絲毫沒有能力和精力來確保對中國東北移民計劃的實施。因此,日本《二十年百萬戶移民計劃案》并未完全得以實施。事實上,在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以前,日本對中國東北的移民侵略計劃已全面崩潰。在整個日本侵華期間,對中國東北的農業移民是數量最多,規模最大,也是日本的移民侵略政策、計劃實施最為充分的地區。
二、日本對中國臺灣和東北移民的關聯性
今天看來,臺灣和東北地區一南一北,氣候迥異,經濟環境截然不同,文化差異也較大。就是這樣兩個看起來遙不可及、毫無關聯的兩個地區,卻因為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的入侵,而經歷了一段極為相似的歷史命運。兩地在日本占領期間,“即以容納宗主國所輸出的資本與所移殖之人口和供給原材料提供市場為主要特征”。⑦這種特征,決定“其統治的基本性格,是以強有力的國家支持扶植其產業資本之發展,建立起絕對性資本之獨占;實際上乃至是國家權力‘合法’的掠奪方式,從事原始資本積累。而為了使殖民地人民馴從此一秩序,本質帶有黷武性格,民族性過分自負而不免表現偏狹”。⑧
(一)向臺灣移民的經驗被作為日本向中國東北移民的藍本
最初為了迅速平定臺灣,日本采取了剿撫并用的手法,但前三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桂太郎、乃木希典都沒能控制住臺灣,乃木希典甚至還提出了出賣臺灣論。后來兒玉源太郎任臺灣總督,采取“糖飴與鞭”的懷柔政策,實施官營移民政策。兒玉在臺灣任期長達8年多,是歷任總督中最長的,日本政界評價兒玉源太郎和后藤新平開創了一個時代,奠定了臺灣殖民統治的基礎。通過日俄戰爭,日本從俄國手中奪取了大連租借地和南滿鐵路經營權。1906年1月,兒玉源太郎被日本內閣任命為“滿洲經營調查委員會”委員長,7月13日被任命為“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委員長。他還是偽滿日本移民500萬的總策劃人。
兒玉源太郎又極力舉薦任臺灣民政長官的后藤新平來擔任“滿鐵”總裁。后藤新平1898年出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提出“生物學原則的殖民地經營法則”思想。為了能夠把日本政府對外擴張的殖民統治政策迅速地融入到臺灣當地及民眾之中,他急不可耐地開展對臺灣的舊制、土地資源、人口構成狀況和民俗風情進行大規模細致的調查,并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制定了對臺灣的統治政策和法律制度。1906年11月13日,后藤新平離開臺灣到“滿鐵”就職,期間更以“舉王道之旗行霸道之術”,對東北提出“文武裝備”論,可以視為臺灣“生物學統治法則”的延伸。后藤新平向兒玉源太郎提出經營滿洲的方針,概括起來有四點:第一,經營鐵路;第二,開發煤礦;第三,移民;第四,發展畜牧業。其中以移民為第一要務。后藤新平把對臺灣的移民經驗全盤移植到東北,并加以放大。
1932年被稱為“滿洲移民開拓之父”的加藤完治曾特意考察臺灣的日本移民村落——吉野村,目的是學習和借鑒日本對臺移民經驗。之后在加藤完治的推薦下,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小磯國昭也赴吉野村視察,以實現效尤之效果。日本學者福田桂二認為“滿洲移民以日本移民村作為當地農村的示范的方式,便與臺灣官營移民相當類同。”⑨嚴格意義上講,臺灣的農業移民并不成功,并未達到日本制定移民侵略計劃的初始目的,但日本殖民主義者認為,臺灣移民的成敗是不能以數量之多寡來加以衡量的,日本移民臺灣是一種領土占有的宣示,是日本真正殖民臺灣的象征。臺灣移民無論成敗,都是之后日本軍國主義對外擴張政策的重要一環,是日本對其他占領地區和國家移民的藍本。
日本在對臺灣移民的過程中,總結和積累了系統的移民經驗:殖民地情況研究——土地、林野調查——制定移民政策——頒布移民規則或法律——建立機構——進行公共設施建設——在國內招募移民——修訂辦法,并根據各殖民地實際狀況和反抗程度強弱,相應調整移民政策、移民目標和移民手段。1906年,日本開始對臺灣進行移民;1907年,日本制定樺太(庫頁島)地區農業移民土地相關規則,獎勵移民;1908年,朝鮮成立“東洋拓殖株式會社”,專門經營日本對朝鮮移民;1936年,制定《滿洲農業移民移住計劃》,“滿洲移民政策”上升為日本國策。日本以堆疊式的經驗積累,進行長遠性國家侵略計劃,從而一步步實現其“國家政策”。日本對華移民,以臺灣為初始嘗試,到中國東北移民已經進入到大規模推廣和國策化、法制化階段。
(二)日本對中國臺灣和東北移民都由官方主導
日本對臺灣和偽滿農業移民都是在政府主導下的,設立專門的移民機構進行管理。日本國內實施移民的主管部門是拓務省,但由于同農村經濟更生政策相關聯,農林省也密切參與,對府、縣、市、町、村給予行政指導。1909年,臺灣總督府以預算3萬元進行官營移民事業,首先由殖產局林務課調查適合移民的地區,及研究移民事項、經營農業經濟等問題。1910年編列預算79 755元進行移民事業。同年5月頒布敕令230號發布掌管移民事務之臨時人員,特別設立移民委員會,專門制定移民章程,并由總督府殖產局設置移民課作為執行機構,還設立移民指導所等機構。⑩日本對臺灣的移民,不管招攬者為政府或私營企業,都受到官方移民獎勵政策的支持,只是經營主體的差別。1937年七七事變以后,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臺灣開始積極推動“皇民化”運動。為了加速對臺灣人民的同化,給臺灣農民樹立典范,同時配合日本的“南進計劃”,大量積累熱帶作物的栽種技術經驗,臺灣總督府開始再次大規模辦理官營農業移民。
1935年11月,日本成立了“滿洲移住協會”,負責移民政策的宣傳、啟蒙,移民的斡旋和訓練。同年12月,以獲得移民用地、為移民提供協助和金融服務為目的,日本以1500萬元資金成立了“滿洲拓殖會社”。1937年8月,根據日“滿”兩國的協定,日本政府出資5000萬日元,在吸收合并原拓殖會社的基礎上,又成立“滿洲拓殖公社”。1939年2月偽滿洲國的移民行政機構又擴大,設立了“拓務總局”。同年12月制定了《滿洲開拓政策基本要綱》。《要綱》將移民政策規定為“日滿兩國一體的重要國策”,以“確立并培養為建設東亞新秩序的道義新大陸政策的據點為目的,特別以日本國內開拓民為核心,謀求協調‘開拓’民與原住民的關系,以期強化日‘滿’不可分的關系,實現民族協和”。
(三)日本對中國臺灣和東北移民都給兩地造成極大危害
大規模農業移民的最直接危害是霸占和掠奪土地。掠奪手段從“商租”、低價勒買、強行沒收到毀契、霸占、抵償債務、驅趕、屠殺原地居民和大面積圈占,無所不有,無論采取哪種形式,都是強制奪占,否則以“通匪罪”處死。對中國東北進行“武裝移民”和圈占土地過程中,更是動用飛機、大炮、機槍,整村地驅趕和屠殺原地居民。據不完全統計,日本共向中國東北派遣“開拓團”860多個,約31.8萬人。“開拓團”到中國東北后,強占或以極其低廉的價格強迫收購中國人的土地,至日本戰敗投降為止,日本為安置日本移民掠奪中國東北耕地達3.9億畝,先后使500萬中國農民失去土地,陷入極端困苦的境地,因此凍餓而死的中國人不計其數。在臺灣全島總計370.7萬甲的土地中,被臺灣總督府強行霸占的土地多達246.2萬甲,被日本財閥和日本移民強行低價收買的土地多達18.1萬甲,兩項共計264.3萬甲,占臺灣土地總面積的68.5%。在臺灣實際可直接耕種的88.6萬甲耕地中,日本財閥和日本移民占有20.4%。另外,在臺灣全島365萬甲森林地中,被臺灣總督府強行霸占為官有森林地的竟高達97%。
大量日本移民的入殖和移民村的建立,不僅完全破壞了中國臺灣和東北地區農村原有的村屯組織結構,而且給中國農民生產、生活帶來了極大災難。日本農業移民團強行掠奪土地后,他們自己并不直接經營,而是轉租給流離失所的中國農民,對他們進行二次剝削。被迫為日本人做工的中國人,被任意摧殘和遭受欺侮之事常有發生,日本移民以高高在上的姿態在中國人面前耀武揚威,十分霸道。日本移民侵略的根本目的就是改變中國人口的民族構成和土地占有關系,使中國民族日本化,生活方式日本化,土地占有日本化,行政體制日本化,最后中國版圖日本化。日本移民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在潛移默化中感染了一代臺灣人,造成部分民眾中存在著一種皇民心理,這對臺灣光復后臺灣人民的國家認同形成了障礙。
日本占領臺灣以后,臺灣經濟的發展基本上是以服務日本經濟發展為導向的。日本把臺灣作為農業資源的生產基地,所以對臺移民多以農業移民為主,主要從事水稻經營和蔗糖經營。臺灣經濟嚴重畸形發展,甚至出現了所謂“谷糖相克”的現象。而為了對東北農業、農村進行全面掠奪,將東北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納入日本國民經濟軌道,確定了“日滿經濟體制”,實行日“滿”經濟一元化和日本工業化、“滿洲”原料化的經濟分工。日本殖民主義認為只有推行農業移民,才能直接掠奪到自己“所缺乏的物資”和“所需要的資源”。日本農業移民在到中國臺灣和東北地區試圖改變其個人命運的同時,也有意或無意地成為日本掠奪中國資源的得力助手,是日本侵華的幫兇和犧牲品。
三、日本對中國臺灣和東北移民的差異性
(一)一是“南進踏板”,另一是“北進基地”
一戰以后,日本趁機占領了德國在南洋殖民地,日本打算繼續擴大南洋領地,“入主”南洋,臺灣便成為日本的“南進踏板”,因此,日本海軍大力主張“南進政策”。日本陸軍則一直以俄國為假想敵,為防范俄國,主張“北進政策”。侵占中國東北,日本一方面是為了防止俄國報復,再次發動戰爭,另一方面又可以伺機擴大對中國的侵略范圍,滿洲便成為了日本的“北進基地”。1936年,在軍國主義野心不斷膨脹的背景下,日本內閣首相廣田弘毅決定北進兼南進政策。在日本的對華侵略中,臺灣和東北的戰略地位都極為重要。臺灣日本移民兼具國防、同化和經濟開發的目的,農業移民的大規模入殖,加快了日本對臺灣資源的掠奪,并成為日本產業向東南亞地區擴張的重要踏板。
日本對中國東北移民,則是軍事色彩更為濃郁。偽滿洲國成立后,在日本關東軍的主導下,日本將移民東北上升為國策,以防范北方的蘇聯,并把東北視為日本侵華的總根據地。日本對中國東北實行半軍事化管理,政治、國防和經濟目的十分明顯。作為日本在中國東北的最高權力擁有者,日本關東軍實際上早已把農業移民規入到日本總體的軍事部署當中。從當時的地圖上看,大約半數的日本“開拓團”部署在從偽間島省經偽牡丹江省、偽東安省、偽三江省、偽黑河省、偽興安北省至興安南省的“開拓第一線地帶”,隨時都兼有軍事防范蘇聯的功能。從長白山、哈爾巴嶺、老爺嶺及大小興安嶺內側至松遼平原外緣一線稱作“開拓第二線地帶”,在這里的日本移民超過總數的40%,日本軍國主義以此用來阻斷中國東北抗日武裝和當地老百姓的聯系,從而削弱中國人民的抗日武裝力量;“開拓第三線地帶”是交通要道和大城市,安置在這一地帶的移民只占日本移民總數的10%。可以想象,這樣的布局會使得80%的日本“開拓團”集中在中蘇邊境線上。
太平洋戰爭時期,伴隨著日本關東軍主力部隊的南移,臺灣和東北地區日本農業移民應征入伍的人數迅速增加,所有具有戰斗能力的男性移民全部應征入伍。此時,日本農業移民已不僅僅是支撐日本關東軍軍事活動的協助者,而是成為日本擴大侵略戰爭的主要兵力來源。
(二)移民來源和數量之差異
由于日本較早侵占臺灣,實施農業移民的時間也相對較早。但日本對臺灣的農業移民官方主導政策是時斷時續的,是官營移民和私營移民交錯進行的。比較而言,臺灣的農業移民多來源日本偏南部地區,尤其適合日本的制糖公司,側重積累熱帶經濟發展的經驗。而日本對中國東北地區農業移民的官方主導性則更強一些,為適應中國北方地區生活環境,日本移民也多選擇日本北方地區農民。兩地的農業移民都曾由于自然環境惡劣、時疫時常流行、原住民襲擾、糧食不足和交通不便利等因素出現過失敗和歸國現象。臺灣農業移民的成效并不十分顯著,主要原因之一,是臺灣當時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554人,和日本人口密集的九州、四國地區不相上下,除了東部蕃地以外,能容納移民之處并不多。中國東北地區地大物博,對日本農業移民的接納能力則更強一些。因此,偽滿后期的日本農業移民多以集合移民、集團移民和“分村分鄉”移民為主要模式,以提高移民的規模和效率。據統計,到臺灣光復時,在臺日僑總數為308 232人。琉僑(琉球群島的居民,屬于日本)總數為13 917人,全臺灣地區日琉僑總數為322 149人。截至1944年9月,中國東北日僑日俘人數達到166萬人,單純的農業移民就達到31.8萬人。
(三)移民最終命運也有差別
隨著日本戰敗投降,日本的移民侵略計劃也隨之土崩瓦解。昔日在臺灣和偽滿洲國趾高氣揚的日本移民成了難民和逃亡者。1945年8月9日,蘇聯對日宣戰,出兵中國東北。10日,日本大本營向日本關東軍首腦部傳達“可以放棄滿洲全土”的命令。日本政府和關東軍在危機時刻竟然對“開拓團”封鎖消息,采取了令日本移民齒寒的棄民政策,即優先將日本軍人、軍隊的文職人員、家屬撤退輸送回日本,而將在偏遠內地的一般移民拋棄。
據統計,日本戰敗后,“開拓團民”死亡總數為78 500余人,其中有11 520人自裁;被蘇聯扣押在西伯利亞的有34 000人;下落不明的36 000人;遣返回國的110 000人,占開拓民總數27萬人的40%。中國政府和人民以德報怨,以博大的胸襟善待了殘留在中國的日本移民。1946年5月7日至1946年12月25日,中國遼寧西部的葫蘆島港遣返日本僑民和戰俘158批總數超過100萬人。
日本宣布投降以后,移居在臺灣的三十幾萬日本移民的去留成為一個突出問題。1945年10 月1日,原日本總督府應受降需要,舉行“日僑歸國志愿之調查”,志愿留臺者14萬余人,而志愿返還日本者18萬余人。12月27日,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成立臺灣省日僑管理委員會,除部分技術人員外,日僑一律遣返回國。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后,留用的日本技術移民也全部遣返回國。
日本對臺灣和東北地區的農業移民政策看似有很大地域差異,實則異曲同工,都是日本對華殖民侵略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移民臺灣到移民東北,是日本兩次對華戰爭的產物,是日本對華侵略不斷深化的結果,也是深入剖析日本對外擴張政策的一個獨特視角,應當作為專門史加深化以研究。
①張素玢:《臺灣的日本農業移民(1909-1945)——以官營移民為中心》,臺北:臺灣國史館印行,2001年,第32頁。
②鐘椒敏:《日據初期臺灣殖民體制的建立與總督府人事異動初探(一八九五—一九〇六)(上)》,臺北:《史聯雜志》(第十四期),第84頁。
③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總督府檔案中譯本(第三輯)》,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1994年,第688頁。
④小林勝民:《臺灣經營論》,第3~5頁,吳密察:《臺灣近代史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1990年,第121頁。
⑥滿洲移民史研究會編:《日本帝國主義下的滿洲移民》,日本東京:龍溪書舍,1976年,第47頁。
⑦⑧黃靜嘉:《春帆樓下晚濤急——日本對臺灣的殖民統治及其影響》,臺北: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48、38頁。
⑨福田桂二:《花蓮——臺灣開拓移民的70年》,日本東京:《世論時報》(昭和五十四年一號),第63頁。
⑩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移民課:《臺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1910年,第18頁,東鄉實:《臺灣農業殖民論》,日本東京:富山房,1914年,第517頁。
[責任編輯 李振武]
作者簡介:孟月明,遼寧省社會科學院邊疆史地研究所副研究員。沈陽 110031
[中圖分類號]K31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14X(2016)02-009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