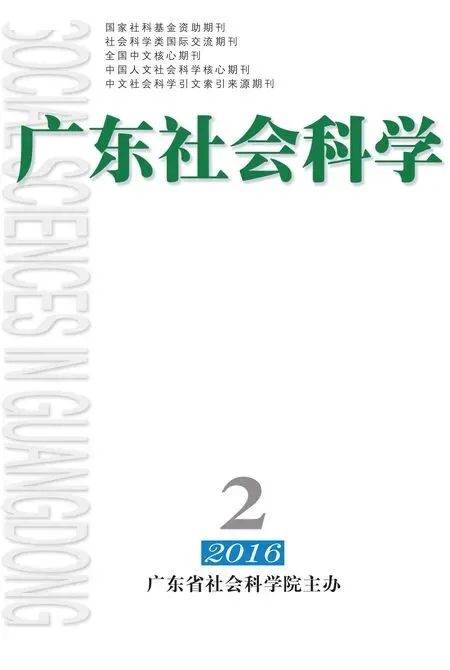試論江南制造局與近代中國早期的企業社會責任*
侯中軍
?
試論江南制造局與近代中國早期的企業社會責任*
侯中軍
[提 要]近代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不應局限于官督商辦企業,而應結合歷史實際,考慮類似江南制造局等官辦軍事工業對后世中國企業發展的影響。官辦企業和官督商辦企業雖不完全符合近代企業的運作特點,但相比于西方各國,晚清中國的企業承擔了更多的國家責任。江南制造總局的企業社會責任可歸結為:為政府生產合格的軍工產品,為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培養技術人才,為近代科技儲備基本的理論基礎。
[關鍵詞]官辦軍事工業 洋務運動 江南制造局 企業社會責任
*本文系2015年教育部留學歸國人員科研啟動基金資助項目“企業、外交與近代化:論晚清中國的國家契約”的階段性成果。
學界近年來引入了企業社會責任的理念,并試圖尋找企業社會責任的本土話語,以期與西方理論相抗衡,并析出中國特色。管理學界、經濟學界為了這一理論訴求,將目光投向晚清以來的大型企業,洋務企業即是關注的重點。但學界迄今為止所關注的洋務企業,主要是官督商辦企業,不包括官辦的軍事工業在內。如果溯源中國的國有企業制度,則官辦的江南制造局在更多的方面值得我們去關注。本文在梳理學界現有對企業責任研究狀況的基礎上,準備將官辦的軍事工業納入研究視野,以期全面認識近代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本土源頭。
一、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
“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這一概念最早源于美國,自1923年正式提出已有近一個世紀的時間了。一般認為,美國學者歐利文·謝爾頓(Oliver Sheldon)是該概念的首倡者,他把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經營者滿足產業內外各種人類需要的責任聯系起來,并認為公司社會責任含有道德因素在內。①而在此之前的西方工業國家,大家對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的認識并沒有觸及到該層面,人們普遍認為企業的目標就是股東利潤的最大化。從1920年代開始,經濟學界對企業社會責任內涵的界定經過持續發展,直到1953年,被稱為“企業社會責任之父”的伯文(Howard R.Bowen)發表了《商人的社會責任》一書,提出了“商人應該為社會承擔什么責任”的問題,從而開啟了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現代研究。
受國際學術界的影響,國內學界對于企業是否應當承擔社會責任,應當承擔什么樣的社會責任同樣存在分歧,并認為企業社會責任作為一種概念,“至今仍是眾說紛紜”。②最近的研究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利益相關者關于企業合作剩余分配的契約”。之所以為企業社會責任做出如此定義,可以用作者的話表述為:“這一認識源自企業社會責任的兩大理論基石——企業理論和利益相關者理論”。③有的著作干脆就以《企業社會責任與可持續發展研究——基于利益相關者和社會契約的視角》來命名,作者在前言中指出:“本書從企業與社會的視角出發,在利益相關者理論和社會契約論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新的企業社會責任分析框架,系統地回答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基本問題,有力地反駁了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批評”。④目前的研究認為,雖然關于企業社會責任有多種解釋,但研究內涵基本一致,“企業在承擔經濟責任的同時,還要對員工、債權人、供應商、客戶、政府、社區等其他利益相關者以及自然環境承擔社會責任”。⑤
近年來有研究者以輪船招商局為個案,探討了近代中國的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將其概括為專利制、報效制和官利制三種形式。⑥如果考慮到企業社會責任的核心觀念并未得到學界一致肯定,即使是在經濟學界內部亦有爭論,則將其應用于晚清企業的研究須更當審慎。在探討處于萌芽時期的晚清企業社會責任時,除探討企業自身的經濟行為之外,還應關注其圍繞經濟行為而展開的社會活動。圍繞企業自身的經濟行為展開探討是所有企業社會責任理論的核心觀念,只有從企業出發,才能逐步引申到其他社會問題。另一方面,既然企業社會責任為多學科共同關注,其依據學科特點各有側重,歷史學自然亦應有自己的特點。曾有學者概括性指出各學科之間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的特點:經濟學界一般從產權理論出發,論證股東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然后以此角度分析企業社會責任與利潤最大化的沖突;管理學界則主要從如何對利益相關者進行管理,從而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和增強企業的競爭力,認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有利于提高企業社會聲譽,增強利益相關者的認同度;社會學界主要是放在企業捐贈和企業公益上;法學界從法學的角度分析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中參與者的權利和責任,試圖從中找到企業社會責任存在的根據。⑦
基于對上述概念的理解,學界將其應用于近代中國的企業社會責任研究時,目光集中于官督商辦企業上,并從中提煉出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社會責任。經濟學界和管理學界對近代企業社會責任的梳理,雖然運用了自身的概念,但其基礎是建立在史學界對晚清企業的論述之上的。梳理文獻可以發現,經濟學界所提出的三個特點,史學界已經提出,只是并未明確為近代企業的社會責任:“企業需要向政府報效、分配中實行‘官利’制、面向社會直接吸收儲蓄和企業內部資金的調撥等等,就是中國近代股份制企業資金運行中的本土特點”。⑧
鑒于近代中國的歷史實際,如果在總結近代中國的企業社會責任時,完全無視曾經開風氣之先的官辦軍事工業,必將影響最后結論的合理性。通過梳理江南制造局的相關史實,結合近代企業社會責任概念,可以初步探討官辦軍事工業與近代企業責任這一命題之間的關聯。
二、企業社會責任概念下江南制造總局的生產和經營
由于晚清時期特殊的歷史社會狀況,清政府對官辦和官督商辦企業的定位遠非一般的營利,而是有更為宏大的理想與目標:通過民族企業實現國家的富強。這也是洋務運動的基本目標之一。當近代新式企業在中國的大地上產生時,擁有先進技術和強大資本的列強環伺周圍,并試圖瓜分中國。帝國主義各國通過在中國設礦、辦廠、修筑鐵路,壟斷了中國的工商業,如何挽回這些利權是晚清企業面臨的主要社會責任之一。之所以會出現上述狀況,與近代中國所面臨的形勢有關,也是中國歷史傳統中官商關系的延續和反映,它的形成是國內外各種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晚清時期的公司制企業承擔著諸多非營利方面的職能和目標,這一方面支配著公司制企業的行為,一方面左右著公司治理思想。⑨如果將公司制企業承擔的非營利方面的職能和目標與官辦企業相比較,尤其是與江南制造局這樣的軍工企業相比較,在公司制企業那里的企業社會責任,在江南制造局身上則成為正常的企業責任,如果將這種責任進行概括,可以將其稱為國家責任。概略分析洋務運動的興起及發展過程,可以體現出上述基本特征。
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清政府內部興起了一股以學習西方為手段,以自強、求富為目的的洋務運動,又稱自強運動。運動期間,先后創立了安慶內軍械所、江南制造總局、福州船政局等軍事工業以及輪船招商局、漢陽鐵廠等民用工業。
洋務運動興起于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軍的過程之中。戰爭期間,非但清軍使用了新式的西洋武器,農民起義軍也使用了同類武器。這些新式武器的引進和使用促使統治階級內部的有識之士認識到生產該類武器的重要性,并開始著手創辦了中國最初的一批軍事工業。江南制造局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誕生的。
1863年,曾國藩在清政府內部討論采購船炮的基礎上,建議“購其機器自行制造,經費較省,新舊懸殊”。⑩容閎在曾國藩支持下,“一星期而有委任狀,命予購辦機器。另有一官札,授予以五品軍功”,“又有公文二通,命予持以領款。款銀共六萬八千兩,半領于上海道,半領于廣東藩司”。自此拉開了江南制造總局建設的大幕。經前期籌備,至1867年,江南制造局初具規模,“上海制造局,同治四年五月初購洋人機廠,在虹口開辦。六年夏始移城南高昌廟鎮,分建各廠”。在最初的設計中,制造槍炮遠較制造輪船迫切,“就中國情形而論,購求制軍器之器,似較急于制船之器。緣軍器不精,雖有船只,猶多后慮”。直到1867年才開始造船,“因經費支絀,難興船工。至六年(1867年)四月,臣奏請撥留洋稅二成,以一成為專造輪船之用,仰蒙圣慈允準”。1868年,第一艘輪船“惠吉”號出廠。
江南制造總局不僅是當時設備最齊全規模最大的工廠,而且是一個機器母廠。研究江南制造局所擔負的企業社會責任,一是要考察它是否能生產合格的產品,服務社會;二是要考察它對促進社會發展所起到的作用。江南制造總局產品分為兩類:軍用和民用。其軍用部分,可視為總局對清政府擔負的“國家責任”,因其經費來自政府;其民用部分可視為其擔負的企業社會責任之一。“從所有那些機械結構情況看,專用于軍用生產的車間設備占的比例很少,絕大多數車間設備既可以為軍用生產服務,也可以廣泛地制造機械設備、工業、農業等各種民用器皿服務”。在最初的設計中,為民生服務亦是江南制造局既定目標之一。“查此項鐵廠所有系制器之器,無論何種機器逐漸依法仿制,即用以制造何種之物,生生不窮,事事可通,目前未能兼及,仍以鑄造槍炮藉充軍用為主”。李鴻章強調:“臣尤有所陳者,洋機器于耕織、印刷、陶制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專為軍火而設”。
江南制造局的資金來源,主要由清政府從各種稅收中撥付:一是作為原始資本的開辦費用,大部分是政府的軍費,小部分是犯罪官員贖罪的貪污贓款;二是中途增加的擴建費用,由政府從國家稅收中撥付;三是經常費,主要依賴政府撥付的稅款項,占總收入的比重達87.72%;四是企業本身的生產收入,該部分在總收入中所占比重不大。江南制造局的產品,絕大部分都是供應國家直接作為軍事消費,并未作為商品流向市場。只是在1902年之后,才有小部分煉出的鋼材供應上海廠商,算是正式商品。研究者甚至明確指出,江南制造局的生產經營不以追求利潤為目的,產品基本上不受價值規律支配,管理缺乏經濟核算,周轉資金不是來自工廠自身的經營收入。但亦有不同的意見出現:“國際軍火市場價值規律既對‘自造軍火’起到了促進作用,也必將影響制造局的生產過程”,“從長遠說,還是要把自造與購買作價格上的比較的:那就是造價高于購買是不能長時間堅持下去自造的”,“從勞動力商品化、價值規律對軍用工業作用及軍用產品進入流通領域等方面綜合起來看,剩余價值規律在其中起著作用就毫無疑義了”。學界對江南制造局生產產品的評價存有不同意見,如果不去考慮是否封建性及資本主義性等較為籠統的概念,而是從具體的產品成本和價格比較,依據所能掌握的資料,“這些軍火成本,比較當時國內市場上的買價是要低一些,而比起向外國軍火廠直接定購的價格,便顯得高了”。
建立煉鋼廠是因為購買鋼材費用太高,“惟造炮所需之鋼料、鋼彈,造槍所需之鋼管,必須購自外洋,其價值運費已不合算”,另一方面在于“一旦海上有事,海程梗阻,則輪船不能抵埠,而內地又無處采買,勢必停工待料,貽誤軍需,關系實非淺鮮”。劉坤一亦強調獨立煉鋼的重要性,“惟需用鋼料仍須取資外洋,不獨利源外溢,遇有緩急,更慮受制于人,亟應設爐自煉,以資利用而杜漏厄”。
清政府致力購買船艦,而非讓江南制造局仿照鐵甲艦,系出于實際情況的考慮:一是北洋艦隊的成軍目標瞄準的是當時最為先進的鐵甲艦,這顯然并非江南制造局所能勝任;二是仿造鐵甲船耗費過大而價值過低。針對江南制造局要求仿造鐵甲船的要求,劉坤一曾專門提出不同意見:“查該局現在制造槍炮藥彈,業必專而始精,不必再造鐵甲船,致糜工費”。
但是江南制造局卻采用了“按勞付酬的自由雇傭勞動制度,與大規模的機器生產相結合,是江南制造局現代化企業的重要標志”,“工人對制造局并不存在人身依附關系”。“機器局制造諸事悉仿外洋辦法,其委員、司事、學徒人等俱不論官階,但照差事之繁簡及資格之深淺,以定薪水多寡”,“內地工匠、小工則人無定數,視工務之緩急為衡,價有等差,較技藝之優劣為準,多寡不等,加減不一”。
與上述江南制造局的經營方式相伴隨,該局被認為是洋務運動中最先進、最完備的資本主義近代化工業之一,“不但創辦早,而且規模大,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很高的歷史地位、重要的意義和重大的作用”。
江南制造總局制造了大量的機器。計有車床138臺,制造母機型機器117臺,起重機84臺,汽爐機32臺,汽爐15座,抽水機77臺,軋鋼機5臺,其他機器135臺,機器零件及工具110余萬件。這些機器既有自用者,亦有賣給或調給其他機器局和民用工業廠家。“在中國機器制造完全是一張白紙情況下,應該承認它對于技術發展是起到相當作用的”。
制造槍炮彈藥:江南制造局的的經常任務是為清軍制造槍炮。制造局起初造的是舊式前膛槍,后膛槍興起后,即于1871年開始試造。1893年又開始試造德國的新毛瑟槍和奧匈帝國的曼利夏槍。該局從1867年至1894年間,所生產的主要軍火數如下:1,各種槍支,51285支;2,各種炮,585尊;3各種水雷,563具;4,銅引,4411023支;5,炮彈,1201894發。軍火供應的范圍遍及全國各單位。
槍炮都離不開火藥,火藥離不開化學。江南制造局對中國近代化學發展的貢獻,可謂是奠基之舉,建成“中國最早的鉛室法硫酸廠,制造出栗色火藥、無煙火藥,對中國近代化學的引入、傳播、應用作出了開創性貢獻”。洋務派自制軍火和近代火藥都要求能生產“三酸”,主要是硫酸。徐壽父子于1870年左右致力于研究鉛室法制硫酸,并于1874年在江南制造局龍華分廠建成中國第一座鉛室法硫酸廠。
造船:自第一艘輪船“惠吉”(初名“恬吉”)下水后,又陸續制造了“操江”、“測海”、“威靖”、“海安”、“馭遠”等八艘兵輪。還制造了7艘小型船只,其中5艘是雙暗輪小鐵殼船。
冶煉鋼鐵:制造局在制造槍炮過程中,出于自給自足的考慮,建立了第一個“洋式煉鋼爐”。制造局于1890年籌建煉鋼廠,在向英國購買15噸的煉鋼爐后,即于1891年煉出第一爐鋼。初期所產鋼材為數不多,“大部分留局自用,小部分供應其他軍事工廠。后來產量增加,自用有余,便以一部分供應上海市場”。
在上述江南制造局的基本數據和事實的前提下,學界對其性質的認識不盡一致。一部分學者認為清政府創辦的軍事工業是封建的、買辦的、反動的,毫無資本主義性;另有學者則認為江南制造局具有資本主義性和進步性。學界目前的研究趨勢,在指出江南制造局存在種種經營弊端的同時,亦指出其在中國近代化方面的積極影響,認為在該局倡率下,一批軍事工廠相繼建立,構成了中國早期現代化多部門、多層次的內容,并進而對思想文化領域的現代化帶來積極影響。
三、比較視野下江南制造局的社會責任
經濟學界、管理學界將近代中國的企業社會責任聚焦于官督商辦企業,但這里有一個基本的史實,且為史學界所普遍認可:國家資本企業在中國近代的發展歷程中居于主導地位和作用,晚清政府興辦的官辦和官督商辦企業是中國近代機器大工業的發端。基于上述歷史事實,如果忽視官辦企業的影響,則難以正確認識近代企業社會責任的本土源頭。
從現有學界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解出發,江南制造總局的企業社會責任可歸結為:為政府生產合格的軍工產品,為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培養技術人才,為近代科技儲備基本的理論基礎。江南制造局的軍工產品雖然不計價值,但須與國際購買價格相較,不能有太大偏差。雖然江南制造總局的軍工產品就中國市場而言不是商品,表面看來不須遵守中國市場的價值規律,但必須遵守世界軍火市場的基本價值規律,如果明顯高于世界市場的價值,清政府寧可購買外國產品。就當時世界市場而言,江南制造局的產品是遵循了一定的價值規律的。前期的研究曾提及此點,指出:價值規律對軍火生產過程將起著重要作用。若軍用產品造價低于外洋購買者,則大批生產,若造價高于從外洋購買價者,那就要停止生產。
翻譯近代科技書籍,培養翻譯人才,是江南制造總局為促進社會發展而做出的舉措。在創辦過程中,江南制造總局先后建設了翻譯館、廣方言館、工藝學堂等機構。
江南制造總局曾組織專門力量翻譯西方近代科技和文化著作,為中國近代科技的發展儲備了基本的知識基礎。“該局陸續訪購西書數十種,厚聘西士,選派局員相與口述筆譯,最要為算學、化學、汽機、火藥、炮法等編,固屬關系制造,即如行船、防海、練軍、采煤、開礦之類,亦皆有裨實用。現譯出四十余種,刊印二十四種”,“又挑選生徒數十人,住居廣方言館,資以膏火,中西并課,一抉其秘,一學其學,制造本原,殆不出此”。這些書籍大都在1870年前后出版,是當時介紹西方科學技術最早的書籍。“有些書曾被后來開辦的各種新式學堂用作正式課本。因此,它在傳播近代生產技術知識方面,是起了有益作用的”。但如同對江南制造局自身的評價一樣,對江南制造局出版譯著的影響也存在不同看法,“從該局出版譯著的銷售數量來看,到1879年6月,已出版的98種譯著只售出3111部;到90年代中期該館共賣出13000部”。認為這些譯著受到了冷遇。筆者以為,這些數字固然能說明一些問題,但考慮到其極強的專業性,分析其影響更多地要從對近代中國科技的發展去考慮問題。
總結近30年來對江南制造局翻譯館的研究,可以將其影響分為三個方面。在工業技術方面:“承擔了當時中國社會急需的基礎科學的傳播和應用技術的傳播兩大任務,對中國近代基礎科學和近代工業技術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在學科建設方面:翻譯館所翻譯的65個化學元素名稱,其中的36個沿用至今,對歷史、農學、測繪、氣象、教育等學科的建設影響巨大;在思想文化方面:培養和促進了近代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成長,成為改良、革命思想生成的知識資源。
建設外語學校和工藝學堂,培養外語、科技和外交人才。1869年廣方言館移駐制造局學館,仍保留廣方言館之名。馮焌光、鄭藻如在所擬開學辦館章程中,對廣方言館所擔負的責任進行了詳細陳述,包括“分教習以專講求”,“集人才以備學習”,“廣制器以資造就”等等。“學館之設,本與制造相表里,況今目擊時艱,創深痛巨,茍非及時振奮,幾無自立地步。所以折衡樽俎,運籌帷幄者,亟宜儲材積學,以期致用”。1874年,江南制造局設立操炮學堂,該學堂是“學習軍事工程的學堂,學習內容為漢文、外文、算學、繪圖、軍事、炮法等”,1881年改為炮隊營。1898年,江南制造局又奏請設立工藝學堂。“前奉憲札行知,以奏明制造添設工藝學堂,飭將江海關道所設之廣方言館及制造局之炮隊營酌量裁并,并擬議辦法”,“擬將職局畫圖房拓為工藝學堂,分立化學工藝、機器工藝兩科,隸入廣方言館”。
江南制造局所設之廣方言館,為晚清外交培養了大批人才。“降至光緒中葉,交涉棘手,需材孔殷,執國柄者始知人才難得,培植之不可不預也。故于館中每期送京學生,率皆甄錄任用之,就中薦歷升階,克躋通顯,膺受中外要職者,已不乏人”,如后來民國外交界的陸征祥、唐在禮、胡惟德、劉鏡人、唐在復、戴陳霖、劉式訓等。
在上兩江總督稟中,林志道指出:“職局開辦三十余年,實為國家總匯工藝之地,則所謂工學者,要惟是精求化學之理法,詳究機器之功用,預計學科必與職局緊切相關,方可共貫同條,交相為用”。對江南制造局在近代科技方面的重要作用可謂一語中的。
作為一種比較,新近的研究從中國電報局入手,分析不同個案之間的差別和共性。研究指出:中國電報局自成立之日起,即不屬于普通的法人企業,它具有清政府主管電報電信業務的政府職能,不但負責政策的制定,而且進行實際的企業經營。與江南制造局相比,中國電報局多了一項制定相關電信政策的政府職能;與輪船招商局相比,中國電報局還負擔有對外交涉的職能。在事關國家政策方面,作為官督商辦企業的中國電報局比江南制造局負擔有更多的責任。中國電報局實際負擔起了本應由政府承擔的外交行為。
研究比較視野下企業社會責任的相關問題,還有一個相類似的概念,即實業救國。在新近的研究中,已經將實業救國作為企業社會責任的一種加以論述,如果仔細考察實業救國在近代中國的情形,或許成為一種思潮,激勵了當時的愛國商人。但問題同樣存在:難以將實業救國作為一個標準去具體量化清末民初的企業。通俗講,實業救國就是鼓勵大家辦工廠、生產出質量好的產品。張謇在1904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果使一國之民,皆能振興實業,舉所謂農工商礦諸事者,開拓經營,不致貨棄于地,則彼外人者,雖有攘取之心,更無著手之處,亦只可為臨淵之羨耳”。作為實業救國的倡導者和實踐者,張謇的本意在這篇文章中說得很清楚,即發展實業以拒外人侵奪。新近的研究強調:“所謂實業救國,即是通過發展工商等實業來改變中國貧困落后的面貌,從而挽救中國、振興中華”。實業救國,仍是要發展工商業之意,與工商業應該如何自律、如何為國家社會服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能否將如此寬泛的實業救國作為近代中國企業的社會責任之一,有待理論界加以探討。筆者以為,雖然實業救國本身有不同爭議,如果出于工業近代化的考慮,淡化該口號的政治派別色彩,其本身符合廣義企業責任的范圍。
如果將實業救國作為近代中國企業的社會責任之一,則中國電報局所承擔的對外交涉就不難理解。中國電報局的確參與了外交,而且其目的是為了維護中國相應的權利,如電信權,但更多的官督商辦企業并未參與外交,洋務派的軍事企業以及大部分商辦企業即屬此種狀況。繼中國電報局之后,具有企業外交行為的有中國鐵路總公司及稍后的路礦總局,但同時期的其他企業則鮮有如此行為。如果我們將目光向后看,從晚清縷述至民國,則氣象似乎為之一變,商人外交運動,以至后來的國民外交運動,在參與的范圍和性質上,都超越了洋務派時期的官督商辦企業。
結語
從近代中國企業的創建及經營事實出發,代表官辦軍事工業的江南制造局、官督商辦企業的中國電報局以及輪船招商局等等洋務企業所表現出來的近代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原始形式是國家責任和政府責任,江南制造局所擔負的正是此種責任的表現形式。就股份制企業而言,官利制和報效制亦屬企業責任的早期形式,但二者更多地是通過企業章程體現,而非企業依照社會發展的要求而去自覺加以履行。現有證據表明:在晚清官辦和官督商辦企業的身上,已經存在近代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本土源頭。
官督商辦等民用工業與官辦的江南制造局相比,二者都強調服務于“自強”和“求富”這一總的洋務運動的大目標,但二者的區別仍然是明顯的。民用企業,如輪船招商局,仍偏重于爭“利權”的方面,而江南制造局則更關注的是影響社會基礎工業發展水平的制造和技術。研究者亦注意到,即使是官督商辦的民用工業,其企業組織形式與舶來的企業社會責任概念亦存在很多的不同之處,近代中國的股份制企業帶有濃厚的中國特點和傳統經濟要素的痕跡。很多情形下,官辦和官督商辦之間的界限并非不可逾越,由官辦轉為官督商辦的例子并不罕見。通過將近代企業責任概念的梳理及對江南制造局相關生產經營情形的概述,筆者以為,近代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源頭,并不僅僅存在于官督商辦企業,通過更多個案研究官辦企業實有必要。企業社會責任是一個正在發展的概念,對于中國學界而言,在追本溯源時,似不妨拋開限定的概念,而從中國近代企業發展的歷史實際出發,將中國企業的發展特點進行理論總結,得出自身的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為方興未艾的企業社會責任研究注入中國元素。
①參見劉俊海著:《公司的社會責任》,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2頁。
②王保樹:《競爭與發展:公司法改革面臨的主題》,重慶:《現代法學》,2003年第3期。
③關于西方企業責任概念的發展,參見黃曉鵬:《企業社會責任:理論與中國實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19~20頁。
④劉長喜:《企業社會責任與可持續發展研究——基于利益相關者和社會契約的視角》,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9年,前言。
⑤楊自業:《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的幾個基本理論問題》,武漢:《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62卷第6期,2009年11月,第815頁。
⑥黃曉鵬:《企業社會責任:理論與中國實踐》,第139~155頁;劉長喜:《企業社會責任與可持續發展研究》,第126~136頁。
⑦參見劉長喜:《企業社會責任與可持續發展研究》,第5頁,表格1.1。
⑧朱蔭貴:《中國近代股份制企業的特點——以資金運行為中心的考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5期,第179頁。
⑨劉長喜:《企業社會責任與可持續發展研究》,第132頁。
[責任編輯 李振武]
作者簡介:侯中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北京 100006
[中圖分類號]K25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14X(2016)02-010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