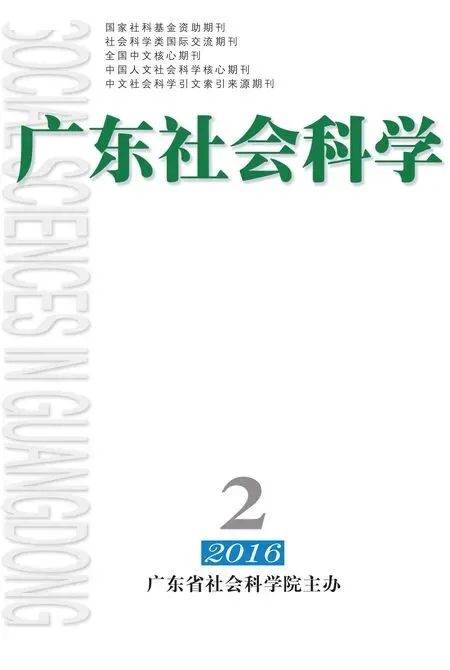南京國民政府第一次全國財政會議新探*
柯偉明
?
南京國民政府第一次全國財政會議新探*
柯偉明
[提 要]為改革財政稅收以鞏固國民黨政權的統治,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于1928年7月召開第一次全國財政會議。此次會議得到中央各部門、地方政府、商會代表及財政經濟專家的積極響應,其代表具有一定的廣泛性和專業性。在為期十天的會議上,代表們圍繞財政、稅制、債務、預算、裁兵等議題展開熱烈討論。經審查和決議,會議制訂了統一財政、劃分國地稅收、整理舊稅和推行新稅的原則和辦法,對南京國民政府財稅政策產生重大影響。
[關鍵詞]南京國民政府 第一次全國財政會議 財政統一 稅收 宋子文
*本文系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二五”規劃項目“民國時期廣東地方稅收研究(1911-1937)”(項目號GD13YLS02)、中山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青年教師培育項目“民國營業稅史研究”(項目號14wkpy61)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1927-1937年的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是從傳統國家走向現代國家的重要階段。在此階段,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經濟得到較快發展,很多經濟指標均達到歷史最高值。這些成績的取得無疑與這一時期的財稅政策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1928年7月,在首都南京召開的第一次全國財政會議對南京國民政府財稅政策有著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就現有研究而言,武艷敏的《統一財政:1928年國民政府第一次財政會議之考察》一文分析了此次全國財政會議的緣起,重點考察了會議對統一財政的影響。①但在筆者看來,關于第一次全國財政會議代表的構成和參會情況,提案的來源、類別和審查情況以及會議對財稅政策的影響均值得深入探討。有鑒于此,筆者擬利用有關歷史資料,對南京國民政府第一次全國財政會議作進一步研究。
一、參會代表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后,為統一中央財政權力,改變軍閥時代國地收支含混、稅收和金融制度紊亂的局面,財政部部長宋子文于1928年6月15日決定召開第一次全國財政會議,派財政部秘書長鄒琳負責會議籌備事宜。6月19日,鄒琳召開財政部職員會議,制定議事規程多項,同時致函各機關、團體等選派代表來京參加會議。②根據《全國財政會議規程》規定,第一次全國財政會議的代表由財政監理委員會委員、總司令及各集團軍代表、政治分會代表、各省政府代表、財政部及其直轄機關代表、各省財政廳長或其代表、各特別市財政局長、財政部選聘的財政經濟專家等組成。③根據財政部秘書處編制的《全國財政會議會員一覽》,筆者對參會代表進行分類統計,其中財政部及其直轄機關代表94人,各省市地方政府代表32人,專家會員23人,中央軍政代表10人,其他部門代表7人,共計166人。④
從代表的構成來看,財政部及其直轄機關代表最多,約占57%;各省市地方政府代表僅占19%,所以很難形成維護地方利益的力量,以至于會議伊始便有地方代表抱怨此次財政會議“多顧及中央收入,而忽略地方支出”。⑤從地方政府代表的構成來看,有19省市派代表參會:安徽4人,河南、山東、廣東各3人,江西、浙江、南京、江蘇各2人,湖北、上海、河北、貴州、陜西、云南、四川、廣西、湖南、福建、甘肅各1人。⑥值得注意的是,四川、云南、廣西等當時尚未處于南京國民政府統治之下的地區也有代表參加會議。雖然地方代表所占比重不大,但其地區分布已經相當廣泛,故此次財政會議是名符其實的“全國財政會議”。
一般來說,與會代表應在會議開幕前提前到達。從到會實際情況來看,6月30日上午報到的代表僅33人,至當天晚上八時,報到者才67人。⑦7月1日上午繼續報到者30余人,中午及下午報到者有二三十人。⑧據統計,在會議開幕當天累計報到人數120人,至會議結束后報到人數累計達166人。也就是說,有40多名代表是在會議開幕以后才陸續趕到。⑨在這些“遲到”的代表當中,某些地方政府代表值得注意。大會開幕后,兩廣代表一直遲遲沒有現身,財政部為此“迭電催請”,結果是“聞已有一人在途”。⑩福建省財政廳廳長陳培錕、福建鹽運使何公敢、福建煙酒局局長史家麟于7月7日才來報到。四川省財政廳廳長以未能及時收到代電為由,“托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函牘科科長林墨代為列席”。也許是隨著第一次全國財政會議“效應”的迅速擴大,兩廣、福建、四川等這些本對會議“漠不關心”的地方因擔心不參加會議會給其帶來不利影響,所以才派代表“姍姍來遲”。
7月1日中午,第一次全國財政會議正式開幕。財政部部長宋子文(會議主席)代表財政部首先作了報告,其后譚延闿、楊樹莊、劉紀文分別代表中央、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致詞,在財政部次長張壽鏞致詞后,貴州省政府代表譚星閣、浙江省政府代表莊崧甫、山東省財政廳廳長魏宗晉、山西財政廳廳長李鴻文紛紛發表演說。出席開幕式的正式代表、黨政要員、商界領袖及其他嘉賓達200余人。此次財政會議共舉行五次全體大會,其報到人數、出席人數和出席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代表們的參會情況。據筆者統計,第一次大會報到人數127人,出席人數110人,出席率為87%;第二次大會報到人數134人,出席人數110人,出席率為82%;第三次大會報到人數144人,出席人數114人,出席率為79%;第四次大會報到人數154人,出席人數96人,出席率為62%;第五次大會報到人數158人,出席人數109人,出席率為69%。出席人數并未隨報到人數的增加而相應增加,以致出席率在前四次大會呈連續下降的趨勢,但每次大會的出席率均遠超過50%的法定出席率,從而保證了會議的合法性。
作為全國財政會議的“總策劃師”,宋子文可謂“參與度最高”的代表之一。由于需要主持第一次全國經濟會議,直至6月30日晚財政部部長宋子文、次長張壽鏞及賦稅司司長賈士毅等才乘夜車從上海趕回南京,準備參加次日召開的財政會議。7月1日上午,宋子文“特邀武漢政治分會財政委員會委員白志鹍,詳詢湖北財政狀況”,爭取了白對統一財政計劃的支持。按照計劃,宋子文得于7月1日下午接見山西、河南等北方各省軍民代表,7月2日接見湖北、湖南、廣東等南方各省軍民代表以及部屬各機關人員。7月1日和2日晚上,宋子文分別宴請了全國財政會議代表和財政會議秘書處全體職員。宋子文不斷與各省市地方政府代表會晤,聽取他們的意見,爭取他們的支持。
實際上,除了主持財政會議之外,宋子文還需要處理很多其他事務,這可從他在開會期間的行程略見一斑。6月30日,宋子文從上海趕回南京主持財政會議,在開完第二次大會之后,宋子文于7月3日連夜前往上海,5日又返回南京,準備主持第三次大會。此時,宋子文接到蔣介石在北平發來的“電召”,要其趕赴北平,“協商軍政費問題及接收舊財部事項”。宋子文原擬7月5日晚乘夜車趕往上海,再轉赴北平,后經與各代表商議,決定赴上海后仍返回南京,待大會結束后再赴北平,并“電蔣總司令,陳述暫緩北上之意”。可見,為全面參與此次財政會議的各項議程,宋子文不得不將蔣介石的“電召”暫時“擱置”。
二、會議提案
提案是參會者密切關注的問題,能夠反映相關利益主體的迫切要求,我們亦可借此窺見會議的主題。根據規定,提案應當在開會前三天提交,其內容包括提出的緣由、解決的辦法等方面;如有臨時提案,須經會員十人以上連署,用書面形式送交主席,酌量編入議事日程。開會前秘書處收到的提案已有80多項,會議期間陸續有代表提出臨時提案。如7月3日劉大鈞、過之翰、黃實、譚星閣等人提出6項臨時議案,7月5日李培天、劉大鈞及湖北省財政廳代表等共提出21項臨時議案。據筆者統計,財政部秘書處編輯出版的《全國財政會議日刊》所載議案共176項:財政部及其直轄機關提案多達70項(約占40%),地方政府提案36項(約占20%),經濟會議移送提案26項,商會代表及財政經濟專家提案24項,中央軍政代表提案14項,大學院、司法部和內政部等部門提案6項。
從地方政府提案的分布來看,山東、浙江、南京等11個省市政府代表及財政廳(局)長提交議案36項:山東8項,浙江、南京、廣東各5項,湖北4項,江蘇、陜西、江西各2項,安徽、貴州、上海各1項。提案多少大致可反映各地參加財政會議的積極性及其在南京國民政府中的影響力。山東省財政廳廳長魏宗晉對財政會議相當積極,提交議案最多;廣東省政府在會議開始數天后才派代表和財政廳廳長馮祝萬來京參會,并提出5項議案。山東、浙江、湖北、廣東等均是當時很有實力的地方,也就是說,地方提案數量與其自身實力大致呈正相關關系。
根據內容不同,筆者對所有提案作了大致的統計分類。在176項提案當中,關于統一財政及劃分國地收支的提案22項,關于整理鹽稅鹽務的提案19項,關于整理中央及地方公債的提案18項,關于改革幣制和發展中央及地方銀行的提案18項,關于發展經濟的提案17項,關于改革及整頓財務行政的提案17項,關于預算、決算及部分機關報送財務經費報告的提案15項,關于裁兵及要求中央劃撥軍費的提案14項,關于裁撤厘金、實行關稅自主及開征特種消費稅、營業稅的提案12項,關于整理煤油特稅、煙酒特稅的提案10項,關于整理土地、田賦及實行禁煙的提案6項,關于開征印花稅、所得稅、遺產稅等直接稅的提案5項,其他提案3項。
各代表提交議案后,接下來的程序便是對提案進行審查。此次財政會議提案的審查和議決采用大會和分組審查會相結合的形式。7月2日下午,全國財政會議召開第一次全體大會,主要圍繞“統一財政”這一重要主題,討論了“統一財政案”、“整理財政大綱草案”、“統一全國鹽稅收入案”、“統一關務用人行政及稅款收支案”、“統一煤油稅收案”等12項提案,最終決定將這些提案交付各組審查。由于提案較多,不可能每個提案人都能就其提案在大會上發言,所以很多提案均由主席指定相關代表陳述。如7月3日下午召開的第二次大會需要討論提案有88項之多。為節省時間,宋子文指定賈士毅代表陳述關于裁厘加稅等提案,陳志道陳述關于鹽務等提案,陳行陳述關于金融等提案,鐘衍慶陳述關于清理漢口庫券等提案,劉紀文報告裁厘經費及建筑費等計劃,張壽鏞陳述確定全國預算宜先確定大政方略案。各代表陳述后,宋子文根據提案內容分別交付各審查組審查。
為更好地審查各項提案,財政會議成立審查委員會,分財務行政、稅務、國用、公債和金融五組。大會開幕之前,各組主任、常務委員和委員已由財政部部長宋子文分別指定。各審查組人員均為熟悉該領域的行政長官或財政金融專家,從而確保各項提案審查工作的有效進行。審查委員會開會時間由各組主任委員自行酌定。7月3日上午起,各審查組陸續展開審查工作。雖然審查委員會共分為五組,但這并不意味著完全由各組獨立進行審查。有的提案涉及內容比較廣,并非一組之力所能審查完成,需要其他組的協助,因而審查工作主要采取分組獨立審查和聯合審查相結合的方式。如7月2日第一次大會交付審查的12項提案就由財務行政、稅務和國用三組聯合審查。7月4日上午,公債組審查提案共有9項,其中有5項由該組獨立審查,另有4項是與金融組聯合審查。由于提案較多,審查工作量大,很多提案須經反復研討才能提交大會審查,以致原本于7月6日召開的第三次大會因“交付審查各案現尚未經各組審查完畢”而不得不延遲至7月7日下午舉行。
在提案審查過程中,由于各方利益難以平衡,意見不一,難免引發激烈爭論。如出席財政會議的武漢商會代表周星棠、劉秉義對金融組收回漢口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發行的紙幣和國庫券辦法表示反對,并強烈要求以上三行“十足收回”。他們的主張和行動得到“湖北全省商聯合會及武漢總商會來電聲援”。7月10日,財務行政組、稅務組召開廣東提案審查會,廣東省財政廳廳長馮祝萬提出,“廣東人民負擔全國革命軍事業之供給為各省之冠”,為此“負債二萬萬元以上”,故要求暫緩一年實行國地財政劃分,以便清理債務。有代表指責該提案實為“破壞財政統一”。馮反駁道:“各省地方確有困難,請求中央允許補助,根本上仍是財政統一,武斷截留國稅,方是有意破壞財政統一也。”經反復討論,審查組認為:“劃一國地稅案,業經大會決議,各省皆有困難,廣東未便獨異,甚望該省遵照此次決議案實行。如確有困難,本會自當請求政府,酌予補助。”雖然此案最終得以審查通過,但廣東省政府代表李民欣在對記者談話中仍有抱怨:“因出席人員代表地方者較少,財部直轄各局人員較多,結果,對地方情形,恐不能盡量討論。”
經各組審查委員會詳加審查后,由各組主任或委員向大會報告審查結果。與第一和第二次大會將提案交付各組審查不同,第三、第四和第五次大會的主要工作是對各組審查結果進行審查和議決。據筆者統計,第三次大會審查各組報告提案41項,決議通過33項,決議通過率為80%;第四次大會審查各組報告提案27項,決議通過17項,決議通過率為63%;第五次大會審查各組報告提案92項(包括經濟會議直接移送的部分提案),決議通過55項,決議通過率為60%。在所有176項提案當中,提交大會議決的提案共有160項,決議通過105項,決議通過率為66%。經大會審查和議決通過的這些提案最終成為國民政府制訂財政經濟政策的重要參考。
三、對財稅政策的影響
在第一次全國財政會議上,參會代表從中國的實際國情出發,借鑒西方國家財政稅收制度和實踐經驗,提出了許多解決中國財政問題的建議。經會議審查和決議通過的提案對南京國民政府財稅政策產生重大影響。
第一、統一財權及劃分國地稅收。在傳統中國,財政大權一般由中央牢牢控制,地方沒有合法的獨立財源。近代以后,中央政治權力逐漸衰落,地方督撫和軍閥的權力日益膨脹,關稅、鹽稅、田賦、厘金等國家稅收多為地方截留。如何統一全國財政,加強中央財政權力,成為此次全國財政會議關注的焦點。財政部提出的“統一財政案”,經審查討論后,在大會得以決議通過。該案提出,統一財政必須從“規章”、“行政”、“用人”、“收支”四個方面著手,其具體辦法為:(1)國稅范圍內的財政規章及用人行政概歸財政部核定處理,各省的中央稅收亦應遵財政部規章辦理。各省任命中央征收人員有成績者,由財政部加委和任免考核;(2)中央稅收一律徑解財政部金庫,支出一律由財政部支付;(3)由會員列表報告各省實在數目作為考核的準則;(4)由會員擬增收減支的數目,為編制預算作準備。
要統一財權,就必須明確劃分國地稅收。中央黨部代表譚延闿在會議開幕致辭中便講到:“大凡國家行政,總要將國地權限分清。國家的稅,當然歸國家;地方的稅,當然歸地方。”經詳加討論,大會決議通過了賦稅司司長賈士毅提出的“實行劃分國家稅地方稅及國家費地方費案”。該案對國家稅和地方稅作了明確劃分:國家稅主要包括鹽稅、關稅、常關稅、煙酒稅、卷煙稅、煤油稅、厘金及郵包稅及將來創辦的所得稅、遺產稅等,地方稅主要包括田賦、契稅、牙稅、當稅、商稅、船捐、房捐、屠宰稅及將來創辦的營業稅、地稅等。盡管此種稅收劃分未能顧及縣(市)級的財政需求,由此而造成地方“財權”和“事權”不均衡,以致地方性苛捐雜稅層出不窮,但其畢竟是中國現代分稅制的初步實踐。
第二、整理舊稅。稅收是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無論是統一財政還是劃分國地稅收,均離不開稅制改革。北洋政府時期,尤其在一戰期間,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經濟進入了快速發展的“黃金時代”。雖然關稅、鹽稅不斷增加,但其在征收過程中仍存在諸多問題,未能滿足政府日益增加的財政需求。在此次財政會議上,代表們就如何整理關稅、鹽稅積極獻言獻策。關稅最大的問題是為外國人把持,不能自主,嚴重影響民族經濟的發展。經熱烈討論,會議最終通過了關稅自主政策:(1)擬由財政部令飭國定稅則委員會編訂國定稅則,于1928年8月31日前編制就緒,呈由財政部轉請國民政府核定,至遲于10月1日公布;(2)依照北京關稅會議議定時間,自1929年1月1日起實行關稅自主;(3)宣告關稅自主以后,華洋職員之待遇一律平等,稅關上一切行政須整齊、嚴肅、合理。鹽稅最大的弊病是稅率紊亂,造成稅負分配不均。正如鹽務署在提案中指出:“是以鹽稅之在今日,不患稅率日重,而患稅率之不均。欲矯其弊,當自劃一稅率始。”經大會審查通過了整理鹽稅辦法,其主要內容有:(1)各省限于一月內造報近三年鹽稅正稅、附稅及附加各項捐費實收數表;(2)由財政部咨請各省政府聲明所有各項鹽稅附稅作為臨時性質,以后須逐漸減少,待財政充裕時一律取消;(3)各地正稅稅率因與產區遠近有關系,待考察情形后再行厘訂。經此整理之后,關稅和鹽稅在南京國民政府稅收收入結構中的地位更加穩固。
煙酒稅、印花稅也是財政會議著力整理的對象。自1915年煙酒實行公賣后,因事權不能統一,產銷數量無精密統計,征收辦法無明確標準,人民深感痛苦,稅收毫無起色。會議為此擬定了整頓煙酒稅的步驟,其主要分為三步:第一步,調查煙酒所在地的產銷數量,以定比額范圍;第二步,調查煙酒實際價格,以定稅率標準;第三步,訓練稅收人才,實行論價收稅,改良包商及委辦制度,計劃待辦有成效以后,再由財政部規定公賣法,實現煙酒公賣政策。印花稅是晚清時期從西方引進的現代稅制,因法規不一,引發各種糾紛,致使征收困難重重。為增加收入,會議決議整頓印花稅,其辦法主要有:稅票均由中央頒發,將以前各省自印稅票一律廢止;稅法均照現行條例辦理,各省單行稅則一律廢止;責成各省局長訓練合格人才,積極宣傳和勸導,使民眾養成納稅習慣;對故意隱匿者及協助不力的官員嚴加懲處。財政會議對煙酒稅、印花稅等舊稅的整理,不僅清除征收管理過程中的積弊,而且有利于國家收入的增加。
與以上舊稅不同,厘金是被裁撤的對象。作為晚清沿襲下來的一種通過稅,厘金因層層剝削而備受詬病。厘金名為國家收入,但長期為地方控制,在地方財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果貿然將厘金裁撤,勢必影響地方財政,所以不少地方在裁厘問題上躊躇不前,甚至極力反對。此次財政會議上,代表們圍繞裁厘及其抵補問題展開討論。賦稅司司長賈士毅主張先將厘金收歸中央,待時機成熟再行裁撤。鑒于裁厘問題的復雜性,劉大鈞提議設立“裁厘委員會”專門負責實行裁厘事宜。此兩項提案均得到眾多代表的贊同,并經大會決議通過了《裁厘委員會大綱》。根據會議決議,裁厘委員會于1928年7月15日召開成立大會,商定裁厘時間及抵補稅項。后因政局影響,直至1931年以后,厘金才逐漸走下歷史舞臺。在此過程中,第一次全國財政會議所確立的原則和辦法無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
第三、推行新稅。在整理舊稅的同時,不少代表提出推行所得稅、遺產稅、營業稅等西方現代稅制的建議和方案。與西方國家以直接稅為主體的稅收結構不同,當時中國各種賦稅皆為間接消費稅。據劉紀文分析,“以我國一般人民經濟力之貧弱,消費品數量,除生活必需品者外,有減無增,消費稅之收入,亦難期發達,影響于國家財政者甚大。”為改變此種狀況,劉紀文提出施行所得稅,并逐步建立以所得稅為主體的稅收體系的建議:“待所得稅收入逐漸增加以后,即可以其為國家之主要賦稅,而將其他妨礙人民生活之消費稅,次第廢止。”賈士毅也主張推行所得稅和遺產稅:“近代賦稅制度有兩大原則:曰均平,曰普遍……如何而能均平、普遍,則所得稅、遺產稅而已。”賈士毅為此專門擬訂了《所得稅條例》、《所得稅施行細則》、《遺產稅暫行條例》、《遺產稅施行細則》等章則,對所得稅和遺產稅的課稅對象、稅率標準、計稅方法及課稅程序等作了明確規定。這些稅則經審查組討論和修正后交付大會決議,為后來實施所得稅和遺產稅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營業稅是此次財政會議討論的熱點,其重要性在于抵補地方裁厘損失。裁厘損失有中央和地方之別,關稅和特種消費稅可抵補中央損失,至于地方損失如何抵補問題,浙江省財政廳代表提議該省“首先實行裁厘并開辦營業稅以資抵補”。經討論后,大會確立了各省市地方舉辦營業稅的原則:(1)將牙稅、當稅擴充為營業稅,廢除牙當兩稅名目;(2)各省舉辦營業稅時,由財政廳自行擬定課稅種類及征收方法,呈由財政部核準備案;(3)已由中央征收的各種物稅不得再征營業稅。會后召開的裁厘委員會會議決議通過了《各省征收營業稅辦法大綱》,對營業稅的課稅對象、稅率和課稅標準、課稅程序等作了明確規定。經此籌議之后,有的省份開始籌劃征收營業稅事宜。浙江省財政廳廳長陳其采及委員莊崧甫計劃取消全省各地統捐局,在省會設立營業稅總局,在各縣設立營業稅分局,廢除苛捐雜稅。但受政局影響,各省市裁厘及開征營業稅進程被迫一再擱置。至1931年1月以后,各省市才相繼制訂征收章則,設立征收機關,逐步建立起地方性的營業稅征收和管理制度。
四、余論
近代以后,中國社會經濟發生了深刻變化,其重要標志之一是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作為國家財政的重要收入來源,稅收是維持政府正常運作及推動各項現代化事業建設的資金保障。政府只有在掌握充足財力的基礎上才能夠大力發展社會經濟,改善民生,乃至維護國家安全。與此同時,工商業經濟的發展為政府提供了豐富的稅源,這要求建立與之相適應的財政稅收制度。1927-1937年的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被稱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白銀時代”,也是中國現代財政稅收制度形成和發展的重要階段。這一時期很多財政稅收政策均源于1928年召開的全國經濟會議和全國財政會議。親歷兩次會議的商界領袖王曉籟有如此之比喻:“經濟會議是雛形的股東大會,財政會議是正式的職員會議。”1928年7月召開的第一次全國財政會議不僅確定了財稅政策改革的大方向,而且制訂了許多具體辦法。正如財政部部長宋子文在致閉幕詞中所言:“在大會里,各會員對于提案都能詳細研究,認真討論。對于各種案件,大概都有一個方針,使辦理財政人員可以有所遵循,或備采擇。”鑒于此次會議所取得的積極效果,有代表甚至提出每年舉行一次財政會議的主張。盡管此種主張最終未能實現,但此后國民政府在面對紛繁復雜的財政問題時,仍采用召開全國財政會議的方式,集思廣益,商討國家重大財政稅收政策,1934年和1941年分別召開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國財政會議。可以說,國民政府每次重大財稅政策的制訂和調整都離不開全國財政會議,而第一次全國財政會議的示范效應不言而喻。不過,由于在南京國民政府初期,國民黨政權尚未完全穩固,中央與地方關系尚未完全“正常化”,有的問題非開會即能解決。第二集團軍代表兼山東省財政廳廳長魏宗晉就坦白地指出:“裁兵問題,為目前財政之先決問題,然必商諸國府軍委會,詳為籌劃,恐非全財會(全國財政會議)所能斷然處置也。”有的財政稅收政策雖已制訂,但要實施卻非易事,如至1931年才正式裁撤厘金,1936年所得稅、遺產稅等新稅才相繼開征。盡管如此,我們都無法否認第一次全國財政會議對南京國民政府財稅政策產生了重大影響。
①武艷敏:《統一財政:1928年國民政府第一次財政會議之考察》,開封:《史學月刊》,2006年第4期,第125~128頁。
②《會議籌備之經過》,上海:《申報》,1928年6月28日,第11版。
③《全國財政會議規程》,《全國財政會議日刊》,第一號1928年第1期,第3~4頁。
④《全國財政會議會員一覽》,全國財政會議秘書處編:《全國財政會議匯編》第一類,1928年7月,第14~25頁。
⑤《代表對提案意見》,上海:《申報》,1928年7月 3日,第17版。
⑥⑨《全國財政會議會員一覽》,全國財政會議秘書處編:《全國財政會議匯編》第一類,1928年7月,第14~25頁。
⑦《會員共到六十七人》,上海:《申報》,1928年7 月1日,第18版。
⑧《昨日續到之會員》,上海:《申報》,1928年7月2日,第12版。
⑩《兩粵代表尚未到會》,上海:《申報》,1928年7 月3日,第17版。
[責任編輯 李振武]
作者簡介:柯偉明,中山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博士。廣州 510275
[中圖分類號]K26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14X(2016)02-011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