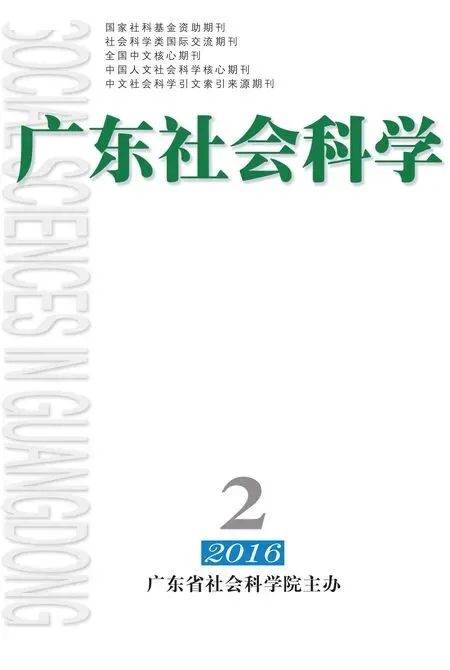日本漢詩引用《詩經》的方式及其學術意義*
毛振華
?
日本漢詩引用《詩經》的方式及其學術意義*
毛振華
[提 要]日本漢詩推崇《詩經》,常用《詩經》的語言和表達形式進行創作,主要表現為對《詩經》中的詩題、詩句、詩詞、意象的引用和化用。日本漢詩引用《詩經》形式的多樣性顯現出,日本漢詩對《詩經》從刻意模擬、融會創新逐漸到適合日本文化審美需要的不斷探索。日本漢詩引用《詩經》時不僅重視繼承《詩經》所蘊含的文學靈性,而且在內在精神上與“溫柔敦厚”的詩教具有一脈相承的關系,顯現出對《詩經》政治教化功能的繼承。這種學中有創的引用《詩經》的方式使得日本漢詩修辭優雅、婉轉含蓄,豐富了日本漢詩的表達方式,提升了其表現力和文化內涵,彰顯了《詩經》在日本的文化影響力,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日本漢詩 詩經 引用 創造力 學術史意義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日本《左傳》學研究”(項目號14YJC751030)、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項目攻關計劃青年重點項目“日本《左傳》學研究”(項目號2013QN047)的階段性成果。
《詩經》是最早傳入日本的中國典籍之一。據《日本書紀》所載,繼體天皇7年(513年),百濟國王派五經博士段楊爾攜帶《詩經》等赴日,深受日本貴族階層推崇。7世紀初圣德太子制定的《憲法十七條》便有援引《詩經·小雅·四牡》“王事靡盬”①等內容。日本《詩經》研究興盛,江戶時期宇野東山的《毛詩國字解》、中井履軒的《詩經彫題略》、皆川淇圓的《詩經繹解》、仁井田好古的《毛詩補傳》、龜井昭陽的《毛詩考》,現代以來白靜川的《〈詩經〉——中國的古代歌謠》、長澤規矩也的《毛詩注疏》、吉川幸次郎的《詩經國風》等都產生了非常大的學術影響力。在日本漢詩創作中,《詩經》也受到特別的取法與借鑒,主要包括對《詩經》詩題、詩句、詩詞、意象的引用和化用,有力地促進了日本漢詩的創作。
一、日本漢詩引用《詩經》的方式②
《詩經》具有鮮明的文化特征和豐厚的文化意蘊,日本漢詩的創作技巧、思想內容等常常受到《詩經》的具體影響。日本漢詩以正面引用《詩經》為主,主要包括以下四種形式:
(一)詩題的引用
日本漢詩善于引用詩題,詩作中所表達的思想內容與所引《詩經》的主旨或主題基本一致。藤原宇合《在常陸贈倭判官留在京序》曰:“義存伐木,道葉采葵。”《伐木》為“燕朋友故舊也……親親以睦,友賢不棄”③之詩,作者引用此意比喻朋友間真摯的友誼。刀利宣令《秋日于長王宅宴新羅客,賦得“稀”字》曰:“相顧鳴鹿爵,相送使人歸。”鳴鹿,即《鹿鳴》,《毛詩序》曰:“燕群臣嘉賓也。”④作者引用此意寓意宴會時的和諧歡愉。橘在列《右親衛源亞將軍忝見賜新詩不勝再拜敢獻鄙懷》曰:“為君更詠柏舟什,莫使風流俗客聞。”柏舟什是指《邶風·柏舟》篇,是“言仁而不遇”⑤之詩,作者借以表達賢者不遇的感嘆。梁田蛻巖《同諸客今泉氏宅賞花得西字》曰:“樽前日日醉如泥,棠棣歌成留客題。”《棠棣》亦作《常棣》,是“燕兄弟之詩”⑥,作者借以表達兄弟情誼的深厚。
(二)詩句的化用
日本漢詩化用《詩經》詩句的形式具有多樣性。有整句化用入詩的,如久家朗《墨竹幅詩》“譬如伯氏塤,和以仲氏篪”語出《小雅·何人斯》“伯氏吹塤,仲氏吹篪”,寓意兄弟二人相應互和。藤田彪《和文天祥正氣歌》“武夫盡好仇”語出《周南·兔罝》“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表現了對宏大的天地元氣的贊頌。三島中洲《富岳》“翼然垂拱溫如玉,君子國中君子山”語出《秦風·小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言說君子之溫和如同玉之純凈光澤。菅原道真《客館書懷同賦交字寄渤海副使大夫》“珍重孤帆適樂郊”語出《魏風·碩鼠》“逝將去女,適彼樂郊”,表達送別副使時的祝福。尾藤孝肇《讀白氏長慶集》“樂天若有知,必不我遐棄”語出《周南·汝墳》“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表達對白居易詩作的喜好。森春濤《春日藍川即矚》“楊柳依依誰”語出《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表達對朋友的依依惜別之情。
有略變詞語化用入詩的,如大津首《春日于左仆射長王宅宴》“飽德良為醉,傳盞莫遲遲”化用《大雅·既醉》“既醉以酒,又飽以德”,表達宴樂之歡和心滿意足之意。古賀精里《訪桐原拈韻》“伯仲塤篪坐上分”化用《小雅·何人斯》“伯氏吹塤,仲氏吹篪”描寫真摯的情感;“江天釀雪正同云”則化用《小雅·信南山》“上天同云,雨雪紛紛”描摹優美的意境。柴秋村《魚目》“詎圖一塊他山石,今日公然稱玉來”則反用《小雅·鶴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諷喻以假亂真的社會現象。
有詩旨、句式兼而化用的,如藤原宇合《奉西海道節度使之作》“往歲東山役,今年西海行。行人一生里,幾度倦邊兵”化用《豳風·東山》“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東曰歸,我心西悲”之句。藤原宇合擔任過西海道節度使,深知兵役、徭役給百姓帶來的苦痛,詩作寫盡了人們厭戰的心聲,與《東山》所表達的主旨基本一致。
(三)詩詞的化用
日本漢詩常常化用《詩經》的詞語入詩,豐富了其文化內涵。有直接引用《詩經》詩詞意義的,如山田三方《七夕》“窈窕鳴衣玉,玲瓏映彩舟”中“窈窕”出自《周南·關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以“窈窕”描繪織女形象,文情并茂,表現出作者高尚的審美情趣。菅原道真《不出門》“萬死兢兢跼蹐情”中“兢兢”、“跼蹐”分別出自《小雅·小》“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和《小雅·正月》“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生動地描繪出了作者小心謹慎的神情。佐藤坦《送河合漢年歸姬路》“靡盬東西不憚頻”中“靡盬”出自《唐風·鴇羽》“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寓意為了國事,不怕麻煩,頻頻奔走東西。新井義質《早春感懷》“近求幽谷友,隨意弄芳辰”中“幽谷”出自《小雅·伐木》“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表達就近尋求逸居幽谷之友的愿望。此外,橘在列《右親衛源亞將軍忝見賜新詩不勝再拜敢獻鄙懷》“泣染箱中綠竹文”中“綠竹”出自《衛風·淇奧》“瞻彼淇奧,綠竹猗猗”;菅茶山《赴鴨方途中》“知是授衣期已近,村家竹里響棉弓”中“授衣”出自《豳風·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榊原篁洲《初冬偶興》“素食誰無恥,空懷報國心”中“素食”出自《魏風·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食兮”;林羅山《江城子》“兆民巖瞻皆敬仰,向殷鑒,鑒無窮”中“殷鑒”出自《大雅·蕩》“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有使用《詩經》詩詞引申意義的,如境部王《宴長王宅》“欲知今日賞,咸有不歸情”中“不歸”出自《小雅·湛露》“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原意為因酒醉不能回家,這里卻烘托了宴會時的歡樂和諧的濃烈氣氛。野村篁園《惜秋華》“點綴墻陰,渾疑七襄新織”,守屋元泰《獨酌得故人書》“坐靜忘三伏,篇新奪七襄”中“七襄”出自《小雅·大東》“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本是指織女七次移動位置,但不能織成文彩鮮明的綢子,這里是活用,寓意為織成的美麗綢緞。林春信《春日漫興》“斯民何蚩蚩,香飯供壞衲”中“蚩蚩”出自《衛風·氓》“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原指笑嘻嘻的樣子,這里寓意其無知愚蠢。
(四)意象的引用
《詩經》中豐富的意象給日本詩人以極大的影響,他們時時加以效仿。有悲情意象,如“禾黍”雖泛指莊稼,但卻用來比喻亡國的悲傷,典出《王風·黍離序》“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松平康國《詠史》“巨橋之粟鹿臺財,身后唯余禾黍哀”借用“禾黍”意象表達對國破家亡百姓的深切同情,同時也為統治者提供了政治上的借鑒。
有愛情意象,如“復關”象征所思戀男子的住地,語出《衛風·氓》“乘彼垝垣,以望復關”,廣瀨淡窗《讀小說》“復關咫尺即千里,懷中錦字憑誰傳”借用“復關”意象抒發了對思慕男人的相思之情。“桑中”象征男女的幽會相戀,語出《鄘風·桑中》“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廣瀨淡窗《讀小說》“為君更固金蘭約,不比桑中契易遷”借用“桑中”意象抒寫桑間歡會之情不若君子之約。
有友朋意象,如“棣萼”象征兄弟,語出《小雅·棠棣》“棠棣之華,鄂不鞾鞾”,賴山陽《下筑后河過菊池正觀公戰處感而有作》“棣萼未肯向北風,殉國劍傳自乃父”借用“棣萼”意象表達對兄弟節義精神的欽慕。“同袍”象征朋友,語出《秦風·無衣》“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廣瀨建《桂林莊雜詠示諸生》“休道他鄉多苦辛,同袍有友自相親”借用“同袍”意象寓意親密無間的手足親情。
此外,“多黍”象征豐收,語出《周頌·豐年》“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菅原道真《路遇白頭翁》“二天五康衢頌,多黍兩岐道路聲”借用“多黍”意象,通過豐收場景反襯百姓生活的苦辛,揭露時政的弊病。“鷹揚”象征威武,語出《大雅·大明》“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伊藤長胤《題太公釣渭圖》“誰知異日鷹揚者,即是當年鵠發人”借用“鷹揚”意象,抒發對得遇文王而成就一番事業的羨慕。
二、日本漢詩引用《詩經》的特點
日本漢詩引用《詩經》與日本漢詩的發展以及積極學習中國文化等密切相關。日本漢詩引用《詩經》形式的多樣性顯現出,日本漢詩對《詩經》從刻意模擬、融會創新逐漸到適合日本文化審美需要的不斷探索。
(一)引用形式的不斷創新
從以上分析可知,日本漢詩引用《詩經》的形式具有多樣性,主要有詩題的引用、詩句、詩詞的化用以及意象的引用等。大部分的詩作以引用一兩處《詩經》為主,也要長篇累牘引用《詩經》的。如佐久間啟《泄泄八章》共17句,化用詩句的有8處,在整體句式和結構上幾乎完全效仿《詩經》。其中略變詞語入詩者5處,“將者泄泄,蠻方孔棘”分別化用《大雅·板》“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和《小雅·采薇》“豈不日戒,獫狁孔棘”;“匪風飄揚,匪瀾澎湃”化用《鄶風·匪風》“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念彼神京,寤嘆有愾”化用《曹風·下泉》“愾我寤嘆,念彼周京”;“憂思如毀,其誰知之。悲憤如噎,其誰思之”分別化用《周南·汝墳》“魴魚赪尾,王室如毀”和《王風·黍離》“行邁靡靡,中心如噎”;“夏夜之短,耿耿如年”化用《邶風·柏舟》“耿耿不寐,如有隱憂”;“摽擗不寐”化用《邶風·柏舟》“靜言思之,寤辟有摽”。整句化用入詩者三處,“云如之何”出自《小雅·小弁》“心之憂矣,云如之何”;佐久間啟《泄泄八章》“載笑載言”出自《衛風·氓》“既見復關,載笑載言”;“泣涕漣漣”出自《衛風·氓》“不見復關,泣涕漣漣”。程千帆評此詩曰:“偶為四言,彪炳可玩。其中有物,雖多用三百篇成語,亦無害也。”⑦另如大須賀履《野狐婚娶圖》字摹句擬,多處摘錄《詩經》詩句,“綏綏成隊鹵籬簇”化用《衛風·有狐》“有狐綏綏,在彼淇梁”;“曾是結縭經母誨”化用《豳風·東山》“親結其縭,九十其儀”;“肯以贈芍頗圣戒”化用《鄭風·溱洧》“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白日青天逾墻走”化用《鄭風·將仲子》“將仲子兮,無逾我墻”。這些詩作言之有物,感情充沛,但通觀全篇似有堆砌《詩經》典型元素之嫌,無論從形式還是內容上都有刻意模仿《詩經》的痕跡。
廣賴旭莊認為:“邦人之才,巧于模仿……至文章經義尤甚。”⑧日本漢詩作家普遍浸潤《詩》學風尚,其《詩》學修養日臻成熟,以上所舉不僅有佐久間啟《泄泄八章》、大須賀履《野狐婚娶圖》等直接大篇幅抄錄《詩經》篇章入詩的,而且還有大量直接截取《詩經》相應句子入詩的,這些都是直接襲用《詩經》篇制、句式等手法,顯現出刻意學習和模擬《詩經》的痕跡,但這些并不是漢詩作家學習《詩經》的最終目的。郭紹虞先生說:“實則昔人擬古,乃古人用功之法,是入門途徑,而非最后歸宿。”⑨廣賴旭莊所言“巧于模仿”即是巧妙的化用,或化用《詩經》的體裁、風格和藝術手法創作詩篇,或化用相應詩題、詩句、詩詞、意象等入詩,根據自己創作的需要對《詩經》篇章、句式等進行能動性的改造、化用和發揮,從而達到一種創新的境界。日本漢詩通過對《詩經》詩題的引用、詩句、詩詞的化用、意象的引用等形式上的有機整合,使得《詩經》成為日本漢詩和日本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日本漢詩引用《詩經》形式的多樣性顯現了漢詩作家對《詩經》的熟悉程度,他們已不再是對《詩經》的簡單模仿或移植,而是廣泛地吸取和借鑒了《詩經》元素進行創造性創作,言己之志,抒己之情,顯示出日本漢詩創作從刻意模擬到融會創新,日臻達到渾融自然,逐漸適合日本文化審美需要的不斷探索。這種藝術形式和藝術技巧上的不斷創新,為日本漢詩創作積累了一定的藝術經驗,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日本文化。
(二)注重對《詩經》的文學靈性和政治教化功能的繼承
《詩經》傳入日本伊始,便被日本天皇納入其“德治”、“仁政”等治國理念之中,人文倫理色彩濃郁。《憲法十七條》中的第十二條“國非二君,民無二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即有模擬《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痕跡。大化革新后,《詩經》等成了為日本儒學教育的主要內容,“立教施政者,必不可不讀《詩》”⑩成為治國理念。
從日本漢詩的發展史來看,王朝時代是日本漢詩的發展期,皇室貴族、高官是漢詩創作的主體;五山時代是日本漢詩的嬗變期,僧人是創作主體;江戶時代是日本漢詩的成熟期,詩壇的主人主要是儒者;而明治時期實現“文明開化”,也是漢詩的日漸衰落期。作為漢詩創作最繁榮的江戶時期是“儒者的文學”,朱子學一度占據統治地位,友野霞舟說:“國初諸老,大抵專意于經學,不屑繪章琢句,故所得不多。間有所得,亦多鄙言累句,固不足傳焉。”儒士多專意于《詩集傳》,受其影響,詩歌中道德教化意味濃郁。而以伊藤仁齋為代表的古義學派、以荻生徂徠為代表的萱園派等竭力擺脫宋學束縛,尊崇人情,重視性情抒發。伊藤仁齋認為:“《詩》以道性情。”“人情盡于《詩》。”荻生徂徠認為:“其(《詩經》)言主人情。”《詩經》“性情說”深刻影響著日本文化及漢詩創作,使得漢詩作家積極融合《詩經》性情元素入詩。俞樾《東瀛詩選·序》曰:“其始猶沿襲宋季之派,其后物徂徠出,提倡古學,慨然以復古為教……傳之既久,而梁星巖、大洼天民諸君出,則又變而抒寫性靈,流連景物。”
夏傳才先生認為,《詩經》等“具有高度的思想和藝術成就與美學價值,反映了人類共通的思想感情,能夠引起日本人士心靈的共鳴,許多優秀作品被日本人作為學詩的范本”。日本漢詩所引《詩經》的內容以表達性情和宣揚道德教化為主,以上所引《周南·關雎》、《豳風·東山》、《邶風·柏舟》、《鄭風》中的《溱洧》、《將仲子》、《衛風》中的《氓》、《有狐》、《淇奧》等是具有鮮明的感情色彩的詩篇,如服部元喬《明月篇效初唐體》曰:“齊什陳篇歌相見,佳人少婦照可憐。”齊什陳篇是指《詩經·齊風》、《詩經·陳風》中與明月有關的詩篇,表達月夜懷人的相思,作者化用此意借以表現佳人少婦的閨怨情思,使得詩作具有濃郁婉轉的情感色彩。而《小雅》中的《哀鴻》、《鶴鳴》、《何人斯》、《正月》、《小》、《大雅·蕩》、《秦風·黃鳥》、《唐風·鴇羽》、《魏風·伐檀》、《王風·黍離》等詩篇具有強烈的斗爭性和批判精神,如“哀鴻”比喻流離失所的災民,典出《小雅·哀鴻》“鴻雁于飛,哀嗚嗷嗷”,森槐南《臺城路》“農夫嗚咽暗哭,似哀鴻遍野,聞者酸鼻”借用“哀鴻”意象表達對水災中流離失所百姓的無限憐憫和對統治者的激烈批判。《小雅》中的《伐木》、《鹿鳴》、《常棣》、《湛露》、《既醉》、《大雅·大明》、《秦風·無衣》、《周南·兔罝》、《衛風·淇奧》等具有維系人倫關系和弘揚道德規范的作用,如息長臣足《春日侍宴》曰:“多幸憶廣宴,還悅湛露仁。”安倍首名《春日應詔》曰:“湛露重仁智,流霞輕松筠。”《湛露》為“天子燕諸侯”“示慈惠”之詩,作者借以表達對高尚仁德風范的贊頌。
日本漢詩作家引用《詩經》時積極繼承其所蘊含的文學靈性,注重引用的抒情性和審美性,賦予了濃郁強烈的情感色彩,更加凸顯詩作的情感特征。與此同時,日本漢詩引用《詩經》時在內在精神上與“溫柔敦厚”的詩教具有緊密的一脈相承的淵源關系,“符合經典性和權威性的教化作用”,重視社會倫理、道德倫理和政治倫理功能,注重個人道德的修養,陶冶人格,涵養德性,顯現出對《詩經》政治教化功能的積極繼承。
三、日本漢詩引用《詩經》的學術意義
(一)豐富了日本漢詩的表達方式
伊藤仁齋認為:“《詩》出于古人吟詠情性之言,而無勉強矜持之態,無潤飾雕鏤之詞,是以見者易入,而聞者易感,故圣人取焉。”從日本漢詩引用《詩經》的史實可知,《詩經》作為典范無論是形式體裁還是語言技巧,都蘊涵著豐富的文化意蘊,成為一種特殊的語言符號系統和表達方式,被日本漢詩作家廣泛地學習、模仿。空海《文鏡秘府論·南卷》:“凡作詩之人,皆自抄古今詩語精妙之處為隨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興若不來,即須看隨身卷子以發興也。”《詩經》等成為日本詩人的囊中之物,是日本漢詩發言立論的重要資料。西方學者在《引用的基本作用》一文中,提出了引用的三種主要作用:一是訴諸權威;二是顯示博學;三是修飾。日本漢詩在藝術精神和題材內容上對《詩經》多有取法和借鑒,《詩經》元素已深深滲透到日本文化之中,成了日本漢詩修飾辭令、豐富意涵、闡釋事理的重要媒介。千余年來,《詩經》影響了日本漢詩,日本漢詩受容了《詩經》,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寶貴資料。
(二)擴大了《詩經》的文化意涵
江村北海《日本詩史》卷四說:“夫詩,漢土聲音也。我邦人,不學詩則已。茍學之也,不能不承漢土也。”日本漢詩不滿足于簡單的模仿,而是把《詩經》作為一個意象符號融會到其詩歌創作之中。金子彥二郎認為日本文化對外來文化具有“攝取醇化”功能,即是“將所有外來文化中優秀的部分賦予日本的生命,以日本國民的血液作為其營養元素,使其生成發展”。如“美人”象征賢人君子,語出《邶風·簡兮》“云誰之思,西方美人”,木戶孝允《逸題》“欲訴憂愁美人遠,滿城梅雨杜鵑聲”;前原一誠《逸題》“一場殘醉曲肱睡,不夢周公夢美人”等都是借用“美人”意象表達對維新志士的追慕。又如釋五岳《蘭圖》“鳥遷喬木后,幽谷亦春風”化用《小雅·伐木》“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句,《詩經》此句本是以鳥與鳥的相求,擇高枝而居,作者這里卻把幽谷和喬木并列在一起,表達遠離現實政治,與世無爭的豁達心態。以上詩作雖然在用詞、意象和象征主義手法上對《詩經》有所借鑒或化用,但在意境上又有所創新,寫出了日本漢詩作家的真實情感和現實心聲。這種學中有創的方式使得其詩作修辭優雅、婉轉含蓄,在日本的文化環境和語言環境中折射出異樣的光彩,提升了日本漢詩的表現力和文化內涵,也是日本漢詩的一種重要生產方式。
(三)彰顯了《詩經》在日本的文化影響力
日本漢詩屢屢引用《詩經》顯現了《詩經》在日本的巨大影響力,是中日文化交流的有力象征。龍草廬《平安城》“文物猶存周禮樂,朝儀久習漢風流”是日本受容中國文化的最好見證和精切概括。在日本詩人心中,《詩經》乃“群德之祖,萬福之宗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長谷允人《客中論詩,偶有懷故人,示兒炗,在天草》“郁郁三百篇,振古難再遇”等表達了對文采斐然的《詩經》的傾慕;廣瀨建《論詩贈小關長卿、中島子玉》“詩歌寫性情,實隨民俗移。風雅非一體,古今固多歧。作家達時變,沿革互有之。茍存敦厚旨,風教可維持……誰明六義要,以起一時衰”則表明了日本漢詩對《詩經》風雅精神、賦比興傳統等的承繼。日本漢詩的創作充分發掘了《詩經》中所蘊含的政治資源、思想資源和文化資源,既反映了漢詩作者對《詩經》的熟悉,也反映出《詩經》對日本文化的深刻影響。
此外,日本漢詩所引《詩經》作為游離于《詩經》文本之外的資料存在,是用文學性的語言表達對《詩經》的理解和體悟,顯現出不同文化相互尊重汲取的精神,使得《詩經》在日本文化中呈現出一種新的光彩,激活了《詩經》在日本文化中的生命力。同時,日本漢詩引用《詩經》為《詩經》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史料,為我們重新認識《詩經》在域外的流傳和接受情況提供了可資參照的范本,可以客觀確認日本《詩經》在《詩經》學史上的地位與意義。
總之,日本漢詩作家積極效仿學習《詩經》,以多樣性的形式大量擷取、借用和吸收《詩經》的語言和表達技巧,他們不僅繼承《詩經》的抒情傳統,而且還傳承了《詩經》的社會政治功能和道德教化功能等。日本漢詩引用《詩經》使得其詩作語言精煉,含蓄典雅,有力地提升了其詩作的表達效果和藝術技巧。日本漢詩作家通過引用《詩經》所構筑的獨特的《詩經》價值體系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①[日]安井小太郎:《日本儒學史》,東京:富山房,1939年,第12頁。
②本文所引漢詩主要參考了俞樾《東瀛詩選》、汲古書院《詩集日本漢詩》、本間洋一《日本漢詩·古代篇》、巖波書店《日本古典文學大系》《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程千帆、孫望《日本漢詩選評》、王福祥《日本漢詩擷英》等。
⑦程千帆、孫望選評:《日本漢詩選評》,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31頁。
⑧[日]廣瀨旭莊:《涂說》,東京:鳳出版,1971年,第18頁。
⑨郭紹虞:《滄浪詩話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第191頁。
文學博士。杭州 310012
[責任編輯 陶 櫻]
作者簡介:毛振華,浙江外國語學院中國語言文化學院副教授,日本東京大學訪問學者。
[中圖分類號]I3/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14X(2016)02-016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