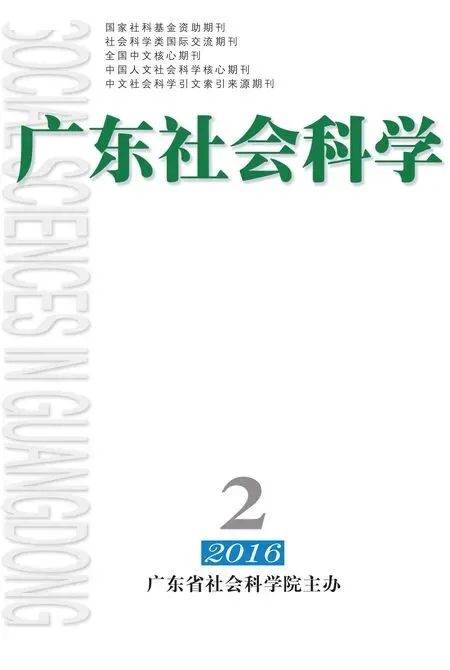壟斷行為刑法規(guī)制的法理分析
胡學相 尹曉聞
?
壟斷行為刑法規(guī)制的法理分析
胡學相 尹曉聞
[提 要]壟斷是伴隨市場競爭而產(chǎn)生的,隨著市場自律調(diào)節(jié)機制局限性的凸顯,其社會危害性也越來越明顯。在我國,長期以來由于沒有充分認識到壟斷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致使規(guī)制壟斷行為的法律制度不夠健全。如今市場自律機制和包括《反壟斷法》在內(nèi)的各種非刑事法律制度對壟斷經(jīng)營規(guī)制的作用日漸減弱,為了更好保護合法經(jīng)營者和消費者的權(quán)益,遏制壟斷對公平競爭秩序的破壞,運用刑法來規(guī)制壟斷經(jīng)營行為就成為國家干預市場經(jīng)濟的必然選擇。
[關(guān)鍵詞]壟斷 刑法規(guī)制 公平 責任自負 威懾陷阱
2007年我國頒布的《反壟斷法》對壟斷的概念和壟斷行為的種類作了明確的界定,確立了經(jīng)濟法對壟斷行為的規(guī)制方式。但長期以來我國對壟斷行為所造成的社會危害性認識不足,《反壟斷法》的頒布和實施并沒有很好地抑制我國經(jīng)濟改革和發(fā)展過程中出現(xiàn)的非法壟斷現(xiàn)象。近年來接連發(fā)生的侵害市場公平競爭和損害消費者權(quán)益的壟斷大案表明,僅依靠經(jīng)濟法和行政法來規(guī)制壟斷經(jīng)營行為顯然是不夠的。隨著人們對市場公平競爭理念的追求和對消費者權(quán)益保護意識的提高,尋求刑法規(guī)范來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和保護消費者合法權(quán)益的愿望日益強烈,運用刑法手段規(guī)制壟斷行為勢在必行。
一、對“壟斷行為無需刑法規(guī)制”觀點的評述
在《反壟斷法》立法過程中,對于是否要為壟斷行為設(shè)置刑事責任的問題存在一定的爭議。例如,針對《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分組審議反壟斷法(草案二審審議稿)的意見》,有代表就提出要求增加刑事責任,①但是正式頒布的《反壟斷法》刪除了有關(guān)刑事責任的規(guī)定。筆者認為,立法者的上述做法主要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一是刑法謙抑性原則的考慮,有觀點認為,壟斷是市場經(jīng)營行為的表現(xiàn),應當由市場自律和國家民事、經(jīng)濟乃至行政政策去調(diào)整和規(guī)范。刑法不可能對所有的違法行為都進行規(guī)制,最好的社會政策才是最好的刑事政策。②二是認為對壟斷行為社會危害性的認定存在困難。由于壟斷是競爭發(fā)展的結(jié)果,與競爭之間的區(qū)別并非涇渭分明。壟斷在危害公平競爭的同時,也可以增強經(jīng)營者的競爭能力,實現(xiàn)資源的合理配置,具有競爭的積極功能。壟斷與競爭區(qū)別的模糊性和隱蔽性造成認定其社會危害性的許多困難。三是認為用刑法規(guī)制壟斷行為的刑罰成本過高。徒法不足以自行,運用刑法對市場行為的規(guī)制是需要成本的。從國外刑法規(guī)范來看,追究壟斷者的刑事責任主要是通過監(jiān)禁刑和罰金刑來實現(xiàn)的,其中監(jiān)禁刑的適用成本比較昂貴。四是認為我國欠缺對壟斷行為進行刑事處罰的經(jīng)濟基礎(chǔ)和文化背景。長期以來,在計劃經(jīng)濟體制下,缺乏市場自由競爭觀念。改革開放以后,盡管市場競爭理念有所加強,但由于我國正處于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的過渡期和轉(zhuǎn)型期,追究傳統(tǒng)體制和制度背景下形成的壟斷經(jīng)營的刑事責任,仍然存在較大的社會阻力。然而,筆者認為,上述反對刑法規(guī)制壟斷行為的理由仍然是不充分的。
首先,刑法謙抑性原則不等于刑法干預最少化。刑法謙抑性是指刑法作為社會秩序的保障性規(guī)范,并不是針對所有的違法行為,刑罰只限于不得不適用的場合才適用。③刑法謙抑性強調(diào)的不是要求刑法從社會規(guī)范大家族中退縮出來,而只是突出刑法應當作為調(diào)整社會關(guān)系的最后手段。當運用其他各種社會規(guī)范都難以控制和防衛(wèi)某種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發(fā)生時,刑法的干預就既是必要的也是正當?shù)摹艛喈a(chǎn)生于市場競爭當中,在市場自由競爭早期,當經(jīng)營者都可以自由進入市場并且可以公平地參與資源分配時,壟斷行為的違法性和社會危害性并不明顯。市場規(guī)律自我調(diào)節(jié)機制仍然可以抑制壟斷的違法性及其社會危害性的擴大和漫延。但當經(jīng)營者的市場支配力量出現(xiàn)嚴重不平衡和壟斷經(jīng)營者對市場資源的占有越來越集中,尤其當消費主體的市場弱勢地位越來越明顯時,市場規(guī)律對壟斷經(jīng)營的自我調(diào)節(jié)就變得更加艱難,此時,國家對市場經(jīng)濟的干預則成為必要。在現(xiàn)代市場經(jīng)濟體制下,國家對市場經(jīng)濟行為的調(diào)控和規(guī)制必須以法律為依據(jù)且須法律授權(quán)進行。因此,國家希望通過《反壟斷法》的實施來規(guī)制壟斷經(jīng)營行為,欲將壟斷行為產(chǎn)生的負經(jīng)濟性控制在最低限度。然而,事實上,自2008年我國《反壟斷法》生效以來,壟斷經(jīng)營現(xiàn)象不僅沒有得到較好的控制,壟斷的程度及其產(chǎn)生的社會危害性反而愈加嚴重。這表明市場規(guī)律和經(jīng)濟法規(guī)在抑制壟斷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方面效果不明顯。以刑法來規(guī)制壟斷行為恰恰是刑法謙抑主義的體現(xiàn)和反映。
其次,對任何違法或犯罪行為的認定都需以客觀標準作為依據(jù)。壟斷作為市場競爭的負面性行為,固然與競爭存在辨別上的困難,但將壟斷行為入罪化,刑法作為規(guī)制壟斷的一種手段,完全可以采用科學的立法來明確罪與非罪的界限,從而將嚴重危害社會的壟斷行為從一般的違法行為中分離出來。更何況《反壟斷法》作為規(guī)范壟斷行為的專門性法律,如果對壟斷與競爭的界限都界定不清的話,那么,對壟斷的任何法律規(guī)制都顯得毫無意義。因此,在筆者看來,也正是由于壟斷具有模糊性和隱蔽性特征,才有必要依靠更加專業(yè)的國家機構(gòu)來界定壟斷與競爭界限,而不能將這個難題推諉給壟斷行為的受害者。
再次,對任何犯罪來說,刑罰的成本都是不可避免的。但任何刑罰的投入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實現(xiàn)刑罰的功能和目的,產(chǎn)生積極的社會效益。對壟斷犯罪適用罰金刑,既可實現(xiàn)刑罰懲治和預防犯罪的功能,還能為國家控制犯罪提供一定的財政保障。監(jiān)禁刑對懲處壟斷的成本固然較高,但監(jiān)禁刑具有的報應性功能可以很好地抑制和預防犯罪的再次發(fā)生。況且,刑罰的種類各異,為克服單一刑種存在的固有弊端,不同種類的刑罰之間的交叉適用是現(xiàn)代刑罰設(shè)置的共同性要求。對壟斷的刑罰設(shè)置除了自由刑和財產(chǎn)刑之外,還可以配置刑罰成本更低的資格刑。例如對壟斷企業(yè)可以設(shè)置停業(yè)整頓、限制從業(yè)和強制解散等資格刑。因為“資格刑的特性決定了它在分工越是精細、行業(yè)越是規(guī)范的社會中,就越能發(fā)揮功效。”④因此,不能因為顧忌刑罰成本上升就放棄對某種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入罪化。
最后,我國國情不應成為壟斷行為出罪的借口和理由。市場機制下,資源的有效利用和配置固然主要通過刺激和鼓勵競爭來實現(xiàn),但我國深化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重點就是要進一步完善公平的市場競爭機制,“打破壟斷也就成為改革的‘重中之重’”。⑤將壟斷行為納入刑法調(diào)整范圍,既有利于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的原則,又能良好的引導和規(guī)范廣大經(jīng)營者的經(jīng)營活動。因此,我國國情不應當成為《反壟斷法》不設(shè)置刑事責任的借口和理由。
在國外,無論是大陸法系國家還是英美法系國家,刑法理論和實踐基本上都認可壟斷的犯罪性。例如,在日本,神山敏雄教授認為,經(jīng)濟犯罪主要是違反反壟斷法和公平競爭法、證券交易法等。⑥日本的《禁止私人壟斷法》第10章規(guī)定了各種壟斷罪,具體包括:私人壟斷、不正當交易限制和競爭限制之罪,國際協(xié)定和違反確定審決犯罪,股份保有和干部兼任等犯罪,其處罰措施包括罰金和懲役,可以兩罰并處之,也可以在處以刑罰同時,宣告事業(yè)團體解散。⑦韓國學者認為,壟斷犯罪屬于妨害企業(yè)管理罪,是典型的經(jīng)濟犯罪。⑧俄羅斯1995年的《關(guān)于競爭和商品市場中限制壟斷活動的法律》規(guī)定,經(jīng)營者在被判處犯有違反反壟斷法規(guī)罪時,將被追究民事、行政或刑事責任。我國臺灣地區(qū)1991年《公平交易法》也為壟斷行為規(guī)定了刑事責任。在英美法系國家里,將壟斷規(guī)定為經(jīng)濟犯罪的立法也比比皆是,例如,美國2004年《反托拉斯刑罰提高及改革法》規(guī)定任何人壟斷或企圖壟斷,或與他人聯(lián)合、共謀壟斷,是嚴重犯罪。又如加拿大《競爭法》規(guī)定了共謀不正當競爭罪、共謀執(zhí)行外國不正當競爭罪、串通投標罪、聯(lián)邦金融機構(gòu)共謀罪、多級市場籌劃罪、非法維持價格罪等與壟斷有關(guān)的罪名。
二、壟斷行為的嚴重社會危害性是刑法規(guī)制的客觀依據(jù)
著名古典經(jīng)濟學家亞當·斯密直言不諱地道出了壟斷的社會危害性,認為壟斷是“良好經(jīng)營的大敵”和“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的‘頭號妖魔’”。的確,壟斷的出現(xiàn)和蔓延,不僅扭曲價值規(guī)律,妨害自由和公平競爭,阻礙了市場機制充分有效地發(fā)揮,而且可能嚴重影響社會經(jīng)濟的總體結(jié)構(gòu)和運行。⑨筆者認為,壟斷的社會危害性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壟斷經(jīng)營嚴重破壞市場自由競爭機制。“沒有競爭自由,就沒有真正的市場經(jīng)濟和市場體制。”⑩自由競爭機制是市場經(jīng)濟體制的核心,是最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由于經(jīng)營自由是不可讓渡的個人固有權(quán)利之一,因此,只有通過競爭機制才可以維持市場經(jīng)濟高效、有序地運行,企業(yè)才能獲得更多的資源,創(chuàng)造更多的價值。“競爭是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的命脈,競爭的削弱通常是產(chǎn)業(yè)發(fā)展和經(jīng)濟進步的掣肘。”而壟斷往往采取以阻礙、限制或扭曲競爭為目的的協(xié)議競爭,導致資源配置發(fā)生錯誤,致使社會財富和收入的分配有利于壟斷者,不利于其他經(jīng)營者和消費者,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社會整體福利。所以國內(nèi)有學者指出:“壟斷不僅會抑制競爭,減損市場效率……,損害消費者的福利。”而且,壟斷經(jīng)營往往采取掠奪性定價、搭售或捆綁銷售、拒絕采購和拒絕供應、濫用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控制和支配地位方式,霸占本不屬于它的資源,使其他經(jīng)營者處于不利的競爭地位,甚至人為減少競爭者的數(shù)量,嚴重損害社會公平價值。可見,壟斷在妨害自由和公平競爭,扭曲價值規(guī)律和阻礙國家宏觀調(diào)控等方面,其社會危害性遠比一般性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秩序犯罪嚴重得多。
(二)壟斷經(jīng)營嚴重侵害消費者的合法權(quán)益。法律的實質(zhì)是利益法,即各種利益的制度安排。經(jīng)濟學理論認為,生產(chǎn)、分配、交換和消費等四個社會生產(chǎn)和再生產(chǎn)環(huán)節(jié)中,消費則是經(jīng)濟行為的出發(fā)點和最終目的。亞當·斯密指出:“消費是一切生產(chǎn)的唯一目的,生產(chǎn)者的利益,只有在能促進消費者利益時,才應加以注意。”可見,對消費權(quán)益的有效保護既是經(jīng)濟秩序的本質(zhì)要求,也是法律制度的神圣使命。德國著名經(jīng)濟學家艾哈德認為,“侵犯消費自由是反社會的暴行。”其實,在經(jīng)濟法的主體關(guān)系中,消費者處于核心地位,生產(chǎn)經(jīng)營的目的是為消費者提供有償商品與服務(wù),經(jīng)營者應服務(wù)于消費者。對于經(jīng)營者而言,“消費者是‘上帝’,這是‘以人為本’的應有之義;也是經(jīng)濟法的立法必須加以貫徹的理念。”所以,筆者認為,壟斷的直觀違法性是破壞市場公平和自由競爭秩序,侵害了合法經(jīng)營者的自由經(jīng)營權(quán)。然而,由于消費是市場行為的最后環(huán)節(jié),因此,無論是自由競爭還是壟斷經(jīng)營,本質(zhì)上都是對消費行為的爭奪。生產(chǎn)、分配和交換的最終目標都是希望占有更多的消費行為,從而獲得經(jīng)營利潤。在自由公平競爭下,消費者獲得相對公平自由的消費權(quán)益。而在壟斷經(jīng)營下,壟斷者不僅經(jīng)常實施價格協(xié)議、附加不合理的交易條件等方式侵害消費者的公平交易權(quán),而且壟斷者還常常采取分割銷售市場和原材料采購市場,限制購買新技術(shù)、新設(shè)備、新產(chǎn)品,以及聯(lián)合抵制交易等行為,剝奪了消費者的消費自由權(quán)。可見,在壟斷狀態(tài)下,消費者應有的合法權(quán)益幾乎都轉(zhuǎn)為壟斷利潤而被壟斷經(jīng)營者所攝取。此外,壟斷行為本身就是對公平競爭原則的挑釁,在侵害消費者合法權(quán)益的過程中,很可能引發(fā)影響社會穩(wěn)定的群體性事件。因此,當社會整體利益概念不斷擴延時,對壟斷行為的法律規(guī)制,就應當回歸到以保護消費者權(quán)益為中心上來。而對消費者權(quán)益的保護理應是各種法律規(guī)范應有的使命,尤其當經(jīng)濟法對于壟斷經(jīng)營日益侵蝕消費者權(quán)益的行為規(guī)制無效時,刑法的運用就顯得更為必要。
(三)壟斷嚴重抑制市場創(chuàng)新發(fā)展。自由市場是創(chuàng)新的最佳環(huán)境。只有開放市場,才能充分發(fā)揮人們的智慧進行改革與創(chuàng)新。而壟斷經(jīng)營者為了堅守其超越的壟斷優(yōu)勢,攝取高額的壟斷利潤,其經(jīng)營理念僅局限于維持和穩(wěn)固壟斷經(jīng)營優(yōu)勢和市場支配地位,不愿意實現(xiàn)管理、經(jīng)營和技術(shù)上的創(chuàng)新。因為壟斷經(jīng)營者不是將壟斷利潤投入到技術(shù)改革、產(chǎn)品升級以及節(jié)能減排上,而是將大量壟斷資金投入到怎樣維護其壟斷優(yōu)勢的措施鞏固上。正如美國學者大衛(wèi)·D·弗里德曼所說的那樣,在壟斷狀態(tài)下,“行業(yè)的收益分配根本就是無關(guān)緊要的,也不是效率定義的一部分,是造成無效率行為的動機。”況且,壟斷者還經(jīng)常采取限制購買新技術(shù)、新設(shè)備以及限制開發(fā)新技術(shù)、新產(chǎn)品的壟斷協(xié)議的方式實現(xiàn)限制競爭的目的,這就更為直接地抑制了市場創(chuàng)新能力。可見,壟斷是市場創(chuàng)新的抑制屏障。
刑法理論認為,犯罪的本質(zhì)是行為的嚴重社會危害性,衡量犯罪輕重的標準是犯罪對社會的危害程度。刑法作為國家調(diào)整行為的一種最嚴厲的法律,應當尊重經(jīng)濟規(guī)律,而不是干涉和阻礙自由競爭。因此,只有當某種經(jīng)濟行為產(chǎn)生了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時,刑法介入才是必要的和正當?shù)模@就是一般意義上的“危害原則”。“危害原則”是刑法懲罰某種嚴重違法犯罪行為的合法根據(jù)。在我國市場經(jīng)濟體制不斷完善和社會不斷發(fā)展的今天,對壟斷行為社會危害性的控制除了經(jīng)濟法和行政法外,還應包括刑法。
三、壟斷行為的刑法規(guī)制是公平價值與責任自負原則的體現(xiàn)
我國《反壟斷法》規(guī)定的壟斷經(jīng)營的法律責任主要是經(jīng)濟性罰款。筆者認為,這種單純經(jīng)濟性處罰措施的弊端相當明顯:首先,高額的經(jīng)濟處罰有時會超出壟斷企業(yè)的支付能力,甚至導致企業(yè)破產(chǎn),從而損害廣大社會投資者和債權(quán)人的合法權(quán)益。其次,對壟斷企業(yè)來說,還可以通過資產(chǎn)與負債的轉(zhuǎn)換以及成本與收益的換算,以降低勞動報酬的方式來沖抵經(jīng)濟性處罰成本,將高額罰款轉(zhuǎn)嫁給企業(yè)員工,從而損害了企業(yè)員工的合法權(quán)益。例如,有報道稱,2015年國家發(fā)改委對奔馳汽車公司的壟斷行為作出了5億元的罰款后,該公司當年中國的員工薪資漲幅明顯降低,5億元的罰款主要由員工工資承擔。實際上,無論是社會投資者還是企業(yè)員工,如同其他經(jīng)營者和消費者一樣,自己本身也是壟斷經(jīng)營的直接受害者,但由于單純經(jīng)濟性處罰責任的規(guī)定,一方面要求他們承擔因企業(yè)壟斷造成的經(jīng)營收益或者消費利益的損害,另一方面又要求承擔轉(zhuǎn)嫁給他們的反壟斷經(jīng)濟性處罰而導致的投資利益或者勞動報酬的損失,這從責任理論上來講顯然是不公平的。再次,經(jīng)濟性處罰責任往往只針對壟斷企業(yè),不適用企業(yè)壟斷決策者或者直接責任人。企業(yè)的壟斷經(jīng)營雖然是法人意志的體現(xiàn),但歸根到底是資本占多數(shù)的投資者以及有決策權(quán)的高級管理人員的意志體現(xiàn)。因此,承擔壟斷法律責任的不應只限于壟斷企業(yè),還應當包括企業(yè)壟斷經(jīng)營的決策者及其他直接負責人。而我國現(xiàn)行經(jīng)濟法規(guī)定的壟斷經(jīng)營的法律責任僅限于壟斷企業(yè),即便是高額的經(jīng)濟性處罰也根本無法制約和威懾企業(yè)的決策者和直接責任人。可見,單純經(jīng)濟性處罰的責任方式并不是法律責任自負的體現(xiàn),損害了法律的公平價值。
筆者認為,刑法對經(jīng)濟行為的介入,一方面是為了保證犯罪人受刑法的追訴、審判與處罰;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保證未犯罪人不受國家權(quán)力機關(guān)的干涉、侵犯或處罰。因此,運用刑法規(guī)范對壟斷行為進行規(guī)制,將嚴重危害社會的壟斷行為規(guī)定為犯罪,并根據(jù)刑法確立的單位犯罪的“雙罰”制責任原則,既可以追究壟斷企業(yè)的法律責任,也可以追究壟決策者和主要責任人的法律責任。這既能體現(xiàn)法律責任自負原則,也可以保護其他社會成員合法權(quán)益,體現(xiàn)了刑法的公平價值。
四、壟斷行為的刑法規(guī)制是對受害人權(quán)益保護的有效途徑
在自由競爭時期,壟斷的結(jié)果往往表現(xiàn)為對其他經(jīng)營者經(jīng)營權(quán)的侵害,因而,壟斷行為一般是被納入民事侵權(quán)的范圍而進行法律規(guī)制的。我國《反壟斷法》第50條規(guī)定:經(jīng)營者實施壟斷行為,給他人造成損失的,依法承擔民事責任。但事實上,民事侵權(quán)責任是平等主體之間的責任,即行為人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權(quán)利并且造成了損失而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在受害人和侵害人之間形成一種債權(quán)債務(wù)關(guān)系,屬于相對性的法律責任。而壟斷行為侵害的一般不只限于某個特定的經(jīng)營者和消費者,而是一個行業(yè)乃至整個社會所有的經(jīng)營者和消費者,受害者具有社會群體性和不特定性。因此,從法律責任的性質(zhì)來看,壟斷責任不完全等同于民事侵權(quán)責任,壟斷行為遠遠超出了傳統(tǒng)民事法律的調(diào)整范圍。況且,在現(xiàn)行的法律制度框架下,壟斷侵權(quán)的民事責任在司法實踐當中往往難以實現(xiàn)。原因在于:一是《反壟斷法》對壟斷行為民事責任的規(guī)定過于抽象和籠統(tǒng)。現(xiàn)實生活當中,由于壟斷經(jīng)營侵害對象的群體性和侵害結(jié)果的間接性,致使司法機關(guān)在認定受害損失與壟斷行為的因果關(guān)系以及量化受害損失時困難重重。二是壟斷行為受害主體的舉證責任艱難。盡管最高人民法院在2012年《關(guān)于審理因壟斷行為引發(fā)的民事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中也明確了壟斷行為侵權(quán)訴訟中某些舉證責任倒置,但壟斷行為的受害人仍然難以通過自己單獨的力量對壟斷行為進行調(diào)查和認定,致使通過民事侵害訴訟求償?shù)母怕蕵O小;三是民事責任確立的“補償原則”不足以激發(fā)壟斷行為的受害人維權(quán)意識。盡管在司法實踐中也規(guī)定了壟斷行為的受害人可以將因調(diào)查、制止壟斷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計入損失賠償范圍,但由于民事侵權(quán)賠償應遵循補償性原則,作為個體的受害人尤其是單個消費者來說,提起民事侵權(quán)訴訟來維護其合法權(quán)益的成本太高。而且,在我國公益訴訟機制不健全的情形下,壟斷行為受害人的訴訟理性非常有限。一般會認為,自己在通過訴訟機制實現(xiàn)損失補償?shù)耐瑫r,也使其他多數(shù)受害人從中獲利,很有可能在衡量訴訟成本和補償收益之后,會滋生出“搭便車”的心態(tài),從而淡化訴訟意識。而事實上壟斷經(jīng)營者恰恰就是利用受害人維權(quán)意識淡薄而肆無忌憚地實施壟斷經(jīng)營行為。一旦刑法介入,將壟斷行為入罪化,基于國家的力量啟動壟斷違法性案件審查,公訴機關(guān)對違法壟斷的認定和調(diào)查就會變得更加專業(yè)化,獲取壟斷的證據(jù)也更加容易。一旦法院認為壟斷者構(gòu)成犯罪,通過受害人登記制度可以在最小的訴訟成本內(nèi)實現(xiàn)對更廣泛受害人賠償?shù)男Ч4送猓斗磯艛喾ā芬?guī)定,對于境外存在的壟斷行為,如果對我國境內(nèi)市場競爭存在排除和限制影響的,可以適用《反壟斷法》進行規(guī)制。但事實上無論是從《反壟斷法》的域外效力來看,還是從反壟斷執(zhí)法機構(gòu)的執(zhí)法能力來看,對于境外損害我國境內(nèi)競爭市場的壟斷行為都不可能通過《反壟斷法》來規(guī)制。因為作為經(jīng)濟法范疇的《反壟斷法》,其域外效力是有限的。反壟斷執(zhí)法機構(gòu)也很難通過國家之間的行政執(zhí)法合作將行政管轄權(quán)延伸到境外。只有當壟斷行為納入刑法規(guī)制后,從單純的經(jīng)濟違法或行政違法行為變?yōu)榉缸镄袨椋涂梢灾糜谖覈谭ü茌牂?quán)之內(nèi),并通過國際刑事司法合作實現(xiàn)其應有的刑事責任。
五、壟斷行為的刑法規(guī)制是國家對經(jīng)濟干預的一種制度選擇
制度經(jīng)濟學代表人物諾斯認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來的規(guī)則、守法程序和行為的道德倫理規(guī)范,它旨在約束追求主體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個人行為。”從制度經(jīng)濟學理論看來,刑法對壟斷行為的規(guī)制顯然是一種制度安排。作為一種行為規(guī)范,刑法以其特有的、最大的強制性成為規(guī)制壟斷的最后制度安排。壟斷非自古有之,也非天生犯罪,它與競爭是市場經(jīng)濟共生共存的一對概念。在自由經(jīng)濟發(fā)展的早期,壟斷行為曾經(jīng)對提高經(jīng)濟效益、促進產(chǎn)業(yè)競爭起到過一定的積極作用。然而,當壟斷開始危害到“自由競爭”這一市場經(jīng)濟存在和發(fā)展的根基,市場自律和經(jīng)濟、行政等法律制度手段的規(guī)制失效時,對壟斷行為的刑法規(guī)制便成為國家干預經(jīng)濟行為的最佳制度選擇。正如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認為的:“從本質(zhì)上說,刑法對某種犯罪的設(shè)立和懲罰,只不過是國家和社會對某種危害社會‘生存條件’的活動的自衛(wèi)性反映。”
筆者認為,當市場自律機制難以調(diào)節(jié)危害市場自由、損害公平競爭的壟斷行為時,國家便選擇法律制度對其進行適度干預。因為法律作為社會控制手段之一,當其他控制力量減弱時,法律的控制力量就應當加強。基于這一理念,規(guī)制壟斷行為的民事法律制度和經(jīng)濟法律制度也就應運而生,并為壟斷侵權(quán)行為確立了以賠償和補償為核心的民事責任。然而,如前所述,由于民事責任的目的在于保護特定的個體權(quán)益,而壟斷行為侵害的不僅僅是特定個體的權(quán)益,而是多數(shù)不特定公眾的權(quán)益。因此,“在受到受害個體不能對與本人無直接利害關(guān)系的違法行為提起訴訟這一古老原則的限制下和我國公益訴訟機制不完善的情形下,壟斷行為的特定受害主體就難以通過民事訴訟的方式予以補救,”致使民事法律制度和經(jīng)濟法律制度對壟斷行為的規(guī)制力量逐漸弱化。與民事法律制度和經(jīng)濟法律制度相比,規(guī)制壟斷行為的行政法律制度也發(fā)揮著較大的功能。在我國《反壟斷法》中,行政性處罰幾乎成為壟斷者責任的核心內(nèi)容。基于行政處罰的靈活性,近年來雖然對壟斷經(jīng)營的行政性罰款金額屢創(chuàng)新高,但反壟斷的效果卻并不如意。筆者認為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原因:其一,行政執(zhí)法權(quán)的分散性導致反壟斷執(zhí)法效率的低下。由于我國長期以來對壟斷的監(jiān)督和調(diào)查分別由國家發(fā)改委、商務(wù)部和國家工商總局等部門來實施,為配合《反壟斷法》的實施,新成立的反壟斷執(zhí)法局還是維持了三個部門聯(lián)合執(zhí)法的局面,這勢必會造成執(zhí)法權(quán)的分散和沖突,影響反壟斷執(zhí)法的效率。其二,行政執(zhí)法的不獨立造成了行政處罰的實效性不足。行政處罰的實效性須以行政執(zhí)法的公正性為前提,即行政執(zhí)法機關(guān)必須是可以真正代表社會公共利益的執(zhí)法主體。然而在我國,反壟斷執(zhí)法機構(gòu)在執(zhí)法過程中經(jīng)常要顧忌上、下級之間以及部門之間的利益,難免會揣著有失公平的執(zhí)法理念,致使對壟斷者行政處罰偏失了法律的公平原則,影響反壟斷執(zhí)法的實效性。其三,有些壟斷行為本身就是濫用行政權(quán)力排除、限制競爭造成的。例如,我國《反壟斷法》第5章規(guī)定的濫用行政權(quán)力排除、限制競爭行為屬于違法壟斷行為。出于維護地方利益、部門利益的考慮,執(zhí)法機關(guān)往往難以無所顧忌地對壟斷行為進行查處和制裁。其四,單純依靠增加罰款等“簡單威懾”的方式顯然不足以達到威懾壟斷行為的效果,反而容易出現(xiàn)“威懾陷阱”,加劇了壟斷行為的發(fā)生。因為當經(jīng)濟性處罰遠遠低于壟斷的違法所得時,它降低了行政法律規(guī)制的威懾力。例如,1997年~2004年期間寶潔、漢高、高露潔等日用消費品企業(yè)因以協(xié)議方式實行限制性競爭,被法國反壟斷機構(gòu)處以高額罰金。但高額罰金并沒有有效制止這些企業(yè)的壟斷行為,致使2011年又因為價格控制被法國反壟斷機構(gòu)處以3.61億歐元的罰款。如火如荼推進的反壟斷調(diào)查,雖然罰單屢創(chuàng)新高,但效果值得懷疑。可見,行政法律制度對壟斷的制約力也越來越弱。
如此看來,刑法規(guī)范對壟斷經(jīng)營行為的規(guī)制便成了國家干預經(jīng)濟行為的制度選擇的必然結(jié)果。因為刑法規(guī)范所規(guī)制的行為不僅是與道德違反、民事違法以及行政不法相比較更加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的行為,還包括國家和社會的其他規(guī)制手段無法處理的行為。“刑法的適用應當是國家在調(diào)控社會關(guān)系、控制社會秩序的各種途徑中的最后的和不可避免的選擇。在市場經(jīng)濟中,經(jīng)濟犯罪的界定也必須遵循這一原則,刑法所調(diào)控的經(jīng)濟行為應當是用盡(或窮竭)其他非刑罰手段都無法調(diào)整(預防和制止)才進行刑罰‘不得已’處罰的行為。”
國家利用刑法規(guī)范懲治壟斷行為不僅可以實現(xiàn)刑法的目的,而且可以實現(xiàn)社會公平和效益。在經(jīng)濟危害性較為嚴重和刑罰措施無可避免的情況下,立法者就應當將該經(jīng)濟危害行為規(guī)定為犯罪。刑法規(guī)制的目的是將某些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規(guī)定為犯罪,從而運用刑罰的方式追究其法律責任。由于民事、經(jīng)濟以及行政法律制度對壟斷行為的規(guī)制效果不明顯,甚至失靈,因此,刑事法律的介入就成為制度選擇的必然。
①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王祖訓和全國人大代表陳舒等在《反壟斷法(草案)》二審時就提出要求增加刑事責任的意見。參見顧功耘、羅培新:《經(jīng)濟法前沿問題(2009)》,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50頁。
②徐久生:《刑罰目的及其實現(xiàn)》,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11年,第4頁。
③[日]川端博:《刑法總論講義》,東京:成文堂,1995年,第55頁。
④楊興培、李翔:《經(jīng)濟犯罪和經(jīng)濟刑法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63頁。
⑤胡鞍鋼、過勇:《從壟斷市場到競爭市場:深刻的社會變革》,重慶:《改革》,2002年第1期,第19頁。
⑥肖榮:《經(jīng)濟刑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頁。
⑦⑨漆多俊:《經(jīng)濟法基礎(chǔ)理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207~208、186頁。
⑧趙可:《國外經(jīng)濟犯罪與對策研究》,北京:群眾出版社,1997年,第155~157頁。
⑩孔祥俊:《反壟斷法原理》,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第19~28頁。
[責任編輯 周聯(lián)合]
作者簡介:胡學相,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尹曉聞,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博士生。廣州 510006
[中圖分類號]D924.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14X(2016)02-024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