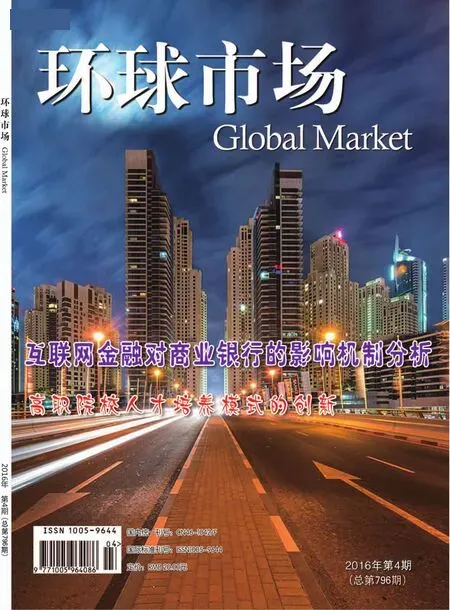全球治理的變革:向國際制度的過渡
史鳳景
河南省舞陽縣委黨校
全球治理的變革:向國際制度的過渡
史鳳景
河南省舞陽縣委黨校
習近平同志指出,“各國經濟,相通則共進,相閉則各退。”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導致落后,這已經被古今中外的發展實踐所證明。這一發展規律在經濟全球化時代表現得尤為明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經濟全球化浪潮風起云涌,生產的國際化程度空前提高,各國經濟聯系日益緊密。根據世界銀行發布的一份報告,全球有13個經濟體實現了持續25年以上的高速增長,它們的共同特征就是實行對外開放。可以預期,隨著全球交流的強度與程度的日益提高,未來對新國際制度的需要將日益增加。
國際制度;全球化
一、全球化為國際制度的產生提供了豐富的土壤
首先,全球化產生的一些問題無法在民族國家的領土邊界內解決。因為日益增加的國家間交易需要在不同國家間進行規范的調整與統一,而產生的注入銀行或生產安全之類的問題,源于民族國家的跨境污染等問題,如影響國內的販毒問題明顯產生于非法的國際網絡,這一國際網絡已經超越了任何單一的國家所管轄的范圍。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有必要發展超越任何單一民族國家單獨行動所不能完成的策略。
第二,全球化可能會創造條件,使某些社會價值觀得到廣泛的接受,這也會導致對國際行動的需求。全球化可能會有助于人們對人權與民主有更全面的理解,盡管積極人權與原則可能會在某些特定國家得到保護。基于民族國家的全球治理體系或許在保證公平與人權保護的統一方面不是最佳的,或許需要有效的國際制度來保證人權。
第三,國際制度可以為政治驅動下的私人利益服務。通過貿易與商業慣例中的一致性,私人的利益將得到有效實現。像國內市場一樣,全球市場上的私人企業存在著追求規范化的動力,因為后者可以作為潛在競爭者參與競爭的障礙。這樣的障礙與其他政治體制如果在國際上被采納,將在全球化市場中發揮更有效的作用。對私營企業來說,與吸引和影響幾十個國家政府相比,它更易于吸引中央集權化的國際制度的注意力與影響中央集權化的國際制度。正因為以上策略性的原因,私營企業有時可能會支持建立國際制度的努力。
二、全球化條件下,民族國家的制度反應
民族國家對國際需求可能會做出怎樣的反應呢?持續的全球化將使國家做出這樣的選擇:內部控制、相互承認、同意、委托與退出。每種可能的反應程度根據國家擁有的政治權力的程度存在不同的差異。
第一項選擇是民族國家實施內部控制,保留其全部的權力。在處理跨越民族國家領土邊界的問題時,這一選擇結果通常是無效的。但是,它有自身的優點,即允許民族國家對境內的經濟交易與其他活動的政治治理進行最大化的控制。
第二項選擇是相互承認,包括民族國家采納的協調原則。根據協調原則,國家在特定的情況下承認其他民族國家的政策。在決定哪條規則應用于不同國家的企業與個體的交易時,相互承認的方式為決定交易規則提供了基礎。兩個或多個相互承認的國家在各自疆域內都保持其內部控制,但是它們將規范涉及國家間交往的情況。例如,A國可能會出售某種產品,這種產品達到了B國的安全標準。當B國同意A國的產品銷售到B國時,這種承認是相互的。
第三項選擇是同意,指民族國家通過條約來采納共同政策。政策權力仍然屬于民族國家,因為每個民族國家必須統一跳躍中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現實中的每個國家,其決定都將在談判中受到限制,因為條約中所包括的條款往往無法與各國的最佳選擇相符。但是,每個國家擁有決定是否同意條約的全部權力。
第四項選擇是委托,意味著建構自己享有政策權力的國際制度。歐洲聯盟與世界貿易組織是這種制度的兩種典型例子。民族國家首先做出委托的決定,但是國際制度在創立、實施與執行政策時有自由裁量權。委托的結構可能會產生極大的變化,以至于一些委托很狹隘,而其他的有可能會寬泛。在決定民族國家將在多大程度上將政策權力委托給國際制度以及這些制度的最終有效性方面,這些委托結構的變化將起到重要作用。
筆者認為,與其他反應相比,即使民族國家經常使用條約來解決跨國境的問題與協調不同的政策,但在日益全球化的情況下,委托將得到更廣泛的使用。條約需要每個國家的同意,這種一致同意的原則會阻礙對全球性問題處理的效率以及影響處理的及時性。民族國家或許日益需要同意(通過條約)把政策權力委托給國際制度,因為這樣做民族國家就沒有必要受條約形式的妨礙。就像立法機關把國內政策權力委托給行政機構一樣,民族國家將常常面臨以下抉擇:是否把需要作出決策與及時實施決策的權力真已給新的國際制度。
三、國際制度的設計
在全球化背景下,委托的需要日益增加,但是我們不應該期望民族國家會輕易地把權力委托出去。在當前的全球化模式產生的同時,人們也開始關注分權與委托。民族國家領導人希望保證自己國家利益不會因為各國在國際制度范圍內創立的新制度而受到損害。
民族國家關注權力向國際制度的委托,就像立法機關把權力委托給行政機構,或者私人參與者把商業決定委托給第三方一樣。委托需要依靠代理來實施任務,因為委托無法有效或低成本實施這一任務。有時候,代理的目標背離了其委托者的目標。對于任何民族國家來說,在創立新國際制度時,都會產生這樣的困惑:多大程度上的制度決定與國家利益相背離。
因為國際制度是在民族國家同意的情況下建構的,它們將受其制約,制度的建立程序與其他情況下委托人把權力委托給代理人的情況相似。為了使代理人的行為與其委托人利益相悖的可能性盡可能最小,委托過程往往包括了委托人監督代理人的措施。
雖然我們需要更多的經驗研究來說明這些機制的不同組合如何在不同情況下影響國際制度的功能發揮,但代理理論也表明了國際制度中可能產生的兩種問題。第一是制度受的約束太強。對制度權力的狹隘描述越多,制度對隨機問題的反應就越困難,也就是說制度缺少靈活性。制度約束的第二個方式是制度決策的自由度。在各種制度中,權力共享是相互聯系的,制度的決定必須所有成員同意,因此制度的發展很困難。這種各成員國制度相互牽制的實施并沒有讓出過多的權力,只不過是提供了國際上同意采取授權某種行動的平臺。約束過于嚴格,制度就不會那么有效。
當然,約束嚴密的制度,其優勢在于它們不會采取有爭議的行動或作出的決定不會遭到成員國的強烈反對。國際制度可能產生的第二個問題是,其約束可能太過松散。如果民族國家真的把許多不受約束的權力移交出來,制度將對新的挑戰作出有效的反應。但是這樣也會使國際制度擁有易犯錯誤的權力,或者在行動時違背委托者的意愿和利益。權力太大的國際制度與隨意行使權力的國際制度會在那些創立它的民族國家中失去合法性。民族國家可能會抵抗那些權力太大的制度的行動,或者撤銷采取措施,退出這些國際制度。
顯而易見,在創立足夠獨立的國際制度的需要與維持民族國家支持的需要之間存在著平衡,民族國家也會對新制度擁有的權力保持高度警惕。任何新制度的確立必須沒有太多的羈絆,從而能夠使制度解決全球問題,但是,任何新制度必須有成分的約束,這才會使制度成為那些同意建立并維持它的民族國家所接受。為了使這兩者充分結合起來,民族國家需要探索如何對權力機制進行組合。
四、結束語
由上文可以看出,民族國家將權力委托給國際制度是為了使自己的國家利益能夠更好的實現,一旦國際制度的實施損害了創立它的成員國的利益,就會被遺棄,失去效力。但是,國際制度的實施并不會讓所有的成員國滿意,這就必然會削減國際制度的法定效力,這就存在著平衡的問題。隨著全球化的程度越來越高,這樣的問題還會在其他領域不斷出現,但是,我們也應該相信,隨著人們認識的不斷提高,隨著國際監督機制的不斷完善,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人類還是可以解決這些問題的。
[1]湯偉.全球治理的新變化:從國際體系向全球體系的過渡[J].國際關系研究.201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