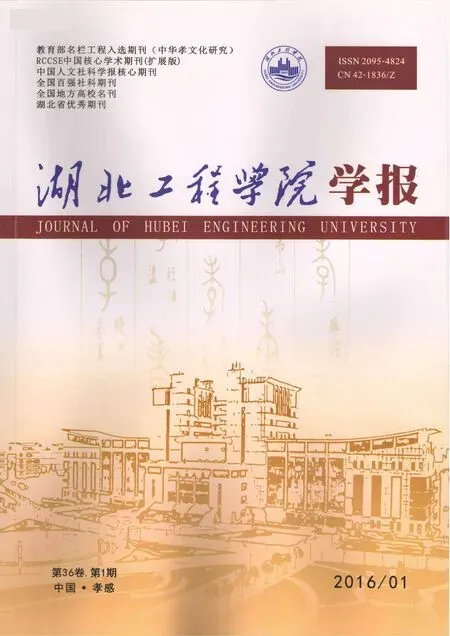礦產資源權的法學分析
胡利明
(中央民族大學 法學院,北京 100081)
?
礦產資源權的法學分析
胡利明
(中央民族大學 法學院,北京 100081)
摘要:礦產資源是儲藏豐富和經濟價值巨大的資源性財產,礦產資源權以礦產資源為對象,是非準物權性質并與傳統物權無異的完全所有權和新型財產權利,既不同于礦業權,又不同于土地權利。“礦產資源權”成為法學上的新型權利,既可保護其“所有”,又提高其“利用”效率。據此,堅持整體宏觀和具體微觀研究,尤其集中于鄰近性分析、微觀分析和衍生分析方面對礦產資源權作比較深入的法學分析,逐漸形成礦產資源的權利觀念。
關鍵詞:礦產資源權;礦產資源;財產權;私權;私法
《憲法》和《礦產資源法》中還沒有“礦產資源權”的“法定地位”,更無“法定名稱”,而學理上研究之應先定義“礦產資源”。所謂礦產資源,是指存在于地殼內部或地表的,由地質作用形成的,在特定的技術條件下能夠探明和開采利用的,呈固態、液態或氣態的自然資源。[1]據此引申,礦產資源權是特定民事主體對特定或控制范圍內的礦產資源依法行使物權權利(權益),享有以礦產資源為特定對象的資源性物權權利。《礦產資源法》總則中只簡要提及探礦權和采礦權,沒有為礦產資源權提供“法律地盤”。根據法律條文分析,此法本質上不是私法性的民事權利法,而是政府行使管理職責的公法,是政府部門行使管理職責的“礦產資源管理法”,重點在于行政管理。
一、礦產資源權的鄰近性分析
1.礦產資源權的鄰近性分析之一:土地權利。與礦產資源權密切相關的土地權利,其核心是土地所有權,衍生出土地用益物權和土地擔保物權。我國土地所有權主要有國有和集體所有兩種形式,以“土地”作為權利客體,特定主體對特定“土地”享有物權法上的權益,并對土地行使支配權。眾所周知,中國是二元土地所有權體制,國家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范圍內屬于集體所有之外的土地所有權,即中國土地原則上屬于國有,集體土地可以經過征收程序轉為國有土地,國有土地不可能轉為集體土地。《礦產資源法》第3條:“礦產資源屬于國家所有,由國務院行使國家對礦產資源的所有權。地表或者地下的礦產資源的國家所有權,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的所有權或者使用權的不同而改變。”這表明只能由國務院代表國家專享礦產資源所有權,礦產資源處于國有土地之下時,兩者主體完全相同;處于集體土地之下時,土地權利屬于集體,礦產資源權利屬于國家,兩者呈分離狀態,集體土地所有者不能享有礦產資源所有權。可知,礦產資源權獨立而不等同于土地權利,并經常相互交織,不受土地所有權性質的影響。礦產資源在物理空間上被埋藏于土地之下,法律上完全獨立并區別于土地權利,導致的常態是國家享有礦產資源權和集體享有土地權利,這樣必然造成主體利益沖突,國家(實際上是各級政府)為追求經濟利益隨時隨地開采礦產資源,必然破壞集體土地實物外貌和質量,集體土地所有者卻永久性失去土地實物。
2.礦產資源權的鄰近性分析之二:礦業權。與礦產資源權密切相關的還有“礦業權”。高富平先生認為,礦業權是指符合資質的開采人依照有關法律規定的條件和程序,在特定礦區和工作區域內勘探、開采礦產資源,從而獲得礦產產品的權利。他引述我妻榮等學者的觀點,認為:(1)礦業權的主體是探采人;(2)礦業權主要包括勘探礦產資源的探礦權和開采礦產資源的采礦權;(3)礦業權必須依照國家有關法律法規規定的條件和程序取得;(4)礦業權的客體是特定的礦區和工作區及附存的礦產資源的組合體,即特定礦區或工作區的礦產資源。[2]《礦產資源法實施細則》第6條:探礦權是指在依法取得的勘查許可證規定的范圍內,勘查礦產資源的權利;采礦權是指在依法取得的采礦許可證規定的范圍內,開采礦產資源和獲得所開采的礦產品的權利。《礦業權出讓轉讓管理暫行規定》將探礦權、采礦權統稱為礦業權。
據此析之,礦業權離不開探礦和采礦行為,它們是礦業權的實現(行使)方式,主要特征為:(1)主體主要是具有相關資質條件的探礦或采礦企業;(2)對他人之物行使非自物權權利(非所有權權利),但最終沒有處分權,屬于用益物權或他物權;(3)主要通過探礦和采礦行為滿足主體需要;(4)一般有償和有期限,卻完全不同于傳統用益物權的有償和有期限;(5)并不是完全獨立的物權類型,依賴于礦業權之“本權”(礦產資源權)。但筆者提出礦產資源權不是,且不等同于礦業權的觀點,彼此之間既有聯系更有區別。兩者的主要聯系是礦產資源權是礦業權的原權和本權,為形成礦業權提供“權源”依據,沒有礦產資源權,礦業權將是“無本之木”;礦業權為礦產資源權的經濟目標尋找出路。二者主要區別是:(1)礦產資源權是派生礦業權的原權(所有權),以礦產資源為權利客體,而礦業權是派生權,雖然會涉及到礦產資源,并不能創造以礦產資源為權利客體的權利;(2)礦產資源權在整體和法律層面上為實物巨大的權利類型,具體和微觀層面上為能被民事主體個體控制和利用的權利類型,而礦產權并不具備之;(3)宏觀上只能由國家享有礦產資源權,微觀上由依法經過許可的探礦和采礦企業、其他組織或個人享有礦產資源權,而不能由國家享有礦業權;(4)礦產資源權依賴于礦產資源,一般是永久性無終期的權利,而礦業權一般是有償、有期限(終止日期)的權利;(5)礦產資源權是法律和經濟意義上完全獨立所有權,而礦業權是不能獨立的非所有權,一般更側重于經濟意義;(6)礦產資源權的價值重心在于確認所有狀態,而礦業權的價值重心主要在于開發利用和實現礦產資源的經濟價值。
二、礦產資源權的微觀分析
1.礦產資源權的權利性質分析。根據通說,法學上公權利和私權利的區分標準主要有:主體標準、目的價值標準、法律地位標準和意志標準(限于篇幅,此處不展開論述)。據此析之,礦產資源權應為公權利,理由在于:(1)根據主體標準,礦產資源權主體只能是國家,國家主體具有絕對性、唯一性和壟斷性,當然成為“公”的權利主體具有公權性;(2)根據目的價值標準,從利益價值角度來說,礦產資源權是國家層面的整體公共利益從而具有公權性;(3)根據法律地位標準,作為礦產資源主體的國家永遠處于強勢地位,相對方處于明顯劣勢地位,地位分殊造就礦產資源權公權性;(4)根據意志標準,礦產資源權并非源于平等協商,而是體制安排,事實上造就其公權性。但筆者認為,私法私權性是礦產資源權的重要特性,國家主體具有唯一性和壟斷性,體現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無法在法學層面改變私權本性。
2.礦產資源權的物權分析。學界對物權基本上有較為一致的意見,卻對準物權見仁見智,很難形成基本一致的意見。目前,關于準物權的代表性觀點主要有:第一,具有權利性質的物權為準物權。理論依據是物權的客體應為客觀實在的有體物,有體物之外的無形財產應為權利,有學者認為此類權利并非真正之物權,只不過是與物權相類似或為與物權相類似的一種變態物權,而使得其準用物權之規定。[3]也有學者認為這類權利是除適用自己特有的個性規則外,準用物權法的一般規定。[4]第二,特別法規定的物權為準物權。理論依據是一般物權由物權法直接規定,物權法沒有直接規定而特別法規定某方面的財產權為準物權。有學者認為準物權為特別法規定的財產權,或謂其為性質和要件相似于物權,準用物權法的規定財產權,采礦權、漁業權、水權等為其典型。[5]還有學者認為,準物權通常只獲得了從事采伐、捕撈等行為的資格,在上述行為完成之前并沒有特定的物作為其客體,很難歸屬于物權,因而由特別法予以規定,并準用物權的規范。[6]第三,將物權將來取得權定位為準物權。具有代表性是先買權、繼承權、采礦權、漁業權等物權取得權,其本身并不是物權(不具有直接支配性),但在效力方面與物權相近,準用物權的有關規定,故稱為準物權。[7]另外,還有學者對準物權作理論解釋,一是準物權是財產權,具有財產價值可以轉讓;二是準物權不在物權法所規定的物權類別之中;三是準物權在性質與要件上相近或相似于物權;四是有關準物權的問題除適用特別法上的規定外,可以適用物權法上的一般規定。[8]據此,礦產資源權根本不符合上述學說特征,需要優先適用廣義物權法將其定位為“物權”,不能以狹義物權法沒有規定反駁否認之,避免出現“法律無明文規定不受理”的消極性錯誤。
3.礦產資源權的所有權分析。《物權法》第39條:“所有權人對自己的不動產或動產,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第40條“所有權人有權在自己的不動產或動產上設立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人行使權利,不得損害所有權人的權益”,第117條“用益物權人對他人所有的不動產或動產,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權利”。目前,學者對所有權和用益物權特征有不同觀點,例如溫世揚教授認為,所有權與其他物權相比具有的特征有:一是自權性,是權利人對“自己之物”享有的權利,所有權主體即標的物的“主人”,因而所有權是自物權,所有權以外的物權稱為他物權;二是完全性,所有權人對于標的物可以進行全面的概括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即享有完全的支配權,所有權又稱完全物權,其他物權稱為限制物權;三是永久性,對所有權標的物的全面支配不僅表現為支配范圍的全面性,還表現為支配時間的無限性;四是整體性,所有權的整體性又稱為“渾一性”、“單一性”或“統一支配力”,是指所有權人對標的物雖然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能,并非各種權能的集合,而是一項整體性權利;五是彈力性,所有權的權能可能通過設定他物權而與作為整體的所有權相分離,然后所有權并不因此喪失其對標的物的支配力。[9]屈茂輝教授認為,用益物權的法律特征有:一是以對標的使用、收益為權利的主要內容;二是以所有權的存在為基礎;三是以物的使用價值為實現的基礎;四是除地役權外,用益物權都為主權利;五是標的物主要為不動產,但不以不動產為限;六是用益物權消滅后標的物以原狀返回到所有權人。[10]
筆者認為,所有權與用益物權的區分標準主要包括:(1)是否對自己的物享有物權;(2)是否享有完全和整體性的物權權能;(3)是否享有永久的物權權能;(4)物權的原始主體是自己還是他人;(5)物權的權能用盡后不能返回原權利人時甚至權利趨于消滅時是所有權,可以按期返回是用益物權;(6)權利人是否具有最終處分權能。據此區分理論,礦產資源權更屬于所有權,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礦產資源權主體是國家或者授權的其他主體,基于原始取得對己物享有全面性、原始性的完全支配權;另一方面,礦產資源權是一次性權利,被用盡時無法恢復到法律上和實物上的原始狀態,更無法返還給最初始權利人。
4.礦產資源權的客體分析。《物權法》沒有直接界定不動產與動產,更沒有作出科學定義,只是籠統概括性地提及,這從反面說明區分兩者有理論難度和立法技術難題,更可笑的是,《物權法》并沒有規定“物”的法律定義,造成無法界定不動產和動產是重大立法遺憾,甚至是重大的立法失誤。但是,《中國物權法草案建議稿》對“不動產”作了排除性界定。梁慧星先生認為:不動產,指依自然性質或法律的規定不可移動的物,包括土地、土地定著物、與土地尚未脫離的生成物、因自然或人添附于土地并且不能分離的其他物。動產,指不動產之外的其他物。[11]另外一個建議稿持基本相同觀點,一個為“定著物”,一個為“附著物”,其他部分完全相同。[12]所謂“附著”,指“定著”之意,指固定附著于土地而不能變更其位置的物。
根據上述理論,兩者的區分標準主要在于:不動產完全固定于地球表面,在物理空間位置上絕對不可移動,甚至是構成地球表層的重要固定物。此處應廣義解釋地球表面,可能是地球直接表面,也可能是最外表面以下一定深度的地表內層,此即物理區分標準。另外,次要區分標準是經濟價值標準,不動產經移動后除物理上不可恢復原狀外,更重要的是經濟價值原則上發生重大貶值(最多為殘值或廢品,甚至變成完全無用的垃圾)。不動產之部分可以與主體分離時,其經濟價值會大幅升值,由不動產之部分脫離之后成為有用的動產,這種升值并不是不動產本身,而是基于變成動產的事實行為,但是不動產的物理形態和價值形態付出了不可恢復的巨大代價。從整體上看,礦產資源是構成地球表層的重要物質資料,完全固定于地球表面并且尚未被開發,完全符合不動產不能在物理空間移動的物理特征,理應成為典型的不動產;從較具體層面來看,特定化過的礦產資源,在物理形態上從不動產通過開發行為變成動產,完全脫離了礦產資源整體意義上的“大主體”,成為名副其實的礦產資源產品,經濟價值發生正向升值,完全符合動產的物理和價值標準。可見,礦產資源在整體上屬于不動產,個體上屬于動產,籠統地說屬于動產或者不動產都是非科學的。
三、礦產資源權的衍生分析
礦產資源補償費屬于政府非稅財產性收入,全額納入財政預算管理,首見于《礦產資源法》第5條:“國家實行探礦權、采礦權有償取得的制度;但是,國家對探礦權、采礦權有償取得的費用,可以根據不同情況予以減繳、免繳,具體辦法和實施步驟由國務院規定。開采礦產資源,必須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繳納資源稅和資源補償費。”另外,《礦產資源補償費征收管理規定》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和其他管轄海域開采礦產資源,應當依照本規定繳納礦產資源補償費;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礦產資源補償費按照礦產品銷售收入的一定比例計征。礦產資源補償費由采礦權人繳納。礦產資源補償費納入國家預算,實行專項管理,主要用于礦產資源勘查。”據此,礦產資源補償費是礦產資源所有權主體(國家或者授權的政府機構)依法向特定的礦產資源開采人(有合法資質的單位或個人)收取一定費用,用于對礦產資源所有權的經濟補償。
據此析之,礦產資源補償費的內涵主要包括:1.通過非稅收收入方式補償給國家財政部門,由國家行使礦產資源的財產權益;2.按照礦產產品銷售收入的一定比例計征,體現國家征收礦產資源補償費,而不是雙方平等協商交換;3.只是彌補國家失去特定礦產資源時,由開采人向國家提供部分性補償,總體上屬于彌補性措施,不是礦產資源的全部財產利益的對價補償;4.目的主要用于將來勘查礦產資源,并沒有補償國家的財產權益;5.先開采后繳費模式,而非財產權使用費或出讓費的先繳費后使用;6.礦產資源補償費不是按照市場規律交換獲得的市場對價。
礦產資源補償費名稱表述上不合理和不具有正當性,也不能全面展現“財產權”屬性和作為財產的經濟性價值對價,建議修改為“礦產資源費”或“礦產資源轉讓費”才能體現財產權性。礦產資源開采所支付的費用并不是補償礦產資源權的主體,也不是用于礦產資源勘查,而是對礦產資源權所有者讓出礦產資源時支出的市場對價,應當是在雙方平等協商基礎上支付的財產權費用。因此,礦產資源權是一種新型財產權,為開采礦產資源支付市場對價,既能尊重市場經濟規律,又能展現礦產資源作為財產的本來屬性,促進礦產資源權主體積極行使和保護財產權益,還能促使開采人更有效、更合理開采礦產資源,有利于礦產資源的有效利用,有利于人們養成節約礦產資源的良好習慣和打造節能氛圍。
總體來說,礦產資源權應運行于私法大環境中,逐步成為財產權利,需要《礦產資源權法》確權,應然上屬于獨立的法定財產權,根本不同于土地權利和礦業權,在權屬上為所有權,客體上為不動產。礦產資源補償費既不科學,又不能體現礦產資源權作為獨立財產權的法學價值,更不能替代礦產資源權的市場對價,應然上屬于國家付出礦產資源后獲得的財產性市場對價,而這迫切需要確認礦產資源權的法律地位。
[參考文獻]
[1]梁慧星.中國物權法草案建議稿[M].北京:社會科技文獻出版社,2000:217,6.
[2]高富平.土地使用權和用益物權[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520.
[3]梁慧星,陳華彬.物權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8.
[4]錢明星.物權法原理[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376.
[5]陳華彬.物權法原理[M].北京: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2000:81.
[6]劉心穩.中國民法學研究述評[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331-332.
[7]溫世揚.物權法要論[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61.
[8]劉保玉.物權體系論[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352.
[9]溫世揚.物權法要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53-54.
[10]屈茂輝.用益物權制度研究[M].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5:5-12.
[11]王利明.中國物權法草案建議稿及說明[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4.
[12]陳華彬.物權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67.
(責任編輯:胡先硯)
中圖分類號:D91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4824(2016)01-0115-04
作者簡介:胡利明(1979-),男,湖北孝感人,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經濟師,法律顧問。
收稿日期:2015-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