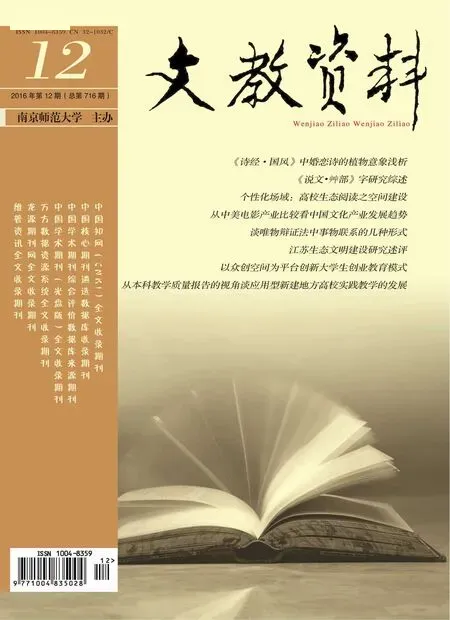明代白話短篇小說藝術衰退的表征與解讀
王 展
(南通大學 文學院,江蘇 南通 226019)
?
明代白話短篇小說藝術衰退的表征與解讀
王 展
(南通大學 文學院,江蘇 南通 226019)
摘 要:明代白話短篇小說自“三言”達到藝術高峰后,其后作品的藝術水準開始逐步衰退。從小說人物、情節、主題之間關系的處理上解讀,表現為人物塑造與情節演繹日漸脫節,過度的主題宣講束縛了情節的健康發展。
關鍵詞:明代白話短篇小說 衰退 人物 情節 主題
自元末明初始,中國古典小說創作步入了繁榮發展的活躍時期,不論長篇短篇、文言白話,諸類型小說競相涌現出大量作品,并在藝術水準上達至了前所未及的高峰。其間,以“三言”為代表的白話短篇小說一支,在傳承宋元話本的基礎上逐漸轉型,由說話人表演時依憑的底本而成為民眾執卷閱讀的物化產品,呈現出市場化、商品化創作與消費的新趨勢。然而,縱覽明代白話短篇小說發展歷程可見,它在藝術上攀越到特定高度后卻隨即調頭走向了衰退之途。這是一個令人遺憾又頗為值得關注和探討的文學現象。
人物、情節、主題是小說藝術的基本要素,三者間的關系能否處理得水乳交融、相得益彰是小說能否文本成功的關鍵。小說表現的人物不是一幅靜止的肖像畫,而是活生生的“行動中的人”[1]P38。哪怕再細膩精工的靜態描摹,對展現人物復雜微妙的性格特征及其豐沛激蕩的內心世界都是蒼白空泛、力不從心的。情節的特點恰在于,它“指的是人物的生活和實踐的演變過程”,“是由一級或一級以上的人物和人物之間、人物和環境之間的關系的具體事件和矛盾沖突構成的,用以展示人物的性格和表現作品的主題思想”[2]P1-2。“人物的行為及其矛盾沖突,構成了情節的主要內容。我們是在人物的行動當中看到他們的性格的。離開人物的行動,離開作品的情節,人物的品質就不能顯示或者不能充分顯示出來”[3]P4。據此,我們不妨對明代白話短篇小說各階段代表作品進行一番檢省,以期從中發現問題與癥結所在。
一、人物—情節:前進中的迷途不返
明代率先面世的白話短篇小說集是“三言”,但由于其中存有少量“宋元舊篇”,反倒更適宜解析從“話本”到“小說”的巨大進步。“三言”存留的宋元舊篇以敘述故事情節見長,甚少將人物與情節演進緊密結合,有時為了一味追求情節的離奇曲折,不惜以犧牲人物形象塑造,違反現實生活的真實面貌為代價,即便經過馮夢龍精心改造,作品的人物形象也始終無法生動豐滿起來。以《白娘子永鎮雷峰塔》[4]為例,小說中的白娘子起初是一位溫柔的多情女子,其后卻陡然間變得心腸冷酷不近人情,前后形象判若兩人,人物性格變化缺乏必然充分的內在依據。敘事者此處的興趣所在,無非是講述蛇精幻化人形后的種種風流軼事和神魔怪異,人物僅是為講述新奇的故事情節而配置的輔助工具,更奢談顧及人物性格的合理轉變。究其原因,宋元舊篇重情節輕人物的建構特點與它脫胎于說話技藝母體,偏重于追求故事娛樂性和商業盈利性的終極目標有直接關系。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說話現場“講述——聆聽”的表演方式所局限的。
馮夢龍殫精竭慮編著的“三言”中的其他篇目,在小說創作上大大糾正了宋元舊篇人物形象呆滯刻板,主要依靠離奇曲折的情節吸引受眾的弊病,注重將人物與情節水乳交融地統一于小說文本中,為中國古典小說史冊奉獻了諸如金玉奴、施潤澤、杜十娘、秦重、莘瑤琴等一大批性格鮮明、形象生動,為人津津樂道的典型人物。不僅小說主角神采飛揚,就是配角也被描繪得活靈活現。《蔣興哥重會珍珠衫》[5]中走街串巷賣珠子的薛婆即為一例。她在小說中屬次要人物,但承載了整個情節的轉捩關鍵,推動故事不斷朝著既定方向前進。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她的及時現身與巧施“謀略”,整個故事就必將重寫,或者根本就沒有發生的可能。小說不惜花費大量筆墨著力經營的,正是她如何心存預謀、步步為營、瞞天過海引誘王三巧落入陷阱的全過程。尤為值得稱道的是,敘事者沒有因為急于向讀者展示小說情節而忽略了人物形象塑造,而是自始至終“將筆觸深入到人物的內心,以性格和心理活動的刻畫作為情節推進的內在線索”[6]P122。當敘事者將薛婆巧設騙局,引誘寂寞空閨中的王三巧一步步走向與陳商私情相會的故事情節講述完畢時,薛婆本人性格特征的塑造即大功告成。她的出現無疑為后世小說塑造此類人物形象樹產了藝術上的標桿。
具有一定文化修養的中下層文人投身小說創作和書坊主在商業運作中取得的成功業績,強烈刺激著后繼者的每一根神經,激勵他們主動投身到白話短篇小說創編中。此后較短時間內,眾多白話短篇小說集在“三言”的直接影響下如雨后春筍般紛起,但就在亦步亦趨、匆匆前行的腳步中逐漸迷失了方向。藝術衰退的跡象在“二拍”已初現端倪。“二拍”首篇《轉運漢遇巧洞庭紅 波斯胡指破鼉龍殼》[7]正話部分講述的是一個做生意屢屢受挫的“倒運漢”文若虛,蹭蹬聊賴之際隨一幫朋友泛舟異域,偶于海上荒島拾得無價之寶鼉龍殼,從而發達致富的故事。該篇題材新穎奇巧,是明代白話短篇小說中少見的細致入微地描寫了海上貿易和異域奇趣的作品。主人公文若虛的形象在篇首被描述為“生來心思慧巧,做著便能,學著便會”,但敘事者對文若虛的性格概括在他經歷的傳奇遭遇中,幾乎都無法得到具體事例的有力印證。無論是“倒運”時的經商失意,還是“轉運”中的獲寶得意,文若虛這一人物形象仿佛被冥冥注定的“運”字束縛,在小說情節被不斷推向曲折精彩的高潮時,自身的獨產性格卻始終沒能被深入地展示與挖掘。出現這種人物塑造與情節敘述分離脫節的苗頭,既是白話短篇小說創作與出版日益商品化背景下草率命筆的后果,又反映出此時作者與讀者的興趣所向依舊難脫熱衷情節新奇的審美桎梏。
從《型世言》開始,小說人物形象塑造不僅與情節演繹逐漸脫節,而且出現了“類型化”的弊端。僅從《烈士不背君貞女不辱父》[8]這個標題就不難發現,小說主人公尚未登場,卻已被敘事者預先貼上某種性格分類的標簽,歸入了“概念化”的人物形象范疇。這種小說“命題”形式在“三言”“二拍”中雖也有見,但只是偶爾為之,到了《型世言》中卻俯拾皆是。與“二拍”中的《轉運漢遇巧洞庭紅 波斯胡指破鼉龍殼》標題比照,“轉運漢”是主人公的綽號,更多的是喻示他的“命運”;而“烈士”、“貞女”指向的則是主人公的“品格特征”,人物早早就被烙上了“類型”的標記。“當敘事者明確告知讀者故事的主要情節和人物的主導品格之后,他所要做的就是通過事件的敘述去表明和證實在題目中所預設的一切”[6]P118。事實情況也的確如此,《型世言》里出現最多的是定型的人物形象和性格刻畫,它們幾乎不隨小說情節的發展而有任何變化,似乎“烈士”、“貞女”具有與生俱來的性格穩定性,小說故事情節的推進不過是對其“烈”與“貞”命題的闡釋論證罷了。
情況發展到《西湖二集》變得更加糟糕。《西湖二集》第一卷《吳越王再世索江山》[9]和《喻世明言》第二十一卷《臨安里錢婆留發跡》[5]講述的都是吳越王錢镠發跡變泰的野史傳說。兩相比較,《吳越王》不僅描寫質木無文,情節粗概簡略,而且教訓滿篇、因果循環,此時小說的整體藝術水平出現了大幅度滑坡。兩篇小說均敘述了錢镠幼年時“照見山石影幻帝王之相”和“召集玩伴樹下演武操練”兩段故事。通過比照閱讀兩篇文字可以發現三處明顯不同:第一,《吳越王》描寫粗糙簡陋,僅用寥寥二百字就交代了故事情節,讀來索然寡味;《臨安里》則描摹細膩,大大擴充了情節內容,并增添了諸多人物言語和心理刻畫,文字飽滿充實。第二,《吳越王》是將故事情節作為貴人發跡前的奇聞逸事來敘述的,著眼點在于表現宿命觀點和小說情節的奇異,對于人物形象塑造幾乎未曾涉及;《臨安里》則抓住情節契機,著力塑造了一個自幼性格特異、智慧過人、氣質不凡的人物形象,預示了人物成年后得以變泰發跡的合理的性格特征。第三,《吳越王》在敘述兩個小故事時采用的是并列式安排,二者之間沒有展現出必然的內在聯系;《臨安里》卻通過調整兩個故事的先后敘述順序,在時間上和邏輯上把二者統一起來,使故事情節的級織更加嚴謹有序、流暢通達。
從宋元舊篇中人物與情節脫離,重情節而輕人物;到“三言”里人物塑造與情節演繹的緊密結合、交相輝映;再到“三言”往后的白話短篇小說集人物塑造與情節演繹越分越遠,小說整體藝術水平逐步下滑,構成了一個巨大的“人”字形。至此,明代白話短篇小說藝術發展的腳步似乎已經走到了終結。很多小說集究其終頁竟幾乎找不出什么 “星光熠熠”的人物形象,充斥文本的,往往是更離奇夸張的情節和愈加喋喋不休的說教。燦爛星辰閃爍過后,留給我們的依舊是一片寂寥迷蒙、黯淡無華的天空。
二、主題—情節:束縛下的痛苦掙扎
明代白話短篇小說由于歷史地繼承了宋元說話技藝口頭表演的特征,因此作品一般都具有相對固定的體例形式,由篇首詩、頭回、入話、正話、結語、篇尾詩等部分級成。小說經常在篇首詩等處就直接點明了意欲表達的主題宗旨,造成“主題先行”的現象,使小說整體藝術水平和作品風格的和諧性、統一性遭到了嚴重的破壞。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指出:“宋市人小說,雖亦間參訓喻,然主意則在述市井間事,用以娛心;及明人擬作末流,乃誥誡連篇,喧而奪主。”[10]P143這里所指的“誥誡連篇,喧而奪主”,主要就是明代白話短篇小說在開篇處枯燥呆板的說教性質文字。那些談因果、講報應、論宿命的小說主題闡述幾乎充斥了整個小說的開頭部分,沒有絲毫精彩可言。由于短篇小說篇幅關系,在有限的作品長度內硬扣上一頂“大而空”的帽子,就顯得愈發突兀滑稽,而且已經嚴重影響和束縛了后續小說情節的發展。主題宗旨歸納在前,故事情節展示在后,兩者相對獨產地存在,在這種固有表現形式的直接影響下,小說的主題與情節之間不可避免的矛盾自然就接踵而來。
一種情況是,小說力圖宣講的主題內容,已經無力涵蓋小說的主要情節。出現在小說篇首“這等中庸老套的主題歸納,表明作者面對新鮮有趣的世相,有追逐、探詢、表現的欲望和熱情,但當他回到理性的認識和把握的時候,就顯出空乏和無力。這樣,主題自身的容量和生命力比作品的人物和故事本身更淺少和短暫”[6]P210-211。有例為證。被視為“三言”中較為精彩別致的《沈小霞相會出師表》[5]在“入話”部分寫道:“只為嚴嵩父子恃寵貪虐,罪惡如山,引出一個忠臣來,做出一段奇奇怪怪的事跡,留下一段轟轟烈烈的話柄,一時身死,萬古揚名。”根據小說開頭這段事先設定的情節簡介和主題概括,本篇小說的主人公應該是沈鍊(青霞),而不是其子沈襄(小霞)及其侍妾聞淑女;小說著力敘述的應該是沈鍊如何與嚴嵩父子權貴抗爭不屈的故事,而不是僅僅把上述情節作為捎帶出下文沈襄如何巧妙逃脫監禁等后續故事的引子。實際情況卻是,我們讀完整篇小說,腦海里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是聞淑女這個弱女子在面對危機時所展現出的機智果敢的性格特征,獨力承擔危難,從而解救和保全了沈襄的不輸須眉的英勇氣概。就是男主人公沈襄,在聞淑女的精彩表現映照下也顯得風采全無,幾乎被聞淑女的生動形象完全淹沒。至于敘事者在作品篇首泛泛提及的忠臣沈鍊“做出一段奇奇怪怪的事跡,留下一段轟轟烈烈的話柄”,更是沒有成為小說真正的主干情節。可見,即便如馮夢龍這般寫作好手,沒能很好地解決小說主題與情節不相匹配的問題。此后出現類似問題的還有《警世通言》第十一卷《蘇知縣羅衫再合》,《拍案驚奇》卷十一《惡船家計賺假尸銀 狠仆人誤投真命狀》,《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一《進香客莽看金剛經出獄僧巧完法會分》,等等,各部小說集內所在多多、不勝枚舉。
另一種情況是,雖然同樣是說教意味濃厚的主題彰示在前,如果說“三言”“二拍”中的小說作品還能時不時對應主題,在小說情節內流露出對于人們世俗生活欲望和生存權利的理解、同情和尊重的理性精神,小說情節的演繹表現也不至于過分離奇乖張的話,那么到了“三言”“二拍”之后的《型世言》《西湖二集》等短篇小說集里,小說創作的主要傾向已經把對小說情節敘述的真實可信、合乎情理原則置于無足輕重的地位,而是注重全心全意地進行倫理道德主題的詮釋推演。敘事者常常是從某一種事先確定的主題觀念出發,為了印證主題來設計、安排小說情節,將情節當做主題的具體例證。這種“削足適履”的創作思想和方法,使小說的情節完全被主題所束縛,即使苦苦掙扎亦動彈不得。小說情節變得越來越粗糙鄙陋,有些作品甚至發展到了駭人聽聞、匪夷所思的地步。《型世言》第四回《寸心遠格神明 片肝頓蘇祖母》[8]在小說開頭處,敘事者就饒有興致地大發議論,津津樂道地宣揚了一番自己理解的所謂“孝”的概念。遵循孝道這一盡人皆知的世俗觀念,在這篇小說里已不是傳統的耳提面命、恭奉父母可以涵蓋的了。為了不惜余力地印證小說“孝”之主題,敘事者硬生生地捏造了一個十四歲幼女陳妙珍刳肝救祖母的“孝”的故事大肆褒獎,以圖樹產典型供世人模仿學習。作品里一個未成年的小女孩陳妙珍為了醫治祖母沉疴,居然“輕輕把左臂上肉撮起一塊,把口咬定,狠狠的將來割下”。割肉熬粥還不能醫愈疾患,在仙道神明的指引下她需要繼續奉獻出肝臟,于是“就紅處用刀割之,皮破肉裂,了不疼痛,血不出,卻不見肝”。到了這步田地竟然還顯得她心不至誠,因而“妙珍又向天拜道:‘妙珍忱孝不至,不能得肝,還祈神明指示,愿終身為尼焚修以報天恩。'正拜下去,一俯一仰,忽然肝突出來。妙珍連忙將來割下一塊”。小說情節為了貼合主題,只能從演繹主觀理念目的出發搭建構架,因而迂腐刻板荒誕不經,完全違背了小說基本的創作原則。這種所謂的“孝道”主題宣傳,以及其他陳腐內容的說教訓喻,不是冷酷殘忍就是愚昧虛偽,已經到了不通人情、扼殺人性的可怕地步。
在《型世言》及其后來的小說集中,敘事者自作主張地在儒家綱常禮教內為人們訂產了一整套實際上無法做到的人生準則,作為小說的主題著力宣揚。這樣的價值標準,與市民階層心目中的現實標準是大相抵牾的。再加上小說情節受到主題的束縛牽制,為俯就它而變得粗糙荒誕,本就不甚高明的說教便更顯得曲高和寡。黑格爾的一段論述可謂一語中的:“但是如果把教訓的目的看成這樣:所表現的內容的普遍性是作為抽象的議論,干燥的感想,普泛的教條直接明說出的,而不是只是間接地暗寓在具體的藝術形象中,那么,由于這種割裂,藝術作品之所以成為藝術作品的感性形象就要變成一種附贅懸瘤,明明白白擺在那里當做單純的外殼和外形。這樣,藝術作品的本質就遭到了歪曲了。因為藝術作品所提供觀照的內容,不應該只以它的普遍性出現,這種普遍性必須經過明晰的個性化,化成個別的感性的東西。 ”[11]P154
明代白話短篇小說是中國古典小說發展史上難以忽略的重要一環。盡管由于小說數量眾多,創編人員素質參差不齊,出版目的略帶功利色彩而造成了藝術水準的逐漸衰退,但它仍然具有獨特的歷史地位和藝術價值。客觀公允的解析和評價,有助于在歷史的縱坐標中給予它合理定位。
參考文獻:
[1][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著.陳中梅,譯注.詩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2]吳功正.小說情節談[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5.
[3]冉欲達.論情節[M].北京:新華出版社,1982.
[4]馮夢龍.警世通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5]馮夢龍.喻世明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6]王昕.話本小說的歷史與敘事[M].北京:中華書局,2002.
[7]凌濛初.拍案驚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8]陸人龍.型世言[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9]周楫.西湖二集[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
[10]魯迅.中國小說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1][德]黑格爾,著.朱光潛,譯.美學(第一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