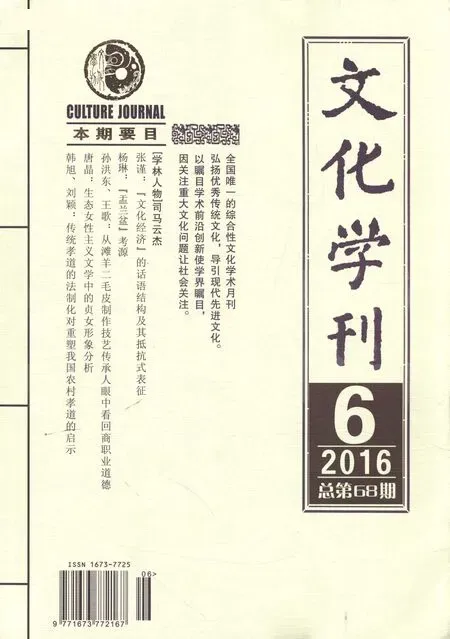“文化經濟”的話語結構及其抵抗式表征
張 謹
(廣東行政學院,廣東 廣州 510053)
?
【文化視點】
“文化經濟”的話語結構及其抵抗式表征
張 謹
(廣東行政學院,廣東 廣州 510053)
要準確理解約翰·費斯克的大眾與大眾文化的基本理論,一定要聯系他的金融經濟與文化經濟的主要觀點。可以說,其大眾文化理論的精髓都是建立在這“兩種經濟”的基礎之上的。基于此,筆者就這兩種平衡的經濟、文化經濟的話語結構及文化經濟的抵抗式表征展開論述。
文化經濟;金融經濟;大眾文化;大眾;話語結構;抵抗式表征
美國文化研究專家約翰·費斯克(John Fiske)以樂觀主義的姿態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大眾文化進行了不同于法蘭克福學派那種悲觀主義的批判式的深入研究。在費斯克看來,文化工業提供的文化產品只是大眾文化形成的一種資源,大眾文化是大眾利用這些資源在日常的消費活動中自我創造并流通意義與快感的過程,它充分彰顯了大眾的主觀能動性和抵制主流意識形態的反叛精神。與法蘭克福學派視野中靜態的、消極的、屈從束縛的大眾相比,費斯克眼中的大眾是流動的、積極的、追求解放的主體。要準確地理解大眾與大眾文化,勢必聯系他的金融經濟與文化經濟的基本理論。可以說,其大眾文化的理論精髓都是建立在這“兩種經濟”的基礎之上的,因為意義和快感是大眾文化的實質性符號表征,而它們的流通就是在與金融經濟相區分的文化經濟中進行的。
一、兩種平行的經濟:金融經濟與文化經濟
費斯克以電視節目的生產和消費為例,將在此過程中所體現的經濟現象區分為金融經濟和文化經濟。金融經濟的財富流通是在前后相繼的兩個子系統中進行的。作為生產者的電視演播室組織相關創作人員編排了若干節目,然后把節目賣給消費者,如廣播公司或電影公司的經銷商,完成了金融交換,獲得了商品盈利。在費斯克看來,整個流通過程并沒有結束,因為文化商品不同于一般的物質商品,一般的物質商品經歷了買賣流通環節后,其經濟功能就會完成,而電視節目這種商品在被消費的同時本身就是商品生產者,收看電視節目的無數個觀眾成為了商品,對廣告商而言,觀眾的消費者就是廣告商。[1]由此觀之,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大眾成為商品是由于他們的經濟地位決定的,就像恩格斯所說的那樣:“……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是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這里表現出這一切因素間的相互作用,而在這種相互作用中歸根到底是經濟運動作為必然的東西通過無窮無盡偶然事件(即這樣一些事物和事變,它們的內部聯系是如果疏遠或者是如此難于確定,以致我們可以認為這種聯系并不存在,忘掉這種聯系)向前發展。”[2]然而,經濟基礎決定論只能解釋文化商品的某些“物質性”的東西,如質地、價格、數量和購買人數等,諸如流通過程中的意義、價值、象征符號等是無法說明的。也就是說,文化商品所蘊含的文化的本質性內涵在金融經濟中至少是不能完全揭示的,它只能在文化經濟的場域中和社會生活的關系中加以認知。
文化經濟的生產者既不是演播室,也不是節目,而是觀看節目的大眾,他們在觀看節目的過程中會產生各種各樣的意義和快感,這些意義和快感在此就成為了觀眾生產的商品,觀眾自己也是意義和快感的消費者。文化經濟的語境中,原來的商品,如電視節目、報刊雜志、流行時裝等作為一個文本和話語結構而存在,其潛在的意義和快感就蘊含在話語結構之中,它是形成大眾文化的重要資源。[3]在后工業社會階段,高度發達的現代化生產技術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產生,致使絕大部分大眾失去了批量生產文化商品的能力,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對文化工業商品的生產性使用。費斯克并不否認資本主義受利潤的驅使,其文化工業呈現出中心化、同質化生產的特點,誠如霍克海默與阿多爾諾所說:“文化工業的技術,通過祛除掉社會勞動和社會系統這兩種邏輯之間的區別,實現了標準化和大眾化生產。這一切,并不是技術運動規律所產生的結果,而是由今天經濟所行使的功能造成的”。[4]金融經濟要獲得高額的經濟回報,就必須減少社會差異,滿足大眾的共同需求,大眾在宰制性的意識形態下,其行為總是受體制內權力的限制,因為要符合社會秩序的要求。“于是所有的文化商品,多多少少都具有我們可以稱之為中心化的、規訓性的、霸權式的、一體化的、商品化的(這類形容詞幾乎可以無限繁衍)力量”[5]。與法蘭克福學派不同的是,費斯克并沒有在金融經濟面前就此止步,他認為與這些力量相對抗的是大眾的力量。大眾在文化經濟階段把文化商品轉換成文化資源,并運用這些資源生產更多的意義與快感,這些豐富多樣的意義與快感是對文化商品之規訓的規避與抵抗,也是對文化商品同質化的裂解。[6]大眾文化是大眾在與社會秩序及權力約束的抗爭中自我創造的結果。
二、文化經濟的話語結構:文本的選擇
大眾文化的解釋力不是由金融經濟來決定的,而是由文化經濟所賦予的意義和快感來確定的,而這些意義和快感的創造必須依賴于文本。不同的文本會產生不同的意義與快感,如影視戲劇、流行歌曲、商品廣告、時尚服裝等。費斯克受法國結構主義文論家羅蘭·巴特的啟發,主張大眾文本應該是“生產者式文本”。巴特認為,文本是由語言來決定的話語存在形式,它是人們對真實作品進行論證與闡發的產物,它是無確定結構、無中心意義的能指系統。文本的作者是產生意義的根據,文本的讀者可以讀出比作者賦予的更多的意義,所以,文本是一種生產和生產力,而不是終極結果。鑒于讀者的重要性,巴特把讀者分為消費式讀者和作者式讀者,相應地,文本可分為讀者式文本和作者式文本。讀者式文本是指讀者以被動消極的態度接受文本既成的意義,作者式文本是指否定了作者對作品的絕對“發言權”,更加強調讀者參與意義建構的能動性。雖然巴特討論的文本范疇主要是文學作品,但這些范疇對費斯克的影響是相當大的。費斯克在此基礎上提出的“生產者式文本”,用他自己的話說,生產者式文本的概念“是用來描述‘大眾的作者式文本’的”[7]。這種文本不需要強迫讀者建構新的意義,但它有很大的開放空間。盡管它原本的意義是大眾不情愿接受的,且具有脆弱性、限制性等很多弱點,然而,它能為大眾文化的生產提供多種可能性;它本身隱含著矛盾與沖突;它的結局是松散自由的;它的意義超出了社會秩序的規訓力量;它自身無法控制的裂隙為其創造新的文本提供了條件。[8]作為文化工業產物的商品并不像作者式文本那樣產生控制和規訓的力量,但一旦它與體驗中的社會關系結合,就會成為大眾生產力的驅動力量。資本主義文化工業生產的經濟需求之所以能得到滿足,就在于人們選擇了文化工業商品作為其大眾文化來源;社會體制內的霸權力量之所以能有效運行,就在于人們選擇了能體現霸權的文本來閱讀。“自上而下的力量只有在遭遇另一股自下而上的抵抗力量時才能開始運作。大眾文化充滿了對抗的因素,而‘措辭’(diction)的‘對抗’(contra)力量則來自它(不情愿的)‘生產者式文本’的‘生產者式’讀者”。[9]由此可見,大眾文化是大眾自己選擇、自己生產和消費并具有無限張力的文本系統。
費斯克以牛仔褲為例來說明從金融經濟里保留文化經濟時文化商品所具有的抵抗或規避作用。批量生產的牛仔褲商品的文本符號象征著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表達了粗狂、隨意、無拘無束的自由心境。當牛仔褲的擁有者故意撕破或漂白后穿上它而引以自豪時,它表達的是一種對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抵抗行為。面對這種抵抗,資本主義工業也會就此大量生產有破洞或漂白的牛仔褲,達到收編的目的,因此,廣告業盡量控制其文化意義,使之配合金融經濟來運轉。費斯克舉例說,學童可以將一則啤酒廣告詞改編成黃色順口溜;一則連襪褲品牌的廣告語,調皮的孩子們可以嘗試著轉化為黃色的、對抗性的、屬于他們自己的亞文化。當然,與廣告一樣,所有的文化商品都逃不脫被顛覆、規避或抵抗的命運。
三、文化經濟的抵抗式表征:大眾的創造力
大眾的創造力表現在大眾日常的文化實踐中,“其特征是,弱勢者通過利用那剝奪了他們權力的體制所提供的資源,并拒絕最終屈從于那一權力,從而展現出創造力”[10]。作為弱勢者的大眾通常采用游擊戰術對抗強勢者,“偷襲強勢者的文本或結構,并不斷對該體制玩弄花招”[11]。費斯克比較了德賽都與列斐伏爾等人有關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與權力問題,進而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德賽都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一書中運用了戰略與戰術、游擊戰、偷襲、詭計與花招等詞匯來描述大眾對社會體制的抵抗,以此產生新的文本意義,使之形成自己的文化。強勢者的權力運行空間,包括城市、商場、學校、工場車間等,他們控制了這些場所和商品,弱勢者只能像游擊隊員一樣見機行事地發展自己的“空間”,并逐步以自己的方式適應這種環境。同理,人們所處的文化空間是社會的文化工業提供的,面對該文本,各人有各人的解讀方式。在這點上,德賽都與列斐伏爾的觀點是一致的,即在“強制”與“適應”之間保持著一定的張力。不同的是,列斐伏爾只談日常生活的苦難及權力,而德賽都更強調在適應性的抵抗中被宰制者的力量以及社會體制的脆弱性。他認為,大眾以“權且利用”(making do)的藝術創造了屬于自己的文化。德賽都指出:“戲弄或智勝對方的游戲,有數不勝數的方式……這些方式描繪出各種群體微妙而頑強的抵抗行為。這些群體由于缺少屬于自己的空間,他們不得不進入那些已然確立的力量與表述(established forces and representations)當中。大眾必須權且利用他們擁有的一切。在這些戰斗者的各種計策當中,有一種突然襲擊的藝術,即回避、繞開束縛性空間之規則的快感……甚至在操縱與享樂的場域中也是如此”。[12]在他眼里,抵抗的微空間無處不有,抵抗的微行為無處不在,抵抗的策略也是靈活多樣。
在消費主義盛行的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人人都是消費者,他們的消費包括物質消費,如飲食起居等,以及符號消費,如教育培訓、網絡媒體等。在現實生活中,這兩種消費也難以有很明晰的區別,如汽車既是交通工具,也是一種言語行為。任何“會言談的物品”都無法區分哪些是花錢直接購買的,哪些花費是間接的,哪些是免費的。在此過程中,它們所傳達的意義與“純粹的物質商品”一樣受到社會體制的指教與權力的分配。它們都是日常生活的資源,是大眾文化形成的基本條件。[13]故此,費斯克把大眾的消費行為等同于文化生產行為,把消費過程等同于意義的生產過程,不過,這一切都是商品在文化經濟中發生作用的結果。只要有消費存在,就會有對資本主義體制的戰術襲擊,有些襲擊是非物質的、不可見的,有些襲擊是物質的、可見的,前者如個人身份的隱匿變化、與體制對抗的電視觀眾仍然被賣給廣告商等,后者如利用“權且利用”的藝術進行戰術調遣。“這種藝術會在他們的場所內,憑借他們的場所,構建我們的空間,并用他們的語言,言傳我們的意義”。[14]費斯克引用德賽都所舉的典型例子來說明自己的觀點:“因此一個住在巴黎或魯貝(法國)的北非人,通過住在‘低收入住房發展規劃’所建造的樓房,或者憑借某些‘居住’的方式(無論是住在一間房子,或是一種語言),即憑借有異于其母語卡比爾語的法語,迂回進入了那個強加在他身上的體制。經由這種結合方式,他添加了若干意義,并為自己開創了一處空間,在這一空間里,他可以從該場所或者該語言的束縛性秩序中,找到利用之的方式。那一場所會把它的法律壓在他的頭上,而他在無法離開那一場所、別無選擇、只能生存其間的條件下,卻可以在該場所內部,建立某種程度的多元性與創造性。憑借一種‘介乎其間的藝術’(an art of being in between),他從自己的處境中創造了意想不到的結果”。[15]這種結果就是因為商品使用者與“秩序”之間的縫隙的存在而產生的新的意義。
四、結語
從某種意義上說,金融經濟與文化經濟的基本思想支撐起費斯克大眾文化理論的整體構架。《理解大眾文化》的翻譯者之一宋偉杰在該書的后記中寫道,費斯克在本書中論及了大眾文化的三種走向:一是將大眾文化放在精英文化、主流文化的關系中進行探討,但并沒有關注到大眾階層對權力集團的抵抗;二是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觀過分強調了宰制者的力量,對大眾文化持悲觀、否定的態度;第三是將大眾文化視為權力斗爭的場所,充分肯定大眾的活力與創造力,即大眾通過“游擊”戰術,躲避、消解、冒犯、轉化乃至抵抗那些宰制性力量,此種研究走向是費斯克極為首肯的。[16]由此可知,費斯克的大眾文化理論之所以令人耳目一新,就在于他不僅僅看到了文化的商品特性,而在于他更加敏銳地洞察到了文化的政治屬性和語境特征。然而,沒有對文化所屬商品作“兩種經濟”的劃分和解讀,其學理的深刻度是根本達不到的。
[1][3][5][6][7][8][9][10][11][12][13][14][15][16][美]約翰·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M].王曉玨,宋偉杰,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32.33.34.34.128.128.129.58.39.41.42.44.44.248-250.
[2]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5-696.
[4][德]霍克海默,阿多爾諾.啟蒙辯證法[M].渠敬東,曹衛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36.
【責任編輯:王 崇】
G05
A
1673-7725(2016)06-0006-04
2016-04-05
本文系廣東省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視域下文化治理機制與路徑研究”(項目編號:GD15CMK05)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張謹(1966-),男,湖北仙桃人,教授,主要從事哲學與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