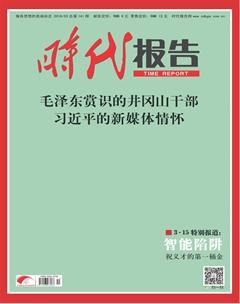改革大潮中的老支書
穆青 孟憲俊


冀中平原上的蠡縣辛興村,從來還沒有像今天這樣令人羨慕。
在這里,寬敞、明亮的新式農舍,一排接著一排,一棟連著一棟。那些造價幾十萬元的別墅式小樓,更顯出辛興人的氣派。一些人家不僅擺著時興的家具,還鋪著彩色地毯。
全村擁有各類私人轎車39 輛。
這個共有6700口人的村莊,建起了57家工廠。農業實現了機械化,糧食畝產800公斤。1990年,全村工農業總產值2億元,人均收入2700元。
村頭,一個占地70畝的化纖毛線市場,已成為辛興的“聚寶盆”。四方涌來的購銷人員,每天多達一兩萬人,平均日交易額300多萬元。
現代化的文化活動中心和衛星電視地面接收站給村里帶來了豐富多彩的業余文化生活。國家大事,世界風云,成了辛興人關注的話題。
這情景,如果出現在我國沿海發達地區,也許算不上什么,但出現在歷史上貧窮落后的華北腹地,就不能不令人驚嘆了。
向當地人問起這一切,他們都深情地談起了老支書閻建章。
“共產黨不姓窮,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事情要從1977年7月1日說起。
這天一大早,村上小學校的院內院外就站滿了人,選舉村支部書記的黨員大會正在這里舉行。大家心里都清楚:這不只是選支部書記,更是在決定辛興村未來的命運。
消息傳出來了:120名黨員一致選舉閻建章為村黨支部書記。全村人像過年一樣地興高采烈。
從冀中抗戰最艱苦的1943年到“文革”開始,閻建章一直擔任辛興村黨支部書記。戰爭年代,他領導群眾打游擊,敵人曾懸賞一萬元要他的人頭。“文化大革命”期間,他被打成“走資派 ”,含淚離開了支書崗位。20多年時間,辛興的盛衰起落, 把他和群眾緊緊地聯在了一起。他的心是通著人民的。
第二天,他感觸萬端地來到了大隊部。這里的房子是他親手修建的。“文革”前的十幾年間,他和戰友們在這所房子里領導全村人民治鹽堿地,建豐產田,上技術課,紅紅火火地度過了不知多少個難忘的日日夜夜!今天,這里卻變得這么冷清:年久失修的房子裂痕縱橫,門窗上破舊的窗紙在沙沙作響。辦公室內,地上堆著垃圾,墻上掛著蛛網。只有老會計還守在那張已經很破舊的辦公桌旁。
閻建章問他:“隊里還有多少錢?”
老會計拉開抽屜,找出了一枚硬幣,說:“只有這兩分錢。”
閻建章愣了。他知道,十年動亂把辛興折騰苦了,可萬萬沒想到竟窮到這個份兒上。
老會計又說:“庫存現金是二分,實際上欠銀行貸款是42萬。”
一切都不必再問了,閻建章心里明明白白。眼下村里糧食畝產100多公斤,一個勞力一天只掙一角二分錢。生產隊糧倉空空,社員飯桌上每日兩稀一干:稀的可以數出米粒來,干的是紅薯和菜窩窩。全村還有300多戶人家在外討飯。
在歷史的新起點上,閻建章面前就是這樣一條布滿荊棘的路。
老貧農王眼章找他發牢騷:“從前跟日本鬼子和國民黨打仗的時候,你是黨支書。你叫我出錢出糧,我餓著肚子也往外拿;你說出擔架,我站起來就走;你說給咱的隊伍送東西,我馬上套車。我圖啥?圖的就是跟著共產黨鬧革命,有一天能過上好日子。萬沒想到,解放好多年了,鬧得連肚子都填不飽,真叫人寒心。”
當年和他在地道里戰斗過幾個春秋的崔春峰,拉著閻建章的手,眼含熱淚說:“建章啊,俺什么都不想,往后你能讓大伙吃飽紅薯,俺就知足啦。”
聽了這些話,閻建章流淚了。干了這么多年社會主義,至今還讓全村吃不飽,作為一個黨支書,再沒有比這更刺痛他的心了。
他永遠也忘不了十歲那年,父親慘死在天津一家工廠里,母親拉著他們要飯,妹妹病餓而死,兩歲多的弟弟被賣到山西。正是為了使自己和天下窮人都能過上好日子,他才參加了共產黨。他也不會忘記,在革命戰爭年月里,和他一起浴血奮戰的戰友,不知有多少人獻出了生命。可是幾十年過去了,在這塊血染的土地上,鄉親們的生活還是這么苦。他深感對不起鄉親們,對不起犧牲的戰友。
在支委會上,在黨員大會上,閻建章曾多少次激動地說:“共產黨是從窮人堆里發展起來的,但共產黨不姓窮,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如果我們不能帶領群眾富起來,那還算什么共產黨員,還要共產黨干什么!”
這發自一個老共產黨員內心的聲音,像春雨滋潤著人們的心田。它給窮困的辛興人民帶來了信心和力量。
“改革開放是個大舞臺,就看咱能不能唱大戲。”
鄉親們的知心話,辛興艱難的日子,使閻建章輾轉反側,夜不能寐。
他以十倍的辛苦工作著。除草滅荒,挖溝排水,他搶在前頭。耕地、播種、田間管理,樣樣農活他都過細地安排。5000畝棉田是全村的“銀行”,群眾打油買鹽全指望它,棉籽一下地,他每天都要去看一次,扒開浮土,仔細地察看棉籽是否發了芽。澆麥季節,他日夜巡視在田間地頭,用步子丈量著每一塊麥地。誰家澆了多少,誰家還有多少沒有澆,他心里都一清二楚。
村頭小河里來了大水,小橋被沖垮了。他第一個跳進冰冷刺骨的水里,帶著大伙搶修。村子里打井,他在井口搭起窩棚,和大家一起吃住,一起下井。
時間一天天過去了,可是群眾生活依然困難。
他思索著:全村6000多口人,在人均只有一畝多一點的土地上繡花,繡得再好也只能混個溫飽。如果不放開手腳發展工副業,把農民中蘊藏的生產潛力發揮出來,講富民,只能是一種良好的愿望。
他去到北京,向幾個老戰友傾吐了自己富民的愿望。人們告訴他,這不僅是他一個人的想法,也是當時具有遠見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農村問題的深沉思考。
在一個親戚的幫助下,他從北京合成纖維廠買回了5公斤氯綸,用彈棉花的舊弓弦彈好,交給村里的幾個紡線能手試紡,居然紡出了很好的氯綸毛線。
閻建章喜出望外。他像捧著一個十世單傳的嬰兒一樣,把毛線捧給大家看。他和幾名支委變賣家私,求親靠友,集資1200元,很快帶領全村搞起了紡毛線的副業。一年半時間,他們竟用手搖紡車紡出了100噸氯綸毛線。
這件事給辛興帶來了希望。但沒過多久又出現了新的困難——他們的毛線積壓了。看著一捆捆凝結著大伙兒心血的毛線賣不出去,閻建章,心急火燎。他坐上村里的卡車,走山東,下江蘇,跑安徽,闖山西,行程幾千公里,調查市場需求,尋找毛線銷路。路上,他一連發了幾天高燒,醫生見他這么大年紀了,非讓他住院不可。可他打了一針,吃了點藥,就又出發了。
這次大江南北千里行,是閻建章第一次涉足于商品生產的海洋。透過這五光十色的商品大世界,他發現了商品生產和交換中的無窮奧秘,明白了自己生產的毛線一時找不到市場并不等于沒有市場。回村后他親自挑選了一批骨干,組織起一支上千人的推銷隊伍,背著五顏六色的毛線,走鄉串戶去了。
辛勤的耕耘終于結出了果實:毛線的銷路逐步打開了,許多農戶開始有了積蓄。村里欠銀行的貸款也陸續在償還了。當女社員楊立格從大隊會計手中接過上千元的加工費時,激動得流下了眼淚。她小聲對別人說,自打記事的時候起,她手里還沒有攥過這么多的錢。
可是,正在這時,從四面八方飛來不少的指責。一個和閻建章有著莫逆之交的老同志關切地提醒他:“快收攤子吧。這樣干下去會走偏方向,對你不好。爆了豆大家吃,炸了鍋可要你一個人賠上。”
閻建章笑著說:“我不怕。咱們這樣做是為了把辛興幾十年的窮根挖出來。群眾歡迎的事,我相信黨和政府會支持。”
他硬是撐著勁兒,挺過了三中全會前那段非常困難的時期。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閻建章感到像徹底解放了那樣痛快。他逢人便說:“改革開放是個大舞臺,就看咱能不能唱大戲。”他的第一個目標就是在村里開辦紡織廠,用機器代替手工。他跑了四個省,東拼西湊,買回了幾臺舊機器。但要把這些舊機器組裝起來,沒有工程技術人員不行。他又西跑保定,東奔天津,到處打聽一些棉紡廠工程技術人員的姓名、住址,一次次登門懇請人家能利用星期天或節假日去為他們安裝機器。有時候,為了請上一個人,他一連幾天冒著嚴寒,甚至頂著大雪,蹲在人家宿舍的胡同口上,默默地等待著。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一些技術人員被這位老支書為群眾致富的苦心感動了,表示不要報酬也去幫忙。
機器安裝過程中,工程師們來來往往,閻建章都親自陪在現場忙上忙下。半年多時間,他累得人瘦了、嘴唇裂了口子,有時嗓子腫得說話都很困難,但他一次也沒有離開過現場。小兒子病得幾天吃不下飯,老伴田素花叫他三次,他都不回家。到他家里串門的人問閻建章哪里去了,老伴氣得說:“他不要這個家了,跟機器結婚啦。”
話雖這么說,但田素花對老伴的心地秉性還是理解的。當年,她同閻建章結婚那天,花轎剛抬到門口,就碰上黑壓壓的一大片敵人前來掃蕩。閻建章連新娘的模樣都沒有看清,就把手一揮,叫她跟著鄉親們轉移,自己帶著游擊隊打仗去了。從那以后,她跟著閻建章風里來雨里去,幾十年共同生活,她深知老閻為了大伙的利益,干起事來九頭牛也拉不回來。
紡織廠開工的那天,村里一幫老太太來看稀罕,閻建章笑著對她們說:“別看這堆鐵疙瘩,紡起線來,能頂你們幾百個老太婆!”
1988年,工廠辦多了,生產發展很快,閻建章又開始了建立大型毛線市場的壯舉。他深知,發展商品生產沒有發達的市場不行。他要把全國各地生產、經營毛線的大客戶、小商販,都吸引到辛興來,在家門口進行交易。他要主動把自己的企業推向商品經濟的海洋,參與競爭,接受檢驗。為此,他在村邊劃出了70畝地,從縣里村里集資80萬元,在上級的支持下,創建了冀中平原上第一個設備齊全、具有相當規模的毛線大集。經過幾年艱苦的經營,現在這個集市已成為全國中低檔毛線的集散地,不僅為辛興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也從四面八方帶來了各種信息,打開了千百條與全國各地經濟相溝通的渠道。辛興人眼界開闊了,經營水平提高了,集市的繁榮促進了全村百業興旺,辛興愈來愈紅火了。
閻建章是一個農民,文化僅是“掃盲班”水平。他自己常說:“耕地,我行;辦企業,不會。”可是,商品生產這所大學校,給了他許多前所未有的知識和經驗。改革開放十多年來,他那現代經營思想和商品競爭意識,他那尊重人才、善用人才的領導藝術,他對科學技術的信賴和追求,他那爭分奪秒的時間觀念,已使他判若兩人:他是老支書,也是“頭裹著白毛巾的企業家”。
這張企業家的“證書”是閻建章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跑出來的,干出來的,闖出來的。
為了發展辛興的事業,他的老伴說,他一年要穿壞四五雙鞋,雙雙鞋的幫底都磨出了大窟窿。
兒子們說,他騎壞了四輛自行車,有紅旗、飛鴿、燕牌,還有外國出產的“富士”。
支委們說,村里沒有汽車時,他坐著“鐵牛”跑;有了汽車,又跑壞了好幾輛。
他不僅跑遍了大半個中國,同幾百家公司、企業、經貿和科研單位建立了聯系,還東渡日本,學習人家的管理經驗,引進先進的技術和設備。如今的辛興村,舊機器大部分已更新換代,產品的花色品種已增加到上百個,同北京合資生產的純毛毛線,已成為全國市場的搶手貨。全村擁有熟練工人5000多人,一大批技術和管理人員也已成長起來。他把一個封閉落后的窮村莊,跑成了一個工商發達、惠及四方的“小城市”。
富民——閻建章半個世紀的執著追求,終于在改革開放的今天一步步變成了現實。
“共產的目的就是共富,共產黨員要永遠姓共。”
辛興村富了。1400戶人家,住小樓的130戶,住新式平房的1000多戶。可閻建章仍然住著土改時分的土房。房間低矮昏暗,室內一鋪土炕,待客、吃飯都在炕上。家里擺的依然是老伴當年陪嫁的老式板柜和土改時分的方桌、條凳。一部電話和二臺電視機,是僅有的現代用具。
辛興人都很有錢,萬元戶已很平常,幾十萬元戶也不稀罕。就連老太太在毛線市場上幫別人捆捆線,一天也能掙上幾十塊。可閻建章的工資,每月僅有100元。
村里男男女女不少人穿戴著“新潮”服飾。但閻建章,仍然是冀中農民傳統的打扮:一條白毛巾裹頭,一身老式布衣褲。許多人家吃飯都講究個新花樣,可閻建章還是老習慣:燴餅、疙瘩湯。老戰友來了,往炕上一坐,叫老伴煮上小米綠豆粥,弄上餑餑炸小魚,喝上兩盅好酒,掏掏知心話,這就是他的樂趣。
“群眾富了,你還是這個老樣子,大伙兒看不下去呀! ”上面來人這樣說,辛興人更是這樣念叨。黨支部、村委會每次勸他搬出那間土房,都被他堅決拒絕。四個兒子也多次商量為他蓋新房,還設計了新房的式樣,但每次都挨他一頓罵。
近些年,人們發現老支書臉上的皺紋多了、深了,頭發稀了、白了。大伙兒心里都感到不安,總覺得欠了他一筆賬。
可是,閻建章從不這樣看。每當有人提出這個問題,他總是說:“究竟誰欠誰的賬,我看這個大問題可不能含糊。”
閻建章16歲擔任黨支部書記,在冀中抗戰最艱難的時刻,他帶領游擊隊打鬼子,捉漢奸,在炮樓下與敵人周旋。有一回,敵人突然包圍了辛興村,把全村人集中起來,逼著交出閻建章。當時,閻建章就在人群里,可辛興人都說:閻建章早跑了!敵人施盡各種辦法,折騰了一整天,也沒有把他抓到。
“文革”期間,閻建章被打成“走資派”。全家人受到牽累。造反派連續一年多不給他家分口糧分柴草,老伴氣不過,到大隊說理:“閻建章‘走資’,我和孩子不‘走資’,為啥沒有俺們的糧?”結果,不但沒要到一粒糧,頭被打成了腦震蕩。 1972年年關將近,缺吃的少燒的,一家人愁眉不展。一天夜里,忽聽屋外有聲響,出去一看,院里竟飛進了大包小包的豬肉和白面……像這樣的事,發生過好多次。有時,早上一開門,門口堆滿了柴草。至今,閻建章也不知這些都是誰送的。
想起這些往事,閻建章總是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靜。他常常這樣對人說:“從抗戰到現在,老百姓豁出命來保護咱,圖個啥?不就是看咱是個姓共的,指望咱帶著大伙過上好日子?共產黨幾十年前赴后繼又是為的啥?還不是想讓大伙都富起來?依我看,共產的目的就是共富,共產黨員要永遠姓共。我寧愿一輩子吃苦受累,也要使辛興人過上好日子。”
閻建章這些樸素的語言和執著的信念,道出了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更喊出了一個老黨員對黨、對人民的全部忠誠。
閻建章在精神上是一個富有者。他曾榮獲“全國勞模”“全國優秀共產黨員”“優秀農民企業家”等光榮稱號。但在成績面前,他卻不是裹足不前的人。他說:“不能當上萬元戶、幾十萬元戶就心滿意足了,還要看到周圍還有很多沒有富起來的群眾。”近幾年,他曾出巨資幫助貧困地區建立工廠;也曾親自出馬,帶著本村優秀的技術人員和管理干部到外地傳播致富經驗。辛興的工廠,每年能容納5000多名就業者,他總是優先接收省內外貧困地區的年輕人,因此每年給這些地區帶來上千萬元的勞務收入。
他說:“說心里話,俺已是60好幾的人了,有時真想過幾天清閑日子,可是,撂下群眾交給咱的擔子,心里不踏實啊!”
這就是閻建章向黨和人民捧出的一顆赤子之心。用他自己的話說:“我這顆心是黨和人民給的,敵人的刺刀例不去,‘四人幫’的棍棒打不碎,金子銀子買不走。”正是因為這,閻建章在群眾中的凝聚力和號召力從來不減,大伙服他、敬他、知他、愛他。
在辛興,誰也不懷疑共產黨的先進性,誰也不懷疑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因為他們看到了: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建設時期,領導他們翻身求解放、奔富路的,都是他們的老支書,都是一批優秀的共產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