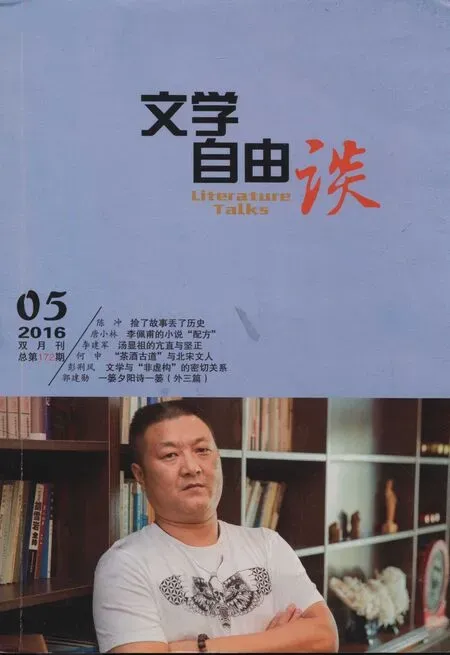李佩甫的小說“配方”
□唐小林
李佩甫的小說“配方”
□唐小林
在未獲得“茅獎”之前,李佩甫在當(dāng)代文壇,也算得上是一位頗有影響的當(dāng)紅作家,但盡管如此,我卻從未讀過他的任何只言片語。我對李佩甫的認(rèn)知,完全來自于媒體的高度贊揚和圈內(nèi)的如潮好評,如有學(xué)者高度贊揚他的《羊的門》:“是一部改變了五十年來中國鄉(xiāng)農(nóng)文學(xué)面貌的作品,一部前所未有地演繹和再現(xiàn)了特定時代風(fēng)貌和特質(zhì)的作品,一部對于當(dāng)代中國史有著社會百科全書意義的作品。”面對這樣驚人的評價,好長一段時間,我都在為沒有讀過李佩甫如此優(yōu)秀的小說而自責(zé)和感到遺憾;我總是擔(dān)心,因為我狹窄的閱讀視野,錯過了我們這個時代一位優(yōu)秀的作家。當(dāng)李佩甫的長篇小說《生命冊》獲得“茅獎”之后,我立即買來了此書,以彌補我曾經(jīng)的“過失”。但讀完這部鮮花云集、滿身光環(huán)的小說,我卻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難道是我的文學(xué)鑒賞和審美眼光出了問題?眾多的專家和學(xué)者都盛贊李佩甫,作為鄉(xiāng)土敘事的卓有成就的實力派作家,其《生命冊》有著厚實的根基,濃郁的鄉(xiāng)土氣息,語言硬實,具有不可低估的分量;而何以我的鑒賞和理解能力,卻完全跟不上專家們的腳步,怎么也看不出這部獲得“茅獎”的小說究竟“經(jīng)典”在何處?
2016年這個炎熱的夏天,我決心要為心中的疑問找到一個能夠說服自己的答案,給自己一個確切的交代。我在深圳火爐般的酷暑中,用了大量的時間,讀完了李佩甫被書商和文學(xué)批評家們稱為“經(jīng)典”的多部長篇小說和主要中短篇小說,從而獲得了冰窟般的“涼爽”感受——我清晰地看到了一個當(dāng)代作家是怎樣自我復(fù)制,追尋著一條工業(yè)化生產(chǎn)的寫作之路的。如:
他(某省委副書記)說:“我一生曾遭遇過六個女人,這六個女人是各有千秋哇。頭一個女人,讓我懂得了眉毛。從她那里,我才知道人的眉毛是干什么用的。眉毛這東西,可不光是眼的簾子,它的妙用主要在性上,眉毛其實是一種性器官,它就跟花的蕊一樣,是性欲的外在反應(yīng)。你如果稍加注意的話,你就會發(fā)現(xiàn),人的眉毛是千姿百態(tài)的。眉毛的形態(tài)跟人的性形態(tài)是一致的。尤其是女人。女人的外‘好’看臉蛋,女人的內(nèi)‘好’看眉毛。別笑。女人媚在眉上,柔也在眉上,蕩也在眉上,寡也在眉上。床上功夫好不好一看眉就知道了。……凡是結(jié)過婚的女人,有過第一夜之后,她的變化首先反映在眉毛上。”(《羊的門》)
鄒志剛悄悄對她說:“看他們在那兒胡吹,我也就湊個數(shù)。說實話,關(guān)于說她有男朋友,我是從眉毛上看出的。眉毛就像花蕊一樣,是人的生理器官,也可以說是性器官。年輕女孩,只要跟人發(fā)生過性關(guān)系,她的生理就會發(fā)生變化,眉毛也跟著必定會發(fā)生變化……”(《等等靈魂》)
誠如法國文學(xué)批評家納塔麗·薩羅特所說:“自從 《歐也妮·葛朗臺》全盛時期以來,同樣的內(nèi)容像過分咀嚼以后的食物一樣,對讀者來說,已變得糊爛如糜而且淡而無味了。運用這樣的材料所塑造的客體,在今天看來,已顯得是像那逼真模擬的畫幅一樣,看上去是立體的,事實上是平面的。”李佩甫的小說,恰恰正是“看上去是立體的,事實上是平面的”。其小說中的許多人物,都像是被作者任意操縱的提線木偶,缺少血肉和靈魂。只要將這些小說做一比較,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李佩甫就像是開設(shè)了一個“小說作坊”,這些小說的主料,一律都是書寫欲望的膨脹,其“配方”無非官場文學(xué)(臉厚皮黑+勾心斗角)、商場文學(xué)(明爭暗斗+你死我活)、情場文學(xué)(臍下三寸+權(quán)錢交易)這類市場上司空見慣的工業(yè)組裝品,無怪乎《羊的門》和《城的燈》在再版時,分別被改成商業(yè)氣息非常濃厚的《通天人物》和《上流人物》這樣的名字。這兩部小說和李佩甫的《生命冊》一起,被稱作“平原三部曲”。但無論是“平原三部曲”也好,還是《等等靈魂》、《金屋》和《李氏家族》也好,這些長篇小說萬變不離其宗,講述的都是農(nóng)村人如何擺脫農(nóng)村和貧瘠的土地、欲望膨脹、寡廉鮮恥、拼命攀爬、損人利己的故事,框架都大體相似,人物更是有著高度的重復(fù)性。
李佩甫的小說動輒喜歡拿有生理缺陷的人來說事,殘疾人往往多如牛毛。《生命冊》中的男主人公駱國棟,因為天生就是一個“羅鍋”,所以被人們稱為“駱駝”,女主人公蟲嫂天生就是一個侏儒;《城的燈》中的主人公馮家昌,十二歲那年,母親因病不幸去世,其從外鄉(xiāng)入贅而來的父親,因為拉扯著五個幼小的孩子,沒過多久就貧病交加,成了一個羅鍋;《金屋》中,小時候窮得長年沒有褲子穿的楊如意,其繼父也是一個羅鍋;《羊的門》中,運來的父親德順,同樣因為積勞成疾,變成了羅鍋;《春滿荷花》中的老搬運工,居然也是一個羅鍋……
除了羅鍋扎堆之外,還有一些被描寫成歪瓜裂棗的殘疾人。《紅螞蚱綠螞蚱》中的舅舅是一個瞎子;《城的燈》中的女主人公劉漢香的父親劉國豆?jié)M臉都是麻子;《麻雀在開會》中的表姐一歲多喪父母,幼兒時因發(fā)高燒成了“聾子”;《黑蜻蜓》中的二姐,照樣是一歲沒爹,兩歲沒娘,三歲發(fā)燒,燒成了聾子;《寂寞許由》中的“五爺”是麻子,“老三”不僅是個瘸子,而且走路就像劃船一般,一悠一飄的;《羊的門》中帶領(lǐng)當(dāng)?shù)厝嗽旒儇溂俚牟滔壬切r候爬樹摔下來成了瘸子的;蟲嫂的丈夫老拐,也是一個瘸子,在和蟲嫂做愛時很不給力;《生命冊》中的老光棍,年輕時就成了獨眼龍……
說臟話的人也出奇的多——李佩甫筆下的中原地區(qū),仿佛就是一個臟話的世界。不管在什么時間,什么地點,人們一張嘴,出口就是臟話,不僅是村支書,甚至連市長對自己的下屬講話也照樣是滿嘴污言穢語:“薛市長一拍桌子,黑著臉說:‘我告訴你們,誰影響招商引資,我撤他的職!也別給我這這那那、長毛短,就現(xiàn)在,現(xiàn)場辦公!……’”“薛市長臉一沉:‘你慌個,又不是割你肉?你聽我說。你聽清楚再說。我說的是借!只借一天。’”至于農(nóng)民說話,簡直是須臾都離不開臟話,仿佛不說臟話,他們就不會說話。可以說,“”字已經(jīng)成了李佩甫小說中人物的口頭禪和標(biāo)志性語言。
在李佩甫筆下,村民們似乎把偷當(dāng)成了一種職業(yè),張三偷李四,李四偷王五,王五偷趙七,趙七偷黃八。農(nóng)民為了防止家里的豬被偷,一律都是在豬圈里守著豬睡覺;蟲嫂見什么就偷什么,一畝地的西瓜被她幾乎偷去了一小半,而且在偷竊被抓時,居然公開拿性來和抓住自己的老光棍做交易。而就是在這偷盜成風(fēng)的村莊中,卻不斷上演著一部又一部咸魚翻身、烏鴉變鳳凰的神奇故事。
這些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幾乎套用的都是董永遇到七仙女的故事模式:窮得喝西北風(fēng)的農(nóng)村男青年,一律都是學(xué)習(xí)的天才,個個都會交上桃花運,遇到一個心儀自己的當(dāng)官的女兒;這些當(dāng)官的女兒,一股腦都像是腦子進水一樣,必定都會莫名其妙、死心塌地地愛上他們,并且毅然地將自己的身體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他們,從而使他們在時代的大潮中,上演出一幕幕驚人的大戲。
然而,這一幕幕的大戲,卻讓我在觀看之時常常忍不住“笑場”。在當(dāng)代作家的小說中,我很少能接二連三地看到如此之多低估讀者智商的故事。在《城的燈》中,羅鍋來順年輕時就失去了妻子,一個人含辛茹苦地拉扯著五個年幼無知的孩子。其中最大的兒子馮家昌,成為了家中唯一識字的人。馮家昌十二歲的時候死了母親,如此貧困的家庭環(huán)境,根本就沒有上學(xué)的條件,他卻在沒有上過幾天學(xué)的情況下,居然成了一個學(xué)霸,不僅以優(yōu)異的成績考上了鎮(zhèn)上的中學(xué),而且還贏得了村支書劉國豆的女兒劉漢香的芳心。不久,馮家昌就將劉漢香生米煮成了熟飯,使本來看不起他的劉國豆顏面盡失,而劉漢香就像是吃錯了藥一樣,愛他愛得死心塌地,十條牯牛也拉不回頭。劉國豆只得退而求其次,想辦法將馮家昌送進部隊,希望他能夠在部隊立功受獎,將女兒帶到部隊。到了部隊后,馮家昌成為了一名令人羨慕的文職人員,并被首長的侄女李冬冬一見鐘情。
我不知道,李佩甫究竟憑了什么魔法,使人相信接下來的情節(jié)不是天方夜譚?李冬冬的母親是一位醫(yī)生,父親是一位市長。馮家昌在部隊八年沒有回家探過一次親,而李冬冬的父母居然在絲毫都不了解他的家庭狀況的情況下,就稀里糊涂地將寶貝女兒嫁給了馮家昌。這種不合常理的事情,在李佩甫的小說中,卻成了一再出現(xiàn)的“常態(tài)”。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馮家昌的遙控指揮下,馮家的幾個兄弟仿佛個個都有一顆“最強大腦”,盡管從來就沒有上過幾天學(xué),居然都能夠無師自通,最終成為國家的棟梁之才。老三馮家運,通過馮家昌的關(guān)系來到部隊當(dāng)兵,在新疆一個荒無人煙的哨所,憑著馮家昌帶來的一些書,從ABC開始學(xué)起,不久就考上了陸軍學(xué)院,并以優(yōu)異的成績獲得碩士學(xué)位。多年以后,馮家昌成了副廳級干部,老二馮家興成了地級市的公安局長,老三馮家運成了駐外武官,老五馮家福成了一家民營公司的董事長,資產(chǎn)過億。而劉漢香一直居住在馮家,八年未與馮家昌見過面,馮家昌升為團級干部前也從未給她寄過一分半文——我不知道,劉漢香及其家人的智商是否正常?據(jù)我所知,部隊一年至少有一次探親假,馮家昌八年不回家,別說是“守活寡”的劉漢香及其父母,就連部隊首長和戰(zhàn)友,也必然會懷疑這其中一定有問題,更不要說李冬冬的市長父親了。
再來看《生命冊》中的另一則“天方夜譚”。蟲嫂作為一個侏儒,在村里的名聲壞到了極點,卻為殘疾的老拐生下了大國、二國和三花三個孩子。大國不愛讀書,十歲多的時候,就爬上火車,一跑就是三天,說是要去烏魯木齊,結(jié)果被警察給扣住了。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太陽卻從西邊出來了,大國突然愛上了讀書,考上師范,還被一位女同學(xué)莫名其妙地愛上了。這位女同學(xué)的父親是縣教育局的一名副局長。就像《城的燈》里的馮家昌一樣,大國結(jié)婚,同樣沒有告訴家里人。而作為教育局副局長的老岳父,怎么同樣是對女婿及其家庭情況不聞不問?之后,二國和三花也都考上了大學(xué),成了村里人無不夸獎和羨慕的一家人。
運用這套寫作模式,李佩甫制作出了許多來料加工、如出一轍的面孔。在《羊的門》中,馮家昌因為家里窮,買不起作業(yè)本,作業(yè)本全是煙盒做的。而《敗節(jié)草》里的李金魁,同樣是因為窮,在六年的時間里,用掉了一萬八千多張煙盒紙。和馮家昌和大國一樣,有結(jié)巴毛病的李金魁,同樣是“理所當(dāng)然”地交上了桃花運,遇到了暗中愛上自己的李紅葉。李紅葉不僅人長得漂亮,而且還有一個當(dāng)校長的父親——在李佩甫的小說中,似乎所有當(dāng)官的女兒都像三伏天快死的魚,生怕沒人要——為了能夠贏得李金魁的“愛情”,李紅葉甚至不惜為他脫掉褲子,把整個身子都趕緊交給了他。在徹底征服李紅葉之后,李金魁進一步時來運轉(zhuǎn)。李紅葉的父親升遷為市領(lǐng)導(dǎo),李紅葉利用父親的關(guān)系,親自將一張上大學(xué)的推薦表送到了正在廢品收購站靠撿垃圾為生的李金魁的手中,而大學(xué)畢業(yè)后的李金魁,居然從副鄉(xiāng)長一路做到市長。《無邊無際的早餐》中的治國,平時成績也不怎么樣,但中考時,大李莊小學(xué)有六十四個學(xué)生參加了考試,卻只有治國一個人考上。之后因為讀書,治國的人生一路綠燈,從鄉(xiāng)里調(diào)到縣里,并經(jīng)由縣委書記親自做媒,和一位副市級干部的女兒結(jié)了婚,最終攀上了縣長的位置。
在當(dāng)代文壇,自我復(fù)制的作家,可說是不少,但像李佩甫這樣毫不掩飾地自我復(fù)制、不少作品近乎雷同的作家,即便是在古今中外的文壇上,恐怕都不多見。吊詭的是,李佩甫卻煞有介事地宣稱:“我從上世紀(jì)70年代開始寫作,至今寫了38年,總共寫了10部長篇。從80年代以后,我就找到了自己的寫作領(lǐng)地,無論是《羊的門》、《城的燈》還是《生命冊》,都是一個共同的主題:土地和植物的對話。”在我看來,如果真要說李佩甫找到了什么“自己的寫作領(lǐng)地”的話,這個“領(lǐng)地”的名字就叫做:不斷重復(fù)自己。
在李佩甫的小說中,只要寫到農(nóng)民的野心和炫耀自己,必定是建一座令人人都羨慕不已的大房子。《生命冊》里的蔡葦香,在城市里做小姐,后來成為一家板材公司的老總,發(fā)達(dá)之后回到村里,僅用十幾天時間便蓋起一座三層小樓,而且里外都貼了瓷片,讓全村人羨慕不已。《金屋》里的楊如意,從小失去父親,之后又失去母親,靠跟著羅鍋繼父來順艱難度日,外出幾年后,居然成為了一家涂料廠的老板,回到村里建起了一座二十四間的現(xiàn)代化小洋樓。《等等靈魂》中的暴發(fā)戶商人任秋風(fēng),居然大腦膨脹,發(fā)誓要在中原建造世界第一高樓。
《寂寞許由》中的老郭,討好市長,用新鮮的嬰兒胎盤烘干,給市長配了一味藥。在《羊的門》中,李佩甫又將這個“橋段”進一步升級和改裝,就成了給公社書記當(dāng)通訊員的王華欣,為了討好書記,天天晚上主動給書記提夜壺;為了巴結(jié)院長,就到刑場上去挖活人腦子,用來治院長孩子的病;為了進一步得到提升,利用老婆在醫(yī)院產(chǎn)科的工作之便,將烘干的“嬰兒胎盤”當(dāng)作大補品送給領(lǐng)導(dǎo)。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李佩甫采用了一種快餐制作的生產(chǎn)模式,無論是故事的結(jié)構(gòu),還是人物的設(shè)置,以及情節(jié)的展開,幾乎都如同一個模具里澆注成型的工業(yè)產(chǎn)品,沒有什么區(qū)別。
李佩甫小說中的許多人物,都是苦水里出生,從小就死了父母,靠吃百家奶長大的。這些靠鄉(xiāng)村婦女的奶水辛勤養(yǎng)大的人,非但不知道感恩,反而從小就知道怎樣調(diào)戲和意淫這些辛勤養(yǎng)育自己的鄉(xiāng)村婦女。《無邊無際的早晨》中的治國,在襁褓中,娘就因病去世,七天之后,他的爹又在挖煤時被砸死在井下,從此成了吃百家奶的孩子。多年以后,他對人吹噓說,他摸過一百多個女人的奶子,并常常回憶起吃奶時的情景。那些裸露著的鄉(xiāng)下女人的奶子,經(jīng)過他想象的渲染,一個個肥滿豐腴地出現(xiàn)在他的眼前。《金屋》里的來來,母親生他時,在床上折騰了七天,也是由他的父親抱著,一家一家求奶吃。《生命冊》中的吳志鵬,從小就失去了父母,同樣也是吃百家奶長大的,他居然還無恥地炫耀說:“在我的記憶里,無梁女人高大無比,屁股肥厚圓潤,活色生香。……站在石磙上碾篾子的女人,屁股都是緊繃著的,就像是一匹匹行進中的戰(zhàn)馬,一張張彈棉花的張弓,捏一下軟中帶硬、極富彈性,回彈時竟有絲竹之聲。那時候,在初升太陽的陽光下,我會沿著村街一路捏下去,捏得女人哇哇亂叫‘吃涼粉兒’。我也承認(rèn),我還曾經(jīng)摸過無梁大多數(shù)女人的乳房。在這個世界上,毫不夸張地說,我是見識乳房最多的男人。”接下來,他還逐一點評著國勝家女人、紫成家女人、寶祥家女人、三畫家女人、海林家女人、印家女人、水橋家女人、麥勤家女人、大原嫂子、寬家女人的乳房,并稱:“女人跟女人是不一樣的。”看到這樣的描寫,我就可以肯定李佩甫是一個缺乏科學(xué)常識的人。請問,這個世界上,誰能記起自己小時候吃奶的情景?科學(xué)告訴我們,一個人的記憶是從三歲以后才開始形成的。一個襁褓中的嬰兒,居然能夠分清誰的奶子像歪把茄子,誰的乳頭潤著一片麻點點……這樣缺乏常識的描寫,如何能讓讀者信服。
事實上,在李佩甫不經(jīng)意的寫作中,已經(jīng)暴露出了其方方面面知識的欠缺。如:“上海人說話儂來儂去,辦事小里小氣。他們尤其對上海人印象不好。上海人不是斤斤計較,簡直是兩兩計較……”(《等等靈魂》)“你想,做的是小買賣,本太小,利太薄,自然是‘兩兩計較’了。”(《羊的門》)漢語成語“斤斤計較”里的“斤斤”,出自《詩經(jīng)·周頌·執(zhí)競》:“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它指的是明察、看得清,引申為苛細(xì)、瑣屑。除此之外,漢語成語還有“斤斤較量”,同樣是指在瑣細(xì)的事情上過于計較。這里的“斤斤”,與表示重量的單位沒有絲毫關(guān)系。《城的燈》中的老二馮家運,僅僅讀了六年軍校,拿到一個碩士文憑,一出校門就被破格授予少校軍銜,作為代表著一個國家的武官,成了住南美國家的一個使節(jié)。李佩甫對我國駐外武官的要求,可說是連基本常識都不求甚解。我國的駐外武官,是由中央軍委責(zé)成總參外事局,從全軍優(yōu)秀現(xiàn)役軍官中選拔出來的,一般都是上校甚至少將以上的軍銜,哪里會將一個不符合基本條件的馮家運派駐到南美代表國家?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等等靈魂》中,一睡覺就打呼嚕的任秋風(fēng),入伍后干的是偵察兵,并且參加過對越自衛(wèi)反擊戰(zhàn)。在我看來,部隊的首長也是夠粗心的,他們怎么會將一個睡覺打呼嚕的人安排去搞偵察?《金屋》中的獨根四歲,哥哥五歲,姐姐六歲。哥哥在坑塘邊洗豆芽,不小心滑進塘里,一群小孩,只有獨根的姐姐慌忙去拉,結(jié)果被哥哥死死抓住,一起沉到了水中。待小孩們回家告訴大人,來到坑塘?xí)r,姐弟倆的尸體已經(jīng)白脹脹地在水面漂著,姐姐的小手還死死勾住弟弟的手。李佩甫并不知道,人被淹死之后,是不可能立即就浮起來的。人在淹死停止呼吸之后,由于體內(nèi)的密度大約和水的相等,所以尸體就會沉入水底。隨著尸體逐漸產(chǎn)生越來越多的腐敗氣體,才會浮出水面,這個過程通常要三天以上。
文學(xué)批評家們痛感當(dāng)今某些作家只講高產(chǎn),不講質(zhì)量。李佩甫也算得上高產(chǎn),但這樣的高產(chǎn),往往都是一種為了寫作而寫作的文字堆積。尤其令我感到吃驚的是,他的長篇小說《李氏家族》完全就是由其過去的幾個中短篇小說改寫、拼湊、混搭而成的一部所謂的“新作”。為了吸引讀者的眼球,在李佩甫的小說中,各種與性有關(guān)的段子和噱頭就像走馬燈一樣,不斷出現(xiàn)。《李氏家族》中的嬴,陽物大得出奇,他甚至將自己的陽物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甩一甩地在村里走。每當(dāng)嬴從街上走過,連母羊也開始發(fā)情,跟在他的后邊。他拋棄了跟他逃過難的女人,強行霸占了漂亮的堂姑。嬴走到哪里,就讓堂姑跟到哪里,像公狼和母狼一樣隨處交歡。于是,村里成了亂倫的世界,哥哥與妹妹,叔子與嫂子,母親和兒子,人人都像畜生一樣。被嬴拋棄的女人卻誓死都要復(fù)仇,終于有一天,她跟蹤到了嬴,懷著滿腔的仇恨,比母狼還要兇狠地將嬴拽到了茅屋里,將嬴的陽物血淋淋地割了下來,嬴最終慘死。然而,這個女人卻不僅將其陽物珍藏起來,而且每到嬴的祭日,還會將珍藏的陽物請出來,擺在供桌前恭恭敬敬地磕頭,似乎是有了這個陽物,她就有了精神支柱。看了這樣的描寫,我們不得不說,當(dāng)今的作家在性描寫方面,實在是太有才了,即便是蘭陵笑笑生再世,也會自嘆不如。
李佩甫的《等等靈魂》被出版商飆捧為“傳世經(jīng)典”,并宣稱讀這樣融合了豐富系統(tǒng)人文知識的小說,會讓讀者充滿閱讀的樂趣,成為汲取知識的智慧之旅。但我在拜讀了這部長篇小說之后,非但沒有汲取到知識的智慧,反而看到了一部草率之作是如何的漏洞百出。小說的主人公任秋風(fēng),就像《城的燈》里的馮家昌一樣,在部隊十二年,就從一個士兵干到了副團職。他的妻子在他轉(zhuǎn)業(yè)回家的當(dāng)天,與商場老板鄒志剛發(fā)生了婚外情——她這樣一位頭腦聰明、有頭有臉的報社首席記者,十二年漫長的日子都等了,卻何以非得要在丈夫回家的這一天出軌不可?任秋風(fēng)在部隊這么多年,從來就沒有干過任何一件與商業(yè)有關(guān)的事情,市領(lǐng)導(dǎo)就敢把一個大型商場交給他管理,而他也一夜之間就成了一位商業(yè)奇才;更為蹊蹺的是,三位商學(xué)院畢業(yè)的女大學(xué)生竟然莫名其妙、心甘情愿地到他那八字都還沒有一撇的商場來工作,甚至站柜臺。任秋風(fēng)憑著我們常在報刊雜志上看到的那些并不高明的商戰(zhàn)故事,就成為了聞名中原乃至全國的商業(yè)巨頭——如此小兒科的商戰(zhàn)小說,幾乎就是弱智的代名詞。我們看到,《等等靈魂》中的任秋風(fēng),就像《生命冊》中的羅鍋駱國棟一樣,雖然從未經(jīng)過商,卻是經(jīng)商的天才,手里動輒控制著多少個億的資金,且生錢的速度簡直超過了印鈔機,乃至人人都對他們崇拜得五體投地。尤其是那些年輕漂亮的女人們,更是爭先恐后,個個都恨不得以身相許。出生在條件優(yōu)越、很有教養(yǎng)的家庭的上官云霓,在明知道任秋風(fēng)還沒有離婚的情況下,就主動投懷送抱,挑逗勾引。小說中寫道:“這一刻,在上官,是沒有羞恥感的,她心中升起的是一種圣潔。”我不知道,上官云霓究竟被什么邪教洗了腦,簡直不知道世界上有羞恥二字,居然把寡廉鮮恥當(dāng)成了圣潔。在李佩甫的筆下,那些成功的男人就像種豬配種一樣,隨時都可以不分時間、地點地發(fā)情。難怪李佩甫的小說中聽起來最爽,且屢屢出現(xiàn)的一個字,就是男人對女人的一聲令下:脫!
更抓人眼球的是,長篇小說《羊的門》中,在呼風(fēng)喚雨的通天人物呼天成六十大壽時,村子里清純美麗的小雪兒代表母親前來祝壽:“我媽說,今天是您的生日,是您的六十大壽,讓我給您送禮來了。”這份大禮,就是少女寶貴的貞操。總之,把寶貴的身體送給那些所謂成功的男人,幾乎成了李佩甫小說中所有女人的夢想。難怪小說中議論說,什么叫做“獻身”?這才是“獻身”哪!我想請教李佩甫的是,世界上有什么樣的大恩大德,永永遠(yuǎn)遠(yuǎn)都報答不完,用盡了母親的身體,還要讓女兒心甘情愿地用貞操來償還?如果真有這樣的母親,那簡直就是禽獸不如。
因為構(gòu)思粗疏,寫作倉促,李佩甫的小說常常丟三忘四,總是犯迷糊,呈現(xiàn)出一種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的敘述。我國法定的征兵年齡,應(yīng)該是年滿18歲的青年。《等等靈魂》中的任秋風(fēng),并非有什么特長,卻在16歲就入了伍。16歲當(dāng)兵,在部隊十二年,1990年轉(zhuǎn)業(yè),這說明他轉(zhuǎn)業(yè)時的實際年齡只能是28歲。任秋風(fēng)轉(zhuǎn)業(yè)后,李佩甫寫道:“轉(zhuǎn)眼近二十年過去了,他仍然還記得齊康明的發(fā)問……是啊,他已過了而立之年。”28歲怎么就已經(jīng)過了而立之年?當(dāng)兵十二年,怎么就成了將近二十年?這中間幾年的“虧空”怎么填補?又如,在《學(xué)習(xí)微笑》中,馬科長等人晚上九點鐘到卡拉OK廳K歌,一直唱到凌晨兩點半,歌已唱到了374首——請李佩甫掰著指頭認(rèn)真算一算,九點到凌晨兩點半,一共是多少個小時?以一首歌平均三分鐘計算,而且K歌的人一秒鐘也不要停頓,五個半小時最多能唱多少首歌?這樣簡單的加減法,李佩甫在寫作時難道只是為了趕速度,就沒有一點耐心去仔細(xì)算一算嗎?由此,我們還能相信,他的創(chuàng)作有什么真正的思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