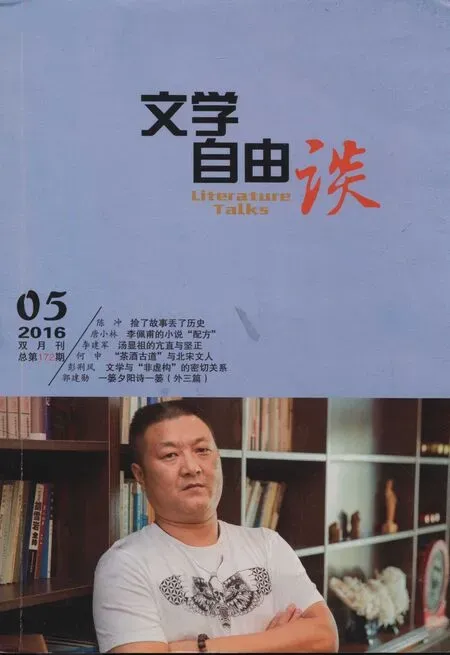《陳忠實傳》:忠于歷史,實于作家
□陳紅星
《陳忠實傳》:忠于歷史,實于作家
□陳紅星
2016年4月29日,作家陳忠實先生逝世,官民同悼,哀榮備至。在這一文化事件下,與陳忠實及其作品有關的話題再次成為廣大讀者關注的熱點,而邢小利所著《陳忠實傳》(陜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版)一書自然引起讀者的濃厚興趣。
通過對《陳忠實傳》的認真研讀,我深切感覺到這確實是一部忠于歷史、實于作家、評傳結合且頗有理論建樹的作品,是研究陳忠實及其文學世界必不可少的重要學術著作。這部作品不僅從生平方面讓讀者對陳忠實的人生有了更多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在陳忠實研究的一些微觀和宏觀認識問題上,提出了一些具有撥云見日和猶如四兩拔千斤作用的重要觀點,從而廓清了長期以來的一些模糊認識。
《陳忠實傳》體現了作者對于與陳忠實有關的人、事、物的嚴謹求實的精神,體現了傳記作品的嚴肅性和作家本人的史家態度。如陳姓祖先遷徙蔣村的時間、蔣村村名的來歷、陳忠實上初中時的助學金數額、陳忠實和柳青的三次見面、《無畏》的創作過程、陳忠實的個人藏書、《白鹿原》出版后正反兩方面的評價等,作者通過對這些史實的鉤沉,為讀者提供了關于陳忠實研究的相對可信的資料;對一些尚不能確定的問題,也注明是聊備一說。這樣的嚴謹態度和真實性,增加了《陳忠實傳》的權威性。
真實性方面的另一個體現,是作者刻畫了真實可信的陳忠實本人形象。如陳忠實關于在“文革”中受毛主席接見的紀念文章、請《北京文學》編輯部的編輯劉恒吃羊肉泡饃、撰寫《白鹿原》書訊的過程、對國家關于城鄉政策的區別問題的看法、談對官員上下臺的感受、“不愿意這樣大過生日”的態度等,這些細節進一步豐富了讀者對于陳忠實的認識,為讀者還原了有血有肉的傳主形象。可以看出,作者對陳忠實采取了平視的觀照視角,這就避免了將其神秘化和神圣化。
對傳記作品,讀者更為關心的是它的邏輯性,即:在涉及人生的重要節點時,哪些人、事、物對傳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些節點之間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這樣,一部傳記作品才呈現為有機的統一體,而不是毫無關系的事實羅列,讀者也才能夠更好地理解傳主的人生軌跡和發展邏輯,從中獲得有益的啟迪和思考。
《陳忠實傳》很好地滿足了這些期待。比如,讓陳忠實產生寫小說念頭的趙樹理,讓他產生強烈好奇心的神童作家劉紹棠,讓他“把截斷了六年的那根文學神經接通了,干涸了六年的那根文學神經也潤澤了,變得有些僵硬的思維也柔軟了,靈活了”的《西安日報》的張月庚,將他的散文《水庫情深》推薦給《陜西文藝》的徐劍銘,在他倍感壓力和困難的時候幫他解困的崔道怡,向《人民文學》推薦《信任》的王汶石,鼓勵和支持他的杜鵬程,以《人生》獲獎從而刺激了他的路遙,從“今年再拿不出來,你就從這七樓跳下去”到“咋讓咱把事給弄成了”的評論家李星,高度評價《白鹿原》的何啟治等等。可以說,陳忠實的成長、成熟和成功,與他生命中出現的這么多文學好心人密不可分。
在傳記的認識性上,《陳忠實傳》最大的亮點和意義在于幫助讀者更深入地理解了陳忠實及其文學世界,廓清了讀者及研究者長期以來所形成的一些模糊認識。這些認識可分為兩個層面:一是微觀層面,二是宏觀層面。
先說微觀層面。《陳忠實傳》對一些敏感話題做了嚴肅的探討。如陳忠實對女性的態度問題——由于早年目睹了一位男教師因為男女關系問題所導致的嚴重后果,陳忠實終生與女性保持著一定的距離,這甚至影響到其作品中人物的性別比例。在《陳忠實傳》中,作者沒有做庸俗化的隱私“揭秘”,而是從創作層面去追根溯源:“縱觀陳忠實的人物塑造,總體上看,寫男性多,寫女性少。即使是他的代表作《白鹿原》這樣一部描寫一方地域50年歷史風云和生活變遷的巨著,也是群雄競出,而只有寥寥數個女性。此種葉繁花稀的創作性別偏差,顯然與創作主體的生活經驗特別是深層的生命體驗與文化心理有關。”這體現了作者認識問題、研究問題的學術高度。再如陳忠實對創作中的政治問題的認識,書中提到了2008年10月陳忠實在寧夏大學的談話:“要把真正的政治和極‘左’政治區分開,不能用給人造成極大傷害的極‘左’政治來概括所有政治,同時排斥所有政治,不能因噎廢食。作家感受生活,完成生活體驗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思想,作家的思想也可以看成作家的政治……”我以為,這種對政治具有正本清源作用的觀點,才是作家應有的認識。
對陳忠實閱讀古典詩詞的原因,《陳忠實傳》認為:“一直以來,陳忠實的閱讀,基本上是功利目的很明確的,那就是為了自己的寫作。他主要寫小說,偶寫散文,他的閱讀也就主要圍繞這么兩個方面。”而在《白鹿原》完成的前后,他卻將興趣轉移到了閱讀中國古典詩詞上面,而這其中,他讀詩賞詞的心情是不一樣的。在等待《白鹿原》書稿審讀意見的日子里,“此時他之讀詩詞,不是想讀,不是愛讀,完全是為緩解內心的焦慮,這樣的救心之法,想來不會真正進入詩詞的意境。”后來,他獲得了一連串的肯定意見,“他的心放下了,踏實了,心態也放松了,自由了,他才被古典詩詞之美打動了,被古典詩詞的萬千氣象和意境感染了,最后竟然沉湎其中了。”由此,他得出結論說:“要能閱讀古典詩詞,是需要一定的心境和處境的。也許,心境來自處境,處境影響心境。”陳忠實閱讀古典詩詞的例子證明,中國古典詩詞是被一定的心境孕育的,也能反過來孕育一定的心境。
陳忠實何以在50歲以后特別鐘愛散文?邢小利認為:“散文是一種貼近心靈的文體,比起小說能更直接更自由地抒發作家自己的生命感受與體驗。同時,散文是一個與創作主體自由而活躍的生命狀態關系密切的文體。陳忠實之迷戀散文,也顯示了他生命狀態的自由和活躍。”作者客觀地分析了陳忠實由小說轉向散文寫作的緣由,在不同生命階段散文創作的特點等,由此也可以看出,和閱讀中國古典詩詞一樣,作家的寫作也和人生的生命狀態有很大關系。
關于《白鹿原》的創作動機,我們固然可以從《人生》獲獎所產生的刺激、李星的激勵、陳忠實個人的藝術探索等方面來探討,但是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陳忠實從一位鄉村老漢的“太陽的升落”這個隱喻所領悟到的來自生命的壓力;正因為這樣一種壓力,他才需要創作一部“墊棺作枕”的作品。這是從形而上的高度認識了《白鹿原》創作的無形推動力,也是《白鹿原》創作最為根本的人生動力。這樣來理解陳忠實的創作動機,就和作家的人生價值追求這一根本問題緊密地聯系了起來,從而具有了人生論的意義。
在宏觀層面,《陳忠實傳》涉及到這樣一些問題:
一是故鄉對陳忠實的意義。邢小利指出:“陳忠實寫完一篇或一部作品,往往在文末綴上時間地點,地名喜歡用帶‘村’或‘莊’的字,感覺像在農村。這也反映了陳忠實濃厚的鄉村情結。”陳忠實將自己的工作室稱為“二府莊”,也包含一種“鄉村情結”。他人生的前五十年生活在鄉村,年近花甲時又回到了鄉村。他說:“在原下進入寫作,便進入我生命運動的最佳氣場。”這種氣場就是他所說的“老屋是一種心理蘊結”;在邢小利看來,這正是一種“給心理以力量的蘊蓄”。我認為,“心理蘊藉”是理解陳忠實與故鄉的關系的一個很關鍵的詞,它概括了故鄉對于陳忠實的文學意義。邢小利通過大量的事實證明,陳忠實在“摸上60歲的時候,復歸老屋祖居,一個人再住上兩年,仔細分析,除了逃避或者說躲開他屢次有意無意提出的‘齷齪’之外,還有更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在重新打量世事人事的同時,他也要重新打量自己,調整自己的心理”。這正是故鄉對于陳忠實的意義,它孕育和哺育了陳忠實的文學與人生。
二是關于陳忠實的人生價值取向問題。邢小利認為,雖然陳忠實“性格中無關于隱,甚至絲毫無關”,但是“如果仔細讀他復歸原下這一階段的散文,就會發現他居然步上了千百年來中國傳統文人走過的路子,歸去來兮,隱于鄉村”。這一點其實不難理解,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是千百年來中國文人的基本生存選擇,陳忠實也一時無法超越。邢小利分析說:陳忠實“出身貧寒的農家,從小受苦受難,一直在人生之路上奮斗掙扎,在文學之路上走得也不易”,期盼著有朝一日能浮出水面,放出光彩。“今天好不容易有了這個機會,有了今天的地位,怎么會輕言淡泊,又怎么會自我隱退且甘于寂寞呢?一直沒有的人怎么會輕言放棄呢?”這是理解陳忠實的人生價值取向的中的之語。另外,關于陳忠實的身份定位,邢小利認為:“從中國文化和精神的譜系上看,陳忠實就不屬于傳統意義上的文人,也不屬于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他的經歷,他所受的教育,以及由經歷和教育所形成的生活觀念和思想觀念,都更接近于中國農民的生活觀念和思想觀念。”這一點對于理解陳忠實的文學思想和個人定位非常重要,它廓清了長期以來讀者和研究者在這方面的模糊認識。
三是關于陳忠實在文學史中的位置問題。《陳忠實傳》認為:“在描寫社會的鄉村和自然的鄉村兩方面,魯迅和沈從文,雙水分流,各有側重,從而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一個側重于展現社會的鄉村,一個側重于描繪自然的鄉村的藝術流向。而陳忠實在承續展現社會的鄉村這一脈的同時,在藝術上不斷更新,也吸收和融入了現代小說的魔幻、心理分析等藝術表現手法,而他的《白鹿原》更是表現了文化的鄉村。”并評價說:“陳忠實是描寫農民生活、鄉村社會和文化的高手。”這是陳忠實對于鄉村創作所賦予的新內涵,也正是他的文學創作的意義之所在。
四是關于陳忠實研究的意義問題。《陳忠實傳》的最后一節,將陳忠實的精神進化比喻為由蛹變蝶:“聽命與隨順,反思與尋找,蛻變與完成,三級跳躍,陳忠實走過了從沒有自我到尋找自我最后完成并確立自我這樣一個過程,成為一個具有時代標志性和代表性的作家。”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也就明白了研究陳忠實的真正意義:陳忠實就是一個作家不斷超越自我、不斷實現創作新高度的縮影。
《陳忠實傳》以大量的人生及文學事實,為我們描述了陳忠實的漫長而艱難的文學人生,也為我們展示了中國當代文學所走過的漫長而艱難的歷程。邢小利舉重若輕,深入淺出,樸實真摯,娓娓道來,使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既感受到了仿佛身臨其境的陳忠實的舊日生活,也看到了作者邢小利個人的性情志趣。可以說,《陳忠實傳》既是一部忠于歷史、實于作家的嚴肅的學術著作,又是一部超凡脫俗、引人入勝的紀實作品。
當然,正如邢小利自己所言,“也有許多還沒有寫出來。……寫出來的,有重要的,也有不重要的;沒有寫的,卻還有很多我認為是重要的,甚至是特別重要的。”“這部書還有許多不足,這是我日后要盡力彌補的。”(邢小利:《我為什么寫陳忠實傳》,《光明日報》2016年5月6日)隨著中國社會歷史進程的不斷演進,對于陳忠實及其創作的研究則可以跳出其在世時的某些局限性,從而獲得一種更客觀更公允的認識和評價。這是續寫《陳忠實傳》的意義之所在,也是陳忠實的研究界和讀者所翹首以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