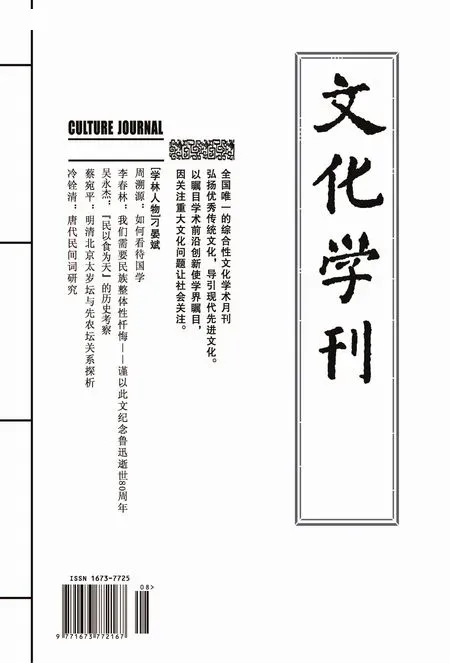《穆斯林的葬禮》中長女梁君璧形象透視
蘭奐錚
(河南大學,河南 開封 475001)
?
【文化藝術視野】
《穆斯林的葬禮》中長女梁君璧形象透視
蘭奐錚
(河南大學,河南開封475001)
《穆斯林的葬禮》深刻反映了中華民族傳統的道德倫理觀念與穆斯林宗教教義文化的撞擊中所迸發的心理結構對人性困頓與追求的領悟。在“家族長子”缺席的環境下,梁君璧踐行著長女的身份、責任和義務,犧牲自己寶貴的青春和夢寐以求的理想婚姻,以修身、持家、躬親仁悌的品性維系家族。梁君璧作為穆斯林的傳統女性,既成就了個體家庭的光輝,也造就了一串串令人扼腕嘆息的愛情悲劇。
《穆斯林的葬禮》;梁君璧;長女;信仰;存在感;女性
霍達以玉器梁家愛玉、守玉、護玉為線索,在《穆斯林的葬禮》中展現了時代大背景下一系列悲情的故事。小說著力透析特殊生活背景長女梁君璧的成長經歷,并揭示她處于重重矛盾下的畸形性格。在整部小說中,作者基于梁君璧特殊的“長女心理結構”,創作了一個生與死起承轉合、愛與恨縱橫交織、悲與喜巧妙交匯的情感故事。
一、長女文化心理
梁君璧本是一個溫柔、賢淑的長女,端茶倒水、洗衣做飯樣樣令人稱贊,但卻始終不能繼承父親的琢玉手藝。當梁爸爸因為玉器船操勞而死,梁君璧更是以威震須眉的氣勢勸說母親應對匯遠齋老板蒲壽昌的百般刁難:著手變賣家中值錢的財物還債,以賣大碗茶為生,用單薄的脊背撐起母女三人的清貧生活;全力幫助韓子奇重振奇珍齋,把玉器生意做得風生水起、有聲有色。與此同時,韓子奇與梁君璧這種只有責任意識而缺乏愛情的結合也是悲劇婚姻的開始。
信仰是人類心靈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類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雨果也認為信仰是人們所必需的,無信仰的人是不會幸福的。廣義的信仰涵蓋面廣,可以是對信念的追求,對理想的憧憬,對事業的執著,也可以是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的某些成分。[1]如韓子奇對玉的癡迷,韓新月與楚雁潮對翻譯事業的追求、鐘愛,以及梁冰玉對尋找自我的堅定、執著等。狹義的信仰主要偏重于宗教信仰,如梁君璧對宗教教義和族規的捍衛、堅守。由于她盲目固守,親手毀掉了自己的婚姻,因此也葬送了兒女的幸福,留下的只有對凄涼人生的哀嘆。
長女的文化心理結構促使她對于長期依賴自己的兒子天性有一種占有欲。這一戀子情結對個體行為來說,具有極大的制導力。它往往使人根據情結的指向選擇行為對象,抑制其他意識的活動。就像榮格所說:“不是人支配情結,而是情結支配著人。”[2]
作為封建家庭的傳統婦女,她身上有一種不服輸的勇氣,當年父親的突然離世以及生活的重擔突顯了她堅強不屈、精明能干的性格層面。面對抗戰爆發和韓子奇遠赴英國避難這一系列變故,她臨危不懼,一手撐起廢墟中的玉器生意,掌管一家老小的日常生活。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知識女性在社會的地位不斷提高,越來越受到社會的尊重,她越發感覺缺乏知識文化使她博雅齋的女主人地位受到了威脅。尤其是社會制度改變之后,大部分珍藏的玉器充公,一家人的生活起居全靠韓子奇的工資苦苦支撐。這在某種程度上損害了她的自尊心,她本是一個只手撐起全家生活的倔強女性,而如今,歲月的變更卻將她打磨成一位忙于瑣事、依附丈夫的中年婦女。尤其是新月時常在家中與韓子奇用英文對話,從側面更是激起了內心壓抑的憤怒和不滿,一種所謂的占有心理和存在心理推動著她要在新舊文明沖突之中不斷尋找存在感來鞏固博雅齋女主人的地位。
二、兒女婚姻的摧毀者
宗教信仰及門第觀念支配著梁君璧的處事方式,天星與容桂芳愛情悲劇便是其處事方式的產物。兩個年輕人的真誠相戀并沒有因此而產生婚姻,梁君璧有濃厚的門第觀念,致使她一向看不起做小生意買賣的切糕容家,便想方設法以天星的上海表妹為幌子,精心設計了連環套,使兩個年輕人產生誤會,造就了一段愛恨交織的悲劇。而面對新月的好朋友陳淑彥,梁君璧看中了她也是生于玉器家族,有一種門當戶對的觀念,之后抓住韓子奇愛女心切的心理,用天星隆重的婚禮作為新月上大學的條件。
從宗教信仰和宗教族規出發,她既要遵從內心的信念,找到一個出身穆斯林家庭的回族人,同時又要考慮門第、地位等因素,找一個家庭背景與韓家相匹配的兒媳婦。對于未來的兒媳,梁君璧既恐懼又高興。令她興奮的是,兒子“在外邊像個人兒似的,這讓當媽的高興”;但她又感覺到一絲凄涼:兒大不由娘,這么大的事兒,她要是不主動問,兒子都不對他說,一瞞就是半年,把媽擱到什么地方了呢?”[3]想到這里,梁君璧內心不由得有一股無名的悲傷和冷寂。
長期的戰爭造成韓子奇與梁君璧夫妻產生疏離,在潛意識中她感覺博雅齋女主人的地位受到了挑戰,故而她只能將希望寄托在兒子天星身上,并借助這股新生的力量來鞏固女主人的地位,但是,從心理學角度來講,她對兒子天星的愛是深沉的,她自知與韓子奇的婚姻岌岌可危,便以兒子婚禮與新月上大學進行交換,以此置辦在親朋好友眼中熱鬧豪華的婚禮;另一方面,長女心理結構下形成的獨立和多年來慣有的占有欲支配著她,使得她不惜犧牲兒子的幸福也要堅守內心的門第觀念,設計種種誤會,親手毀掉兒子天星與容桂芳的幸福。
在她心目中,倫理綱常與信仰大于親情。在人倫道德與血脈至親的抉擇間,她忠誠執著地固守著心中的那份信仰,卻又在現實生活中處處碰壁,屢屢失敗,所以,無論是對崇高信仰的執著,還是對其固守的宗教倫理的虔誠,當客觀現實與主觀思想意識發生激烈碰撞時,其悲劇便由此產生。
“服從是任何一個文化都崇尚的社會規范,但服從的極端負面影響之一便是會衍生出許多悲劇產生的土壤,伊斯蘭文化亦不例外”。[4]在新時代中成長的韓秋月,堅守心中對愛情的那份執著,認為“我們有權利生活,有權利愛”,不顧種族的規制與世間傳統的異樣眼光,與老師楚雁潮相戀,擦出愛情的火花。思想和情感成長的土壤和空氣,她耳濡目染,伊斯蘭教文化對她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回族血液給予她一種命中注定的悲劇性。鑒于回族與卡斐爾不得通婚的宗教族規,虔誠的穆斯林教徒梁君璧極力阻止二人交往。
盡管楚雁潮在愛情道路上不顧父母的反對,克服了諸多難題,但當梁君璧堅定地說明新月只能嫁給回族同胞時,他終于明白曾經的相知、理解、鼓勵和支持在宗教信仰面前也僅僅是過眼云煙。于新月的愛情而言,更為可怕的事情是這種教規已內化為自己“母親”的一種思維方式、處事原則,“我寧可看著你死了,也不能叫你給我丟人現眼”![5]這種近乎畸形的決絕,徹底抹殺了新月人生中的最后一點光亮,終帶著遺憾離世。相比之下,在新月身上,少了傳統的負累,多了更多現代文明的氣息,這是新一代穆斯林教徒的宗教信仰跟隨時代發展變化的印記,更是華夏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沖撞之下新生命孕育與發展的碩果。
三、結語
人物是一個建構過程,他將在矛盾中不斷地被否定和置換;自我的連續是一種神話,一個人就是一個原子,他不斷地分裂和重新組合。[6]梁君璧是一個在自我的矛盾中痛苦生存的人物,作為一位普通的穆斯林婦女,在其大膽潑辣的性格,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逐漸演變為刻板執拗、冷酷無情,在新舊時代的交接處,時時處在矛盾之中不能自拔。作為新時代中的傳統女性,她既要守住玉器韓家的好名聲,又要保衛自己的婚姻,日子要像多數普通家庭那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正常運轉。女性,是一個常新而永恒的話題;女性,又是一個復雜多元的主題。一端是情到深處的婚姻背叛,一端是血脈至親的女兒,她處在新舊時代交織的風口浪尖上不能自拔,在人性的關愛與理解中陷入了一種深深的自我折磨。這就是本我與自我的矛盾,本我即從心底里盼望著丈夫的歸來,更希望一雙兒女都能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從自我的角度來講,昔日的理性和信仰造就了一雙兒女的悲劇人生。
[1]霍達.精選霍達作品集[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12.
[2]趙德利.20世紀中國小說長女形象的文化心理透視[J].社會科學,2012,(10):176-182.
[3]申丹.敘述學與小說文體學研究[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201-202.
[4]霍達.穆斯林的葬禮[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48.
[5]歐陽可惺.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批評與地域文化[J].西部,2010,(22):89-90.
[6]秦人.人文北京[M].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4.118.
[7]馬海燕.從文化認同看電影《穆斯林的葬禮》[J].雞西大學學報,2009,(3):56-59.
【責任編輯:王 崇】
I207.42
A
1673-7725(2016)08-0066-03
2016-06-05
蘭奐錚(1991-),女,河南平頂山人,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