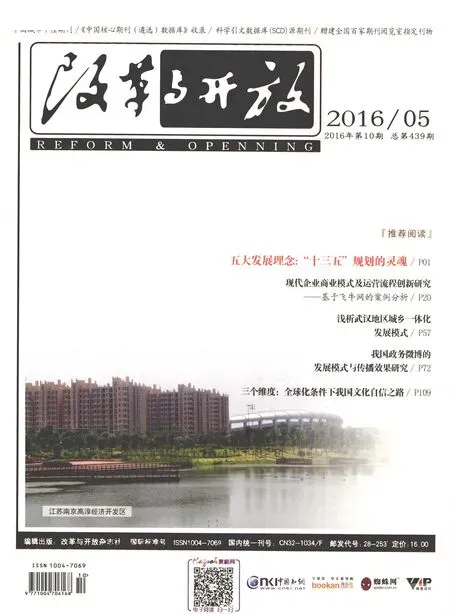《1844年經濟哲學手稿》中人的類本質思想的探討
陳 淼
?
《1844年經濟哲學手稿》中人的類本質思想的探討
陳淼
摘要: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中提出的人的“類本質”思想雖然是從費爾巴哈基礎上繼承發展而來,但賦予了其新的內涵和意義。本文從馬克思和費爾巴哈關于“類本質”兩者之間的關系以及馬克思“類本質”內涵方面進行分析,探討馬克思“類本質”思想在當代的價值和意義。
關鍵詞:馬克思;《手稿》;類本質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中關于人的類本質有大篇幅的闡述,通過人與動物的比較,他提出,人是類存在物。這也表明人只有在類的意義上才能獲得人的本質。雖然馬克思在后來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和《資本論》中已不再提“類本質”,但是并不代表馬克思否定《手稿》中關于“類本質”的內涵。每個偉大的哲學家和思想家從來都不是一開始就是一個哲人,而是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斷發現思考問題,賦予其新的概念、新的意義。“類本質”概念最初也不是馬克思提出的,而是費爾巴哈提出的,馬克思從當時的資本主義生產生活條件批判地繼承了費爾巴哈關于人的類本質的思想。任何哲學家和思想家,必定會有一套自己的理論系統,名詞概念,這大概也是馬克思后來放棄“人的類本質”概念的原因。重讀《手稿》這一經典著作,里面仍閃現著馬克思智慧的火花,而關于人的類本質,仍有很多值得我們深思的地方,在當代,仍然有重要地現實價值和意義。
一、馬克思關于“人的類本質”與費爾巴哈關于“人的類本質”的關系
人的類本質概念最早是由費爾巴哈提出,費爾巴哈是人本主義者,最初在批判宗教的基礎上,提出人的類本質概念。在他看來,意識是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費爾巴哈的類本質概念僅僅關注于人的精神世界,因此對現實社會所進行的政治批判和道德批判無法越出精神活動的范圍,僅僅局限于“思想批判”,而不涉及對現實世界和現存社會關系的革命性改造。費爾巴哈通過對人和動物的意識比較,認為兩者之間的區別僅僅是抽象意義上的,他所闡述的人的類本質主要體現為理性、意志和心,這些都是人們通過抽象思維思考出來的理論知識,而動物沒有這些抽象出的意識。只有將自己的類當做對象性的生物,才具有嚴格意義上的意識。動物也有自我感,但是它不能把類當做對象,所以動物沒有這種意識。在費爾巴哈看來,這種意識主要體現在人的宗教意識上。只有人才能產生宗教意識,人是類存在物恰恰是宗教的存在證明的。宗教的本質就是人的類本質的異化,宗教本來是人們想象創造出的產物,應該是受人控制的,然而宗教的產物“上帝”發展成可控制人們的存在,成為人們的對立面。費爾巴哈通過批判宗教,揭露了基督教的本質,不是神創造了人,而是人創造了神,歸根結底,人們對上帝地崇拜實際上是對人的本質的崇拜。而現實生活中卻顛倒過來了,通過人們的想象,上帝具有至高無上、超越現實的力量統治著人們,人們依賴上帝,這本來都是毫無根據的想象,卻因為宗教的發展,使這種想象深入人心,變成人們所信服的東西,人們必須臣服于上帝,這是一種不正常的異化現象。費爾巴哈在談到“人的類本質”時脫離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生活條件、勞動狀況,抽象地談論,通過批判宗教,得出人的類本質異化,卻無法找到真正的社會根源,而關于“類本質異化”的思維方式是當時主流的本體論思維方式,也是一種“還原論”,通過思辨邏輯的方法,先在理論上預先設定一種抽象的本真狀態,然后是異化,最后是人的類本質的復歸。
馬克思進一步分析宗教產生的社會根源,從現實入手分析人的類本質。馬克思也是用動物與人做比較,但是其從實踐層面來做比較,跳出宗教這種虛無縹緲的產物,從當時資本主義生產生活條件著手分析,批判當時流行的國民經濟學,考察資本主義異化勞動現象,指出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特性。目前學術界對馬克思和費爾巴哈關于“人的類本質”之間的關系有兩種看法,一種是馬克思關于人的類本質仍有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的遺跡,另一種是馬克思在《手稿中》已經超越費爾巴哈,不存在費爾巴哈階段。持第一種看法的學者認為,馬克思雖然從現實出發,但仍然采用人本主義思路闡述人的類本質,人的類本質-類本質異化-復歸。馬克思還是先在理論上設想人的類本質,這種思維方式還是很抽象的,是形而上學的,并沒有擺脫人本主義。持第二種看法的學者認為雖然馬克思先提出人的類本質,但這里的“人”結合馬克思后來的著作應是“現實的人”,而“現實的人”是在不斷發展中豐富起來的,而不是一開始就有的類本質。
筆者認為,馬克思雖然在《手稿》中已經從當時資本主義私有制角度思考問題,但是還是使用了人的類本質概念,并有大段的語言來表達人的類本質,說明馬克思是比較認同費爾巴哈關于人的類本質這個提法的。雖然馬克思關于人的類本質所表達的含義已經不同于費爾巴哈所闡述的,但馬克思還是先入為主地使用了這個概念,這里的人還不是在后來的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提到的“現實的人”,也還沒有達到“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里的“人”是一種理想化的人,是基于現實資本主義異化現象所設定的理想的人,這還是比較抽象的,是一種人本主義思維。在后來的著作中馬克思不再提人的類本質,也說明了他后來跳出了費爾巴哈人本主義思維的遺跡。
二、馬克思“人的類本質”的內涵
通過比較,我們知道馬克思“人的類本質”思想來源于費爾巴哈,但這里的“人的類本質”已不同于費爾巴哈關于“人的類本質”的內涵。那么,馬克思“人的類本質”的內涵是否在《手稿》中明確提到,目前學術界有三種看法,第一種認為“人的類本質”就是實踐或者是勞動,馬克思摒棄德國哲學從天國到人間的思維方式,批判資本主義社會這一現實世界,認為資本主義出現種種現象都是勞動異化的產物。第二種認為“人的類本質”是實踐或者勞動的特性,畢竟越是本質的東西越是抽象概括出來的。第三種認為馬克思根本沒有指出“人的類本質”是什么,后人過多地解讀了《手稿》,馬克思消解了“人的類本質”的意義。
持第一種看法的人是從《手稿》中“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特性”出發,把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稱為實踐或者勞動,認為“人的類本質”就是實踐或者勞動。持第二種看法的人也是從“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特性”出發,但是他們認為“人的類本質”本身是抽象概念,而實踐或者勞動是比較具體的,不能突出這種內在規定性,“人的類本質”應該是實踐或者勞動的特性,即自由,有意識。持第三種看法的人認為,馬克思通篇沒有具體指出“人的類本質”是什么,當提出這個問題時,必然會追根溯源,陷入形而上學的本體論思維,而這是馬克思不認可的,馬克思只是具體地、歷史地分析了人的真實生存狀況,馬克思始終從現實條件思考問題,在對現實世界的批判中,馬克思消解了“人的類本質”的意義。
筆者認為,《手稿》中大篇幅地討論“人的類本質”,基本都是跟異化勞動結合起來,雖然馬克思并沒有指出“人的類本質”究竟是什么,其關于“人的類本質”更多的是關注在“類”上,但是通過后來“人的類本質異化”現象,指出勞動本來是自由的、自主的,然而在當時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勞動異化成被迫的,僅僅變成維持人的肉體生存的手段,人在勞動時本應是肯定自己,是愉悅的、幸福的,然而卻異化成否定自己,感到不幸,這種勞動不是滿足一種需要,而是僅僅滿足生存的手段。從這里可以看出,馬克思還是委婉地指出“人的類本質”的內涵是自由的、有意識的。
三、馬克思“人的類本質”的當代價值意義
從個人層面來說,我們應該正確認識自己,通過馬克思“人的類本質”思想,我們知道不論在學習還是在工作中,應該是真正喜歡自己所做的事情,而不是被學習或工作所奴役、捆綁,我們應該在學習或者工作中感到幸福、愉悅、滿足,而不是不幸、厭惡,反感,但這并不代表我們可以不學習或者不工作,試想,如果一個人整天吃喝玩樂、不勞動、不工作也不學習,最后也會感到空虛、精神上迷茫、自己也會反感自己、懷疑自己,畢竟人與動物不同,人是有意識的、是會思考的。當今社會,學習、工作、娛樂方式更加豐富,人們的選擇也多種多樣,在信息化高速發展的時代,多元文化地交織,不同價值觀地碰撞,我們要有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要堅定馬克思主義理想信念,利用信息化時代各種有利因素,發揮自己的優勢,使自己全面發展。
從社會層面來說,馬克思“人的類本質”思想與“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主題息息相關。當今社會,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物質財富極大增長,但也帶來了一些問題,金錢至上、拜金主義、仇富心態隨處可見,腐敗現象也層出不窮。在有些人眼里,財富就是一個人成功的標志,這種社會現象是極其不正常的,會腐蝕人們的內心,助長社會不良風氣,降低社會文明程度。社會應該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創造出更多的精神文化產品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而不僅僅是簡單的感性娛樂,應提高精神文化產品質量,創造出更多體現中華文化精神、有思想、有藝術性的優秀作品,這樣人們才有正確的價值取向,精神文明才能提高。
從國家層面來說,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如何能使我們國家獨善其身,保持獨立,不被錯誤思潮所侵蝕是我們面臨的嚴峻考驗,經濟全球化不代表政治、文化全球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通過走資本主義道路在經濟上迅速發展起來,他們的“自由、平等、博愛”思想以及新自由主義思潮使得我們國家的很多人所向往,但是我們要清醒被認識到這些思想和思潮背后的本質,他們所謂的“自由”只是形式上的自由,只是少數人的自由,實際上仍存在剝削和被剝削的關系,只不過形式發生了變化、轉移,變得更加復雜。我們要反對資本主義自由化思潮,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要矢志不渝地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費爾巴哈,著榮震華,譯.基督教的本質[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3]王東,林鋒.論“類本質異化”與費爾巴哈思想之關系[J].中州學刊,2007(6).
[4]左亞文.重評馬克思的“類本質”思想[J].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4).
(作者單位: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DOI:10.16653/j.cnki.32-1034/f.2016.10.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