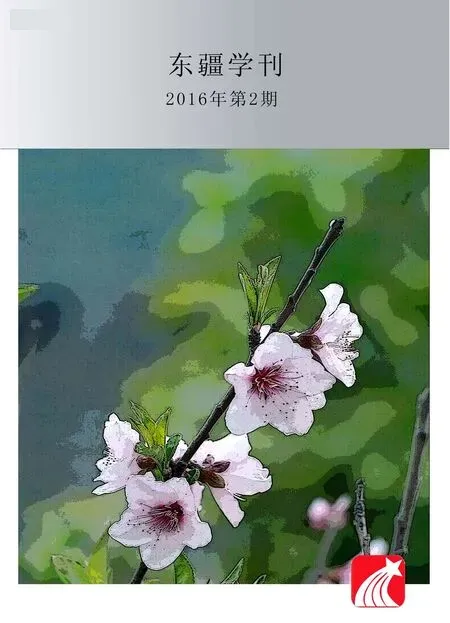東北亞法律文化格局的流變
李曉輝
?
□法學研究
東北亞法律文化格局的流變
李曉輝
“東北亞”作為一個文化地緣概念長期為比較法研究所忽略。分析東北亞法律格局的流變可以成為比較法“地緣研究”、“區域研究”的有益嘗試。東北亞法律文化格局在歷史上經歷了從 “早期的多元”——“中華法文化中心”——“西方化”——“全球化時代的法律多元主義”的不同發展階段。近代西方法律的進入,在東北亞法律文化格局中制造了聚合與分隔的張力。全球化時代的東北亞各國都在經歷著新一波的法律文化獨立運動,以謀求法律文化自主。當代影響東北亞法律格局的要素不僅是國家法,還包括了跨境民族、宗教、學術、地方政治和商業行為的力量,從而生成了東北亞區域的“法律文化群島”格局。
東北亞;法律文化;區域研究
區域是指地理接近、互動緊密、共享制度框架、具有文化認同的綜合體。區域不僅是經濟合作的機制框架,也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單位。鑒于國家接壤區域各種經濟和文化要素更頻繁的流動,因此跨境文化區域也成為各學科區域研究的關注對象。東北亞作為世界格局中具有獨特文化特質和政治經濟合作意義的區域,比較法對該區域的分析仍多局限于當代國家法層面,缺乏歷史流變的考察,而且忽視了其它非國家要素在法律文化格局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基于上述認識,筆者認為,“東北亞”法律文化研究應補足歷史和全球視角,同時也需要強調地緣、民族、宗教等文化要素在東北亞法律文化格局流變中的意義。分析東北亞法律格局的流變可以成為比較法“地緣研究”、“區域研究”的有益嘗試。
一、比較法研究中被“東亞”概念覆蓋的“東北亞”概念
在比較法的法律傳統研究中,學者們多使用“遠東”或者“東亞”作為基本研究單位。即便是使用“亞洲法律傳統“這一概念,也是在大亞洲范圍內,在單獨分出了印度法和伊斯蘭教法傳統之后,而專門討論東亞,特別是儒家法律文化傳統[1](352~370)。1913年,法國比較法學家紹塞爾·霍爾持“種族說”,以蒙古人種為基礎分析了東亞法律文化。勒內·達維德在《當代主要法律體系》中,將“遠東各國法”列為一個獨立的法律文化單元,其中僅分析了中國法和日本法。[2](483)茨威格特和克茨的研究中使用了“遠東法系”這一概念,[3](507)以非常有限的篇幅主要討論了中國和日本法律文化。茨威格特和克茨在遠東近現代法律的部分強調了:盡管東亞國家引進了西方法律,但西方法律在遠東社會仍存在著一段“懸浮時期”,西方法律基本上沒有進入人們的生活,中國也存在一段長期的域外法與傳統分隔的階段,而且西方法律被理解為一種在文化中剝離傳統的力量。特姆·魯斯克拉(Teemu Ruskola)對東亞法律文化的研究范圍涉及中國、日本、韓國和越南。特姆·魯斯克拉認為進入現代以來的東亞法律文化總體態勢是:中國法律文化在這一地區的影響至少在國家法律的層面已經被西方法律與政治文化所取代,呈現出了一種混合了古典東亞法律傳統、西方大陸法傳統和英美法傳統的復雜結構。相比于中國法律文化為基礎整合而成的古典東亞法律傳統而言,現代東亞法呈現出一種多元格局。[4](275~276)由上述分析可見,在西方比較法研究中,基本上沒有將“東北亞”作為一個地緣法律文化單元,比較法學術史上的“東亞”概念只覆蓋東北亞國家中的中日韓,最多到達蒙古,而將俄羅斯的遠東部分隔離在外。并且這些比較法研究主要關切的是古代東亞法律傳統(儒家法律文化),而對于近當代的法律文化格局缺乏有說服力的分析。
二、作為文化地理概念的“東北亞”
“由于文明受制于無法改變的和不可復制的地緣環境,于是,千百年來的歷史進程造就了‘地緣文明’的穩定性和持久性,這對于人們和決策者具體理解國際社會發展與國家沖突無疑具有極大的影響效力。”[5](10)“東北亞”是一個“心理地理”概念,為韓國、朝鮮、美國、中國、日本和俄羅斯所共同認可。“東北亞”這一區域地理名詞,首次出現在日本學者鳥居龍藏(Torri Ryuzo)的《東北亞搜訪記》中。“純粹地理意義上的東北亞,以經緯度劃分,大致指東京114度以東至亞美分界線,北緯38度以北的亞洲區域,包括中國華北的東部、東北部,東北三省,內蒙古的東部、東北部;蒙古國東部;俄羅斯東西伯利亞的東南部和遠東地區的北部(包括東北西伯利亞)、濱海省、庫頁島等地;朝鮮半島和日本。”[6](1)在很多學者的研究中,較大范圍的東北亞概念被理解為“東亞”和“北亞”的相加,包括俄羅斯、中國全境、蒙古、朝鮮半島和日本。這一理解多被應用于以國家為單位的地緣政治研究中。也有的學者將東北亞作為與“東南亞”相對的概念而使用,并在上述較大范圍概念包含的地區之外,還包括了中國臺灣。地緣政治意義上的東北亞概念在二戰后逐漸清晰起來,替代了此前從歐洲、俄羅斯角度定義的“遠東”概念。可以確定的是:“中國東北地區、朝鮮半島、日本列島、蒙古東部地區和俄羅斯遠東南部地區共同構成了東北亞的核心區域。”[6](1)而且,東北亞的核心區域并不是完全由國家構成的。中國傳統上將東北三省理解為東北亞的核心區域,在日本的文化理解上,東北亞也不包括日本全境,而主要是指較為北部和西北部的海域和島嶼。在所有東北亞地區涉及的文明體中,恐怕只有朝鮮半島承認東北亞包括了其全境。東北亞區域由龐大文明的邊緣部分,如中國的東北(范圍可以擴大到華北和山東)和俄羅斯的遠東地區(濱海邊疆區,薩哈林島等地),加上體量(地域和人口)不大,但相互間經濟發展與國際政治影響力失衡的文明體:日本、韓國、朝鮮和蒙古國組成。東北亞的地緣結構決定,以民族國家作為政治經濟和文化分析框架并不合適,有較大局限。
從東北亞的地域結構組成來看,不僅東北亞核心區域的地域單位都是各自所屬國家一個部分,而且在歷史上相對于各自的主流文明,往往是非主流的、欠發達的和邊緣的。東北亞文化中隱含著一種邊疆心態和邊緣處境。以中國東北為例,從中原漢文化的視角來看,漢民族政權在長久的歷史時間里并沒有實現對該區域的完全控制,東北亞文明始終處于漢文明的邊緣,同時東北亞也是漢文明與北方游牧文明融匯交流的前沿。越是處于宏大文化邊緣的“邊疆”文化,對于主流文化的認知越會出現某種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對強勢文明體崇拜向往,一方面又對保護自身的文化認知非常敏感。在文化上這種“中心-邊緣”的結構性思維影響了對東北亞區域文化的客觀認知,且總是偏向于用“依附”的邏輯去進行解釋。從文明史的角度來看,史家仍然習慣用理解強勢文明的思路來理解東北亞區域,這種“瞥視”的角度并非東北亞本位的視角,并不能建立客觀的區域分析框架。“相對于‘國家中心’主義敘事的歷史傳統,在人類近現代歷史發展過程中,特別是民族學、人類學學科興起之后,人們開始關注邊緣、偏遠、無國家中心的定位。‘邊疆中心’視角的出現,是人類國家社會由中心邊緣不斷擴大治權,并逐步加深認識而出現的一個必然結果。”[7](241)歷史各階段東北亞區域內部發生直接接觸的正是不同歷史時期的邊緣區域之間,而不是各自所屬的王朝大國之間。這一視角的轉換尤其對于俄羅斯和中國來說具有突出的意義。
東北亞地區實際上是一個與中心隔離的多個邊地組成的、松散的地緣文化結構。作為一個文化地理的概念,“東北亞”可以被理解為一個類似美國人類學家詹姆斯·C·斯科特關注的東南亞高地。[8](1~10)廣袤的東北亞區域,北靠歐亞內陸,東西面向太平洋。大興安嶺和錫霍特山脈兩組東北-西南走向的高大山系,一左一右平行排列,與橫亙在北部呈東西走向的外興安嶺,共同搭建起一個面向日本海和黃海的π字型地理結構。在這片廣袤的區域中,以平原為主,還包括了草原、丘陵和山地。東北亞大陸的氣候由北向南從寒溫帶——溫帶向海洋氣候過度。東北亞的人種構成,多為黃種蒙古后裔。在東北亞大陸上,古老文明以游獵為主,隨著歷史發展,到了16-17世紀,大面積農業墾殖才使農耕文明在東北亞區域成為主流。東北亞地緣文化,帶有強烈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彪悍與粗放,帶有底層莽原拓殖移民的文化相對性和冒險精神。東北亞法律文化從北向南呈現從游牧法律文化(具有關注自然、強調部落族群集團性、比較粗曠、尚武等特色)向細致的海洋法律文化(注重家族倫理和血緣關系,趨于開放包容,更加注重制度的細節)發展,向西則更貼近中原儒家傳統為底色的漢民族倫理法文化。
三、東北亞法律文化格局的歷史流變
縱覽東北亞法律史,大體上其法律格局的演變經歷了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約公元8世紀之前,各文化體以自身的民族文化交織成早期的東北亞法律文明形態。該階段的東北亞以游牧文明為核心,與古代中國中原文明開始早期交流。其早期文化體的法律形態都以民族習慣法為主,吸收了西部中原文明的部分內容,如高句麗王朝(公元前37年-公元668年)法律制度中,吸收了漢民族中原法律文化,但也保留了諸如“婿屋”制度、“責禍”制等帶有鮮明民族文化色彩的制度形態。[9](65)
第二個階段是公元7世紀至18世紀,以中國法律文化為整合力量的法律融合階段。日本從圣德太子時代開始向中國隋朝學習法律。直至大化革新之后,日本仿效唐朝建立了自己的成文法體系。《大寶律令》大體上承襲唐律,僅做部分修改。自德川時代至明治13年為止,日本法律受到中國明朝律令的深刻影響。朝鮮半島自中國三國時期(公元3世紀)起就受到中華法律文明的直接影響,后期的《高麗律》直接仿效唐律。中國明朝的《大明律》為朝鮮朝大體采用。中國的滿清王朝處理邊地司法的“理藩院”體系,也支持使用東北亞地區的民族習慣法。
東北亞法律格局發展的第三階段是近代,具體指18世紀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這段歷史時期。在這一階段,東北亞各文化體都在外強挾持和內部壓力的雙重作用下開始了面向西方的法律現代化。西方法的進入在東北亞區域產生了聚合與分隔的張力。一方面,東北亞各國在向西方大陸法系學習過程中走到了一起,溝通交流學習西方的經驗教訓,并特別關注鄰國在調試改造西方制度的本土化過程。西方法在東北亞的傳播格局顯示出了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復雜格局,同時也反應了“和你比著學,參考著你學”的比較方法論。另一方面,學習西方法在東北亞區域內部也制造了“誰是優等生”的負面競爭。俄羅斯和日本法律文化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獲得了優勢地位,進而影響了東北亞廣大區域。俄羅斯在彼得大帝改革后開始面向歐洲,開啟了歐洲化進程。在彼得大帝和葉卡捷琳娜二世開始至十月革命前夕,沙皇俄國的法律已經實現了現代法典化。出現了《法令全集》(1825年)和《法律全書》(1833年)為代表的法典集成。“俄國十月革命前的法律,特別是19世紀的法律中已在封建法律基礎上注入了很多資本主義的因素,基本上屬于歐洲大陸法系的一員。”[10](429)日本也在福澤諭吉等思想先鋒的引領下面向西方,而舊有的中國儒家法影響則被刻意淡化。日本開始視中韓為“壞朋友”,而全力追求與西洋文明比肩。[11](279)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羅斯的遠東戰略和日本的大東亞戰略對抗,在東北亞地區形成了半個多世紀的沖突。學習西方法律的過程中經過自身演繹形成的近代俄羅斯法律文化和日本法律文化,成為影響東北亞地區法律文化格局最重要的兩股力量。自1858年中俄《璦琿條約》后,沙俄勢力開始進入中國東北,并逐步控制了中國東北廣大區域,[12](32~33)直至日俄戰爭后,其影響力為日本所取代。日本在1931年9月18日后,開始了14年對于中國東北的占領。朝鮮半島從1894年甲午更張之后逐漸成為日本的殖民領地,直至二戰后才完全結束日本殖民統治。近代以來,日本經由德、法獲得的大陸法制度與司法體系以及帶有東方式權威主義、國家主義色彩的法律文化影響了廣大的東北亞區域。
東北亞法律文化格局流變的第四階段是二次大戰之后至今。在這一時期,東北亞法律文化格局呈現了從“意識形態分隔”到“全球化背景下多元開放格局”的演變。二戰后,蘇聯、中國和朝鮮及蘇聯影響之下的蒙古國,在意識形態上與韓國、日本形成了社會主義法與資本主義法的意識形態分隔。20世紀末,蘇聯解體、中國改革開放之后,意識形態對于法律文化格局的影響逐漸減弱。東北亞法律文化在全球化過程中形成了更加多元的格局。東北亞各國都不同程度地在現代西方法律的基調之上尋求法律文化的自主和獨立。俄羅斯和中國兩大國在法律交流方面所持的態度趨于開放。蒙古則提出了“第三鄰國”概念,努力擺脫中、俄兩個大國的絕對影響。韓國在美國式民主憲政影響之下努力重塑韓民族文化自覺。日本也在繼續學習西方具體制度的同時不斷調整,以建立日本式的法律制度與結構(如陪審制度的變化、建立法科大學院過程中的不斷調整等)。朝鮮從經濟方面進行了小范圍的開放,如建立開城工業園和羅津先鋒開發區等。東北亞法律文化在繼續深度學習、調試、消化西方制度的同時朝向多元并立的方向發展。東亞各國的法律發展,在開放的視域之下猶如西方各法系、各國制度的大雜燴:各種西方法律概念、原則和制度紛紛出現,在東北亞各國被展示、推介、討論和試行。東北亞各區域的法律文化呈現出:以大陸法為主,揉合英美法制度和理念,并結合本國、本民族文化的多樣格局。另外,近現代以來,在尋求法律文化自覺的過程中,東北亞各文化體繼續撇清與中國古典儒家法律文化的親緣關系,如韓國通過文化上的“去中國化”,以實現更好地貼近西方,更好地完成民族心理重塑。“去中國化”和“脫亞”過程弱化了東北亞各文明體原有的,經由古典東方儒家價值觀建立的聯系,加速了法律文化上的分隔。俄羅斯和日本,特別是日本,已經成為或者號稱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茨威格特和克茨也認為日本由于在二戰后受到普通法的強烈影響已經開始脫離遠東法律圈,進入西方法律傳統。[3](517)日、俄的西方定位,在東北亞內部制造了“東-西”問題,從而使東北亞在掙脫西方中心主義的同時也加劇了一種內部的張力。在這種更加多元自主的情勢下,東北亞區域法律文化特色的歷史基礎(比如儒家法律文化)不斷被消解,現實基礎又不斷被多樣的法律移植和復雜的政治對立碎片化,區域法律文化整合的力量不斷弱化。東北亞法律文化形成了一種浸潤(抑或漂浮)在古典東亞法律價值觀和西方大陸法基調中,呈現相互關聯又彼此獨立的、多中心的“文化群島”格局。當下法律融合的推動力量開始轉向跨境文化要素融通和經濟開發合作。
四、當代東北亞區域法律文化的多樣要素:跨境民族、宗教與學術
在文化人類學的研究中,涂爾干曾經指出社會學長期將國族生活視為群體生活的最高形式,尚未認識到沒有清晰邊界的社會現象的存在,這些社會現象超越了政治邊界,向難以界定的空間延展,社會學有必要確定這些現象的存在方式。東北亞研究中不應忽視這些基礎性的“超社會體系”,從民族、種族和文化傳統的角度尋找更多的區域化紐帶與聯系中介,在這些基礎性因素中發掘共同的生活方式作為區域法律比較與發展的基礎。
共同的民族語言和文化、頻繁的跨境人口流動,形成了跨境民族文化的獨特單元。法律作為“民族精神”的產物,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形成民族認同的媒介之一。跨境民族沿襲了共同的民族習慣法規則,并在國家法之外拓展了以民族習慣法為內容的自治糾紛解決機制,從而在民間層面開拓了法律融匯融通的另一個通道。
歷史上東北亞地區基于戰亂、殖民、經濟拓殖、強制遷徙等原因造成了多次大規模人口流動,形成了復雜交錯的民族分布格局。在中國東北的邊境兩側,朝鮮族、滿族、赫哲族、鄂溫克族、俄羅斯族和蒙古族這6個民族的1 000多萬民眾,在3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跨境而居。以朝鮮族為例,除了主要分布在朝鮮半島的韓國和朝鮮以外,在中國東北約有200萬,在日本約有64萬,在俄羅斯有52萬。[13](251~280)朝鮮的民族文化帶有“二元性”特征,呈現出相對于強勢文明的“邊緣化”。“邊緣文化體系的功能在于文化轉換、文化中介、確保文化信息。”[14](85)正是這種邊緣文化功能在跨文化交流中起著重要的中介作用。朝鮮半島的法律文化受到中國、日本和西方德國、美國的多重影響,注重集團利益,強調權威主義,既表現出很強的融通整合能力,也體現了東亞價值觀。
另一個東北亞重要的民族——蒙古族,主要分布在中國的內蒙古自治區、遼寧省和黑龍江省和吉林省,人口約600萬;在蒙古國分布有近300萬;俄羅斯有大約100萬蒙古人,主要是分布在西伯利亞布里亞特共和國的布里亞特蒙古族。蒙古民族有強悍的對外征服史,曾建立元王朝。蒙古族擁有特色鮮明的民族法律文明史,成文法典就曾有成吉思汗制定的《大札撒》、建立元朝后制定的《元典章》以及明清時期的諸多自治屬邦蒙古法典,如《阿勒坦汗法典》、《喀爾喀法典》和清王朝《蒙族則例》等等[15](105~111),積累了大量的民族習慣法。蒙古民族的法律文化注重人與生態的和諧,注重血緣血親形成的部族關系,具有宗教基礎(薩滿教和藏傳佛教)、帶有神明裁判色彩。盡管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變化限制了蒙古族習慣法在當代的適用范圍,但蒙古族習慣法仍然在蒙古族聚居地區發揮著作為社會規范的實質作用。如蒙古族習慣法中關于放養、代養、寄養牲畜的制度——蘇魯克制度,經過改良仍然在廣大蒙古族牧區沿用。[16](47)蒙古族習慣法仍然是生活在東北亞廣大地區的蒙古族裔的行為指南和糾紛解決的重要依據。除跨境民族之外,在東北亞還存在著跨境宗教,如在中、日、韓東北亞區域中具有重要影響的佛教禪宗,在俄羅斯遠東并波及東北亞廣大地區的東正教,在蒙古族群和中國東北等地傳播的藏傳佛教,在鄂倫春族、鄂溫克族、蒙古族、滿族等民族中薩滿教的留存。宗教不僅僅是一種信仰體系,也是一種行為規范體系。跨境宗教交流是加深文化融通和觀念融通的重要途徑,必然影響教徒和信眾的行為。
法學學術精英經由對東北亞共通法文化基礎和實現機制的研究成為對東北亞法律發展而言具有較強影響力的一支力量。近年來,東亞民法學者已經開始推出類似《歐洲私法示范法》的示范法律文本。2014年,東亞侵權法學會完成了《東亞侵權法示范法》(草案第三稿)。《東亞侵權法示范法》規定了一般侵權責任,同時有選擇性地規定了三種最具有東亞地區侵權法統一價值的特殊侵權行為類型: “產品責任”、 “環境污染責任”、 “網絡服務提供者侵權責任”,對于推動東北亞法律融通產生了一定的示范作用。自2009年起,東亞學者也已經開始了“亞洲合同法原則”(PACL)項目的緊密合作,有望拿出對于東北亞具有直接制度規范功能與文化關照功能的“亞洲共同合同法”。[17](8~16)
五、經濟的力量:地方政府與商業
“若我們遵循“大外交”、“大外事”的定義,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確實存在對外關系領域穩定的分權趨勢,正是存在制度性和政策性的分權,地方才可能被推到國際合作的前沿。”[18](10)各國中央政府對地方不同程度下放外貿和外事權力。中國地方政府和各國的邊疆“特區”政府往往具有一定的開展經濟和文化合作的能力。這種地方之間的合作,在法律交往上必然打開一個新的層次。各國地方政府之間在地方立法、執法乃至司法上的實質合作更加具體、務實,更能夠體現休戚與共的地域共同文化。更多相互吸收和借鑒的制度成果的出現,將推動區域之間在經濟貿易等領域地方規則和政策的融合。
在東北亞次區域合作過程中,特別是在經濟合作關系的發展之中,地方政府擔當了重要的角色。東北亞各國地方政府均活躍于次區域合作的前沿,如中國的東北三省、山東省;俄羅斯的濱海邊疆區、沃洛格達州、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疆區、薩哈雅庫特共和國;朝鮮羅津先鋒經濟特區;韓國的首爾特別市、江原道、忠清北道等地方政府。1992年,圖們江開發以來,中國東北地方作為參與開發的主體已經得到了中國中央政府的肯定。2009年《中國圖們江區域合作開發規劃綱要——以長吉圖為開發開放先導區》(下稱《規劃綱要》)獲國務院批復,吉林成為圖們江開發的主體省份,同時遼寧、黑龍江和內蒙古自治區也成為該次區域開發的重要參與者。《規劃綱要》授權中國吉林省代表中國政府參與大圖們江區域合作開發機制等有關工作,承擔開發中的省際協調人工作。《規劃綱要》還明確提出“進一步合理擴大區域內縣級及以上政府的投資和貿易管理權限”,“適度擴大我地方政府參與圖們江區域合作開發的權限”主張。中國中央政府也強調在圖們江開發和東北亞次區域開發中,應加強地方交流,建立長效工作機制。
在實踐層面,“東北亞地區政府首腦會”自1994年以來已經舉辦了20屆,達成了東北亞地區各地方政府之間的多項《共同宣言》,旨在推動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及擴大人員與經貿往來。2015年9月,在中俄舉行了高級別的“東方經濟論壇”,普京出席該論壇并指出:“遠東應被看作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中心之一。”“這一地區應融入迅速發展的亞太地區”。隨后,“中國東北地區和俄羅斯遠東地區地方合作理事會”成立,這一機制聚合了中俄以及東北亞國家高級別、多部門和多個地方政府的力量,將成為推進中俄遠東開發合作的主渠道。
為了更好地實現區域開發,東北亞各國政府在各自的邊境區域紛紛建立了各種類型的、匹配特殊開發權的“特區”,如朝鮮的羅津先鋒經濟特區、黃金坪和威化島自由貿易區;俄羅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和多個遠東超前發展區。這些“特區”成為區域發展對接的重要途徑,也成為制度合作和法律交流融通的重要平臺。俄羅斯在建設遠東超前發展區的過程中邀請中國中央和地方政府參與制定發展規劃。處于經濟合作最前線的企業,如大型商貿集團、能源、基礎設施開發和制造業集團等也在“政府搭臺、企業唱戲”的過程中成為經濟合作的主要角色。通過企業合作而展開的法律背景調查、協議談判和履行,無疑是加深雙方制度理解、推動制度便利化一體化的主動力量。由此,東北亞地區的次區域經濟合作已經呈現了“多層次、多主體”的局面。
[1][加]帕特里克·格倫:《世界法律傳統》,李立紅、黃英亮、姚玲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2][法]勒內·達維德:《當代主要法律體系》,漆竹生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
[3][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較法總論》,潘漢典、米健、高鴻鈞、賀衛方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
[4]Teemu Ruskola:TheEastAsianLegalTradition,EditedbyMAuroBussanniandUgoMattei:TheCambridgeCompaniontoComparativeLaw,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5]郭銳:《東亞地緣環境變化與中國區域地緣戰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
[6]楊軍、寧波、關潤華編:《東北亞古代民族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
[7]周建新:《邊疆中心視角下的跨國民族族緣政治》,金強一、樸東勛主編:《東北亞國際合作:困境與出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
[8]James C.Scott,TheArtofNotBeingGoverned:AnAnarchistHistoryofUplandSoutheastAsia, New Heaven: YaleUniversityPress,2009.
[9]秦升陽:《高句麗的法律制度》,《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3期。
[10]何勤華、李秀清主編:《外國法制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
[11][日]福澤諭吉:《脫亞論》,林思云譯,轉引自馮玉軍著:《全球化中的東亞法治:理論與實踐》,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
[12]龐業清、梁大慶:《沙俄在中東鐵路初期攫取的司法權》,《地名學研究》,2011年第2期。
[13]李承律:《東北亞時代的朝鮮族社會》,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
[14]李承律:《東北亞國際合作時代朝鮮族社會文化功能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
[15]劉學靈:《蒙古法文化史》,《內蒙古大學學報》,1991年第2期。
[16]張文香:《蒙古族習慣法與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中央民族大學博士論文,2011年。
[17]韓世遠:《亞洲合同法原則:合同法的“亞洲聲音”》,《清華法學》,2013年第3期。
[18]蘇長和:《中國地方政府與次區域合作:動力行為及機制》,《世界經濟與政治》,2015年第5期。
[責任編輯全華民]
D908
A
1002-2007(2016)02-0061-06
2015-10-12
李曉輝,女,北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研究方向為比較法、法理學、知識產權。(北京10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