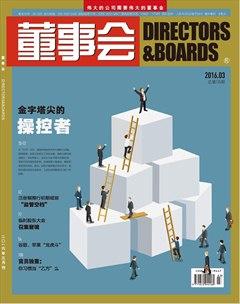堵漏不良股份回購
劉輝
去年6月A股逐漸跌入熊市以來,不少上市公司開始實施股份回購計劃。但國內外屢次回購實踐證明,股份回購如果規制不力,極易成為公司高管和大股東操縱市場的工具
1月18日,新湖中寶對外發布股份回購預案,公司擬以集中競價交易方式回購股份,回購資金總額高達10—20億元人民幣,回購價格上限設定為5.20元/股。如果全額回購,公司預計可回購至少38461.54萬股,約占回購前公司總股本的4.23%。
去年6月A股逐漸跌入熊市以來,不少上市公司開始實施股份回購計劃。股份回購無疑對上市公司股價維護具有重大的利好屬性,但國內外屢次回購實踐證明,股份回購如果規制不力,極易成為公司高管和大股東操縱市場的工具。我國現行公司法對股份回購“原則禁止例外允許”的態度需要改變,但對通過股份回購操縱市場的法律規制必須加強,比如對股份回購的法律性質予以界定,建立股份回購安全港規則以及設置股份回購隔離期制度等。
不良回購魚肉投資者
股份回購對我國證券市場的投資者來說并不陌生,是指上市公司按一定的條件和程序依法買回已經發行或上市流通的本公司股票的行為。從全球資本市場來看,股份回購的途徑主要有現金回購、發行公司債券換取股權、發行公司優先股換取普通股等。
在2005年以前,受制于立法的限制,我國上市公司實行股份回購的寥寥無幾。而2005年《公司法》的出臺適度放寬了對上市公司股份回購的適用,《公司法》第143條規定了四種合法的回購情形。從此,我國股份回購案例不斷增多,但違規事件層出不窮。2008年底,海馬股份宣布實施股份回購計劃,但到2009年卻公布《收購報告書》稱,“在一年的回購期內”,僅有“17個交易日的短暫時間達到回購條件”,因此,公司未能實施回購股份方案。流產的股份回購計劃背后卻是二股東“海馬投資”于6、7、9、11月連續減持,每月減持近千萬股。無獨有偶,2013年9月,禾欣股份拋出不超過三億元的股份回購計劃,但截至2013年12月31日,回購計劃也未能實施。公司最后發布公告稱,“股價未觸及回購條件”。同樣,禾欣股份的高管們大肆地拋售掉持有的股票。
“原則禁止”仍無突破
不得不承認,我國立法者對于股份回購這一舶來品的運用及其規制,存在搖擺不定的態度。一方面,我國主要沿襲著大陸法系國家的立法傳統,公司法著實信任公司資本充實原則,以加強對債權人的保護。為此,公司回購自己的股份,將使該股份所代表的資本實際上處于虛置狀態,從而減少注冊資本,這顯然是違反公司資本充實原則的,對債權人形成不利。
但另一方面,不論是出于反收購、市值管理、調整上市公司股權結構還是對熊市狀態下國家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防范,股份回購都有重要的制度價值。除2005年《公司法》外,中國證監會還在2005年6月16日發布了《上市公司回購社會公眾股份管理辦法(試行)》的通知(以下簡稱《回購辦法》),并于2008年10月9日發布了《關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競價交易方式回購股份的補充規定》(以下簡稱《補充規定》)。上述立法基本確立了我國上市公司股份回購的程序、回購價格和時間限制、信息披露等制度。但是,《公司法》有關“原則禁止例外允許”的規定仍無突破,股份回購的法律性質也未予以明確,安全港規則以及隔離期制度仍然缺位或不完善,這對防止操縱市場和大股東減持顯然十分不利。
放開回購建立“安全港”
首先,《公司法》第143條對于股票回購“原則禁止例外允許”的規定需作修改。在美國,法律對股票回購的態度是十分開放的。因為股票回購這種商事實踐對于上市公司采取反收購措施、市值管理、股權結構調整以及在股票市場步入熊市之后穩定股價、維持市場信心是非常有益的。從另外一個角度講,限制甚至禁止股份回購也并不必然能徹底保護債權人,已成為公司法和證券法學者的共識,這在最新修訂公司法時對注冊資本愈發寬容的態度轉變中可見一斑。因此,問題的關鍵不是“堵住”回購的口子就能解決的,相反,應當打開回購的通道并輔之以有效的監管。
其次,明確上市公司股份回購的要約性質。上市公司不良回購行為,其實質都體現出法律對股份回購規制的不力。換言之,上市公司通過發布股份回購計劃刺激股價上漲而大股東潛逃,盡管股份回購并未真正實施,但法律亦無法對公司追責。受到我國民商合一傳統以及現行合同法規定的影響,股份回購計劃被當然解釋為一種要約邀請,因此,當上市公司怠于履行時,并不能追究其違約責任。對此,一方面,我們必須明確商事要約的特殊性,即商事要約并不絕對要求受要約人的特定性。《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就以受要約人特定為原則,而以不特定為補充和例外。因此,在證券法律中,我們可以明確上市公司股份回購的法律性質為要約,而投資者發出的同意賣出股票的意思表示即為承諾。這樣,上市公司不良回購即納入商事合同予以規制。另一方面,明確上市公司股份回購的要約性質也符合公平原則。在上市公司股份回購的過程中,上市公司及其大股東始終處于信息優勢地位,對回購的操作具有絕對的主動權。當立法作前述安排時,實際上加大了對投資者的保護,體現了證券公平原則。
再次,建立安全港制度。美國和日本建立了不同的安全港(safe harbor)制度。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于1983年創立了10b-18規則,即安全港,明確了股份回購計劃的行為方式、回購數量、回購價格和回購時間等問題,對符合規定的回購無需進行額外信息披露并獲得操縱市場的豁免。相反,如果未按照“安全港”規則實施回購,但依法履行了相應信息披露義務的,也不必然認定其回購行為就構成市場操縱,而需個案認定。日本的安全港則是采取“港內豁免”、“港外違法”的模式:如果回購符合安全港的規定則予以豁免,如果不符合,則至少被處以30萬日元以下的罰款。構成市場操縱的,另行處理。我國的《補充規定》盡管規定了股份回購的相關要求,但對違反的法律責任并未明確,即是否需要罰款,或被推定構成市場操縱。結合我國國情,建議借鑒美國的安全港規則,對我國股份回購的資金要求、回購時間、回購方式以及程序等進行完善,同時明確,對符合安全港規則要求的行為予以豁免,而違反安全港的,并不必然對其進行罰款的處罰,而是否構成操縱市場,由證監會進行個案認定。
最后,建立隔離期制度。隔離期是我國臺灣地區“證券交易法”第 28 條之2項第 6 款之獨創:“公司從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所買回其股份者,該公司的關聯企業或董事、監察人、經理之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或利用他人名義所持有之股份,于該公司買回期間內不得賣出”。隔離期制度有效解決了兩個問題:其一,如新湖中寶公布的股份回購預案,既然是維持股價,那么回購的同時,相關人員不得賣出,這才能真正達到回購的目的。其二,回購的提案是董事會作出的,回購的決議是股東大會作出的,大股東處于絕對的支配地位,那么隔離期“限售”也同樣體現公平的要求。因此,對于隔離期制度,有必要寫入《證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