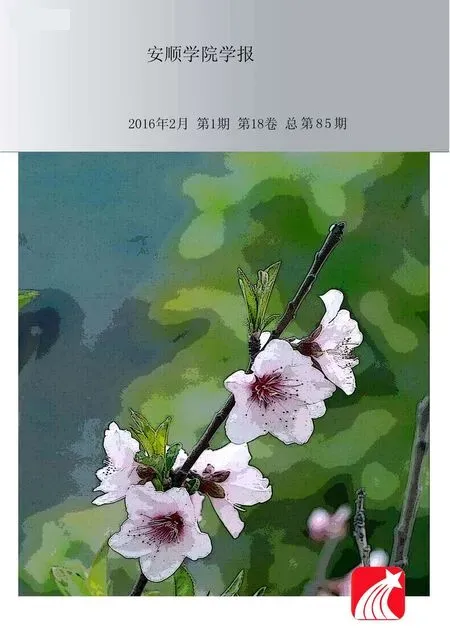“鴻都石經”誤說形成的原因
高 斌
(南開大學文學院 天津300071)
?
“鴻都石經”誤說形成的原因
高斌
(南開大學文學院天津300071)
“鴻都石經”說形成可溯源于唐代《尚書故實》一書,歷經宋代一些非經學著述的推衍,成為對漢代熹平石經的一種稱呼。后人將形成的原因僅僅歸結為時人分辨不清漢代太學與鴻都門學的位置與性質,而未能指出深層次原因。其形成的原因應體現為科舉取士當中明經科較為保守的考察方式,加之漢代鴻都門學之后,文學藝術的社會地位逐漸發生了重大變化,對士人思想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使士人對經學與文學藝術的看法也隨之發生了改變。
鴻都石經;經學;文學藝術;鴻都門學
“鴻都石經”一詞最早完整出現在北宋后期,此后在明清典籍中這種說法被廣泛引用,至清代考據學盛行,在《石經考異》、《漢魏石經考》等著作中作者都已經明確“鴻都石經”確為后人誤說,但只是對這一誤說的最初來源做了考證,而未對這一說法形成的原由做進一步分析,這當然與清代樸學重考據不重闡釋的治學精神有關。今人對“鴻都石經”誤說的研究,也多承襲清人對這一問題的論證思路,而缺乏結合經學發展史及文學觀念對這一說法形成原因的進一步分析。
后人所通稱的“鴻都石經”,原指的是漢代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所刻石經,《后漢書·蔡邕列傳》載:“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飏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丹于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1]卷六十下(P1990)。石經的刊刻是為了改變漢末經籍文字多謬誤、俗儒穿鑿附會貽誤后學的現狀,供后儒晚學取正,這就是經學史上有名的熹平石經。熹平石經在漢末戰亂中嚴重受損,此后石經殘片更是彌足珍貴。鴻都門學則設立于光和元年(公元178年)二月,“(光和元年)己未,地震。始置鴻都門學”[1]卷八(P340)。縱觀《后漢書》所載史料,鴻都門學可大致視為漢靈帝為招納文學藝術之士而專門設立的官方機構,這些士人可以作為漢朝的后備官吏,因此鴻都門學也可以視為當時除了官方規定的取士制度之外,進入仕途的另一種方式。但囿于經學在思想及統治方面的獨尊地位,當時的正統經學之士對以鴻都門學為代表的文學藝術之士表現出了極端的蔑視。“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于時”[1]卷五十四(P1780)“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1]卷六十下(P1998)從中也可以看出,在當時文學藝術只是被經學士大夫視為方技,作為技藝的一種,認為不可能用來作為選拔官吏的一種方式,更不能與經學相提并論。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后漢書·蔡邕傳》中也提及蔡邕也曾多次上書表達對鴻都門學存在的不滿,雖然他本人在文學藝術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熹平石經的刊刻與鴻都門學的設立兩者前后相差數年,一為經學發展的產物,一為文學藝術機構,兩者本無太多干系,后人緣何會將二者混為一談?筆者將做進一步分析。
典籍中最早將“鴻都”與“石經”相聯系的是唐代李綽的《尚書故實》①,其中記載道:“東都頃千剏造防秋館,穿掘多得蔡邕鴻都學所書石經,后洛中人家往往有之”[2](P11)。此處作者認為洛陽人家所得的石經為蔡邕在鴻都門學中所書寫的石經,直接將“鴻都”與“石經”聯系起來。至于李綽其人,史籍無載,但《尚書故實》這本書的性質可以從開篇近似于緒言的文字中得出結論,“賓護尚書,河東張公,三相盛門,四朝雅望,博物自同于壯武,多聞遠邁于咠臣。綽避難圃田,寓居佛廟,秩有同于錐印,跡更甚于酒傭,叨道迎塵,每客侍話,凡聆征引,心異尋常,足廣后生,可貽好事,遂纂集尤異者,兼雜以詼諧十數節,作尚書故實云耳。”[2](P1)從中可以看出,《尚書故實》這本書實為傳聞趣事的輯錄,是唐代筆記小說的代表,所以其中所記載的故事應為當時所廣泛流傳的逸聞趣事,且對時人具有較強的吸引力。引文中所說的這則軼事,也應該為作者聽說并輯錄下來的,由此可見,漢熹平石經到唐代時已經十分稀有,將石經單獨與蔡邕相提并論,可以看出當時的人們對于熹平石經更多的是看重其書法藝術價值,而不是石經殘石所具有的經學價值。
將“鴻都”與“石經”并稱,最早見于北宋晚期黃伯思在《東觀余論·記石經與今文不同》中,其中記載石經殘片落入洛陽諸家中,并選取了兩塊石經拓本引入文中分析,“……此石刻在洛陽,本在洛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洛人好事者,時時得之,若騏驥一毛,虬龍片甲。今張燾龍學家有石版最多,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論語》之末,題云:詔書與博士臣左立劉本無立字郎中臣,‘書’上‘臣’下皆缺,當是著書者姓名。或云此即蔡邕書,姓名既亡,無以辨之,獨刻者陳興,姓名甚完,何其幸與。又有一版《公羊》,不知誰氏所得,其末云:‘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域,議郎臣劉宏,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雜’‘雜’未詳下‘谿’上缺,‘谿‘上當是‘堂’,謂‘堂谿典’也,此蓋鴻都一字石經。然經各異,手書不必皆蔡邕也。三字者不見真刻,獨此一字者,乃當時所刻,字畫高古精善,殊可寶重。開元中,嘗藏拓本于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與法書名畫同藏,蓋唐世以前,未錄前代石刻,獨此見收,其可寶如此‘立’字‘雜’字,案石經古本皆有之”[3]P25。此段文字中,作者對兩版石經拓本進行分析,提供的信息有三點,一點是,漢代殘存石經缺失甚多,僅存些許;二是對于石經本身來說,熹平所刻石經并不都是蔡邕手書,與之相比,魏正始石經更是難見真刻;三是,石經拓本當時是作為書法作品與書畫保存在一起。因此,文中所言“鴻都一字石經”已經不具有經學史的意義,而更多的是書法藝術上的價值界定。值得注意的是,《東觀余論》一書,是一部法帖辨析之作,重點在于辨析各個時代的書法藝術,其對石經的探討也意在考察石經的書法藝術價值,而不是其經學方面的價值。
“鴻都石經”一詞,最早見于董逌《廣川書跋·石經尚書》一篇,“秘書郎黃符,以石經尚書示余,為考而識之。蔡邕以經籍去圣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后學。熹平四年,奏求正六經文字,邕乃自書于碑,大屋覆藏,立太學門外,號鴻都石經”[4](P57)。此篇可與此書中的前一篇《蔡邕石經》相互參照考察,由此可知,作者可以明確知道蔡邕所校刊書寫的石經就是立于太學門外,但作者仍在文中將熹平石經“號”為“鴻都石經”,這里的“號”應為“稱作”的意思,并不是實指。《廣川書跋》一書是一部金石碑帖考據之書,重點探究歷代金石銘文、石刻碑帖及唐宋書法名家作品,也是一部側重書法藝術研究的作品。
綜合上文三處材料可知,理解“鴻都石經”這一說法形成的原因,應主要側重熹平石經所展示的書法藝術價值與鴻都門學所給人的作為藝術代表的符號化印象去理解,而鑒于殘存的熹平石經內容對后世的影響極為有限,不應該從其作為經學代表的角度去探討。“鴻都石經”這一說法的形成,與唐宋大的社會環境密切相關。從思想發展階段來看,隋唐時期是經學處于南北合流并逐漸走向統一的時期,經學發展也由魏晉玄學化的儒學向宋代理學逐漸轉變。在這個時期,除儒家之外的道家和佛家均得到了巨大的發展,思想上由儒家經學居于主導地位逐步變成三教并行,經學在思想上的主導地位也逐漸被取代。而隋唐時期的科舉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經學統一時代的些許弊端。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談到,“唐帖經課試之法,以其所習經掩其兩段,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為通。專考記誦,而不求其義,故明經不為世重,而偏重進士”[5](P210-P211),經學的這種“專考記誦,不求其義”,實則是經學統一時代經學觀念的展現,也是經學發展由魏晉玄學向宋代理學過渡所表現出的特點。這種取士方式使士人由明經科,轉而更重視進士科,進士科則主要考查詩賦,也就是側重文學藝術的科目,加之唐代文學藝術得到了極大的發展,所以,文學藝術的社會地位得到提升,人們對經學以及藝術的觀念也隨之發生了變化。
在唐宋兩代經學和文學思想背景之下,再去探討“鴻都石經”這一誤說的形成原因,似乎更容易理解。鴻都門學首開用文學藝術選拔官吏的先河,此后“鴻都”一詞逐漸被士人符號化成了具有特定含義的歷史典故,縱觀唐代典籍中所有涉及“鴻都”的材料,可以看出唐代士人將“鴻都”一詞的含義設定為以下幾種:技能藝術的代稱(如 《樊川集·文集第十九》、《北史·第七十儒林下》《南史·列傳第二十三》等)、代指入仕為官(如《李太白集》、《黃御史集》等)、藏書之所(如《封氏聞見記》《藝文類聚·雜文部》等)、指都城(如《劉夢得文集》、《北堂書鈔·政木部十三》等)、游仙之人(如《龍城錄》、《玉溪生詩詳注》等)。由此看來,在漢代存飽受爭議的鴻都門學,在唐代士人眼中已經可以視為具有某種積極象征意義的典故,而在唐代士人又較為重視通過科舉進士科中的詩賦創作而求得入仕的機會,這與鴻都門學創立的初衷正好契合,所以將“鴻都”與“石經”相聯系的背后,是士人思想中文學與經學地位微妙變化的一種體現。
宋代的《東觀余論》和《廣川書跋》均與書法藝術有關,它們記載熹平石經更多的是考察石經所具有的書法藝術價值。將“鴻都”與“石經”相關聯,可以看出后人更看重石經或者蔡邕的書法藝術價值,而對蔡邕所書石經的經學價值并未太多關注,后世的史料之中也多將蔡邕定格為文學藝術家,并沒有過于強調其在經學史上的貢獻,這與傳統文學觀念的演變有著密切的聯系。在史料中還可以找到一則關于蔡邕與鴻都門學直接相關的資料,出自于唐代張懷瓘的《書斷·飛白》,“按漢靈帝熹平年詔蔡邕作《圣皇篇》,篇成,詣鴻都門上,時方修飾鴻都門,伯喈待詔門下,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為飛白之書”[6](P80)。這則資料在唐以前現存典籍中無從查考,資料可信度并不高,但這則材料則在唐以后的文獻中大量出現并被廣泛引用,從中可以看出后世學者對蔡邕在書法藝術方面貢獻的肯定,而鴻都門學作為文學藝術的符號化代表,將“鴻都”與蔡邕和石經相關聯,也許正是許多書法研究者主觀臆想而成,從這個角度分析“鴻都石經”這一說法的形成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宋明理學時期,空衍義理成為經學發展的重要特點,不重詞章考據之學,“鴻都石經”這一誤說因而被諸多文獻因襲,直至清代,樸學的出現,“鴻都石經”這一誤說才被考據學家所糾正。由此可見這一誤說的出現、流傳,與經學發展狀況密切相關,當然這中間還夾雜著文學藝術觀念的變化所導致的士人思想變化等因素的影響。
[1](宋)范曄·后漢書[M].(唐)李賢等注,北京:中華書局,1965.
[2](唐)李綽·叢書集成初編·尚書故實[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3](宋)黃伯思·東觀余論[M].北京:中華書局,1991.
[4](宋)董逌·廣川書跋[M].北京:中華書局,1985.
[5](清)皮錫瑞·經學歷史[M].周予同注釋,北京:中華書局,1959.
[6](唐)張懷瓘·書斷[M].石連坤評注,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
(責任編輯:顏建華)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Hongdu Inscriptions Error
Gao Bin
(School of Literature,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Hongdu inscriptions” error can be traced back to Shang Shu stories at Tang Dynasty, which becomes anddress of Xiping inscriptions after deducing of non-Confucian works in Song dynasty. It is not the main reason that people can not distinguish the location and character of the Imperial College and Hongdumen School in Han Dynasty to cause this error.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 classics study’s development in Tang Dynasty contribute to the formation of this error, reflected as the conservative method of Confucian classics study examination to be an official. Compared to it, Jinshi subject(an examination of composing) is more flexible , which is emphasized by scholars. In addition, the changes of art’s status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scholars’ thoughts after the appearance of Hongdumen school, which makes the scholars have different attitude toward arts and Confucian classics study.
Hongdu inscriptions,Confucian classics study,arts,Hongdumen School
2015-11-08
高斌(1988~),男,山東泗水人,南開大學文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文學與文化,中國古代文學思想史。
I206;K204;G256
A
1673-9507(2016)01-00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