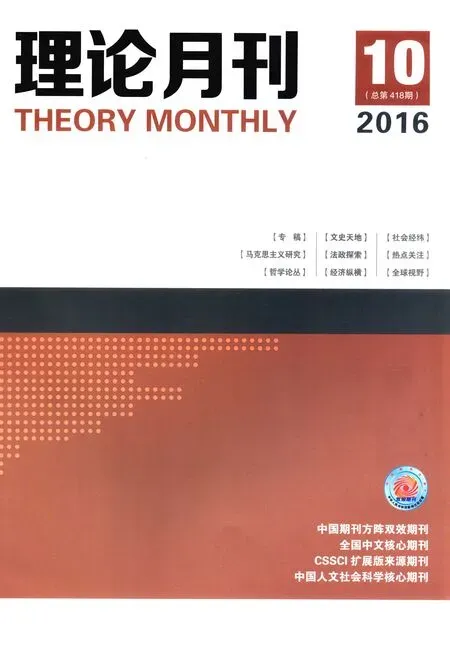論詞義的排斥
□陶 智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浙江杭州 310028)
論詞義的排斥
□陶智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浙江杭州 310028)
詞義演變過程中有一種“由褒而貶”或“由中性而貶”的現象,這是由于語言的使用主體所發生的情感變化,在語言使用中的投射而使得語言要素發生了某種方向的演變。即在一定的情況下,一個語言單位內令人厭惡的語言要素(語音或義位)會排擠或排斥其它的語言要素(語音或義位),語言內部原先存在并一直被使用的某些要素被逐漸排擠出這一語言單位,而使得這一語言單位內發生一些語音或詞義上的變化。一個詞的貶義義位會在社會心理的作用下越來越凸顯,最終削弱甚至完全排斥該詞義的其它義位,而占據該詞全部義域。
詞義演變;貶化;排斥;避諱
[DOI編號]10.14180/j.cnki.1004-0544.2016.10.014
1
“小姐”是現代社會的一個使用頻率較高的詞,也是一個引起語言學界較高關注的詞。一般認為,該詞產生于宋代,據《稱謂錄》載,該詞始為賤稱,至元代成為富貴人家未出嫁女子的尊稱。俞理明詳細考察語料后認為,對宋代“小姐”最初的意義比較恰當的解釋應該是名字用字,稱排行在末的女子。它的使用,沒有貴賤、婚否的差別,大約和《醒世恒言·蘇小妹三難新郎》中的“小妹”相當,用作人名,稱青年婦女或者小女孩都可以,和它相對可以作為佐證的是“大姐”,本是俗間用語,作為小稱,含有愛昵的意義,也可以不拘排行,直呼年輕女子為小姐。[1]至元代,“小姐”一詞和出身門第聯系在一起,成為一個表示女子出身地位的稱謂了。以后,“小姐”一詞也多被用作尊稱為人們使用,至建國后,“同志”成為人與人之間最普遍的稱呼,“小姐”一詞也暫時退出歷史舞臺。改革開放后,由于南方開放地區開始稱年輕女子為“小姐”,很快,這個詞被全社會廣泛使用,一般用為對年輕女子的尊稱。但是,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由于色情行業的猖獗,從事性服務行業的女性也成為“小姐”,這個詞開始成了這一特定行業的職業用語,即妓女的專稱。在民間,現在已經很少再稱普通的年輕女性為“小姐”的了,如果有人稱某女性為“小姐”,很多情況下,對方會很排斥的。這說明“小姐”一詞原先的表敬稱的意義正被 “指稱從事色情行業女性”的意義所排擠,而處于逐漸弱化的過程。這種詞義的變化和社會心理關系密切,劉曉玲認為:“正經人家的女性為了將別人對自己的稱呼與對這些人的稱呼相區別開來,常常自動退出這個稱呼語的應用客體范疇。很明顯,這種排他性和以前有所不同:這次的排他是被動的,其中一部分應用客體的退出不再是由于權勢或者社會地位的迫使,而是由于自身的道德觀念。”[2]
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常常厭惡不好的事物而喜愛好的事物,對于壞的、惡的、丑陋的,不但會羞與為伍,且拒之甚遠,懼怕沾染了這些惡氣,而使得丑惡的事物獨居一處。這種現實生活中“避惡”的情況會投射在語言中:即在一定的情況下,一個語言單位內令人厭惡的語言要素(語音或義位)會排擠或排斥其它的語言要素(語音或義位),使得語言內部原先存在并一直被使用的某些要素被逐漸排擠出這一語言單位,而使得這一語言單位內發生一些語音或詞義上的變化。這是語言的使用主體所發生的情感變化在語言使用中的投射而使得語言發生了某種方向的演變,對某些詞的語音演變或者詞匯替換產生較強作用,避諱即是這種機制的典型表現,其中表現最明顯的就是所謂的“禁忌字”。李榮曾說:“研究語言的人常常排斥有關‘性’的字眼,編輯字典跟調查方言都是這樣。其實說話的時候要回避這類字眼,研究的時候是不必排斥的,并且是不能排斥的。就學問本身說,這類禁忌的字眼常常造成字音的更改,詞匯的變化,對認識語言的現狀跟歷史,都是很重要的。”[3]在現代漢語中,有些字音獨占一個音節,很可能是和避諱相關,如“死”,李榮說:“北京的‘死’字沒有同音字,大概是因為別的按照音變規律可能讀si的字都避開了。”“廣州‘死’沒有同音字,可能也是同樣的原因。而‘糙’北京話和河北等地方言不讀去聲,而且也沒有一個字和‘糙字去聲’同音,也是和避諱相關。”[4]其實,還有“尿”“屌”等字在現代漢語中也都幾乎獨占一個音節,應該也是出于避諱的原因。這種機制對于歷時上的詞匯替換也會起到很大作用。王力曾指出:“避諱和禁忌是概念改變了名稱的原因之一。”[5](P643)汪維輝指出,如“雀”對于“鳥”、“太陽”對于“日”等就是屬于這一類型。[6]
從“小姐”一詞的詞義變化過程,可明顯看出這種排斥機制也可在詞義演變中能產生較為關鍵的作用。“小姐”本指對年輕女性的尊稱,這種稱呼在使用的時候是不避身份、職業、地位等因素的,故而,對于從事色情行業的女子當然也可以“小姐”稱之。當一些人知曉對“妓女”一類的人也可稱之為“小姐”,從內心對該詞產生了反感和厭惡,而不愿讓“小姐”一詞來指稱自己,使得該詞指稱妓女的意義凸顯,而變得越來越鞏固,并漸漸開始排斥原先表尊稱的詞義內核,慢慢占據該詞的中心義域。
目前,“小姐”一詞在面稱時已經很少能聽到直呼別人為“小姐”的了,這一稱呼基本已經被其它詞代替,如“女士”、“美女”、“美眉”等。當然,這些替代詞目前仍不能完全代替“小姐”一詞的功能。在一些正式場合或強調身份標記的情況下,還是可以使用“小姐”的,比如“售樓小姐”、“公關小姐”等。這也說明目前這種排斥機制對該詞的制約影響并不徹底。這種排斥的程度一般取決于社會對“小姐”所指稱“妓女”意義共識的強弱,當然,和“小姐”這一表敬語的替代詞的成熟也有一定的關系。
2
歷史上,這種詞義排斥現象也影響了一些詞的詞義發展演變。其過程主要有兩種模式:
第一,當一個詞詞義的上位概念包含褒貶兩重意義時,下位概念的貶義有時會直接排斥該詞義的上位概念。比如“臭”,前人所論頗多,本來統指氣味,無所謂香臭。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人通于鼻者謂之臭,臭者,氣也。”《尚書·盤庚》:“無起穢以自臭。”疏:“古者香氣穢氣皆名為臭。”王筠《說文釋例》:“臭為腥臊羶香之總名,引申為惡臭。”上古漢語中,“臭”可以指臭氣,也可指香氣。如《左傳·僖公四年》:“一薰一蕕,十年尚有臭。”“臭”即為臭氣,而《周易·系辭》:“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臭”即為香氣;有時候,“臭”也可以統指氣味,如《詩·大雅·文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鄭玄箋:“耳不聞聲音,鼻不聞香臭。”《孟子·盡心下》:“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聲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蔣紹愚說:“‘臭’從上古統指臭氣和香氣,發展到后來只指臭氣,也就是說:在上古,‘臭氣’是‘臭’在特定語境下顯示出來的下位義,而到后來就成了‘臭’的固定的詞義。”[7]上古漢語中,“臭”表示氣味,至戰國末年,“臭”開始漸漸專門表示臭惡義。王力認為:“漢語里的‘臭’和英語里的smell有相似之點,‘氣味’是向‘惡臭’轉化的,現代吳方言(至少在蘇滬一帶),所謂‘氣味得來’就是‘臭得很’,而上古的‘臭’字正是這樣地由‘氣味’向‘惡臭’轉化的。這一轉化過程在戰國末年就開始了。”①在現代漢語口語中,“氣味”一詞也多偏指臭味,如說“這里氣味很大。”“這是什么氣味?”“氣味”都指難聞的味道;而當特別指稱香味時,一般也說“這種味道(味兒)很好聞”而不說“這種氣味很好聞”。[5](P627)唐鈺明曾調查了先秦兩漢主要古籍后,指出:“戰國后期表‘惡臭’義的臭僅占9%(79例占7例),進入漢代,面貌便大為改觀。查西漢典籍4部,共見‘臭’字24例,表‘惡臭’義的有6例,占25%;東漢典籍3部,‘臭’字24例,表惡臭義的有23例,占96%。”并由此得出結論:“漢代以降,除成語熟語(比如‘乳臭未干’、‘臭味相投’)以及個別仿古的文字外,‘臭’字的確已‘專指氣味難聞’了。”[8]祝注先說:“‘臭’的‘穢惡’義雖然生成古老,但是衍化而為基本詞義,其確立時代,大概就是‘臭’的‘香’義在語言表達中消失的時代。兩者是相為因應的。”[9]從“臭”的詞義發展軌跡可以看出,“臭”本指氣味,無所謂香臭,但正因為如此,該詞常常表示臭惡的事物,這漸漸引起人們在使用該詞時的排斥現象,即不愿意把美好氣味的事物再用“臭”來表示,這一認識逐漸受到全社會的認同,從而凸顯了“臭”的“惡臭”義,導致了“臭”慢慢就縮小了指稱范圍。漢代以后,“臭”的“惡臭”義漸漸排斥了“臭”的“芳香”義,從而完全占據了該詞的詞義構成。如《大正藏》收東漢題安世高譯經中,“臭”出現共23次①安世高譯經頗多爭議,參方一新、高列過著《東漢疑偽佛經的語言學考辨研究》31—34頁,商務印書館2011年。因為此處不涉及東漢以后“臭”的用法,故調查安世高譯經時未辨真偽,《大正藏》所題安世高譯經皆在統計范圍之內。,其中只有《陰持入經》下卷末所附《佛說慧印百六十三定解》:“無臭、無嘗、無更、無識”中的“臭”為氣味義,余者皆為“惡臭”義。而《陰持入經》下卷末所附《佛說慧印百六十三定解》殆為后世經師所撰,②釋印順指出:“(《陰持入經》)經后,麗藏本附有‘佛說慧印百六十三定解',宋本等是沒有的。考六三二《佛說慧印三昧經》說:慧印三昧的境界,‘佛身有百六二事,難可得知'(十五·四六一中—下)。百六三事,與《慧印經》相當,但文字小異。可能是古師對慧印三昧,依原文而校勘修正,別出流行,應編在《慧印三昧經》等以后。”參釋順印《華雨集》中冊《讀〈大藏經〉雜記》中華書局2011年,第171頁。其中的“臭”應為仿古文言詞。另外,“臭”在現代漢語語音上獨占一個音節,應該也是由于避諱心理作用下而引起的對其他同音詞讀音上的排斥。
再如“爪牙”詞義的演變,大致也是屬于這種模式。“爪牙”可指助手,本來應當是中性詞,無所謂褒貶,如《左傳·成公十二年》:“略其武夫,以為己心腹,股肱,爪牙。”《漢書·李廣傳》:“將軍者,國之爪牙也。”這即指褒義方面。也可指殘虐的幫兇,如《史記·酷吏列傳》:“其爪牙虎而冠。”又:“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于文學之士。”這兩個下位概念義并存,直至近世。但在近代而產生了詞義的替換,現在“爪牙”一詞的“得力助手”義已完全被“幫兇”義所排斥。
第二,一個詞先引申出貶義義位,新產生的貶義義位再排斥該詞的舊義,至舊義完全消失,而義域完全為新產生的貶義所占據。如“淫”,本義為浸漬。《說文》卷十一“淫”下:“浸淫隨理也,從水聲。一曰久雨爲淫。”引申為貪色、淫蕩,《易·系辭上》:“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漢劉向《說苑·反質》:“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奸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奸者惑也。”《晉書·刑法志》:“今盜者竊人之財,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無殺害也,則加之以刑。”《紅樓夢》第五回:“情天情海幻情深,情既相逢必主淫。”又特指通奸、奸淫。《小爾雅·廣義》:“男女不以禮交謂之淫。”《南史·袁彖傳》:“茍蔣之弟胡之婦為曾口寺沙門所淫。”《三國演義》第九回:“太師淫吾之女,奪將軍之妻,誠為天下恥笑。”清東軒主人《述異記·飛蠱》:“畜蠱之家,奉此蠱神,能致富,但蠱家妻女,蛇必淫之。”可見“淫”指男女之間不正當關系義起源尚早,至遲在先秦就已有產生。這個義項又可寫作“婬”,《說文·女部》:“淫,私逸也。”段玉裁注:“婬之字,今多以淫代之,淫行而婬廢矣。”《廣韻·侵韻》:“婬,婬蕩。”《集韻·侵韻》:“婬,通作淫。”雖然“婬”專門表示男女不正當的關系,但“婬”“淫”通用,而文獻中一般也多用“淫”來表示“婬”的意義。一直到中古,“淫”的這一意義和其它義可并用。但至遲在元代,“淫”的義域已經被“表示男女不正常關系”所占據,而其他的義項已經在口語中消失。“淫”在《關漢卿戲曲集》中出現十例,分別為“淫欲”(《魯齋郎》第三折)、“富貴不能淫”(《謝天香》第一折)、“飽暖生淫”(《救風塵》第三折)、“淫濫”“淫亂”(《救風塵》第四折)、“荒淫好欲”(《望江亭》第一折)、“淫詞”(兩次,《望江亭》第四折)、“淫奔”(《竇娥冤》第二出)、“好色荒淫”(《竇娥冤》第四出)。從這十例來看,除卻“富貴不能淫”等為古熟語外,余者所用的“淫”指男女間不正當的關系,用法均為貶義。這說明,至少在元代,“淫”這個詞已經完成了詞義的排斥,即指稱“男女不正常關系”的意義已經占據了該詞的核心地位,而其他的義項均被這個義項所排斥而退出了“淫”的詞義系統。清代《鏡花緣》中“淫”出現三十九次,皆指男女不正當關系,且多為詈詞,其中最常見的搭配就是“淫婦”,高達三十六例。從“淫”的意義演變來看,這一排斥過程時期較長,從先秦至唐宋,“淫”的詞義都未曾被排斥,而至元代才發生了質的變化,這有可能是與宋明理學對于兩性關系及女性本我的束縛而形成了對于男女不正常關系的厭惡的社會風氣和社會心理。
“調戲”,一詞現在一般特指對婦女進行侮辱性的挑引戲弄。該詞至遲見于東漢,但非特指該義,《后漢書·馮衍傳下》李賢注引漢馮衍《與婦弟任武達書》:“醉飽過差,輒為桀紂,房中調戲,布散海外,張目抵掌,以有為無。”此述其妻子酒醉之后失態之舉,當為嘲弄之義,本非貶義。至宋代,該詞仍作此義解,黃庭堅《歸田樂引》:“對景還銷瘦,被個人,把人調戲,我也心兒有。”劉克莊《念奴嬌》:“白發長官窮似虱,剛被天公調戲。”宋辛棄疾《尋芳草·調陳莘叟憶內》詞:“更也沒書來,那堪被,雁兒調戲。”這些“調戲”均為一般的嘲弄、戲弄之義,而無關侮辱女性之舉。但至元代,該詞延伸至用言語或行為對女性的侮辱挑逗,而且該義項迅速排斥了“調戲”一詞的通常用法,而占據該詞的核心。元石德玉《秋胡戲妻》第二折:“你怎敢把良人家婦女公調戲。”《醒世恒言·李玉英獄中訟冤》:“玉英將那禁子調戲情由,告訴眾人。”《金瓶梅》中“調戲”一詞出現十四次,《水滸傳》“調戲”出現十次,均指用言語或行為對女性的侮辱性挑逗,可見,至遲在元代,“調戲”已經完成了詞義排斥過程。
3
蔣紹愚曾經說:“詞義的發展不可能是突變,不可能昨天是褒義,今天就是貶義,中間必然有一個過渡時期,那么在過渡時期中,是否會一個詞同時兼具相反二義呢?我們想象,在過渡時期,應該是褒義逐漸模糊,變為中性,然后由中性逐漸變為貶義。”[10](P143)張永言曾介紹了赫爾曼·保羅所提出的意義的 “貶降”:“所謂意義貶降是指一個詞的否定的感情色彩產生和加強,甚至吞沒其他意義,成為詞義的中心。這種詞義變化過程往往跟一定的社會階級對人和事物的評價有關,主要見于某些指人的名詞。例如:老爺、少爺。又如:英語knave(無賴,壞蛋,流氓)本是男孩子的意思。舊時窮人的男孩子常常給人家當仆人或聽差,所以knave的意義很自然地轉為‘仆人’,而主人對仆人的態度又給這個詞加上否定評價的感情色彩,這個色彩逐漸變成了詞的中心意義,于是在現代英語里knave就只有 ‘無賴’、‘壞蛋’、‘流氓’的意義了。”“類似的例子在英語里還有不少,如black-guard:仆人→壞蛋,惡棍。Villain:田莊上的農民→鄉巴佬,粗人→壞蛋,惡棍。”[11](P57)
從本質上看,詞義的“由褒而貶”或“詞義的貶降”,內在的原因即是由于詞義義位的排斥而造成的。很多由褒而貶,或由中性而貶的詞,如“勾當”“妓”“流氓”“同居”“玩弄”“賄”“誣”“嫖”“蠢”“媚”“奇葩”等,應該都是受詞義排斥模式的影響而完成了詞義的演變。①當前對于由“中性而褒”的詞義演變,已有較多學者討論,如鄒韶華指出現代漢語中有一些中性名詞在一定的語境中會產生語義偏移,且多為正向偏移;沈家煊介紹了國外學者通過實驗提出的“樂觀假說”,其心理基礎是總是看重和追求好的一面,摒棄壞的一面;江藍生提出了詞義演變的語義正向偏指機制。都從不同角度對該問題進行探討。參鄒韶華《名詞在特定環境中的語義偏指現象》,《中國語文》1986年第4期;《中性詞語義偏移的原因及其對語言結構的影響》,《語法研究和探索》4,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沈家煊《不對稱和標記論》185—189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江藍生《“趁錢”南北詞義考》,《歷史語言學研究》8,商務印書館2014年。這種排斥機制對詞義的影響是和人們的集體共知密不可分,而且決定于集體共知的程度。當一個詞所指稱的概念為社會心理共同排斥,比如“臭”的“惡臭”義對于其上位概念“氣味”義,則排擠過程較為徹底。如果詞所指稱概念為言語社團所接受的程度不完全,則詞義排斥的影響會弱化,詞義變化也不徹底,比如“小姐”的尊稱義在某些地區、某些社團容易被接受,而對于其他一些地區、一些社團則更易被排斥,這應由于該詞所指稱的妓女義未能完全取得社會共識,而導致了詞義排斥過程比較緩慢和不徹底。
[1]俞理明.小姐正名[J].語文建設,1997,(5).
[2]劉曉玲.淺論“小姐”“先生”的歷史發展[J].語言研究,2002,(特刊).
[3]李榮.談“入”字的音[J].方言,1982,(4).
[4]李榮.語音演變規律的例外[J].中國語文,1965,(2).
[5]王力.漢語史稿[M].北京:中華書局,1980.
[6]汪維輝.說“鳥”[A].太田齋·古屋昭弘兩教授還歷記念中國語學論集(中國語學研究開篇(單刊))[G].東京:好文出版社:2013.15.
[7]蔣紹愚.從“反訓”看古代漢語詞匯研究[J].語文導報,1985,(7-8).
[8]唐鈺明.“臭”字字義演變簡析[J].廣州師院學報,1987,(2).
[9]祝注先.一詞三釋辨疑—關于‘臭'的詞義[J].語文研究,1983,(2).
[10]蔣紹愚.古漢語詞匯綱要[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11]張永言.詞匯學簡論 訓詁學簡論(增訂本)[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
責任編輯文嶸
H13
A
1004-0544(2016)10-0076-04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項目(12JJD740003);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第58批面上資助項目(2015M581915)。
陶智(1978-),男,安徽蕪湖人,文學博士,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博士后流動站研究人員,嘉興學院文法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