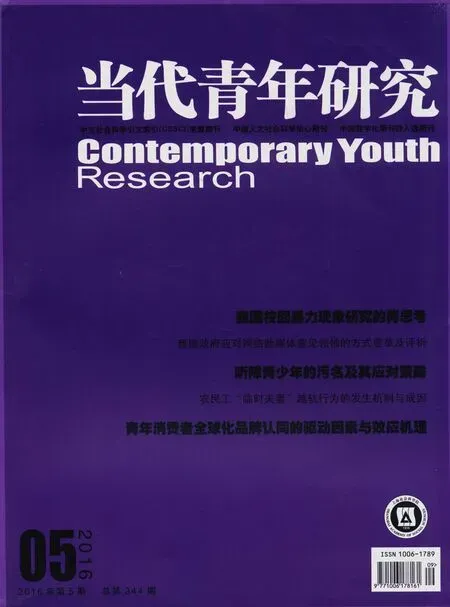網絡社交歷史與中國早期網民個體生活空間變遷
畢曉梅
(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
網絡社交歷史與中國早期網民個體生活空間變遷
畢曉梅
(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
中國最早的網絡移民自始至終伴隨了中國互聯網的發展,他們的網絡使用行為形成了一段不長但至少可以追溯的歷史。早期的網絡社交將個體從現實物理空間局限中解放出來,具有高蹈于日常生活之上的虛擬色彩;隨著網絡空間中現實好友的增多和移動位置社交的興起,網絡空間的虛擬色彩漸漸褪去;如今,日常生活中的人際交往不再是在某一單一空間中進行,人們不斷地在物理空間與網絡空間切換,亦或同時在場。
網絡社交;個體生活空間;臥談會;宅男宅女;移動位置社交
十幾年來,中國早期網民的個體生活空間隨著生命軌跡的變遷發生著巨大變化,從大學時代的集體宿舍到畢業之后的私人空間,再到結婚生子之后的家庭空間。也正是在十幾年的時間里,網絡社交日漸滲透到他們日常生活的空間結構中。如今在城市中,網絡已經如水、電、空氣一般無處不在。網吧,帶著互聯網發展早期的鮮明時代印記,已經黯然退居一隅,在城市中慢慢消失。網絡使用的空間和情境都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它已經滲透到個體日常生活空間的核心區域,甚至成為個體身體的一部分,對個體生活空間結構的分析開始變得重要——現實空間和社會空間,即以個體身體位置為出發點的現實空間和個體借助網絡社交等媒介所能觸及的社會空間。如今個體生活空間越來越變成虛擬與現實交織的領域。以手機、平板電腦為代表的便攜式移動終端突破了個體生活空間的物理邊界,使人們從家庭、學校、辦公室等各式各樣的物理空間中解放出來,使個體與他人、與世界保持連接,同時也使人們互相隔絕。此時,回顧互聯網發展早期開始的這段變化歷程,有助于我們理解新媒介環境下個體如何將網絡社交納入并建構自己的生活空間,網絡社交如何參與個體協商和維護自己與他人、與社會的邊界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使用者如何賦予技術以個人化的意義。本文的數據資料來自從2008年開始的訪談和參與式觀察,這些受訪者都是網絡社交的早期使用者,他們都參加了2007年騰訊的“十年”故事大賽,筆者當時搜集了數百篇網友對10年來自己使用QQ的回憶和描述性文本。利用NVIVO對其進行編碼,篩選出了焦點議題,并選擇了其中的十幾位進行了深度訪談,并與其中部分人成為朋友,見證了十幾年來他們個體日常生活的變遷及網絡在其中的意義。
一、社會中個體生活空間結構
個體生活空間并非一個物理學意義上的邊界概念,而是個體與他人、與世界之間的文化邊界,既有現實物理空間因素,也有虛擬空間和虛擬聯系的內涵。本文以個體生活空間作為分析單位來考察新媒體環境下個體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借助網絡社交協商與他人及世界的關系、建構自己的生活空間。
個體的行動不是發生在真空中,而是要受到日常生活中特定環境和時間的局限。日常生活是人們直接經驗的文化世界,區別于科學的、理性化的世界。胡塞爾和舒茨的生活世界更重視其整體性和哲學意味,但舒茨在《生活世界的結構》一書中深化了對于生活世界的分析,進一步分析了生活世界的層次和結構,加入了時間和空間的視角。就空間的維度而言,生活世界是以個體身體位置為坐標原點,根據“社會距離而進行的空間分布”[1]對于每個普通個體來說,在其所處的生活世界中, 他/她主要是對日常生活世界中以他/她為核心的、處于他的活動范圍之內的那一部分感興趣。他/她的身體位置始終是各種行為和空間系統的出發點。本文所談的個體生活空間正是以身體為核心和起點,個體與他人與社會之間互動所形成的社會文化空間,是包含著物理現實和社會互動兩個維度的潛在空間,是個體與社會發生作用的節點。
日常生活中人們不是以物理距離來認知空間,也并非把自己視為空間中的一點并以此來衡量距離,真正有意義的空間決定于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關注焦點的距離。[2]因此,以個體實際的“此在”為出發點的個體生活空間具有一定的層次和結構。在個體可觸及的區域中, 一些核心區域是可以由直接行動來參與、影響和改變的部分,由此向外延伸便是那些可以“潛在地觸及的區域”、不可以直接觸及“卻可以通過間接行動影響的區域”,上述兩種區域構成了舒茨所稱的可以“直接經驗”的世界,在可以“直接經驗”的世界之外還有“同時代世界”“前人世界”和“后人世界”[3]。本文所要探討的個體生活空間也就是舒茨所說的“直接經驗”的世界,它具有自己的核心區域、邊界,同時也有著一定的結構。
在西方語境下的個體的獨立性特征,例如,以弗洛伊德為代表的西方心理學家將個體視為無意識和本能的結構體,將個體與他者隔絕開來。但是,這一理論越來越多地受到挑戰,以溫尼科特為代表的“客體關系理論”學者認為個體是交流的執行者,也是互動行為的產物,個體的獨立是以意識到自己與他者的聯系為前提的。中國語境下的個體更是關系性的存在,個體與他者的關系是分離中有聯系、獨立中含依賴。本文中的個體生活空間正是上述文化形式和文化行為發生的空間,一個充滿了張力和矛盾——依賴和獨立、信任和焦慮、滿足感和挫敗感、內在現實和外在現實——的空間。個體與世界之間以身體為邊界的物理界限是明晰的,使個體表現為自主的、獨立的個體,然而每個人又都與周圍的世界有著聯系。
有學者根據不同文化中的自我概念,提出了“獨立性自我”和“互賴性自我”的概念。“獨立性自我”強調個體的完整性和獨立性,“互賴性自我”強調個體與他人、與社會的聯系和依賴。[4]其實,每個人都同時具有這兩種自我特性,個體生活空間的邊界正是這兩種自我特性、內向性和外向性協商協調的結果。個體在日常生活中需要不斷地與周圍的世界協商,以調整自我的邊界,平衡這些矛盾和張力。列車是中國人主要的交通工具之一,列車車廂是一個特殊的微型生活空間,然而它也具有自己的結構。對于旅客來說,它是一個陌生的環境,人們匯聚在這個陌生的環境中之后,會迅速建立起自己的空間秩序——將行李和生活用品分別擺放好,根據自己當時的心境和同車廂旅客的情況、離睡眠時間和到達目的地時間的長短,決定低頭把玩手機或拿出一本書,將自己與外界隔絕,或者是與他人侃大山、玩游戲。這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建構和維護個體生活空間結構的一個例子。
二、消退的“臥談會”
寢室是中國早期網民大學階段非常重要的生活空間,也非常具有中國特色。進入大學之后,原本天南地北的4個人或8個人集中到一個特定的空間,共同度過接下來的幾年時光,經歷從陌生人到親如手足的過程。在這樣一個特定的共享空間中,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區分著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學習并逐漸習慣富有彈性地管理自我和他人的邊界。在早期網民關于大學生活的敘述中,寢室臥談會出現頻率非常高。晚上熄燈之后,寢室里往往不會馬上安靜下來,室友躺在床上談天說地,有時甚至通宵達旦。
寢室“臥談會”是中國的大學校園長期以來就有的傳統。20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的大學教育逐漸開始恢復,那時候好好讀書的氣氛比較濃,臥談較少,但彼時經濟困難,晚上有時會談論吃的,當時實行計劃分配,大概也很少談未來;20世紀80年代大學生的寢室臥談非常活躍,喜歡討論公眾話題;20世紀90年代可能是臥談會最盛行的時期,隨著改革開放,臥談內容也更加豐富,理想、擇業、愛情、搖滾、詩歌。那時網絡尚未普及,大學校園中的人際傳播媒介主要是固定電話、書信等。與今天的大學生相比,那時的學生與外界聯系相對較少,與今日的大學校園相比可稱得上是封閉的“象牙塔”,但彼時的校園并非缺乏活力。1999年進入大學的受訪者宏博在談到剛入大學的生活時說:“那時的人際交往主要就是同宿舍、同班同學之間,聊天、玩撲克、體育活動等。偶爾學校同級同學會組織一些活動,僅此而已。那時與校外的人接觸很少,與外校的人多是書信聯系,大多是與以前的同學交往。剛上大學時,書信保持聯系的人有六、七個,(頻率)大概是一兩個月甚至兩星期一封信。與家里人聯系通常是一周一次電話,偶爾也會寫信。”(2009年11月的訪談)
到了21世紀,大學校園中的寢室“臥談會”仍然廣受歡迎,《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和新浪校園頻道于2005年實施的一項調查顯示:“臥談會在學生中間有著廣泛的基礎:它以37.5%的獲選率位居學生最喜歡的校園交流方式的榜首,甚至超過了朋友私聊、集體活動和在BBS上灌水。”[5]但是不得不承認,由于手機、電腦以及眾多網絡社交媒介的出現,臥談會正在受到沖擊,甚至在某些情境下逐漸淡出大學寢室文化。20世紀90年代的大學生幾乎每日必談,而現在的大學寢室進行臥談的頻率已經大大降低,一周能有兩三次就已經算比較多的了。宿舍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電腦,大家晚上回來,寒暄幾句,便各自玩手機玩電腦了,每個人都很忙的樣子,有打游戲的、聊QQ的、看視頻的,就是沒有人說話。臥談會的盛況不再曾引起了媒體的注意,2007年搜狐新聞頻道編輯發表了題為“拯救宿舍臥談會”的專題報道,描述了作為大學校園的特殊現象——寢室“臥談會”近年來發生的變化,并提倡以新形式來拯救逐漸淡出校園生活的“臥談會”[6]。
“臥談會”的逐漸淡出源于各方面因素的綜合作用:一方面,大學生面臨的就業壓力逐漸增大,在校期間同學之間的競爭也日漸激烈,如競選學生干部、爭取保研、出國名額等。這些使得一些寢室即便是晚上的閑暇時間也是死氣沉沉,每個人都帶著自己的面具,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另一方面,部分年輕人越來越個性張揚,不喜歡整個寢室扎堆做一件事。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手機、電腦等新媒體技術及其所帶來的虛擬社交對原有的大學寢室文化產生著非常大的影響。
這里不是要判斷臥談和虛擬社交孰優孰劣,思考網絡社交不應該僅僅局限于網絡社交使用的即時效果、與面對面交流相比較的優劣,而應該將其放在人際傳播和日常生活的整體中來考察。關鍵問題在于,虛擬社交是否有助于個體維護自己日常生活的邊界,支持整體的人際關系的維持,使個體更加靈活自由地掌控自己的生活。大學寢室是一個具有豐富意涵空間,在大學寢室臥談會這個特殊情境中,物理意義上的個體空間與社會文化意義上的個體生活空間高度重合。本研究中的訪談對象大多對寢室臥談會記憶深刻,并在言談中流露出懷念的語氣。隨著個人電腦、筆記本、手機等終端日漸嵌入個體生活空間的核心區域,早期網民也大都經歷了畢業、就業、建立家庭的過程。但是,對于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說,傳統意義上作為一個物理空間的“家”的概念被隨時隨地可以攜帶的社會文化意義上的“宅”所取代。
三、“宅男宅女”的產生
《說文解字》云:“宅,所托居也。”“乇”有“長高”“升高”之意。“宀”為家的省略。“宀”與“乇”聯合起來表示墊高地基的住所。在中國古代文人的筆下,“宅”是安居樂業的物理空間,如“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寄托了知識分子對于“修身齊家”之“家”的豐富情感和道德意涵。近年來,作為一種生活狀態的“宅”文化十分流行。“宅”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本的“御宅族”,指那些對于某種事物或某個領域非常執著和沉迷的人群,他們對于自己沉迷的事物無所不知,而且隨時通過互聯網追趕最新的文字、音頻、視頻等相關的一手資料。他們的這種狂熱甚至到了封閉自己的地步。然而在中國年輕人中流行的“宅”未必對某個領域狂熱,而是指終日與電腦相伴,全天候地鎮守互聯網的生活狀態。“宅”已經成為一種比較普遍的社會現象,甚至成為年輕化的潮流。下面是一位宣稱“幾乎可以依靠電腦獲得想要的一切”的典型“宅女”的生活狀態:“不能與外界太脫節了,要不然我會失去方向……”[7]而她與外界保持聯系幾乎全部通過互聯網。中國早期網民如今已經逐漸在職場站穩腳跟,甚至嶄露頭角,具有較強的購買力,成為新媒體技術的主體消費人群。今天所謂的白領正是當年在學生時代接觸互聯網的中國早期網民。他們經歷過學生時代的網絡聊天、網絡游戲,互聯網已經融入他們的日常生活,許多人成為了上文所述的“宅男宅女”。
(一)嵌入生活空間的互聯網技術
早期網民較早使用互聯網技術,在他們畢業之后也繼續保持這一習慣。工作以后擁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間的早期網民,家中可以沒有電視,但是電腦和互聯網則不可或缺。在本研究的受訪者中,大多數單身受訪者在畢業后尋找住房時考慮的重要因素為是否有寬帶網絡。受訪者小陳前年畢業,在北京與朋友合租了一套兩居室的房子。房東留給他們一臺電視機,擺在客廳中,但是他們基本上不看電視,“回家以后基本上也都在網上晃悠,能上網誰還看電視呢”。(2009年年底的訪談和在線參與式觀察)
雖然,早年的網絡社交曾經掀起一股網絡交友的文化浪潮,但是當網絡社交的神秘色彩逐漸退去,網絡社交開始滲透進個體日常生活的時間和空間結構,并且形成凝聚各種社會聯系的文化、社會、心理空間,網絡人際媒介的形式本身卻在遁形,以至于人們慢慢地漠視它,視其為透明的、理所當然的存在,只有在網絡賬號被盜之后才發現網絡社交在自己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幾年下來,我的QQ上也有了一百多個好友了。現在這個網絡時代,這個物欲橫流的時代,這個依靠競爭才能生存的時代,人的精神越來越需要一種寄托。那一百多個好友成為了我精神寄托的載體,現在這個載體突然消失了,我的精神在這些日子里也似乎處于游離狀態,無法擱淺。當然,這個QQ號也發生了許多故事,伴隨我成長,帶給我許多源于友誼、愛情上的歡樂,也有讓我難以忘懷的心酸。那些曾經的歡樂與痛苦,歡笑與淚水,充斥著我空白的人生,我真的很感謝這個QQ號帶給我的一切。有些東西,失去了才發覺它的珍貴。失去了QQ號的那一刻,我才將這句話理解得那么透切。”(2011年網友X自述)
早期網民大多有過號碼被盜的經歷,他們對這些經歷的描述從另外一個側面闡釋了網絡人際媒介在他們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和意義。很多人在描述號碼被盜的經歷時使用了這樣的語句:“心被抽空了”“別扭”“心痛”。一位網友這樣講述他QQ號被盜的經歷:“當我發現跟隨我6年多的QQ號被盜的那一刻,我才意識到我不只是失去了一個由數字組成的號碼,我將失去QQ號上那么多高中同學、大學同學以及網上認識了幾年的貼心網友的聯系,于是,我開始心痛起來。每天,已經習慣了打開電腦的時候,就隨手打開QQ,看看上面同學、朋友的留言,或者把自己的近況告訴他們。現在,我重新申請的一個QQ號,可上面卻空無一人,怎么用著都感到別扭。”(2011年網友XZ自述)現在的騰訊QQ已經加大了對于號碼的密碼保護力度,QQ號碼也不再像當年那么難申請,雖然沒有了幾年前盜號瘋狂的現象,但是風險仍然存在,尤其是隨著QQ會員、QQ游戲等業務的擴展,擁有大量虛擬貨幣的網絡賬號更存在風險。
總而言之,中國早期網民接觸網絡時間比較早,對于網絡社交應用或多或少都產生一定程度的依賴;同時,隨著早期網民相繼離開大學校園,擁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間,同時也將網絡帶入個體生活空間的核心區域——書房、臥室,乃至隨身攜帶。網絡社交已經嵌入個體日常生活的空間結構,成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虛實之間:“隱身”在線
“我們奔三的80后,我們隱身上QQ看看誰在線呢,看見熟悉的人,想說點什么 ,竟又什么也沒說,就這樣糾結著。我們把空間刷新了一遍又一遍,看看誰更新心情了,誰更新日志了,回復了符號,卻沒有回復句子。”這是2011年在網上瘋傳的一個視頻《今年我二十七八歲》中的對白,很形象地描繪了“宅男宅女”們使用網絡社交的典型行為和心理特征。
最早流行的即時通訊騰訊QQ具有自定義在線狀態的功能,“QQ 2007 正式版”開始增加了豐富的“在線狀態”(簡稱為:狀態)功能,在原有“在線”“離開”“隱身”和“離線”等四種狀態的基礎上,新增了“Q我吧”“忙碌”“靜音”三種狀態,使用者可以在狀態菜單中自由切換在線狀態。同時,使用者還可以根據需要編輯短語或句子,將其作為自定義狀態,編輯成功后狀態文字直接在自己與好友的列表中展現,以便好友隨時了解自己的在線情況,也為對方是否選擇與你即時聊天提供指引。當時,在這些眾多的在線狀態中,被使用最多最頻繁的便是 “隱身”狀態。在經歷了早年網絡聊天的瘋狂階段之后,早期網民大多養成了以下習慣:亮著的電腦屏幕右下角,眾多圖標中總是少不了小企鵝QQ,有的人甚至幾個賬號同時在線。然而,不管擁有幾個帳號,統統選擇隱身。他們既不愿意現身,也未必在等某個人上線,可是還要登陸即時通訊,然后置于隱身狀態。這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這一類人也有了“潛水族”等稱謂。移動終端的多樣化和便攜性將人際傳播行為編入無處不在的網絡中,個體隨時隨地都可以與他人、與世界聯結,他人“神秘地存在又缺席,在這里也在那里,在咫尺也在天涯,在家也離家,接近也有距離”。[8]通過對網民自述文本資料的整理和分析,使用者選擇隱身在線的原因大致有兩種:
1.個體自我邊界的維護
個體日常生活空間有自己的核心,也有一定的邊界,個體與外界之間的邊界協商和維護每時每刻都在進行。網絡社交所提供的隱身在線功能使個體在保留了一絲與外界聯系的同時,又能免于打擾:“當陌生人打出‘美女,讓我看看你啊’這樣的要求時,我開始隱到屏幕后面,將QQ設成隱身,只有熟識的好友上線,才會聊上一陣。”(2011年網友MC自述)
一些受訪者選擇隱身是因為避免看到不想見的人,獲得一種安然的“隱心”狀態:“曾經因為網絡游戲認識一個女孩,隔著好幾個城市,開始只是簡單地聊天,沒有視頻,僅僅因為發了一張多年前看不清楚的照片,卻莫名其妙地在夜里開始思念起另外一個城市素未謀面的這個女子,每日工作之前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打開即時通訊,顯示在線,焦急地等待著她的出現,我不清楚是否生活中的她也能如此讓人印象深刻,還是僅僅是眾多平凡平淡中的一個。或許是最終厭倦了我無休止的追問,然后她不再理我,終于發現自己的心胸原來也沒我想得那么開闊。不想再見她以及另外的不希望見的人,因為會有所憂傷,于是安靜地將她刪除,回到了我隱身隱心的狀態。”(2011年網友WM自述)
更多人選擇隱身也是出于一種方便他人方便自己的考慮。處于在線狀態則相當于給他人一個提示,歡迎別人來和自己聊天,當在線的其他人看到你在線時,免不了要來寒暄幾句,你也不好意思不去問候一聲,而其實雙方都未必希望聊下去。而隱身便是一個讓彼此都輕松的策略,有事便發條信息過去,愿意聊就聊幾句,不愿意聊或正處于忙碌狀態,那也省得麻煩。
2.獲得心理安慰
既然他們不愿意聊天,也未必在等某人上線,那么隱身在線意義何在?許多網民在敘述中都提到了“溫暖”“信任”“安心”等字眼。“直到今天還是習慣打開電腦后,就在即時通訊上掛著。然后,在日志上寫下這一天的心情。隱身也好,忙碌也好,只要看著朋友們的頭像,即使彼此不說話,心里也會溫暖。”(2011年網友ZLY自述)
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行動主體,個體需要一種植根于無意識中的對于他人和世界的信任和依賴感,形成吉登斯所說的“本體安全”,而這種信任與本體安全需要在日常生活的互動與聯系、事件與規范、交流與語言中產生。網絡社交所提供的人際互動似乎有助于使用者獲得這樣的安全感:“我們的好友名單常常灰暗一片,卻很少有人將他們刪掉。也許,我們在乎的只是一種感覺,一種在偌大的城市里依然有自己熟悉的人的感覺,呆在QQ上,我們就似乎還呆在一種溫暖和熟悉的群體里。雖然彼此都隱身,但都在關注著對方,當你有所需求,登錄的上線提示就會從右下角一直頂到屏幕的頂端,在鋼筋水泥的城市,在灰暗的QQ頭像后面,依然隱藏著可以釋懷的溫暖和信任。”(2011年網友XZ自述)
綜上所述,隱身作為網絡社交媒介的一種特定功能,它使個體可以靈活自由地轉換和協商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的邊界,滿足自己對本體安全和個體生活空間的需求。在隱身的過程中,個體將網絡社交媒介納入自己日常生活的時間和空間結構中,掌控它并使之或多或少在日常生活的常規中變得無影無蹤。
四、從移動位置交友到隨身攜帶的“朋友圈”
移動位置交友是基于地理位置的移動社交應用,使用者通過安裝有特定軟件的移動終端認識周圍的陌生人,將網絡關系轉換為線下的真實關系。移動社交的新意在于提供了一種新的基于現實位置的社交形式,也就是先定位再社交。如果說傳統網絡社交嵌入個體生活空間的過程,更多的是將個體從現實物理空間引入經過網絡社交中介的空間,那么移動位置交友則將有助于將使用者從中介化的脫離物理身體為核心的空間拉回直接經驗的世界。曾經出現很多這種通過地理位置進行社交的網站,如國外的Banjo、Sonar、Yobongo、Lokast等。以Sonar為例,使用者可實時看到身邊的社交好友或好友的好友。每次簽到時,Sonar.me便會自動檢查并顯示附近是否有其他使用者,將社交網絡帶入現實生活。[9]
傳統社交網站也相繼推出類似服務,如Twitter的Nearby功能,根據手機的GPS定位判斷使用者所在的位置,然后搜索使用者附近其他的Twitter使用者的狀態、留言等。國內基于LBS的應用曾經百花齊放,如“陌陌”“幾米”和“微信”。下面這段話似乎能夠代表目前國內基于LBS應用的設計初衷:“我們與陌生人之間似乎總有一堵墻,看上去不可逾越,但常常只需要一個微笑或簡單的一句Hi就可以打破,可是大部分宅男宅女們都難以跨出這一步。而幾米的誕生則是為了幫你解決這一問題,打破這堵高墻。”[10]
“幾米”網的名稱源自臺灣繪本作家幾米。幾米的漫畫《向左走,向右走》是早期網民非常熟悉的。漫畫的男女主人公居住在同一幢公寓里,但是彼此習慣不同,一個出門總是向左走,一個出門總是向右走。于是,如此相近的兩個人不斷擦身而過,旋轉門一進一出,電梯一上一落,月臺上分站兩旁……雖然也曾經相遇并一見鐘情,但是互留的電話號碼被雨水淋濕而失去聯系,他們不知道彼此的距離其實只隔一面墻。如果男女主人公都使用移動位置交友,那么相遇相知便是很容易的事,生活中便不會有上述遺憾。
2007年,手機小說《我在地鐵上用藍牙追到一個MM》在中國的白領圈中廣為流傳。小說的男主人公宋無衣是一個單身白領,在每晚回家的地鐵上,備感無聊的他常用手機的藍牙功能搜索身邊的人:“坐地鐵的時候,我會拿出手機聽著歌,順便開著藍牙,至于為什么要開藍牙,因為我把這個動作當成我內心世界通往外在的一個出口。每當用藍牙搜索到別人手機的時候,就覺得這人的距離就離我近了些,當然,我習慣性地篩選出女孩子。如果我的精神可以依附在無線藍牙中,我就可以進入她的手機,進入她的世界,雖然不能改變什么,但至少我可以微笑著在她的小樓庭院漫步而行。原諒我的陰暗,我也在為自己的卑微而苦惱,我是沒有膽量任意和漂亮的女孩搭訕,只能用此招自我幻想著。”而女主人公Candy這半個月以來,每天都與宋無衣同時下班,因為“太無聊了,所以每次就打開藍牙搜索這個地鐵上的人,看看他們的反應,每次搜的時候,都能搜到NEO這個名字”,所以某一天就忍不住發送了一個記事本,兩人的故事開始了:“天啊,她正主動和我連線,并在傳輸文件。我慌張地抬頭望了望面前的幾個人,全是男人,而且都在睡覺,又轉頭望了望另外左右兩個車廂的人,其中有幾個女孩,但都是一副與世隔絕的神態,我心中驚訝,但又不能拿著手機上的藍牙顯示跑過去問:你好,是不是你和我連線啊!又或者大吼道:你怎么總是在線啊!我此時一邊回復,一邊悄悄用眼睛瞄看四周的人,可惜看到的是一群女孩,也不知道是哪一個。”[11]在地鐵這個每個人都用耳機、手機屏幕、電子書將自己與他人劃定隱形界限的公共空間,兩個人的這種奇妙聯系讓他們備加珍惜。
2009年,社交網站Skout做過的一項調查顯示:“69%的受訪者愿意與通過手機認識的人見面,40%的受訪者習慣在酒吧、俱樂部和餐廳使用移動約會服務。”但是,如何讓陌生人從半生不熟的狀態過渡到親密關系狀態,如何幫助陌生人完成這個破冰之舉,尤其是在中國根深蒂固的熟人圈子社會,這是現在讓很多移動位置交友應用的設計師絞盡腦汁思考的問題。移動位置社交也如QQ一樣經歷了非理性到理性的過程,最初的一些基于“簽到模式”的移動社交應用風風火火一陣后,就停留在“秀”的層面,使用者新鮮感過后,已經漸漸地步入了冷冬。
中國早期網民已經經歷過網絡聊天室以及即時通訊最初的陌生人交友的瘋狂階段,但是這一階段形成的關系最終沉淀并維持下來的并不太多,大多數人的網絡社交開始重新回歸現實生活中的親友,專注于熟人圈子的微信成為最受歡迎的軟件。2015年5月中旬,騰訊公布了2015年業績報告:截至今年第一季度末,微信每月活躍用戶已達到 5.49 億,覆蓋 90% 以上的智能手機,移動應用對接數量超過 85000 個,微信支付用戶達到了 4 億左右。在所有微信用戶中,25-36歲的比例達到40.8%。[12]
微信最大的特點在于它對小圈子的關注,在信息傳播的過程中具有一定程度的閉合性。對比上述移動位置社交的式微和微信的一枝獨秀,我們可以看到,移動社交應用的多樣化并沒有太多地改變個體社交的習慣和心理。只有符合中國網民人際交往習慣和心理的應用才得到最大程度的傳播。“宅”已經借助移動社交所創造的技術空間脫離了物理意義上的“家”的范疇,“朋友圈”就是一個可以隨身攜帶的人際交往空間,原來日常生活中的那些發楞、觀察路人等無所事事的時間也可以用來在手機中“宅”了。
五、對于中國早期網民的總結
本文描述了十幾年的時間內,網絡社交如何嵌入中國早期網民日常生活的空間結構,個體如何經驗和評價網絡社交在他們生活中的角色,并按照自己的習慣和需求選擇并賦予網絡社交以意義。所探討的日常生活空間聚焦于個體與他人互動的層面。從中國早期網民十幾年的經歷可以看出,總體上網絡社交讓個體直接經驗的世界邊界擴大。但是,我們還可以更深入地辨析個體生活空間結構不斷變遷的內在張力。
第一, 在移動位置社交之前的網絡社交應用將個體從現實空間中解脫出來,更多地投入到中介化的虛擬空間互動,最明顯的表征便是大學寢室“臥談會”的式微、“宅男宅女”的產生和“宅文化”的流行。作為網絡社交的早期使用者,中國早期網民的使用行為經歷了從初次接觸到積極協商,最終有選擇地將其嵌入個體的日常生活空間中,有時以微妙的方式(如隱身在線等)進行著個體生活空間的建構和邊界維護。雖然這一批人接觸網絡社交有早有晚,動機、過程、方式各不相同,但總的來說,正是特殊的生理年齡和人生階段、特殊的社會歷史環境,使得他們成為早期網絡社交的主力軍。不管是網絡社交的早期采納者、晚期采納者,還是網絡社交的抵制者,早期網民與網絡社交的遭遇伴隨著他們協商自己與他人、與世界關系的過程,是處于人生轉折階段建構個體生活空間努力的一部分。
第二,移動位置社交則先定位后社交,與傳統的網絡社交反其道而行之,傾向于建構與現實空間相重合的個體生活空間。早期的微信一個重要功能就是移動位置社交,但是讓它迅速普及的不是這一功能,而是“朋友圈”。雖然此類應用的運作模式目前無法改變中國人的社交習慣,但是這種應用在與具體情境和特定需求相結合的前提下,其新的運作模式和商業前景也是值得期待的。更重要的是,在虛擬空間與現實空間這一對張力中,它代表了一種以現實空間為核心的取向。
網絡社交改變著我們對于空間概念的體認。日常生活中的人際交往不再是在某一個具體空間場域中進行,我們不斷地在物理空間與虛擬空間之間做出選擇,或者同時在場。不管是將個體從現實物理空間的局限中解放出來,還是促進人們與身邊的陌生人之間的交往,虛擬空間與現實空間之間的界限日漸模糊,而在這個過程中,個體是有選擇地、不斷嘗試和調整地將網絡社交納入日常生活空間。
[1]范會芳.舒茨現象學社會學理論建構的邏輯[M].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2009:111.
[2]劉丹鶴.賽博空間與網際互動:從互聯網技術到人的生活世界[J].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
[3]舒茨.社會世界的現象學[M].盧嵐蘭譯.臺北:桂冠圖書有限公司,1991:167.
[4]Markus H, Kitayama S. Culture and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1(98):224-253.
[5]金陵.調查顯示大學生最愛臥談會[EB/OL]. http://news.sina.com.cn/c/2005-10-11/09307138428s.shtml.
[6]拯救宿舍臥談會[EB/OL]. http://news.sohu.com/s2007/wotanhui/.
[7]高邦仁、王煜全.流動的世界,奔向移動互聯網時代的生活[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
[8]胡春陽.如何理解手機傳播的多重二元沖突[J].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10):57-64.
[9]五款值得推薦的LBS約會應用.[EB/OL]. http://www.leiphone.com/location-based-dating-apps.html,2012-02-27.
[10]幾米.讓你打破陌生人間的高墻. [EB/OL]. http://www.leiphone.com/news/201406/jimi-break-the-wall.html.
[11]宋無衣.我在地鐵上用藍牙追到一個MM[M].朝華出版社,2007.
[12]2015年微信用戶數據報告. [EB/OL].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NzUzNTc5Nw==&mid=207038828&idx=8&sn=49b a78744d1a6d4af373af5e7efb55cb&scene=1&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rd.
Discussion on the Social Networking and Individual Life Space
Bi Xiaomei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In the early stage of internet development in China, it sets people free out from the fetters of physical space with a virtual fascination;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s of old friends transferring onlin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ocation based socializing service, the magic of internet fade; nowadays, the everyday interpersonal contacts happens no longer in single dimensional space. People constantly transfer between the physical and internet space, even stay in multiple spaces at the same time. The Chinese early netizen this essay focus on has experienced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stages of Chinese internet which is helpful to study this issue.
Social Networking; Structure of Space; Slumber Party; Indoorsy; Social Mobile Location
C913
A
1006-1789(2016)05-0040-07
責任編輯 曾燕波
2016-03-04
畢曉梅,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傳播學理論、新媒體與文化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