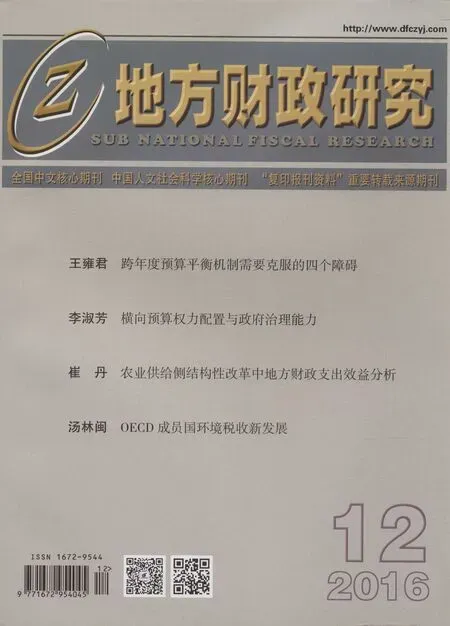跨年度預算平衡機制需要克服的四個障礙
王雍君
(中央財經大學 北京,100081)
跨年度預算平衡機制需要克服的四個障礙
王雍君
(中央財經大學 北京,100081)
2015年開始實施的新《預算法》在一般公共預算的框架下確立了跨年度預算平衡機制,使財政政策從傳統上遵從的謹慎財政原則轉換為全新的逆周期規則。然而,該機制的有效性取決于能否成功地克服四個主要障礙:財政赤字與可持續性計量、預測誤差與控制、縱向財政紀律、與結構調整政策的兼容。
跨期平衡 赤字計量 預測誤差 財政紀律 結構調整
一、引言
新《預算法》規定:一般公共預算按國務院規定可設預算穩定調節基金用于彌補以后年度預算不足,省級公共預算執行中短收通過調入該基金和減少支出等平衡,仍不能平衡可報省級人大或其常委會批準增列赤字、報財政部備案且應在下年預算中彌補。跨年度預算平衡(以下簡稱跨期平衡)機制自此在中央和地方兩級被確立起來,作為應對經濟周期性波動的財政政策工具。
該機制的邏輯十分簡單:經濟衰退時期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以刺激經濟,經濟繁榮時期則采取緊縮性財政政策抑制需求并形成足以彌補前期赤字的財政盈余。這種逆周期規則的財政穩定政策的思想淵源,可以追溯到20世紀40年代的凱恩斯革命——其核心成為可概括為宏觀預算①世界銀行曾將預算區分為三個層級:宏觀預算、配置預算和運營預算,分別處理宏觀經濟穩定(逆周期財政政策)、財政資源部門間與規劃間配置和運營績效(經濟性、效率與有效性)三個基本的預算問題。其中,宏觀預算指按照大類規劃分組的政府功能和經濟分類。革命:預算不僅要呼應常規財政管理 (基于年度平衡的謹慎理財)的需求,還應成為分析和實施宏觀經濟政策的有力手段。這一革命打破了傳統理論中的財政與經濟兩分法,帶來了財政政策對宏觀經濟運行具有深遠影響這一全新理念,并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發達國家預算制訂的方法。其精華在于:預算的宏觀經濟效應必須在預算籌劃時就要考慮到,預算籌劃不應簡單地側重于如何達成年度平衡。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逐步完成了從傳統年度平衡向跨期平衡的轉換,期間的赤字年份遠多于平衡年份以及2011年來迅速增長的政府債務,即為明證。如今,要求嚴格遵從年度平衡原則制訂預算的觀念早已消失,即便對于地方預算也是如此。取而代之的主流觀念是:年度平衡即便可行亦無必要,跨期平衡更為可行和必要,因為客觀存在的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尤其是經濟危機——需要政府實施財政干預,地方財政亦無例外。
然而,真正的問題不在于可行性與必要性,而在于跨期平衡機制有效運作的基礎條件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達成這些基礎條件。這里涉及四個基本問題:(1)財政赤字與可持續性計量;(2)預測誤差與控制;(3)縱向財政紀律;(4)與結構性調整的兼容。
二、預算赤字與可持續性計量
跨期平衡機制的有效運作,首要要求預算制定所依托的宏觀經濟政策意圖的清晰表達,以及向市場發出“政府打算在來年做什么”的信號。這就要求有可準確表達政策意圖的預算赤字和可持續性計量,分別回答“什么樣的預算赤字最能準確體現政策意圖”和“預算赤字是可持續的嗎”這兩個基本問題。無論意圖不明還是不可持續的財政赤字,都會損害跨期平衡機制的有效性。
理想的計量是采用現金基礎的綜合赤字,定義為與“凈借款”嚴格對應(相等)的現金赤字,即預算年度的現金流出(支出)減去現金流入(收入)后的差額。其真實含義是:政府在償還舊債和回收貸款后,還需增加多少新借款?如果綜合赤字為2萬億元,意味著政府在該財年的新增借款需求也是2萬億元。數值越大,表明刺激經濟(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意圖越明顯。
為使赤字與凈借款嚴格對應,在計算綜合赤字時,政府總支出中應包括現有債務利息、轉移支付和補貼,政府總收入中包括接受的轉移支付、公共資產收益 (比如土地出租出售和國有企業利潤上繳);支出中不包括債務本金的償付和金融資產累積——比如“調入預算穩定基金等”增加的現金儲備,收入中也不包括現金儲備的提用。現金儲備指本年和以往年度結余的政府銀行存款和現金。在這些條件得到滿足時,預算赤字總額就嚴格對應 (等于)政府新增借款需求(包括國內和國外)。
基于宏觀經濟政策準備和預算執行控制的目的,借助綜合赤字概念,將“赤字”與“凈借款”之間保持清晰的對應關系非常重要。然而,中國現行赤字概念與綜合赤字概念并不一致,兩者存在重要偏差。其中一個是把以前年度的結余(現金儲備)提用列為“收入”,另一個是以撥作支——把撥款記作支出。正如結余不應列為“收入”一樣,當年已經劃撥給支出機構但后者并未實際用于商品或服務購買或做出購買承諾,也不應列作支出。
“以撥作支”導致錯誤的“支出”概念,并使以“收支差額”定義的“赤字”與政府凈借款需求不再存在對應關系。其他扭曲因素還包括收回以前年度的拖欠——最明顯的例子是補繳以前年度的稅款。將這些資金記作政府在新財年的收入同樣是錯誤的。如同出售資產和財政結余的提用一樣,它們都是彌補財政赤字的手段,而不是真正的“收入”。
為監控財政可持續性和完整捕捉財政政策的宏觀經濟效應,有必要將綜合赤字擴展為“公共部門赤字”,覆蓋目前的四本預算以及國有企業和國有金融機構(包括央行)①《中國人民銀行法》規定:中國央行的全部資本由國家出資,央行每會計年度的凈利潤要全部上繳中央財政,虧損則由中央財政撥款彌補。由此亦可知,將央行損益計入公共部門赤字概念合情合理。。凡是政府承擔預定財政義務的機構或實體,均應納入公共部門赤字的計算中,如此即可得全面的公共部門新增凈借款需求。后者與政府債務總量的可承受性和債務融資的可行性之間的比較,可作為判定財政可持續性的一個重要方法。目前中國沒有這樣的赤字概念。
即使有嚴格定義的現金基礎的綜合赤字,亦須判斷其可持續性。一種方法是使用標準赤字比率(不高于3%)或類似比率——比如歐盟債務比率(不超過60%)——判定赤字的審慎水平。但這種方法并不可靠。這些標準是經驗性的,從未得到嚴格檢驗,實際上也從未得到嚴格執行。各國的具體情況也很不相同,經濟增長速度、潛力和規模較大的國家承受赤字和債務的能力高得多。正因為如此,判斷財政赤字維持能力應轉到更有前途的方向上:赤字水平是否足以影響債務、通脹、私人投資的目標(期望)水平以及貿易平衡?任何政府都有一組期望達到的宏觀經濟目標,包括增長、就業、國際收支、外匯儲備、利率和匯率穩定等。其中,與政府赤字關系最為直接的主要有債務、通脹、私人投資水平和經常賬戶余額。
判斷赤字維持能力的另一個方法是可吸收性:國內私人部門(主要是家庭部門)的儲蓄。與許多國家相比,中國國民整體儲蓄率高得多。以此言之,中國經濟吸收政府赤字的能力是很強大的。但這一觀點不能過分強調。民間的吸收能力再強大,也不能避免政府赤字和債務的擠出效應。
使用財政赤字判定財政可持續性雖然最為常見,但有其局限性:沒有考慮政府凈資產變化。凈資產定義為資產減負債,即資產負債表(也稱平衡表)中的凈資產。無論公共部門還是私人部門,通常都不會因為預算赤字的壓力走向崩潰。即使赤字持續多年,政府也有辦法通過干預使其恢復平衡。因此,許多情況下,財政上的不可持續并不通過財政赤字表現出來,而是隱藏在平衡表中:凈資產的減少令人擔憂。凈值法(平衡表法)可以揭示出某些看似不起眼的變化,很可能對政府凈值帶來重大影響,從而置財政可持續性于危險境地。這些“小幅變化”包括匯率、利率和資產價值的波動。
三、預測誤差與控制
即使跨期平衡機制能夠得到適當計量,其有效性亦深受預測誤差與控制的影響。在存在系統性誤差并且缺少適當控制的情況下,財政穩定政策①財政穩定政策有不同的術語,常用的有補償性財政政策、反周期財政政策和宏觀財政政策。這些術語表達的基本含義相同:以財政擴張刺衰退期的經濟復蘇、以財政緊縮控制經濟“過熱”。的三要素都將出現重大失靈:支出總量大致多少?可否解決衰退問題?引發持續通脹時支出應如何削減?
與年度平衡機制相比,跨期平衡機制對預測質量的要求高得多,因為后者涉及“多大的赤字或盈余才能與宏觀經濟目標相匹配”這一重大、復雜和跨年度的問題。在這里,重要的不是誤差,而是誤差的性質與控制措施。兩類誤差——非系統性誤差和系統性誤差——之間存在根本差異。前者指不可避免的、偶然的、實際值高于和低于預測值的概率大致相等的那類誤差,不會導致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增長率、就業率、通脹率和國際收支缺口等——出現系統性偏離或失效,因而可以忽略不計。系統性偏差指較大幅度的、持續的、具有特定指向性(比如總是低估收入或高估支出)的那類誤差。在缺少適當控制時,這類誤差將導致財政穩定政策所鎖定的宏觀經濟目標發生重大偏離。在這種情況下,宏觀預算再現的不是可信與可靠,而是理想與決心,成為典型的“不現實的預算”。
與跨期平衡機制不同,年度平衡機制引導的預算制訂關切的是“平衡”。年度預算平衡本身就是政策目標,無須融入一個將財政總量(收入、支出、赤字/盈余、債務)與經濟政策目標(增長率等)匹配起來的預測程序與機制,對預測質量的要求也就低得多,即使出現較大誤差,也不必擔心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相比之下,跨期平衡機制要求預算過程必須以牢固的中期收入預測為起點,并與各個領域清晰的中期政策和“硬”中期支出限額結合起來,融入部門預算申請中。由此可知,中期預測的質量不僅取決于預測模型與技術,亦取決于預測程序能否被妥當地安頓于預算日程表中。這一日程表不僅能為預測留下充足的時間,也能嵌入適當誤差控制機制:當誤差達到一定幅度(比如5%)從而足以影響預算的宏觀經濟目標時,該機制必須能夠適時做出適應性調整,從而保證宏觀經濟始終在“可信”與“可靠”的軌道上運行。
現行的預測程序與機制并不能完全滿足上述要求。主要問題有三:(1)缺少共識性和競爭性預測——兩者雖然在政治過程中并非必需但很重要,(2)人為低估收入的傾向非常普遍——各級政府都存在相當明顯的“超收”動機,(3)缺失將財政預測與經濟預測緊密銜接的適當程序與機制。此外,預算日程表過于短促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預測質量。
除了開發更好的預測模型與技術外,優先的改革應集中于完善中期財政規劃——國際上通常稱為中期支出框架(MTEF)。中央政府從2015年開始實施了MTEF。這項旨在強化預算與政策間聯結的重大舉措,其主要作用在于強化財政紀律和促進財政資源的優先性配置。就強化財政紀律而言,MTEF主要作用在于建立針對政府和支出部門的中期支出限額,據以對支出、赤字和債務總量實施控制;就優先性配置而言,MTEF的主要意義在于通過嚴格的支出審查機制來確保預算過程受政策驅動而非收入驅動,以及促進預算資源在各項政策目標間和規劃間作出更好的選擇。
以上兩個方面都高度依賴預測質量與誤差控制,包括對經濟周期拐點(增長底谷與高峰)何時出現、情況多嚴重的預測。這是因為,跨期平衡機制的焦點不在于確認“平衡”,而在于確認“衰退期多長、幅度多大、拐點何時出現”,后者是保證中期平衡能夠與宏觀經濟目標相匹配的前提條件。此外,經濟周期影響的不只是對收入、支出、債務和赤字總量的預測,也影響支出結構的安排。明顯的例子是:資本性支出與經常性支出 (大致對應現行部門預算中的“項目支出”與“基本支出”)的比重,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往往大不相同。多數政府都傾向于選擇以資本支出作為應對經濟周期的主要工具,為資本預算建立特別程序與機制因而有其合理性與必要性。
四、縱向財政紀律
財政紀律(fiscal discipline)被普遍視為財政管理的首要價值,可定義為既能滿足宏觀經濟政策目標所需、又能保證中長期財政可持續性的赤字和債務水平。這也是深度影響跨期平衡機制有效性的兩個方面,因為不能滿足宏觀經濟政策目標所需的跨期平衡,屬于沒有意義的平衡;不能保證財政可持續性的跨期平衡,屬于不合需要的平衡。
鑒于地方政府合并的赤字與債務具有重要的宏觀經濟效應,對財政紀律的籌劃不應只是橫向的——合并中央與地方的赤字與債務總額,亦應是縱向的——單獨考慮地方赤字與債務水平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地方財政(赤字與債務)影響宏觀經濟穩定的觀點,很早就得到了大量文獻的確認,中國更是明顯的例子。與多數國家相比,中國擁有數目與層級更多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支出比重(超過支出總額的75%)也比多數國家高得多。因此,雖然單個地方政府的財政影響可以忽視不計,但合并的整體的地方財政對整體宏觀經濟的影響大得無法被忽略。此外,大量研究表明,大國的宏觀經濟波動往往具有明顯的區域特征。這些都要求在制定預算時,充分考慮地方財政的宏觀經濟影響,使地方財政成為穩定政策的重要一環。
縱向財政紀律因而非常重要,其含義是:(1)地方層次上的跨期平衡機制很可能是必要的和適當的;(2)轉移支付體制必須具有靈活性以使地方財政具有反周期的特性;(3)中央政府應避免“道德風險”——向地方政府發出“將為地方赤字與債務買單”的錯誤信號。滿足這些條件要求特定的法律與制度建構,包括清晰劃定中央預算與地方預算的邊界。在任何情況下,中央財政都不應承擔彌補地方赤字的責任。
縱向財政紀律的本質是在嚴格的硬預算約束下,確保地方政府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現行的央地財政體制和轉移支付并不能滿足這一要求。實際上,地方政府自2008年以來迅速累積的地方債務,包括直接借債、承擔擔保責任與救助責任的債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道德風險”的產物——有缺陷的體制賦予地方政府“中央將最終為地方赤字與債務買單”的普遍預期。弱勢地方稅、強勢轉移支付的組合,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彌補縱向財政赤字(控制地方財政)的考慮。這些特征與作為,均有悖于跨期平衡機制的內在要求。
五、與結構調整政策的兼容
短期性的穩定政策與長期性的結構調整政策之間的潛在沖突,有時會以尖銳的形式表現出來:持續的財政擴張為結構性調整政策設置障礙。與財政緊縮政策相比,財政擴張政策在政治上更受歡迎,這也是邏輯清潔明了的逆周期規則,在實踐中很容易變異為“半邊凱恩斯主義政策”①完整的凱恩斯主義政策要求經濟衰退期的財政緊縮與經濟繁榮期的財政收縮交替實施,以實現商業周期內的財政平衡。然而,即使在經濟景氣時期,政治決策也偏向實施繼續實施財政擴張而非緊縮,由此形成持續的財政赤字和不斷累積的政府債務。這種只有擴張沒有緊縮的政策反映反周期政策的實踐中的困難,以致凱恩斯主義政策被異化為順周期政策,從而直接違反逆周期的操作規則。的主要原因,也是跨期平衡機制遭遇破壞和失效的主要原因。許多研究表明,中國過去30年中,順周期的財政政策在中央和地方一直占據主導地位。
基本結論是:穩定政策雖然是必要的,但并不能解決經濟體系累積的結構性矛盾,后者大多源于政府過度干預扭曲與壓制市場機能以及壟斷、信息不對稱和創新不足(外部性)造成的市場失靈。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經濟中存在大量的閑置資源和高失業率,也不能通過財政擴張來激發經濟增長的潛力,除非在體制與機制層面做出深刻的結構性調整。當前經濟結構升級轉型中面臨的“去產能”和“去庫存”問題,其癥結正在于經濟的結構性失衡,因而很難在財政穩定政策的框架下得到解決。不僅如此,如果應用不當,擴張(“積極”)的財政政策甚至會加劇產能與庫存過剩,從而為結構調整政策制造障礙。
與反周期的財政穩定政策的運作規則不同,結構調整政策直接或間接觸及深刻的既得利益關系的再調整,面對的困難與阻力因而大得多。兩類政策間存在復雜的互動,既可形成良性循環、也可形成惡性循環,這取決于改革議程能否有效調和兩者的潛在沖突。中國已經持續5年的經濟低迷的深層根源,主要源于結構性調整政策的滯后而非財政穩定政策的不當。無論如何,回避利益沖突的財政擴張性政策雖然在政治上極受青睞,卻暗含了不可持續和阻滯結構性調整的高風險。
結構調整政策的滯后,反過來也會損害財政穩定政策的有效性。沒有深刻和適時的結構性調整政策,財政穩定政策的效果將被大打折扣。但在理論研究與實踐中,宏觀經濟的內外失衡的原因經常被錯誤地解讀為缺乏適當的穩定政策措施,尤其是被視為財政政策的擴張力度不足。這種認知導致對結構調整政策的重要性長期被嚴重低估,等到穩定政策失效時,最佳的結構性調整政策時機往往錯失了。所以,特別需要警惕的是:把只能在結構調整政策下才能解決的問題,錯誤地置于財政穩定政策的框架下去解決。在這里,可以再次看到跨期平衡機制的有效性通常被高估,其復雜性則往往被低估。
六、結語
跨期平衡機制將財政政策與經濟的關系分析從割裂轉向聯結,以此將傳統的財政健全目標轉向功能財政領域。其基本要求是:在預算籌劃的早期階段,即應確認預算政策的經濟效應——經典理論將其表述為預算的三項經濟職能:穩定、配置與再分配。然而,以法律確立跨期平衡并取代傳統的年度平衡原則是一回事,要使這種機制真正有效完全是另一回事。傳統的宏觀財政理論強調了反周期財政政策的合理性——尤其是在經濟衰退期實施財政擴張的必要性和相對(于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同時認為這類政策的有效性主要取決于財政乘數:乘數越大越有效。本文則強調其有效性取決于更為復雜和多樣化的背景因素,即財政赤字與可持續性計量、預測誤差與控制、縱向財政紀律以及與結構調整政策的兼容,它們在解讀“跨年度預算平衡機制”的近期文獻中大多被忽視了。
〔1〕F.STEVENS REDBURN:Practical Imagination:A Possible Future for Federal Budgeting.Public Budgeting & Finance,Winter 2015,Volume 35,Issue 4,pp.1-17.
〔2〕BLANE LEWIS:Local Government Capital Spending in Indonesia:Impact of Intergovernmental Fiscal Transfers. Public Budgeting&Finance,Spring2013,Vol.33,Issue 1,p76-94.
〔3〕DANIEL W.WILLIAMS:The Politics of Forecast Bias: Forecaster Effect and Other Effects in New York City Revenue Forecast.Public Budgeting&Finance,Winter 2012.Volume 32.Number 4.pp.1-18.
〔4〕 ISABEL M.GARCIA-SANCHEZ,NOEMIMORDAN,AND JOSE MANUEL PRADO-LORENZO:Effectofthe Political System on Local Financial Condition:Empirical Evidence for Spain’s Largest Municipalities.Public Budgeting&Finance.Winter 2012.Volume 32.Number 2. Pp.40-68.
〔5〕王雍君.《預算法》修訂中的四個關鍵性問題探討[J].地方財政研究,2011(1):14-17.
〔6〕王雍君.財政赤字該怎樣解讀?[J].中國財政,2016(8):29-32.
〔7〕王雍君.如何管控財政可持續性?[J].新理財,2016(4):28-30.
【責任編輯 郭艷嬌】
F812.3
A
1672-9544(2016)12-0004-04
2016-10-17
王雍君,政府預算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政府預算。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公民友好型政府預算報告模式研究”(11YJA630137)后續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