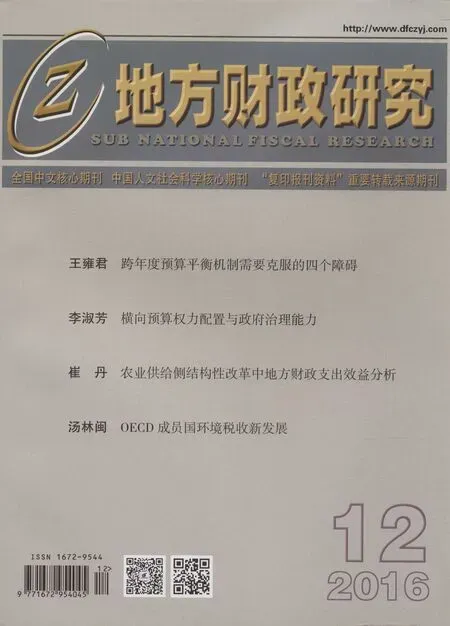普惠金融發展區域差異及影響因素研究
——以甘肅為例
崔治文 張曉甜 白家瑛
(西北師范大學,甘肅 730070)
普惠金融發展區域差異及影響因素研究
——以甘肅為例
崔治文 張曉甜 白家瑛
(西北師范大學,甘肅 730070)
文章以甘肅省14個市州2007年-2014年的面板數據為樣本,計算普惠金融發展指數(IFI),對甘肅省普惠金融發展狀況進行了綜合分析。通過構建影響因素分析模型,實證檢驗四類因素對甘肅各市州普惠金融發展的影響程度。研究表明,全省普惠金融發展水平較低,各州市發展水平差異明顯;各地區存款資源運用水平、交通便利程度、城市化率滯后期水平對甘肅省普惠金融區域性發展具有正效應,而農業發展水平和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對其發展具有負效應。
普惠金融 區域差異 影響因素 甘肅 變異系數法
普惠金融(Financial inclusion)是指能有效、全方位地為社會所有階層和群體提供服務的金融體系,發展普惠金融有助于進一步加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和改善民生(周小川,2013)。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正式提出“發展普惠金融,鼓勵金融創新,豐富金融市場層次和產品”,這是“普惠金融”第一次寫入黨的執政綱領,“發展普惠金融”成為完善金融市場體系的重要內容。金融的核心作用就是通過金融資源的配置,促進實體經濟資源超越主體、跨越區域、穿越時期進行配置(李揚,2014)。作為金融實踐與技術進步、理念轉變相結合的產物,普惠金融是對傳統金融邊界的拓展,既有助于提高經濟運行的效率,又有助于提高社會福利,是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撐。
甘肅省是全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集中度高的省份之一,2014年GDP為6835.27億元,總量全國排名倒數第五,占全國GDP總量的1.07%;人均GDP僅為26433元,全國倒數第二;與排名第一的上海市相比,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為上海市的43.6%,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上海市的27%,經濟社會發展相對落后。加快甘肅經濟社會發展,對構建和諧社會、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愿景意義重大。普惠金融對于促進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深入研究甘肅省各市州普惠金融發展現狀、厘清影響甘肅普惠金融發展的因素和影響程度,加快甘肅省普惠金融發展,提高普惠金融服務社會經濟發展的水平,對于加快甘肅省經濟社會快速全面發展及國家發展戰略的實現具有重要意義。
一、衡量普惠金融發展的指標體系構建及測度方法
(一)指標體系構建
Beck(2007)提出了一國(地區)普惠金融發展水平的測度指標,包括金融機構網點數、自助存取款機數、存貸款總額/GDP、存貸款賬戶數。Mandira Sarma(2008)在Beck的基礎上,借鑒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HDI)的構建方法,選取銀行滲透度、銀行服務的可利用性和使用狀況等三個方面的指標,首次創建了普惠金融指數(inclusive finance index,IFI),用來衡量不同國家的普惠金融發展狀況。目前對于普惠金融發展的研究,主要從兩方面展開:一是直接測量普惠金融發展水平,即直接構建普惠金融指數(IFI);二是間接衡量普惠金融發展水平,即通過衡量一國或地區金融排斥程度,間接說明該國或地區普惠金融發展水平,金融排斥程度越高,普惠金融發展水平就越低。
本文主要借鑒Mandira Sarma創建普惠金融指數測度的方法,從金融服務的可得度、使用度、效用度三個維度衡量甘肅省各州市普惠金融發展水平。金融服務的可得度亦稱為金融服務覆蓋度。考慮到我國金融體系的特征,參考王婧,胡國暉(2013)、肖翔,洪欣(2014)、張國俊(2014)、焦瑾璞(2015)、蔡洋萍(2015)等學者的研究成果,選取了每百平方公里銀行業金融機構數、每百平方公里銀行業金融機構從業人員數、萬人擁有金融機構網點數、萬人擁有金融機構服務人員數作為可得度的具體評價指標。該類指標值越高,表明金融服務的覆蓋度越廣,普惠金融度越高。金融服務的使用度是指金融服務在其用戶中的滲透程度,即有多少用戶能夠使用金融服務,參考李明賢,李學文(2008)、高沛星,王修華(2011)、徐敏(2012)、胡宗義等(2012)、李春霄,賈金榮(2012)等學者的觀點,我們用一個地區的人均存貸款余額來具體表示使用度。該類指標值越高,表明普惠金融度越高。金融服務的效用度是用來反映金融服務的使用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大小,參考王偉等(2011)、王婧,胡國暉(2013)、蔡洋萍(2015)等學者的觀點,我們選用地區的存貸款余額占該地區GDP的比重來評價。該類指標值越高,表明普惠金融度越高。具體指標見表1。
(二)測度方法
1.指標權重確定
由于普惠金融指數是一個相對值,在分析中必須確定各個指標的權重。本文選用變異系數法對各個指標進行客觀賦權,具體步驟如下:用變異系數來衡量各指標取值的差異程度,以消除不同指標的量綱不同;本文假定第i個指標的平均值為,標準差為δi(i=1,2,…,8),因此第i個指標的變異系數Vi可以表示為:


2.構建普惠金融指數
為了消除指標之間的量綱影響,解決數據指標之間的可比性問題,必須對各指標進行無量綱化處理。根據HDI的有關計算方法,普惠金融指數中第i個指標的歸一化數值di的表達式為:


表1 普惠金融的衡量指標體系
式(3)中,wi∈[0,1]為求得的指標權重,xi為第i個指標的實際觀測值,mini為第i個指標的最小觀測值,maxi為第i個指標的最大觀測值,xi∈[mini,maxi]。從di的表達式,有0≤di≤wi≤1,di越大表示該地區在指標i上的表現越好。本文共選擇了8個指標用以衡量甘肅省普惠金融發展水平,則普惠金融狀況在8維笛卡爾坐標系中表示為Di=(d1,d2,…, d8),假定一個地區各個指標的計算得分都為0,即Dmin=(0,0,…,0),則IFI為0,代表這個地區在各個指標的計算值都是最低值,表明普惠金融程度最差;如果一個地區各個指標的計算得分都為相應的wi,即時Dmax=(w1,w2,…,w8),則IFI為1,表示該地區在各個指標的計算值都是最高值,普惠金融程度最好。因此,構建普惠金融指數就是計算各個指標的測算值與最理想值的距離,并最終把所有距離整合在一起形成一個測度結果。我們將普惠金融指數的測度公式設定為:

二、甘肅省普惠金融區域性發展水平指數測算及結果分析
(一)測算結果與類型劃分
本文以2007年-2014年甘肅省14個市州的相關年度數據作為樣本數據,利用公式(3)和(4),計算出甘肅省各市州2007年-2014年普惠金融發展指數。相關年度數據來源于2008年-2015年《甘肅發展年鑒》、2008年-2015年《甘肅金融年鑒》、銀監會網站、Wind資訊等。測度結果見表2。
根據表2的測度結果,如果按照Sarma(2008)的做法,將IFI值在0.5-1.0之間界定為金融服務高水平,在0.3-0.5之間界定為金融服務中等水平,在0.0-0.3之間界定為金融服務低水平(王修華、陳茜茜,2016),則僅有蘭州市的IFI值大于0.5,屬于普惠金融高水平范圍,嘉峪關市的IFI值在0.3-0.5內,屬于普惠金融中等水平,而其余12個地區的IFI值均低于0.3,處于普惠金融低水平。盡管有12個市州都處于低水平,但是各自的發展水平仍有不同:根據各市州2007年-2014年普惠金融發展指數的平均值,將金昌市等7個IFI平均值處于0.1與0.3之間的市州歸為普惠金融發展低水平,將隴南市等5個IFI平均值低于0.1的市州歸為普惠金融發展最低水平。據此可將甘肅省14個市州普惠金融水平劃分為4個類別(表3)。

表2 甘肅省各市州普惠金融指數的測度結果(2007年-2014年)
(二)甘肅省普惠金融區域性發展水平差異特征
1.普惠金融區域發展水平總體穩定,但空間差異大
比較14個市州2007年-2014年普惠金融指數并建立其趨勢圖(圖1),結合表2顯示各市州IFI的標準差均低于0.1,即測度值的離散程度較低,可知各市州普惠金融發展平緩,總體比較穩定。但是從IFI值來看,各市州普惠金融水平存在著較大的空間差異;根據2007年-2014年普惠金融指數平均值,普惠度水平最高的蘭州市(0.900)是普惠度水平最低的慶陽市(0.064)的14.06倍;分析12個處于低普惠度的市州,發現普惠度水平最高的金昌市(0.201)是普惠度水平最低的慶陽市(0.064)的3.14倍。

表3 甘肅省各市州普惠金融發展水平等級分類

圖1 甘肅省各市州普惠金融指數趨勢圖
2.經濟發展水平和城市化發展水平高的地區,普惠金融發展水平也越高
根據表2,只有白銀市、武威市和張掖市普惠度從2007年的最低水平發展到2014年的低水平,其他地區等級分類保持不變。分析2007年-2014年各市州相關數據,發現普惠金融發展水平與地區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程度基本趨同。蘭州作為全省經濟文化中心,科技實力強,交通建設及基礎設施發達,城市化率高,經濟發展水平領先于其他市州,普惠金融發展水平遠高于其他地區,處于第一類。嘉峪關作為不設市轄區的地級市,其人均總產值、人均純收入和城市化率處于全省最高水平,較發達的經濟和較高的城市化率促進了普惠金融發展,使其僅次于蘭州市處于第二類。處于第三類的7個市州,除了臨夏州,其他6個地區人均生產總值、人均純收入和城市化率均處于全省中上水平,臨夏州雖然經濟水平及城鎮化率較低,但近年來其GDP增長率較快,再加上歷史原因和民族習慣,金融需求和供給水平發展較快。處于第四類的5個市州,經濟發展水平和城市化率都處于全省最低位。上述分析表明,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與其普惠金融度基本處于相同層級,經濟發展和城市化能夠促進普惠金融的發展。
3.產業結構越合理的地區,普惠金融發展水平就越高
根據2007年-2014年各市州的年度數據,全省產業結構整體上呈現為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第一產業,將各市州普惠金融發展指數從高到底排序,結合三次產業占GDP比重均值得到圖2。
分析圖2發現,各市州普惠金融發展程度與產業結構逆相關,各市州普惠金融指數由高到低的排序,對應第一產業比重整體上是由低到高排序的。普惠度最高的蘭州市和普惠度處于中等水平的嘉峪關市第一產業比重最小,普惠度最低水平的市州第一產業比重最大,普惠度低水平的市州第一產業比重處于兩者中間。蘭州市三次產業比重分別為3%、46.4%、50.6%,三次產業協調發展,產業結構優化度高;嘉峪關市第二產業比重為78.9%,在各市州中占比最大,工業化水平較高。普惠金融低水平的市州第二產業比重普遍高于普惠金融最低水平的市州,但是這兩類地區各市州第三產業比重大部分在40%左右,差距不大。因此可以得出結論:產業結構越合理,越能保證經濟發展水平的持續增長,普惠金融發展水平越高;第二產業對于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帶動能力最強,對促進普惠金融的發展具有優勢;第一、三產業對促進普惠金融的發展相對處于劣勢。
三、影響甘肅省普惠金融區域性發展水平的因素分析
發展普惠金融是政府踐行黨的群眾路線,推動國家經濟轉型的重要戰略。厘清影響普惠金融發展的因素及各因素對普惠金融的影響機理和影響程度,對積極有序發展普惠金融、提高經濟運行效率和增進社會福利意義重大。基于相關專家學者的觀點,結合甘肅省的實際情況以及數據的可獲得性,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從經濟因素、金融發展因素、農戶因素、社會因素四個方面分析各因素對普惠金融發展水平的影響。

圖2 甘肅省各市州IFI與三次產業占比
(一)指標選取
經濟因素指標。一般認為一個地區的農業化水平越高,其工商業化水平越低,金融創新和服務就會相對較少 (王偉等,2011)。農業化水平較高的地區,經濟結構中第二、第三產業比重較低,不利于金融機構的生存和發展,從而抑制了農村的金融供給,容易形成農村金融排斥,導致普惠金融發展水平較低(高沛星、王修華,2011)。
金融發展指標。金融機構存款資源運用水平越高則表示該地區金融發展效率越高,進而促進普惠金融發展水平也越快,徐敏(2012)選用金融機構將農村地區存款轉化為農村地區貸款的效率來表示金融發展效率。
農戶指標。農戶是普惠金融最直接最主要的受眾,隨著農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人們對金融產品與服務的需求增加,從而提升普惠金融發展水平(張國俊等,2014)。農村居民人均收入也直接影響金融機構對其信用的評級,并直接影響到農村居民是否被排除在金融機構之外,所以人均收入的增加會促進當地普惠金融水平的提高(蔡洋萍,2015),而銀行在進行縣域營業網點布局時也更多地關注人口規模與居民收入(董曉林、徐虹,2012)。
社會指標。一個地區的金融發展狀況與其所處的社會環境密切相關。城鄉二元結構對農村金融發展具有一定的不利影響(劉俊杰、王海洋,2009),城市化不僅是農業人口向城鎮人口轉變的過程,更重要的是在人口城市化過程中,需要真正實現“農民”轉變為“市民”,增強市民在居住、教育、醫療等方面對金融產品的有效需求(張國俊等,2014),城市化會促進第二、第三產業的發展,同時增加金融服務和產品的需要,推動金融普惠進程(徐敏,2012)。基礎設施的建設能提高金融供需雙方接觸的便利度,降低金融機構在偏遠地區開設分支機構的成本以及偏遠地區居民使用金融服務的成本,從而促進普惠金融指數的提高(王婧、胡國輝,2013),而地區公路里程數越大,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金融服務更能向弱勢地區延伸,里程數越小,說明交通不方便,會阻礙金融機構金融服務的延伸(蔡洋萍,2015)。
根據以上分析,本文選取了以下變量來衡量各因素對普惠金融發展水平的影響,具體指標見表4:
(二)實證檢驗及結果分析
本部分將普惠金融指數作為被解釋變量,構建其與以上四類因素5個指標之間的計量模型,再利用OLS回歸的方法來檢驗這些因素指標對普惠金融指數變化的影響。為消除解釋變量間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線性問題,常用方差膨脹因子VIF來判斷,經驗表明當VIF值大于10時,認為回歸存在多重共線性。由表5所示的結果看出,各指標方差膨脹因子VIF值均小于10,解釋變量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
根據以上檢驗,為消除單位根的影響,對各個解釋變量進行自然對數變換,建立以普惠金融指數為被解釋變量的多元線性回歸模型:

上式中i表示甘肅省14個市州;t表示年份;被解釋變量lnIFIit表示i市(州)第t年的普惠金融發展水平;ui表示隨機擾動項,β0為常數項,βj(j=1,2,3,4,5)表示解釋變量的系數。

表4 甘肅省普惠金融發展影響因素指標體系及其含義

表5 多重共線性檢驗結果

表6 甘肅省各市州普惠金融影響因素的OLS回歸結果
根據已測算出的甘肅省各市州普惠金融發展數據和本研究所需從《甘肅省發展年鑒》、Wind咨詢整理的相關數據,運用stata11.0對2007年-2014年甘肅省各地級市普惠金融影響因素進行回歸估計,結果如表6所示。
從表6可以看出,所選模型解釋變量的T值均在1%的置信水平下顯著,F值也通過顯著性檢驗,可決系數值為0.82,修正后的可決系數為0.81,因為選取的是面板數據,所以指標模型擬合效果較好。對模型進行調整得到最終的回歸模型:

實證結果表明:
1.農業發展水平對普惠金融發展具有負效應。這說明農業產值占比較高的地區,經濟結構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比重就越低,因此對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的需求就降低,這不利于金融機構的生存與發展,從而降低了農村的金融供給,導致普惠金融發展受到抑制。
2.地區存款資源運用水平對普惠金融發展具有正效應。地區存款資源運用水平反映金融機構將農村存款轉化為農村貸款的效率,效率越高,服務農民貸款性需求越強,普惠金融水平發展越快。而且隨著這種效率的提高,金融機構對該地區金融服務供給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會增強,該地區普惠金融發展水平也會提高。
3.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對普惠金融發展具有負效應。這說明甘肅省各市州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提高并不能促進農村的普惠金融發展,這可能與農村居民仍習慣將純收入以現金的形式儲存于家中用于生產生活支付而很少將其存入金融機構有關,也可能與金融機構在農村地區服務水平低密切相關。純收入雖然得到提高,但農村居民并不去主動享有金融服務,從而使普惠金融的發展速度減緩。
4.年末公路里程數對普惠金融發展具有正效應。年末公路里程越長,表明該地區交通越便利,越能提高金融供需雙方接觸的便利性,進而可降低金融機構在偏遠地區開設分支機構的成本以及偏遠地區居民使用金融服務的成本,從而提升普惠金融發展水平。
5.滯后1期的城市化率水平對普惠金融發展具有正效應。這說明上一年度城市化發展水平對下一年度普惠金融的發展有正向的促進作用。城市化將人口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將減少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提高農業生產率,同時使農民收入來源多元化,增加收入。另外轉移到城市的剩余勞動力更多的使用金融機構的服務把結余收入匯到農村形成可利用的存款資源。
四、結論與建議
通過測算2007年—2014年甘肅省各市州普惠金融度,將普惠金融發展水平劃分為四類。從年度發展趨勢看,各市州普惠金融發展水平略有提高,但總體穩定;從總體來看,各市州普惠金融發展水平普遍較低,空間差異大。從影響因素來看,農業發展水平、存款資源運用率、交通便利程度和滯后1期的城市化率均對普惠金融的發展具有正向作用,而農村居民收入具有負向作用。因此,要推動甘肅省普惠金融區域性發展,必須從以下方面著手:
1.在發展地區經濟,提高居民收入的同時應促進其經濟思想的轉變。區域經濟發展有助于居民收入的提高和金融機構的擴張,增加居民享受金融產品與服務的機會,從而提升普惠金融度。傳統經濟思想抑制了富裕資金的使用,對普惠金融發展起到負向作用,因此必須轉變經濟觀念才能促進普惠金融發展。
2.推進交通和城市化建設,促進普惠金融發展。通過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及加快城市化進程,為金融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充分發揮現有金融機構作用,以最大效率為居民提供優質的金融服務;提高金融服務創新能力,提供多樣化金融服務,滿足不同群體的需求,全面促進普惠金融發展。
3.優化產業結構,促進金融發展。根據地區實際,優化資源配置,發揮金融作用,促進第一、二、三
產業的協調發展,提升經濟發展,增加居民收入;反過來三類產業的協同良性發展及居民收入的增加,會刺激普惠金融發展,實現區域經濟的全面良好發展。
〔1〕周小川.踐行黨的群眾路線推進包容性金融發展[J].求是,2013,(18):9-12.
〔2〕李揚.獲取金融服務是天賦人權 [J].金融博覽:財富, 2014(2).
〔3〕Beck T,Demirguc-Kunt A,Peria M S M.Reaching out: Access to and use of banking services across countries.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7,85(1):234-266.
〔4〕Mandira Sarma.Index of Financial Inclusion[J].Working Paper,2008.No.215.
〔5〕王婧,胡國暉.中國普惠金融的發展評價及影響因素分析[J].金融論壇,2013.6.
〔6〕肖翔,洪欣.普惠金融指數的編制研究 [J].武漢金融, 2014(9):7-11.
〔7〕張國俊,周春山,許學強.中國金融排斥的省際差異及影響因素[J].地理研究,2014.12.(12):2299-2311.
〔8〕焦瑾璞,黃亭亭,汪天都,等.中國普惠金融發展進程及實證研究[J].上海金融,2015.4:12-22.
〔9〕蔡洋萍.湘鄂豫中部三省農村普惠金融發展評價分析[J].農業技術經濟,2015.2.
〔10〕李明賢,李學文.對我國農村金融服務覆蓋面的現實考量與分析[J].調研世界,2008(3):17-21.
〔11〕高沛星,王修華.我國農村金融排斥的區域差異與影響因素——基于省際數據的實證分析[J].農業技術經濟, 2011,第4期:93-102.
〔12〕徐敏.農村金融普惠的水平測度及影響因素分析——以新疆為例[J].開發研究,2012,第5期:104-107.
〔13〕胡宗義,袁亮,劉亦文.中國農村金融排斥的省際差異及其影響因素[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2,(08).
〔14〕李春霄.農村地區金融排斥研究[D].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2013.
〔15〕王偉,田杰,李鵬.我國金融排除度的空間差異及影響因素分析[J].西南金融,2011,第3期(3):14-17.
〔16〕董曉林,徐虹.我國農村金融排斥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基于縣域金融機構網點分布的視角.金融研究, 2012(9):115-126.
〔17〕劉俊杰,王海洋.農村區域金融發展:影響因素與政策選擇[J].開發研究,2009(06):88-91.
〔18〕王修華,陳茜茜.農戶金融包容性測度及其影響因素實證分析——基于19省份的問卷調查數據[J].農業技術經濟,2016(1):108-117.
【責任編輯 成 丹】
F832
A
1672-9544(2016)12-0080-07
2016-04-25
崔治文,經濟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財政理論、政府投融資;張曉甜,經濟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金融理論與政策;白家瑛,經濟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財政理論與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