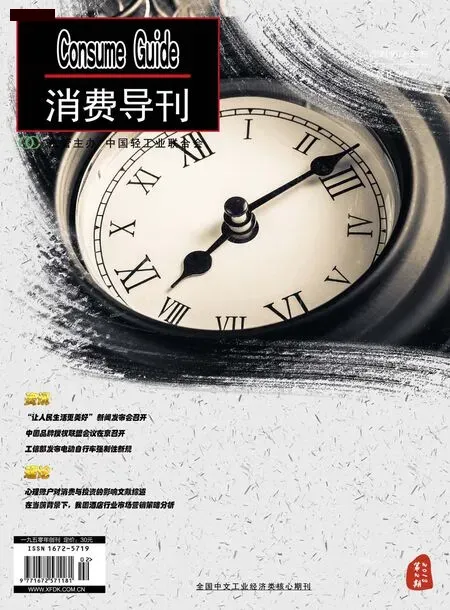實踐建構過程論:一種社會分析視角的新嘗試
王成林 安徽大學社會與政治學院
?
實踐建構過程論:一種社會分析視角的新嘗試
王成林 安徽大學社會與政治學院
摘 要:社會建構主義無疑對實在主義范式與人文主義范式的認識論基礎構成了較大挑戰,本文通過分析社會變遷視角下無數個體的能動實踐、體現反思和重塑自身文化預設而存在的社會科學知識以及無法從微觀角度把握的宏觀社會歷史轉型過程三者的不斷互構過程構成了一個循環的整體鏈條,提出知識社會學領域新的觀點和分析視角:實踐建構過程論。拋磚引玉以啟后者。
關鍵詞:實踐建構方法 知識社會學 互為建構
一、問題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社會學的遺產,社會科學的前途》一文中指出,社會科學的前途在于傳世的,構成了現代社會科學基本內核的“社會學文化”能否有效地應對來自六個方面的知識論挑戰,其中就有來自建構主義的挑戰。[1]
社會建構主義直接質疑古典實證社會學和人文社會學預設的兩端:社會唯名論與社會唯實論。認為任何社會科學的知識都逃脫不了建構的過程,只有深刻理解了知識生產與建構過程,才算是深刻準確理解了世界。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曾為了化解古典理論中的預設主義認識論危機,提出的“場域”概念旨在實現預設主義實體論向關系論的轉變。這一步驟無疑是個良好的開端。本文認為我們應該將關系論所采取的相對立場與建構主義的過程論思維結合起來,即:建構過程即是隨時間流淌的過程,同時也體現著互相建構雙方的關系。本文試圖進行更進一步的細化,將知識生產過程與個體的能動實踐、以及社會歷史的變遷過程聯系起來,力圖更全面地理解社會建構主義。
二、實踐建構方法的提出
把哲學家們的思索明確地立足于人類的無限推演著的實踐基礎的觀點最初是由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闡明。“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2]它確立了社會研究的嶄新的立足點,而由于實踐是主觀與客觀的現實的統一,是具體的歷史的統一,這在認識論上實質上超越了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只看到社會生活單一方面的長期分歧。布迪厄敏銳捕捉到這一點,提出了從實踐角度出發來看個人與社會關系的實踐理論(theory of parctice)。這被認為是開啟了社會研究的實踐轉向。
后來的研究有黃宗智依據對于中國特殊經濟與法律實踐國情的研究提出了從實踐歷史出發把握這一充滿著各方矛盾過程的實踐邏輯的觀點。這里明確提出社會科學(雖然是在針對中國學研究的意義上)在認識方法上要向實踐邁進。
法國社會學家米歇爾.德塞意(Michel DeCerteau)認為要進入日常生活實踐的場域中,而不是像站在高處俯覽大眾去構建理論,強調一種從微型實踐(minor parctice )出發來把握社會,由于一個社會是由一定的實踐構成的,要了解它就要去理解所有一般人的行動策略,它指的是人們在各種錯綜復雜場所中的,在各種機制力量,具體欲望,條件限制下的小心翼翼地探求各方面的微妙平衡。德塞意隨后指出了一般人的日常實踐固然處于絕對權力的壓制之下,但是它并未被這種權力擠壓成為索然無味的單面體。日常實踐中生活并不單一,在人們的日常舞臺上既存在著支配性力量,又有被壓制者和反抗者。他揭示出了既定秩序強加給大眾身上的并非是完全被動的木偶。雖然對于此有很多質疑,如認為作為一般人的弱者發動的游擊戰術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很容易被主流結構吸收、削弱,以致擊敗。[3]
本文認為這里可以變換分析范式,從一般邏輯上的對于消費社會大潮強權與所有一般人之間誰更占主導權,轉換到對于權力關系規則、權力關系實踐邏輯為主題的范式討論上來。
以此走向從發展的角度,變遷的角度看待問題,我們知道社會變遷或快或慢是一直進行著的,所以廣義和宏觀上應該對于一般人的實踐和洪流強權的并列對待,因為在社會結構相對穩定期,個體實踐很容易被洪流擊潰和吸收,但是當處于巨大飛速的社會轉型期,無數的一般行動者身上蘊含的龐大能動性就不容忽視并一躍升為主體了。并且思路一變,我們就不像以往僅執念于一般人弱者的命運到底如何,可以更多地去關注歷時性的宏觀層面發生了什么,怎么發生的,雙方是如何互相作用的。這就把問題引向了另外一個方面:建構論。
當代社會科學中興起的既振聾發聵也充滿爭議的社會建構論思潮,它和包括布迪厄從反思社會學和馬克思從實踐觀點在內的各方都以下基本立場:社會生活對于一切認識具有本體論的先在性和認識論的母體性;一切知識立場都有其內在價值性;對于知識本身采取相對主義和科學知識反原教旨主義。
它對于社會研究的意義,蘇國勛認為在應用層面上有社會問題建構論(constructing social problems)。它一改以往認為社會問題是某種客觀狀態的觀點,而是將其看成一種詮釋過程,要去探究它如何在某種取向上被修辭(rhetoric),被宣稱(clain-making),被建構出來的社會過程。[4]沈原借鑒法國學者阿蘭.圖海納提出了“行動社會學”理論和“社會學干預”的特有方法。它主張社會學知識并不是單一屬于研究者,它在本質上是研究者與行動者通過互動過程生產出來的。我們知道社會變遷與轉型是永遠進行中的,它同時意味著所有行動者透過自己的能動行為,改變社會的制定安排,重建基本的社會秩序,行動者身上蘊含的巨大能動性只有從行動社會學視角出發,才能深刻把握;另外在研究方法上,由于對于行動者而言,他們不知道學術研究調查和治理術的調查有何區別,往往會努力將真實生活掩蓋起來。所以要想獲得真實有效的社會認知,社會學干預或者才是有用的途徑。所以強調通過對于行動者的積極實踐影響來生產真實有效的社會學知識。而且現實中的社會關系只有受到擠壓時才會暴露出來,于是還不如把社會學的研究技術當做自覺的可控制的變量或手段。[5]
上面兩位學者提出的觀點表明了這樣一點,社會建構主義提出者們重在強調知識認識論上的相對主義,偏廢了更重要的問題:建構主體與建構物之間本質上是互為建構的關系。雙方在社會實踐過程中互相建構并且不斷超越歷史,不斷相互促進,這是一個循環不止的辯證過程。
本文結合實踐觀點與社會建構論,以此為基礎提出一個名為“個體實踐——整體建構”的方法。即是個體實踐層面上強調社會生活物性與人性的統一、主客觀的統一;整體社會結構文化層面上強調社會與個人的互為建構。它既關注個人在結構之下會被深刻影響又注意到個體也會不斷反思、能動實踐對于社會整體的塑造過程。
它認為,對于自然科學而言,知識的目的在于描繪真相和解釋原因,但是他們從來沒有想過人們是具有反思自身文化預設的能力的,人們可以重繪,重塑身處其中的社會世界。就是在此意義上社會科學知識才有其用武之地。正是它溝通了微觀層次的個體實踐與宏觀歷時性的整體建構。
一方面,從實踐——建構的過程性角度出發才能更加真切地把握所處的社會世界,才能獲取和生產真實有效的有關社會的科學知識;另外一方面社會科學知識對于社會的作用并不僅限于揭示隱秘的真相,發揮智性美德。它實際上通過參與了科學知識與常識的社會建構過程進而促成人的建構和社會的轉型的過程。這也是科學知識與它的母體的互為建構性的辯證關系。需要指出的是這里的做法并非是要模糊和否認科學與社會之間的真實差別,具有互構性的雙方在本質上是互為主體的,互為主體并非是要將有區別的東西混為一談,而是說科學知識中間很多地方都能表露出社會因素的影響,社會中間發生的各種現象也能從個體實踐和個體所掌握的知識中找到根源。過程上的互為建構,宏觀上的互為主體,微觀上卻只有個體的消解掉意義的枯燥實踐。這在一般邏輯上像是有悖于常識,這是因為建構實踐過程的宏觀歷時性和生成性導致的,只有在階段性完成態的節點上才可見。
其中關于科學知識對于現實社會實踐層面的影響,有西庫列爾對于美國少年犯罪的研究的例子,他分析了美國警察的行為是怎樣受到常識性的犯罪理論的影響的。比如,警方對待來自離異家庭的少年嚴厲的多。結果許多來自破碎家庭的孩子更易被逮捕,并以被捏造的罪名治罪。這種做法反過來又被犯罪學統計知識的形式提供了對上述常識的有力證據。因此警察們的常識性理論會成為生產和再生產其相關佐證的根源。[6]
另外一個方面的過程,也能看出對于上述觀點的支持。從社會科學知識對于常識的影響角度上,我們知道社會學不僅要以日常社會生活為研究對象,理解行動者自己的詮釋,或者為人們共享的常識性的詮釋。正如舒茨(Alfrd.Schutz)認為社會學知識的建構乃是第二層次的建構需要建立在第一層次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建構之上。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社會學知識不能完全等同與常識,它有自己理論性的立場和興趣,從這些出發能發現生活表象之下的深層的關系和結構,在認知上具有超越性。社會科學的概念是被制造來分析社會世界的, 卻又反過來被納入這個世界。因此, 社會科學的實踐影響并非主要是技術實踐層面的來自于改良社會方面影響, 而且更為重要的卻易被人忽略的通過社會科學的概念被吸納到社會世界中并成為它的構成內容來發揮作用。當社會科學概念為常人行動者所接納并融入社會活動中,它們自然成為社會例行實踐中人人諳熟的要素了。這從社區、社區建設、社會指標、社會發展、勢群體、社會支持等等社會學的專業詞匯逐步推廣到變成大眾的日常用語的一部分這樣一個程中可以清晰的看出來。所以說, 社會科學的概念不可避免地為常人行動者的理論和實踐所熟悉, 它不會局限為一種專業的話語。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學生黃平先生曾指出,在社會-人文環境中, 每一個被專家視為“外行”的社會成員作為具有掌握知識和技能的行動主體都在時時處處參與著社會的建構過程;并且, 這既是行動的過程, 也是闡釋的過程, 而他們對在自己的行動參與下建構起來的社會生活的闡釋, 若照專家看來也許無非是“常識”而已。不過,情況也有正好調轉過來的時候, 所謂的關于社會-人文的專業知識, 倘依常人的(或外行)看來, 也不過是用某種學術語言講述的常識。而最重要的問題還在于, 由于常人也是知識者和闡釋者, 任何一種社會-人文的專業理論都是在被常人從自己的眼光和角度不斷進行再闡釋著。正是這種“雙向闡釋”構成了社會科學不同于自然科學的基本品質。[7]
接下來的過程就是所有一般人在知識和自身實踐邏輯的影響下,發揮其社會轉型期的能動性了。我們舉消費社會為例,首先,處于消費社會宏觀敘事強權下的一般人會透過每日的生活實踐,反過來操弄或解構加于其身上的限制,開創出自主性的行動空間,雖然人們從未真正離開過這個受宰制的大環境,但是人們可以消解掉來自于宏觀方面的負面影響。第二,本文認為一般人的個體實踐的作用并不止于此,由于實際上每一次較大的社會結構的轉型都正是這些所有一般人看似毫不起眼的微觀實踐的群力導致的。至于這一過程所具有的隱秘性。這是由于,我們普通人都有這樣的經歷:花兩個小時閱讀一本書,獲得了新知。雖然人們都具有每一秒都能反思到自己身上的變化的能力,但是由于自我意識的“一心不能二用”,在純粹意義上讀書實踐過程中每一秒人們是無法自省自知的,只有當他完成了階段性的過程他才可以意識到自己身上的變化。這就是所謂實踐過程的歷史性和宏觀性。這是從共時性的任意微觀角度無法體認和把握的。這一過程就好比在社會結構轉型期所有一般人的合力所導致的整體社會結構的變動過程,處于其中的人們只有在階段性過程結束的節點上意識到好像發生了什么,但是貫穿整個過程無數人的實踐狀態其實是不自知的。這也就是為什么雖然是我們所有人自己導致的變化卻最容易被人們被社會所忽視。
以上過程的分析展現了一個整體循環鏈上的一次循環過程,實際上這一過程是不斷進行的,永不停息,往復不止。
三、作為分析方法的新意
以往人們對于社會研究的基本期待就是分析真相,解釋原因。或站在價值立場上采取批判性的和指引式的姿態。仔細分析會發現,僅僅是這種回顧性的分析研究除了在人們現實行動之前交代清楚發生了什么之外毫無增益。它不僅不能真正提出解決的方法,更加無法預測未來將要發生什么。
這是因為微觀層次的反思是根本無法把握從個體實踐到整體建構的宏觀歷時性過程導致的。而且這種反思難以捕捉,沒有抓手。只有站在微觀與宏觀相結合的角度,才能真正看清楚過程性的充滿了實踐邏輯和意義的真相,才能從這樣的過程性和生成性上去把握真正的解決之道。
例如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對于現代社會已經被消費社會的倫理和邏輯所侵蝕的判斷。如果我們變換視角,站在對于社會與科學知識與實踐個體三者循環建構的角度上分析,會發現任何學者的分析都只是整體鏈條上的一個環節。以此觀照鮑德里亞的觀點就會發現,雖然消費社會大潮對于人們的強制影響是不可避免且無從逃脫的,但是人們絕不會任由擺布,人們不僅會拿起弱者的武器消解掉這種影響,并且會在新的生活空間和領域開創出新的社會結構。當然新的結構會導致新的壓制,新的壓制會引起新的反抗,往復超越,不斷前進。至于人們如何走出誕生于后資本主義時代的消費社會的牢籠,雖然說消費社會的轉型過程是不可逆的,但并非一點思路沒有,有啟發性的觀點來自于加拿大傳播學者達拉斯·斯邁思(Dallas Smythe),他曾經給予毛時代的社會主義中國予以厚望,希翼當政者能夠有效控制好現代技術和資本主義消費品對于人們的沖擊,雖然目前看來一籌莫展,但是至少說明并非滴水不漏。[8]
又如社會學脫胎于社會哲學或社會理論的誕生與發展歷史也能說明這樣的過程。知識領域的范式革命模式也說明了這一點。雖然我們所立足的文化土壤塑造了我們自身,來自社會結構的力量制約著我們的行為,但是我們都相信我們的未來是充滿無限可能性的,尤其是在當今這樣社會進入快速變動的歷史時期,正是無數個體最生動的日常實踐時刻在形塑著行為,知識與社會。
四、對于認識論和思維方式的挑戰
首先,這一分析方法的局限。由于它在局部過程上直接吸收了社會建構論,所以建構論固有缺陷也被它全部繼承了,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知識相對主義”帶給建構論自身的悖論:任何知識都是由社會因素歷史地建構出來的,那么建構論作為一種觀點本身不也屬于知識嗎?這一問題直指近代西方科學理性誕生的認識論文化基礎,即建立在注重形式邏輯和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之上的固有矛盾。但是我們不必悲觀,因為在近代西方誕生的科學并非只有形式理性的一面,它還包括科學精神的一面,即認為科學知識總是可以被改進的,科學知識永遠處于發展狀態中。這種對于未知的開放態度是科學、社會以及實踐個體向前進步的前提。
其次,這一分析方法對于二元對立思維方式的挑戰。我們都知道人類歷史中有所謂實然和應然的對立,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對立。即嘴上說的是一回事,實際做的又是另外一回事,站在西方文化中的原子論、形式邏輯立場上看,科學與社會是截然對立的、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構成了分立對決,但是中國人的文化傳統中的實然和應然混合卻又是另外一回事,它顯示出中國文化的彈性,“人的舌頭是活的,你發達了說你天命所向,你落魄了說你活該”,黃宗智稱之為實用道德主義。就是說要尊重中國人歷史實踐過程形成的實踐邏輯。東方文化中歷史形成的善于綜合的思維方式無疑對西方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是有益的補充。本文并不妄求兩種思維方式的綜合統一,而且,從我們堅持的立場出發,不論不同文化,不同思維方式中誰會最終占據主導,都只是說明知識被重新定義和塑造。而另外一方面范式轉換,視角變換帶來的替代性和可選擇性也正是社會生活實踐的意義所指。它也是人們發揮能動性的抓手所在。
參考文獻:
[1]景天魁主編.社會學原著選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444)
[2][德]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56)
[3]吳飛.“空間實踐”與詩意抵抗[J],社會學研究2009(2)
[4]蘇國勛,社會學與社會建構論[J],國外社會科學2002(1)
[5]沈原,“強干預”與“弱干預”:社會學干預方法的兩條途徑[J],社會學研究2006(5)
[6]同[4]
[7]黃平. 未完成的敘說[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 120-121)
[8][加拿大]達拉斯?斯邁思.自行車之后是什么?——技術的政治與意識形態屬性[J],開放時代,2014(4)
作者簡介:王成林(1989-),男,河南汝南縣,安徽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會學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