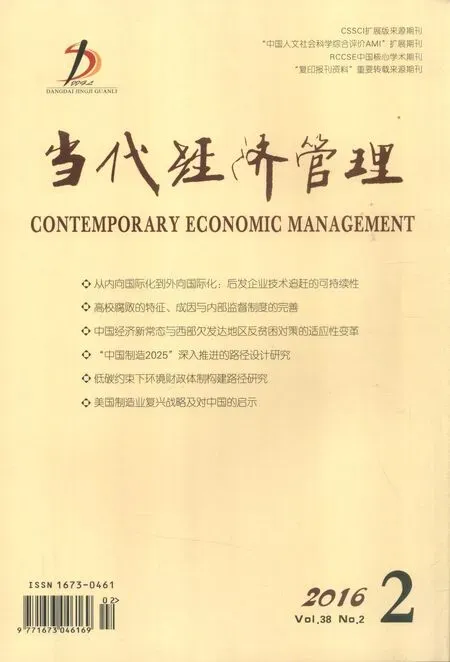地方官員與城鎮化扭曲性發展
■曾 冰
(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北京100081)
?
地方官員與城鎮化扭曲性發展
■曾冰
(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北京100081)
[摘要]以地方官員為視角,在地方官員具有理性經濟人特征的基礎上,將土地制度,財政分權等內容納入了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進而分析得出:地方官員對土地城鎮化偏好要強于人口城鎮化,同時又造成了戶籍人口城鎮化和常住人口城鎮化的脫鉤。因此,對于當前的城鎮化扭曲性發展,地方官員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關鍵詞]土地城鎮化;地方官員;戶籍人口;常住人口
網絡出版網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356.F.20160201.1137.002.html網絡出版時間:2016-2-1 11:37:33
一、問題提出
改革開放以來,在實現經濟快速發展同時,我國城鎮化進程也獲得了巨大成就,并逐漸成為我國經濟社會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大部分學者都把城鎮化視作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和轉型的重要引擎,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甚至斷言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將會是影響本世紀世界發展的兩件大事之一。目前無論學界還是國家層面都對城鎮化給以極大的關注和期待。黨的十八大報告中共有7次涉及到城鎮化,而且明文把城鎮化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載體,甚至把其作為解決我國經濟結構性問題的重要手段。
城鎮化發展核心在于人的城鎮化,不僅僅表現為空間上不斷擴展,不斷演變的過程,更是人口遷移并不斷融入城市生活,公平享受城鎮化成果的過程。然而我國目前城鎮化進程表現出一種扭曲性發展現象:即人口城鎮化要滯后于土地城鎮化進程,而人口城鎮化中又面臨著戶籍人口城鎮化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的不協調。具體表現為:我國城鎮化更多地依賴土地上的空間擴張,片面追求城市規模,使得人口城鎮化要遠滯后于土地城鎮化,兩者間關系極不協調。同時由于我國戶籍制度等帶來的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使得我國人口城鎮化內部也出現了結構性的扭曲問題,在城鎮常住人口中存在很多來自農村的務工人員,盡管這些人完成了地域和空間上的轉移,卻難以獲得身份上的認可,從而難以平等享受到城鎮化發展的成果。由此帶來了人口城鎮化進程兩張皮合不攏現象,即戶籍人口城鎮化與常住人口城鎮化錯位不協調發展。據統計,目前我國城鎮常住人口中仍有2億多人的身份還停留在農業戶口上,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難以和城鎮非農人口享受同等待遇。毫無疑問,這種城鎮化扭曲性發展不利于我國經濟健康有效地發展,甚至容易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
用量化方式來描述這種城鎮化扭曲性發展,將上述三種城鎮化進行操作化和定量化,分別采用土地城鎮化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標準,土地城鎮化主要表現在城市化進程中農業用地轉化為非農業用地或城市用地的過程,因此我們采用城市建成區面積在區域總面積占比作為土地城鎮化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以城鎮人口中的常住人口為口徑,即城鎮常住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采用戶籍特征的非農業人口為標準,即非農業戶籍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通過圖1可以看到土地城鎮化與人口城鎮化發展尤其是戶籍人口城鎮化進程極不匹配。此外,戶籍人口城市化進程十分緩慢,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的差距不斷擴大,表明了在那些伴隨著城鎮空間擴張而增加的城鎮常住人口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未能實現身份上的有效轉變,沒有完全融入城市中去。
考慮到土地城市化率與人口城市化率在指標度量上存在差異性,故其之間絕對值難以進行直接對比,但我們再通過三者增長率來進一步分析城鎮化扭曲性發展。從圖2清晰看到,我國土地城市化的增長率大部分年份尤其是2002年以后不僅要高于戶籍人口城市化的增長率,同時也高于常住人口城鎮化。顯然,我國人口城市化與土地城市化總體上是不相協調的,這也說明我國當前城鎮化發展中一個明顯的特征就是城鎮建成區發展超前,而人口的集聚和發展要明顯滯后。我們再從人口城鎮化結構來看,常住人口城鎮化增長率總體上都是高于戶籍人口城鎮化增長率,說明了城鎮化進程中,城鎮中常住人口的增長速度要快于農業人口轉化為非農業人口的速率,進一步反映了當前城鎮化發展中未能完全有效吸收農業剩余勞動力,人口城鎮化伴隨著半拉子城鎮化,偽城鎮化問題的出現,城鄉二元化問題依然嚴峻。
那么,這種扭曲性問題主要原因在哪里?我國城鎮化進程與西方國家最大的不同在于我國城鎮化更多是由各級政府主導的,“自上而下”(李強等,2012),而政府行為又是官員行為“加總”的結果,政府的決策事實上是官員決策的體現(周黎安,2007)。因此,城鎮化的進程同地方官員尤其是市級官員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曾任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曾說道:“市委書記、市長是城市發展的策劃者、決策者和管理者,市委書記、市長的思路和政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城鎮化建設的方向”。進一步而言分析城鎮化扭曲性問題不能繞開地方官員這重要一環。目前有學者把這種城鎮化扭曲性問題戲稱為“市長城鎮化”對“市場城鎮化”的替代。從這個意義上講,將視角停留在政府管理和制度分析等層面上是難以觸及其根本原因,只有深入分析和解釋地方官員行為對城鎮化的作用機理,才是理解城鎮化扭曲性問題的關鍵所在,從而能更好地為新型城鎮化的發展提供理論借鑒意義。

圖1 三類城市化率比較①

圖2 三類城市化增長率比較
二、機理分析
要想理解地方官員對城鎮化的發展,必須明晰地方官員的行為邏輯出發點和背景框架(見圖3)。首先,地方官員應具有理性經濟人的特征,由于其任命是由中央和上級政府決定,因此地方官員的利益主要來自于政治晉升利益,其目標函數是在任期內實現利益最大化②。其次,中央和上級政府對地方政府予以行政管理權和經濟管理權下放,從而使得地方官員在當地的經濟發展具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第三,中央會通過相應的制度安排對地方官員提供激勵和約束,從而影響到地方官員決策與行為的動機,同時這種制度的安排會直接影響到經濟發展。

圖3 地方官員的行為邏輯框架圖
誠然地方官員對城鎮化發展帶來扭曲性影響除了地方官員自身對城鎮化認識和管理上存在不足的原因外,背后其實還有更深層次的機理。而要挖掘這種機理,就需要我們在上述邏輯框架的基礎上,分析地方官員如何對城鎮化扭曲性發展產生作用:即為什么地方官員對土地城鎮化偏好要強于人口城鎮化。其次,分析地方官員為什么會帶來人口城鎮化產生“兩張皮”現象,即在對待常住人口城鎮化和戶籍人口城鎮化為什么會出現不同的態度。
命題1:地方官員對土地城鎮化偏好要強于人口城鎮化
中央和上級政府對地方官員績效考核的重要內容是轄區GDP的增長,因此作為政府的代理人——地方官員在這種激勵機制下完全有動機去做能夠使自己獲得晉升的事情,并積極地致力于發展其管轄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而土地城鎮化要比人口城鎮化具有更強的經濟關聯性(例如房地產業,道路建設),更能拉動GDP增長,容易在短期內顯效果,因此土地城鎮化推進無疑成為地方政府官員追求政績和晉升空間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徑。同時土地制度和財政分權制度又為這種晉升途徑產生了“錦上添花”的效應。財政分權一方面使得地方政府對經濟發展享有一定的自主權,另一方面遺留下了地方政府事權與財力的不匹配問題,導致了地方官員晉升壓力加重。這種導向會促使地方官員從預算外尋求途徑彌補財力不足,并大力加強交通、能源等生產性基礎設施建設推動經濟增長,最終獲取晉升。而當前的土地制度恰好迎合了這種需求。我國當前土地制度主要體現在土地出讓制度和土地補償制度,這種制度安排使得地方官員對土地使用具有一定的自主權,并不斷地通過征地為起點,低價取得土地,高價獲取土地出讓收入,并進行土地融資,進而推動新城投資開發,房地產發展等。而后者又會反過來帶動土地升值,并獲得高額土地出讓金,產生循環累積效應,帶來經濟快速增長,形成了我國特有的“土地財政”。此外,在土地出賣過程中,地方官員對賣地收入具有一定的可支配能力,不僅可用于本期的建設投資和政績的形成,還使得地方官員從土地出讓和投資中得到很多尋租機會,獲得巨大的利益。上述因素會刺激地方政府官員賣地、不斷擴展城鎮空間,最終表現為地方官員對土地城鎮化發展的積極性。
而另一方面發展人口城鎮化不僅會加大政府財政壓力,而且又是一個長期過程,很難在短期收到效果,地方官員任期的相對短暫性使得絕大部分財政支出投入到土地開發、城鎮建設領域這些顯性項目,而不是與市民化相關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當中去。因此,地方官員最為關心的是如何將農村土地拓展為城市用地,至于怎樣把農村人口融入并吸收到城市中則表現冷淡。這種“要地不要人”的現象表明了地方官員對土地城鎮化的偏好要強于人口城鎮化。此外,土地城鎮化的發展又會過度拔高房產價格,進一步阻礙了人口城鎮化發展,并滯后于土地城鎮化發展。
命題2:地方官員造成了戶籍人口城鎮化和常住人口城鎮化的脫鉤。
盡管土地城鎮化與人口城鎮化出現失調,但土地城鎮化的的不斷擴展對人口城鎮化也帶來了一定的正外部性:提供了一些優質的公共資源,發展機會和平臺,再加上城市收入水平高,從而吸引農業剩余勞動力不斷流入城市。同時地方官員也希望相當一部分農業剩余勞動力進入城市,一來城鎮化發展需要這些廉價勞動力的支撐,二來當地粗放型經濟增長也需要勞動力數量上的擴張。也就是說土地城鎮化的發展會伴隨著常住人口城鎮化的發展,但是這種常住人口城鎮化并不是地方官員刻意主動追求的,而是由土地城鎮化派生出來的。與此同時地方官員對那些在城市務工的農民工尤其是常住人口如何實現市民化也不會表現出過多的熱情,甚至會抵觸市民化,使得非農人口與城鎮常住人口出現“兩張皮”合不攏,導致了人口城鎮化結構性問題。首先,從成本收益上,市民化要較土地城鎮化和常住人口城鎮化投入的成本高,且短期收益低。由于戶籍人口城鎮化推進最重要的內容就是市民化,而市民化就必須妥善解決好隨遷子女教育、醫療保障、養老保險和保障性住房等問題,而這些問題的解決就代表了更多的成本,據我國社科院課題調研得出我國東、中、西部三大地區目前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依次是17.6萬元、10.4萬元和10.6萬元,全國平均為13.1萬元/人。而這些市民化成本會使得地方政府的財政預算吃緊,還會對經濟增長帶來短期阻礙,使得短期收益低,而這些又會與官員績效考核相抵觸。因此,地方官員會對戶籍人口城鎮化產生惰性。
此外,官員任期對會影響到這種結構性問題。任期制會使得戶籍人口城鎮化成效會在不同任期官員之間出現分配差異,導致地方官員在市民化進程難以實現資源最優化。因為戶籍人口城鎮化只有長期發展才能顯現出效果,極易導致后任官員搭便車,即前任官員花費大量成本推進市民化,再加上任期過短,使得市民化功勞落在了下任或下下任官員身上。由于官員具有經濟人特性,會做出更有利于自身利益尤其是政治晉升利益的決策,因此在任地方官員在任期內對市民化推進會有所保留。總之,對于戶籍人口城鎮化來說,地方官員會存在惰性,有所保留,從而造成了戶籍人口城鎮化和常住人口城鎮化的脫鉤。
三、結論與對策
本文以地方官員為視角,并將土地制度,財政分權等內容納入了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進而分析得出:地方官員對土地城鎮化的偏好要強于人口城鎮化常住人口城鎮化具有推動作用,且對土地城鎮化的作用要強于常住人口城鎮化,不過在戶籍人口城鎮化進程中地方官員影響作用不顯著。因此,對于當前的城鎮化扭曲性發展,地方官員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從對策而言,首先,就地方官員自身來說,應加強地方官員對新型城鎮化的科學認識及其發展規律的把握,樹立官員健康的可持續性城鎮化發展理念。同時,提升地方官員的城市規劃、建設、管理水平,拓寬地方官員的發展視野等。另外,由于地方官員在城鎮化發展中更在乎自身政治晉升利益甚至是個人物質利益,所以也應積極提高地方官員的黨性和政治素養,將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新型城鎮化發展的重要出發點和支撐點。要求地方官員在新型城鎮化的推進中以滿足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
第二,地方官員對城鎮化的扭曲性發展重要根源在于以GDP增長為核心的晉升錦標賽機制的不合理引導。應加強政績考核的科學發展導向,加大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群眾幸福度、農民工市民化等在政績考核中的權重,并將其作為地方官員離任審計的重要內容。并著重考慮將轄區居民對政府行政的滿意度內生于官員績效考核體系中,使官員有更大的動力去推動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的發展,從而保證城鎮化的健康發展。另外任期制容易讓地方官員更注重自身利益和短期利益,導致城鎮化難以科學持續性發展,應對地方官員在城鎮化規劃實施情況實行動態監測和跟蹤分析,并把其納入到績效考核的問責制或終身追究制。
第三,加快戶籍制度及相應的社會福利制度改革。有人把人口城鎮化“兩張皮”現象歸為戶籍制度的原因,其實戶籍制度改革只是實現市民化的一個必要條件,但并非充分條件。我們看到的戶籍只是人口城鎮化“兩張皮”合不攏的一個表象的外殼,關鍵是隱含在戶籍背后的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福利待遇帶來的二元結構化,使得地方官員對市民化存在惰性。因此,對戶籍制度改革不能簡易地理解為戶籍登記的歸類方式改變和落戶條件的寬松化等,其關鍵點在于完善和匹配與戶口相關的社會福利,保證那些完成戶口轉變的居民能平等地享有與原有市民相同的社會福利、保障及其他公共服務。
第四,我國土地具有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二元化屬性,這種屬性容易帶來土地征收和出讓制度不完善,使得地方官員對土地城鎮化有著天然的強烈偏好,并放大了城鎮化發展的扭曲程度。從本文分析角度而言,對土地制度改革最重要的一環就是科學完善土地出讓制度,可考慮把土地出讓金用在社會福利,尤其加大對農民工實現市民化方面的投入和財力支撐。考慮試點實行土地年租制,使土地出讓收益的一次性特征得到削弱。建立以土地為核心的不動產稅體系,大力抑制地方政府或地方官員對土地出讓金的溺癮。同時還應加大農民在城鎮化的受益權,允許集體土地自由進入市場,農村集體宅基地的使用權自由轉讓、抵押和出租。
第五,深化改革財稅體制,依照財力與事權相對稱的準則,明晰各級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合理保障和充實地方政府的基本財力,對地方政府的事權約束設定合理化邊界,激發地方官員推進新型城鎮化的積極性。地方官員對市民化推進持保留態度,原因之一在于推進市民化需加大公共基礎和社會福利,這就意味著較大支出。因此中央政府及上級政府對地方政府的公共基礎和社會福利進行相應程度的支出,使現行的財政體制和公共服務供給機制要能夠負擔起市民化成本,使地方官員在推動市民化進程時免去后顧之憂。
[注釋]
①城鎮化與城市化的概念界限目前還存在一定模糊,有學者也把城鎮化成為城市化,但兩者的劃分對本文意義不大。出于統計意義考慮,這里我們也稱城市化。另外,圖表中的數據資料來自于蔡繼明等人的相關文獻。
②當然,地方官員利益也來自于個人的經濟利益,但遠小于政治晉升利益。
[參考文獻]
[1]李強,陳宇琳,劉精明.中國城鎮化“推進模式”研究[J].中國社會科學,2012(7):82-99.
[2]丁瓊.城鎮化建設過程中的政府主導研究[J].學術論壇,2014(3): 54-55.
[3]陳甬軍,徐強,等.政府在城市化進程中的作用分析[J].福建論壇,2001(9):16-20.
[4]周黎安.中國地方官員的晉升錦標賽模式研究[J].經濟研究,2007 (7):36-53.
[5]汪洋.走廣東特色城鎮化道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N].廣州日報,2010-06-12.
[6]汪冬梅,楊學成.中國城市化道路的反思與探索[J].改革,2003 (5):18-23.
[7]高強.影響城鎮化發展的因素探析[J].經濟與管理研究,2005(2): 13-18.
[8]崔功豪,馬潤潮.中國自下而上城市化發展及其機制[J].地理學報,1999(2):106-115.
[9]李子聯.人口城鎮化滯后于土地城鎮化之謎——來自中國省際面板數據的解釋[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3(11):94-101.
[10]蔡繼明,程世勇.中國的城市化:從空間到人口[J].當代財經, 2011(2):78-83.
(責任編輯:張積慧)
The Local Officials and the Distortion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ization
Zeng Bing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tries to analyze the problem of distortion of the urba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officials. It is on a fact that local officials maintain rational economics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the article integrates land system,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to a unified analysis framework.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local officials are in favor of the land urbanization more than the population urbanization,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 inclination leads to the decoupling between the registered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In a word, the local officials play active role in the distortion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ization.
Key words:land urbanization;local official;registered population;resident population
作者簡介:曾冰(1986-),男,江西九江人,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區域經濟學,經濟地理學。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西部項目(14XRK003)。
收稿日期:2015-05-20
DOI:10.13253/j.cnki.ddjjgl.2016.02.002
[中圖分類號]F299.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6)02-00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