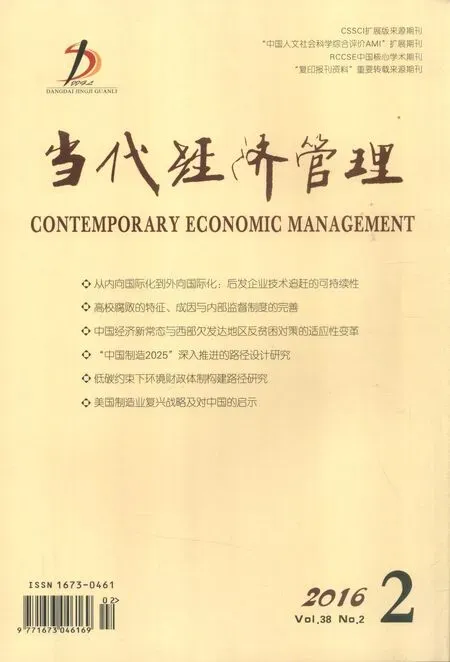從內向國際化到外向國際化:后發企業技術追趕的可持續性
■吳先明,黃春桃
(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湖北武漢430072)
?
從內向國際化到外向國際化:后發企業技術追趕的可持續性
■吳先明,黃春桃
(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湖北武漢430072)
[摘要]基于技術追趕理論,選取我國2003~2013年省際面板數據,對后發企業從內向國際化到外向國際化的技術追趕績效進行研究,同時考察吸收能力及知識產權保護程度的調節作用。研究發現,現階段外向國際化可以顯著提高后發企業的技術追趕績效,而內向國際化卻明顯阻礙后發企業技術的追趕,但內向國際化對外向國際化的技術追趕效果依然具有積極的調節作用,從內向國際化到外向國際化是后發企業實現技術追趕的一個可持續性過程。進一步研究發現,后發企業的吸收能力對外向國際化的技術追趕績效具有明顯的積極影響,而對內向國際化的技術追趕效果缺乏統計上的顯著性。知識產權保護程度對后發企業內外向國際化的技術追趕績效均具有顯著的積極影響,即顯著加強外向國際化與技術追趕績效的關系,而顯著減弱內向國際化與技術追趕績效的關系。
[關鍵詞]技術追趕;內向國際化;外向國際化;后發企業;知識產權保護
網絡出版網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356.F.20160201.1137.003.html網絡出版時間:2016-2-1 11:37:33
一、引 言
發展中國家企業,即后發企業通常面臨市場和技術雙重劣勢,特別是在技術水平上,與發達國家企業存在較大差距,使其在全球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后發企業的發展過程其實就是實施追趕以克服劣勢的過程,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技術的追趕問題,只有通過技術追趕、增強自主創新,才能推動科技進步并轉變增長方式,從而在全球競爭中搶占有利位置。在新的競爭形勢下,后發企業應該如何進行技術追趕?關于這一問題,后發企業追趕理論認為,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后發企業具有后發優勢,既可以通過自主創新也可以通過學習國外企業的先進技術進行模仿創新。較之于自主研發,通過國際化直接或間接學習外部先進技術,可以更快地實現自身技術水平的提高,而且大大節省R&D成本。特別是在產品生命周期日漸縮短、技術日益復雜,R&D成本不斷增加,而全球競爭日漸激烈的今天,單純依賴內部研發很難滿足企業的創新需求,尤其是后發企業的技術追趕需求。只有通過國際化聯系外部資源,引進、吸收和利用國外先進技術才能更好更快地提升創新能力,實現技術追趕[1]。
通過國際化學習國外技術是一個雙向過程,包括內向國際化和外向國際化。所謂內向國際化,即引進國外產品、資本、技術和人才等要素,使本國企業可以學習積累其先進技術與經驗并逐步實現國際化;外向國際化則指本國企業將產品、資本等優質要素延伸至國際市場,主動學習國外技術與經驗從而實現國際化。事實上,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之一,從1980年初改革開放以來就實施“引進來”的內向國際化戰略,至2001年,又提出“走出去”外向國際化戰略,十七大報告中還提到要把“引進來”和“走出去”結合起來,即把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連接起來,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更好更快地提高中國技術水平和國際競爭力。那么,中國后發企業的內外向國際化成效如何,是否通過技術溢出實現了技術追趕?這是學術界、政府和社會都非常關注的問題。
不僅如此,正如芬蘭學者Welch和Luostatinen[2]曾在其《國際化中的內外向聯系》一文中提到,“企業內向國際化過程會影響其外向國際化的發展,企業內向國際化的效果將決定其外向國際化的成功”。特別對于后發企業而言,內向國際化是外向國際化的起點,而外向國際化是內向國際化的進一步發展和提高。在實施外向國際化戰略之前,中國企業確實早已通過合資合作、代工接包等內向國際化方式參與了國際分工,這20余年的內向國際化是否為外向國際化打下基礎,是否能促進外向國際化的技術溢出效果進一步實現技術追趕?有必要對其技術溢出效應做一個全面評估。同時,后發企業通過國際化實現技術追趕還受其自身能力,特別是吸收能力,及其所處創新制度環境的影響。例如在對外直接投資中國有企業占主導地位,很大原因在于其更具財力及研發實力,能更好地引進并吸收國外先進技術及管理經驗。而創新制度環境可能為后發企業技術創新提供機會,也可能制約創新的發展。這些內外部因素是如何影響其技術追趕績效的,亟待進一步補充研究。
針對現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基于技術追趕理論,運用我國2003~2013年省際面板數據,分析后發企業內外向國際化的技術追趕績效及其可持續性,同時考察后發企業內部影響因素吸收能力和外部影響因素知識產權保護程度對內外向國際化技術追趕績效的調節作用。
二、研究假設
(一)內向國際化和外向國際化
早期發展經濟學只關注內向國際化即外商直接投資(IFDI)對東道國經濟發展的直接作用,而忽視其對本土企業技術進步的外部性,即技術溢出效應(spillover effects)。到1960初,MacDougall第一次指出FDI具有技術溢出效應[ 3],此后理論界做了大量研究。但對“IFDI是否有助于本土企業實現技術追趕”這一問題尚未達成一致。有學者認為,后發企業與外國企業前后關聯,可以直接或間接學習其創新經驗,提升自身技術從而實現技術追趕[4];但也有學者指出IFDI會抑制技術追趕的進程[5-6]。Abramovitz[7]的追趕假說認為,技術追趕績效與技術差距呈正比,研究結果的不一致可能與樣本企業所處特定時期有關,技術越落后的后發企業其IFDI技術溢出效應越顯著。后發企業至今大多已實施內向國際化戰略較長時間,隨著技術差距的縮小其技術溢出效應越來越收斂。而且,國外企業進入后發國家是希望利用并維持其壟斷優勢從而獲取超額利潤,必然會防止核心技術外流,所以后發企業要進一步獲取核心技術越來越困難,必須改變追趕策略。
近年來,學者們發現越來越多的后發企業開始進行外向國際化即對外直接投資(OFDI),其目的除了獲取自然資源外,越來越表現為技術尋求型[8-9],即以獲取外國企業的技術、知識、研發機構等為目的,通過并購或新建海外機構,旨在提升企業技術水平的跨國投資。有實力的后發企業到R&D資源密集的國家設立研發機構或直接并購外國企業,在地理上或產權上靠近從而最大可能地尋求和利用先進技術,開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新技術新產品[10-11],并通過內部傳遞和外部溢出兩種方式向投資后發企業轉移[12],以此來提高母國企業的技術能力。
綜上,后發企業若仍然只是依賴IFDI模仿外國技術進行生產,而忽視發展自身核心技術,那么將再次拉開與發達國家企業之間的技術差距,即我們認為IFDI如今已開始制約后發企業的技術追趕,并希望通過實證數據進行檢驗。而通過外向國際化,后發企業向外與國外企業進行合作研發或將其先進技術納為己有,利用國外知識和人才資源,可以進一步推進技術追趕。此外,如Welch和Luostatinen發現,內向國際化是外向國際化的基礎和條件,外向國際化是內向國際化的進一步發展和提高。劉紅艷和崔耕[13]對中國338家企業的調查也證實,“引進來”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走出去”的效果。所以,內向國際化雖然不能促進后發企業的技術追趕,但有利于外向國際化更好地實現技術追趕。綜上,我們提出:
假設1:外向國際化與后發企業技術追趕績效呈正相關關系;
假設2:內向國際化與后發企業技術追趕績效呈負相關關系;
假設3:內向國際化對外向國際化與后發企業技術追趕績效的關系起到積極的調節作用。
(二)吸收能力
Cohen和Levinthal(1989)首次提出吸收能力概念并將其引入追趕理論,即發現和吸收新信息并將其用于創造新價值的能力[14]。此后吸收能力概念層出不窮,已成為技術追趕研究的一個新趨勢。Rogers(2010)將吸收能力定義為獲取、學習和應用國外先進技術的能力,認為其與技術差距一起決定技術追趕的速度[15]。技術創新是科學性活動,后發企業為獲取和利用外部技術,特別是上游先進科學,必須先積累一定的知識和經驗,提高自身吸收能力,即必須先進行內部研發投資。具有較強R&D能力的企業不僅能更好地理解外部技術價值和未來發展趨勢,還能更有效地吸收利用從而促進自身創新[16],內部研發與外部技術引進相結合可以更大程度地提升企業技術追趕績效[17]。在國內研究中,很多學者也發現,后發企業自身的吸收能力是決定其能否抓住國際化創新機會的關鍵,當地企業R&D投入越高,吸收能力越強,其與外資企業的技術差距越小[18-19]。因此,我們提出:
假設4:后發企業的吸收能力對于外向國際化與技術追趕績效的關系有積極的調節作用;
假設5:后發企業的吸收能力對于內向國際化與技術追趕績效的關系有減弱的調節作用。
(三)知識產權保護
制度作為一種游戲規則,是人為設定的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的限制性因素,可以減少社會行為的不確定性[20]。制度本身具有地區屬性,不同地區其制度質量、復雜程度不同,對當地后發企業國際化技術引進與合作研發的影響也就各有差異。近年來,知識產權保護這一制度因素在技術創新研究領域獲得越來越多的關注,已被認為是影響技術創新效果的重要因素。政府實施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干預市場,目的是為創新者提供一定的壟斷優勢,保護其創新免受模仿競爭,獲得更多的市場占有[21]和期望收入[22],如此企業才愿意進行更多的研發投入。外向國際化通過并購或合作研發進行技術追趕,前期投入大,投資回報周期長、不確定,若增強知識產權保護,能提高法律保障,降低投資風險,則后發企業更愿意投資于研發領域,進而有利于提高技術水平[23-25]。而且基于技術的外溢性特點,外國企業為維持其壟斷優勢,獨享超額利潤,會傾向于將先進技術投資于那些知識產權保護程度高的地區[26],從而延緩甚至防止其核心技術外流。所以,那些知識產權保護程度高的地區,其通過內向國際化學習外國技術的機會反而更多,地理上也更接近,那么技術追趕的效果也應該更好。因此,我們提出:
假設6:知識產權保護程度對于外向國際化與技術追趕績效的關系具有積極的調節作用;
假設7:知識產權保護程度對于內向國際化與技術追趕績效的關系具有減弱的調節作用。
三、模型設定和數據說明
根據以上研究綜述,本文模型設定如下:

其中,i表示中國各省,t表示年份,β0為常數項,λi、μt分別表示省份個體效應和時間效應,ξit為殘差項。OFDIit、IFDIit、Foundit、Propit分別表示中國各省的外向國際化、內向國際化、吸收能力和知識產權保護程度。∑nδnCnit為控制變量,包括貿易開放(IMEX)、金融發展(FINA)、投資率(CAPI)和居民存款(SAVE)。
模型中GAPit是被解釋變量,表示各省份當年與世界先進國家的技術差距。參照Kokko[27](1996)、Wei等[28](2006)、李梅和柳士昌[19](2012)等學者的做法,用勞動生產率差距表示技術差距,即用國外勞動生產率與國內各省份勞動生產率的差值衡量技術差距。差值越大,表示該省技術水平與先進地區差距越大。從世界銀行數據庫獲得英、美、法、德、意、日、韓、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亞和中國香港共11個國家(地區)的相關數據,并以2000年為基期平減折算出實際就業人員的人均人民幣GDP收入,取其平均值作為國外勞動生產率。同樣,我國各省份的勞動生產率用平減后地區GDP除以就業人數得到,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和《中國統計年鑒》。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和完整性,最后選取我國30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2003~2013年間的相關數據作為樣本,西藏因有缺失數據予以剔除。有關變量均折算為2000年不變價人民幣,詳見表1。
四、實證結果
表2是各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矩陣。從表中來看,除OFDI和Prop的相關系數為0.75外,其他相關系數都小于0.7,模型不會存在嚴重的共線性問題。進一步檢查各個回歸模型,發現各模型中所有變量的VIF遠小于10,說明變量之間確實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又因本文需考察調節效應,為消除直接相乘所形成的交互變量與原變量之間存在共線性,采取中心化處理,即對交互項變量及涉及的相關變量與其變量均值做差值處理,形成新的變量,用新變量進行回歸。

表1 變量設定及數據來源

表2 描述性統計和相關系數
關于面板數據的回歸模型,可供選擇的有混合估計(POLS)、固定效應(FE)和隨機效應(RE)模型。在確定模型回歸時,首先,進行LM檢驗,若其結果通過顯著性檢驗,則拒絕采用POLS的原假設,選擇RE。其次,進行F檢驗,其結果顯著則拒絕POLS,選擇FE。最后,進行Hausman檢驗,若其結果拒絕原假設,表明應選擇FE模型。模型選擇及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我們采取逐步回歸的方法,將各類變量依次納入模型,檢驗發現每次回歸均應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在整體顯著性檢驗中,各模型R2介于0.521~0.575之間,F值均在1%水平上顯著,表明各模型均有良好的擬合優度。
模型1是對控制變量的檢驗。貿易開放與技術差距呈顯著正相關,與Lin和Lin(2010)的結論相反[36],我們認為這是因為他們研究的對象為發達國家企業,這些企業一般進口自然資源等初級產品,出口具有壟斷優勢的先進產品。相反,后發企業向外出口的通常是初級產品或進口再裝配產品,技術溢出效應并不明顯[37]。而進口的通常為技術水平相對較高的產品,這些產品的進口會讓后發企業產生依賴而忽視自主研發的投入[38],從而影響進一步實現技術追趕。金融發展、投資率、居民存款與技術差距均顯著負相關,與預期一致,即各省金融市場越發達,后發企業可用于技術追趕的研發投入更廣泛、更充足;固定投資比重越大,后發企業所處基礎設施條件更優越,則更有利于吸收利用先進的技術;居民存款余額越多,表明居民生活水平越高,需求產生差異化,進而推動技術的創新,所以都利于后發企業的技術追趕。
模型2和3是對解釋變量的檢驗。模型2顯示,OFDI與技術差距顯著負相關,表明外向國際化有利于提高后發企業的技術追趕績效,因此,假設1獲得實證支持。這與李梅(2010)、李梅和柳士昌(2012)的研究結論保持一致,但類似研究只關注OFDI的技術溢出效應,往往忽視IFDI的影響及其對OFDI技術溢出效應的調節作用。模型3顯示,IFDI與技術差距顯著正相關,表明IFDI對技術追趕具有顯著的消極影響,即假設2獲得實證支持。這與Cheung和Ping(2004)的結論相反,他們認為我國IFDI對企業技術創新具有促進作用。這一情況近年來已發生變化,隨著后發企業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IFDI的技術溢出效應越來越有限,現階段后發企業繼續依靠外商投資的溢出效應已不能再進一步實現技術追趕,反而容易造成自身創新能力后勁不足,拉大技術差距。但是我們不能忽視IFDI的基礎作用,如模型4顯示,IFDI對于OFDI與技術差距關系的調節作用顯著為負,表明IFDI對OFDI的技術追趕績效具有促進作用,即假設3成立。后發企業最早一般先通過IFDI與外資企業產生聯系,學習其先進技術和經驗,大大提高自身研發能力并縮小技術差距,為進一步學習提供基礎條件。然而后發企業技術達到一定水平后,再難進一步吸收其核心技術,此時必須轉換追趕策略,主動并購或向外合作研發,才有可能進一步實現追趕。因此,IFDI 是OFDI技術追趕的基礎,OFDI是IFDI技術追趕的可持續發展。

表3 回歸結果
模型5和6依次納入調節變量吸收能力和知識保護程度,結果顯示,兩個調節變量對后發企業技術差距的直接影響都不顯著,表明提高自身吸收能力以及改善知識產權保護環境并不能直接提高技術追趕績效。進一步地,模型7顯示,吸收能力的調節效應顯著為負,即后發企業的吸收能力對于外向國際化與技術追趕績效的關系具有積極的調節作用,與李梅和柳士昌(2012)、李梅(2010)的研究結果一致,假設4得到論證。模型8顯示,吸收能力對IFDI與技術差距的關系也具有負向調節作用但不顯著,因此假設5未通過檢驗。這可能是因為現階段后發企業已很難從IFDI的技術溢出效應中獲益,即使有很強的吸收能力,涉及到外企的核心技術,依然很難進一步模仿學習。對于知識產權保護的調節效應。模型9和10顯示,知識保護程度對于OFDI、IFDI與技術差距的關系均起到顯著的負向調節,即顯著促進外向國際化的技術追趕績效,而顯著減弱內向國際化的技術追趕績效,與蔡中華等(2014)結論一致,假設6和7均成立。
五、結論與討論
據世界銀行數據顯示,直至2012年,中國研發投入占GDP比重已達1.98%,與中低等收入國家相比處于較高位置,但是距離高收入國家的2.3%還有相當距離。雖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通過引進外資不惜以國內市場為代價,希望“以市場換技術”,顯著提升國內企業的技術水平和核心競爭力,但事實證明,結果并不如愿,“中國制造”仍處于全球價值鏈的底端。為了從根本上改變國內企業嚴重依賴外來技術的局面,2006年政府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力爭到2020年我國研發投入要占到GDP的2.5%以上,科技進步貢獻率達60%以上,對外技術依存度降到30%以下,旨在依靠自主創新打造自身核心技術,以技術驅動經濟增長,并從根本上轉變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至此,“創新”成為社會各界的關注熱點,而技術追趕作為后發企業實現技術創新的重要手段,也倍受關注。為什么中國“以市場換技術”的策略不盡如人意?后發企業又如何通過技術追趕持續縮小與發達國家企業的技術差距?
本文運用我國2003~2013年間省際面板數據,對后發企業從內向國際化到外向國際化的技術追趕進行績效研究,同時考察后發企業自身吸收能力及外部知識產權保護程度的調節效應。研究發現,現階段外向國際化可以顯著提高后發企業的技術追趕績效,而內向國際化卻明顯阻礙技術的追趕,但內向國際化依然對外向國際化的技術追趕效果具有促進調節作用,從內向國際化到外向國際化是后發企業技術追趕的一個可持續性過程。后發企業的吸收能力對外向國際化的技術追趕績效具有明顯的積極影響,而對內向國際化的追趕效果缺乏統計上的顯著性。各地區的知識產權保護對后發企業內外向國際化的技術追趕績效均具有顯著的積極影響。
本文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首先,以往對IFDI技術追趕效果的研究結果具有模糊性,存在不同觀點。本文通過對最新技術追趕數據進行分析,發現內向國際化策略已不能促進后發企業縮小反而會顯著拉大與先進企業的技術差距,這意味著后發企業要進一步實現技術追趕必須轉變策略。這一發現可以增進人們對后發企業技術追趕行為的理解,促進理論發展。其次,外向國際化對技術追趕的影響也具有不確定性,但本文研究修正了Thirlwall(1982)、Canltwell等(2004)的結論,澄清相關爭論,發現外向國際化對后發企業技術追趕已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而且進一步明確外向國際化作為內向國際化的進一步發展和提高,對技術追趕具有可持續性,為更好地發展內外向國際化相結合的戰略提供理論支持。最后,在考慮吸收能力的基礎上,進一步考察制度因素中知識產權保護對內外向國際化技術追趕效果的調節效應,我們發現,企業自身因素和外在制度因素對后發企業的內外向國際化技術追趕都會產生影響,但是較之于以往普遍認為影響顯著的吸收能力(Cohen和Levinthal,1990;呂世生和張誠,2005;李元旭和譚云清,2010),本文結果顯示,外在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影響更明顯。這一發現豐富了以往研究,促進理論界進一步探索。
本文研究同時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第一,我國后發企業技術追趕應該從主要依靠內向國際化轉向主要依靠外向國際化。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以市場換技術”的內向國際化戰略已不能再適應中國企業的技術追趕要求,在不能掌握外方核心技術的情況下,若繼續利用外國專利進行生產產品,長期依賴產生的自主研發惰性必將使得企業研發創新能力越來越弱,反而再次拉開與先進企業的技術差距。而經過前期的內向國際化,一些后發企業已經積累了豐富的資本和技術經驗,此時進一步外向國際化并購先進企業或進行合作研發,通過反向技術溢出方能持續實現技術追趕。同時,內向國際化對外向國際化的技術追趕效果仍然具有促進作用,外資的流入使得后發企業能及時了解當前科技前沿,更好地識別外部技術價值和未來技術發展趨勢,提高外向國際化技術追趕的準確性和有效性。所以,我國后發企業現階段應該主要依靠外向國際化進行技術追趕,但是也要適當發展內向國際化,將內外向國際化結合起來,持續推進技術的追趕。第二,后發企業應重視自身吸收能力的提升,加大研發投入。研究發現,企業吸收能力對內外向國際化技術追趕績效的提升均具有積極影響,特別是對外向國際化的技術追趕,具有顯著作用。對外直接投資能獲得或可以近距離接觸國外先進技術,但是后發企業能否真正掌握和利用這些技術取決于其擁有的吸收能力,企業的研發水平越高,對國外技術的吸收能力就越強,越能促進國際化技術追趕效果的發揮。第三,中國各地區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立法強度和執法力度。完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并提高執法力度,為后發企業創新結果提供法律保護,降低研發投入的風險,可以刺激后發企業外向國際化更積極地投資于研發活動,從而提高技術水平實現追趕。而且,由于技術的外溢性特點,提高知識產權保護強度使外國技術領先企業更具有安全感,能吸引更多的先進技術,為后發企業提供近距離學習的機會,反而提高技術溢出的可能性。因此中國企業要實現技術追趕,立法重點應盡快轉向規范無形市場,特別是知識產權保護上,只有加強了知識產權保護,原創性研發成果才會更多,也才能吸引更多的領先企業與我國后發企業進行合作。
[注釋]
①參照李梅和柳士昌(2012),李梅(2010)等學者的做法,用R&D投入強度表示各省的吸收能力,研發強度越大,對先進技術的吸收能力就越強。
②之前被大量研究所采用的Ginarte-Park指數只是對一國知識產權立法強度的測量,忽視執法強度的影響。參照Kondo (1995)和Lesser(2003)的綜合評分法,許春明和陳敏(2008)、許春明和單曉光(2008)等重新構建并驗證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的指標體系,認為一個地區的知識產權保護程度應該是該地知識產權保護立法強度與執法力度的乘積。各省知識產權立法強度還是采用Ginarte-Park方法測定,則各省立法強度一樣,具體數據參照蔡虹等(2014)的計算結果。執法力度則包括行政保護水平、司法保護水平、社會公眾意識、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國際監督五個方面,它們權重相等,即執法力度等于五個指標得分的算術平均值。本文采用他們的指標體系測量中國各省2003~2013年的知識保護程度。
③參考張軍和金煜(2005)、李梅和柳士昌(2012)的做法,認為非國有部門貸款比重是衡量當期各省金融發展程度較為準確的指標,并假定各省國有企業貸款分配額與其固定資產投資額成正比,即金融發展程度=總貸款/GDP*(1-國有經濟固定資產投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
[參考文獻]
[1] Hagerdoorn, J., Understanding the rationale of strategic technology partnering: interorganizational modes of cooperation and sectoral differenc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J]. 1993. 14(5): 371-386.
[2] Welch L S, Luostarinen R K. Inward-outward connections in internationalizatio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1993: 44-56.
[3] MacDougall G D A. The benefits and costs of private investment from abroad: A theoretical approach [J]. Bulletin of the Oxford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 1960, 22(3): 189-211.
[4] Cheung K, Ping L. Spillover effects of FDI on innovation in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provincial data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4, 15(1): 25-44.
[5] Laursen K, Salter A. Open for innovation: the role of openness in explaining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mong UK manufacturing firm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6, 27(2): 131-150.
[6]陳羽,鄺國良. FDI,技術差距與本土企業的研發投入——理論及中國的經驗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 2009(7): 88-96.
[7] Abramovitz M. Catching up, forging ahead, and falling behind[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86, 46(2): 385-406.
[8]吳先明.中國企業對發達國家的逆向投資:創造性資產的分析視角[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 2007(9): 52-57.
[9]劉明霞.創造性資產尋求型FDI: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新趨勢和新挑戰[J].財貿經濟,2009(4):83-87.
[10]江小涓.戰略性跨越——中國對外投資和跨國公司的成長[J].國際貿易,2000(12):8-13.
[11]馬亞明,張巖貴.技術優勢與對外直接投資:一個關于技術擴散的分析框架[J].南開經濟研究, 2003(4): 10-14+19.
[12]朱閔銘,王繼康.關于對外直接投資及其技術轉移效應的探討[J].國際經濟合作, 2001(6):8-11.
[13]劉紅艷,崔耕.中國企業如何從“引進來”到“走出去”——企業內向國際化模式對外向國際化績效的影響[J].財貿經濟,2013 (4):89-97+110.
[14] Cohen W M, Levinthal D A. Absorptive capacity: 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89, 35(1):128-152.
[15] Rogers M. Absorptive cap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how do countries catch-up [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4, 28 (4): 577-596.
[16] Escribano A, Fosfuri A, Tribó J A. Managing external knowledge flow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absorptive capacity [J]. Research policy, 2009, 38(1): 96-105.
[17] Cassiman B, Veugelers R. In search of complementarity in innovation strategy: Internal R&D and external knowledge acquisition [J]. Management science, 2006, 52(1): 68-82.
[18]李元旭,譚云清.國際服務外包下接包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提升路徑——基于溢出效應和吸收能力視角[J].中國工業經濟, 2010(12):66-75.
[19]李梅,柳士昌.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的地區差異和門檻效應——基于中國省際面板數據的門檻回歸分析[J].管理世界,2012(1):21-32+66.
[20] North D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20).
[21] Yang L, Maskus K 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expor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9, 90(2): 231-236.
[22] Varsakelis N C. The impact of patent protection, economy openness and national culture on R&D investment: a cross -country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 Research Policy, 2001, 30(7): 1059-1068.
[23] Hu M C, Mathews J A. National innovative capacity in East Asia [J]. Research Policy, 2005, 34(9): 1322-1349.
[24] Wu Y, Popp D, Bretschneider S. The effects of innovation policies on business R&D: A cross-national empirical study[J].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nd New Technology, 2007, 16(4): 237-253.
[25]蔡中華,安婷婷,侯翱宇.基于EBA方法的R&D投資影響因素穩健性研究——基于中國省際數據分析[J].軟科學,2014(11): 119-122.
[26]喻世友,萬欣榮,史衛.論跨國公司R&D投資的國別選擇[J].管理世界,2004(1):46-54+61.
[27] Kokko A. Productivity Spillovers from Competition between Local Firms and Foreign Affiliat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96(8):517-530.
[28] Wei Y, X Liu. Productivity spillovers from R&D, Exports and FDI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sector[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6, 37:544-557.
[29]李梅.人力資本、研發投入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逆向技術溢出[J].世界經濟研究,2010,10:69-75+89.
[30] Kondo EK. The effect of patent protection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Journal of World Trade, 1995, 29:97-122.
[31] Lesser W. The Effects of Trips -Mand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n Economic Activit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R]. Prepared under WIPO Special Service Agreements, WIPO, 2003.
[32]許春明,陳敏.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的測定及驗證[J].知識產權,2008(1):27-36.
[33]許春明,單曉光.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強度指標體系的構建及驗證[J].科學學研究,2008(4):715-723.
[34]蔡虹,吳凱,蔣仁愛.中國最優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的實證研究[J].科學學研究,2014(9):1339-1346.
[35]張軍,金煜.中國的金融深化和生產率關系的再檢測:1987—2001[J].經濟研究,2005,11:34-45.
[36] Lin H, Lin E S. FDI, trade, and product innovation: theory and evidence[J].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2010, 77(2): 434-464.
[37] Levin A, Raut L K. Complementarities between exports and human capital in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the semi﹞industrialized countries[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7, 46(1): 155-174.
(責任編輯:張丹郁)
[38] Bebczuk R N. R&D Expenditures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around the world[J]. Estudios de Economia,2002,29(1):109-121.
From In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 to Out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Technological Catch-up Sustainability of the Latecomer Enterprises
Wu Xianming,Huang Chuntao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technological catch-up theory,this study examined the technological catch-up performance of the latecomer enterprises in China concerning their in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 to out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 by using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3 to 2013. Also,it inspected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these enterprises on their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the degree of the intelligent property protection. It is found that out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 c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echnological catch-up. On the contrary,in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 obviously hinders it at this stage. However,in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technological catch -up effect through out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 So it is a sustainable process that enterprises realize their technological catch -up from in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 to out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 Further study found that absorptive capacity has obvious positive influence in technological catch -up through out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 but not in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intelligent property protection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in technological catch -up through both inward and out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which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t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the technological catch-up,and weake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the technological catch-up.
Key words:technological catch-up;in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out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latecomer firms;intelligent property protection
作者簡介:吳先明(1964-),男,湖北黃岡人,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國際企業管理與企業戰略管理;黃春桃(1990-),女,廣西南寧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國際企業管理。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創造性資產尋求型跨國并購的主要影響因素和運作推進機制研究》(12AZD034)、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我國企業跨國并購中的逆向知識轉移研究》(11BGL044)和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戰略性新興產業國際化發展戰略研究》(14JZD017)的資助。
收稿日期:2015-09-29
DOI:10.13253/j.cnki.ddjjgl.2016.02.003
[中圖分類號]F06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6)02-00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