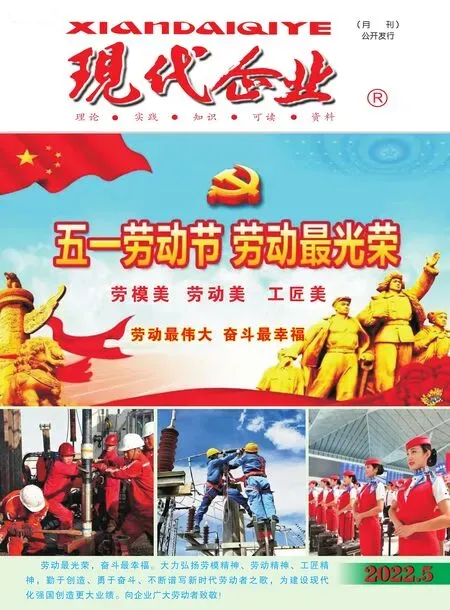“陜西歷史文化使者”百強出爐
2017-06-15 10:21:10郭青
現代企業 2017年5期
郭青
本刊訊 5月9日,經過25天線上線下的積極參與,100名來自海內外的歷史文化愛好者成為2017“陜西歷史文化使者”評選活動百強選手。
據悉,本次評選活動由中共陜西省委宣傳部、省文物局主辦,省博物館協會、省博物館教育聯盟聯合承辦。4月13日至5月7日初賽期間,共有來自9個國家的12794名海內外選手參與。參賽選手線上答題12684人,線下答題110人。參賽選手中年齡最小的為7歲,年齡最大的為85歲,他們中有飛行員、主持人、教授、大學生、導游、農民、企業人員、退休人員等。“陜西歷史文化使者”百強選手名單將于近日在省文物局官方網站漢唐網上進行公示。百強選手將于10日起進入復賽,進一步爭奪決賽資格。
猜你喜歡
湖北教育·綜合資訊(2022年4期)2022-05-06 22:54:06
金橋(2022年2期)2022-03-02 05:42:50
小太陽畫報(2020年4期)2020-04-24 09:28:22
小天使·一年級語數英綜合(2018年9期)2018-10-16 06:30:16
童話王國·原創版(2016年4期)2016-11-23 16:06:06
全體育(2016年4期)2016-11-02 18:57:28
兒童故事畫報·智力大王(2015年11期)2016-01-27 00:55:01
科普童話·百科探秘(2015年6期)2015-10-13 07:21:18
科普童話·百科探秘(2015年8期)2015-08-14 07:13:06
科普童話·百科探秘(2015年4期)2015-05-14 07:2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