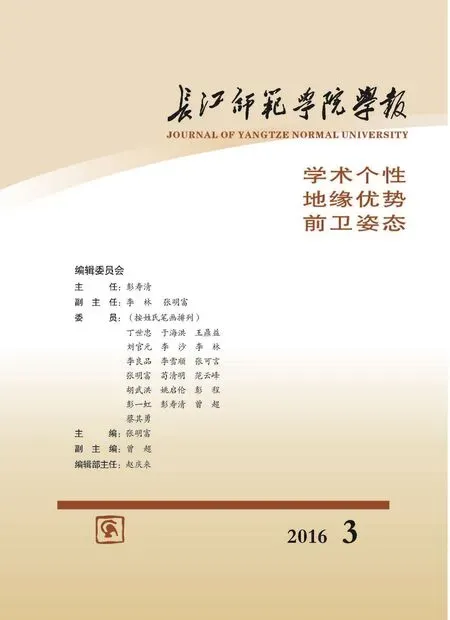我國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的研究現(xiàn)狀與展望
鞠鑫
(廣東財經(jīng)大學 大學生發(fā)展研究中心,廣東 廣州 510320)
我國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的研究現(xiàn)狀與展望
鞠鑫
(廣東財經(jīng)大學大學生發(fā)展研究中心,廣東廣州510320)
近30年我國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研究取得的主要進展是:研究領域突破了思想政治教育單一學科的局限,向多學科領域擴展;研究內(nèi)容從概括性的描述及構想轉向精細化研究;研究方法從傳統(tǒng)的思辨和經(jīng)驗總結向質(zhì)性和量性的多樣化研究范式轉型。未來國內(nèi)研究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應在基本問題的整合研究、發(fā)生發(fā)展的比較研究和培養(yǎng)路徑的實證研究等方面有所突破。
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積極道德品質(zhì);積極心理品質(zhì)
一、引言
“人應該成為什么樣的人”一直是我們思考的哲學問題。在中外學術史上對這個問題的解答聚焦于探究 “哪些品質(zhì)能成為好人的品質(zhì)”,即人的積極品質(zhì)。我國高等教育立德樹人的重要任務亦是培養(yǎng)大學生的積極品質(zhì),特別是近年來高校發(fā)生了諸如藥家鑫案、復旦生投毒案等惡性事件,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日益成為學術界的重要研究課題之一。
國內(nèi)較為系統(tǒng)的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進入21世紀才逐漸繁盛。通過中國期刊網(wǎng)全文數(shù)據(jù)庫的檢索,發(fā)現(xiàn)1994年以前僅有40余篇,1994-2003年有160余篇,而2004-2014年有700余篇文獻研究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總體上呈上升趨勢。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正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關鍵期,高校擴招、大學生自主擇業(yè)等因素影響著大學生的心理和道德發(fā)展,學界從研究大學生的“道德品質(zhì)”開始逐漸重視大學生的積極品質(zhì)。從2004年到現(xiàn)在的10多年,大學校園惡性犯罪案件的頻發(fā)打破了校園的安全穩(wěn)定氛圍,不同領域的學者紛紛關注大學生的健康成長,包括道德品質(zhì)、情感、心理品質(zhì)在內(nèi)的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的研究日漸增多。回顧我國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的研究進展,并對未來的研究走向進行探索,對于深化該領域研究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二、我國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研究的主要進展
(一)研究領域從單一學科向多學科擴展
國內(nèi)較早的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研究集中在思想政治教育領域,“道德品質(zhì)”“品德”成為積極品質(zhì)的主要代名詞。20世紀90年代中期突破了思想政治教育單一學科的局限,在美德倫理學、新品格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學等領域開始了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的研究。
當代美德倫理學首先擴展了積極品質(zhì)研究的學科視野。美德倫理學強調(diào)美德是引導成功的優(yōu)良品質(zhì),有助于實現(xiàn)人的生存目的——幸福或美好生活[1]。大學生美德、德性的研究成為積極品質(zhì)研究的內(nèi)容之一,主要集中于大學生對中華傳統(tǒng)美德的傳承及教育、德性的建構與發(fā)展、德性養(yǎng)成的環(huán)境與路徑、以及個人德性或公共德性的專題研究。新品格教育在21世紀初也開始影響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研究。新品格教育的目標就是培養(yǎng)人的積極品質(zhì),重點是培養(yǎng)社會普遍認為有價值的美德和行為模式[2]。新品格教育的教育理念、品格概念結構和培養(yǎng)方法推動了國內(nèi)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研究的理論進展。探討人類力量和美德等積極心理品質(zhì)的積極心理學是近20年來對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研究影響最大的學科。其中國外學者提出的智慧與知識、勇氣、愛與人性、正義、節(jié)制、靈性與超越6種積極心理品質(zhì)[3]對積極品質(zhì)研究的影響特別深遠。國內(nèi)大學生積極心理品質(zhì)研究涉及大學生積極心理品質(zhì)的結構、發(fā)展現(xiàn)狀、影響因素、培養(yǎng)路徑等基本問題,以及特殊大學生群體的積極心理品質(zhì)發(fā)展等,并且以質(zhì)性或量性實證研究為主,促進了國內(nèi)積極品質(zhì)研究的科學化發(fā)展。20世紀80年代以來社會學領域由 “問題視角”向 “優(yōu)勢視角”的實務工作取向為國內(nèi)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優(yōu)勢視角”著眼于個人優(yōu)勢,以開發(fā)和利用人的潛能為出發(fā)點,激發(fā)人們的樂觀情緒、希望和積極動機以面對生命中的挫折和不幸。借鑒 “優(yōu)勢視角”的賦權、成員資格、抗逆力等基本理念,國內(nèi)學者從大學生弱勢群體的優(yōu)勢開發(fā)、大學生不良行為的矯正及生涯規(guī)劃等方面開展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的研究。
(二)研究內(nèi)容從籠統(tǒng)化向精細化改進
早期的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研究內(nèi)容往往比較籠統(tǒng),傾向于概括性的描述和構想,缺乏深入細致的分析。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逐漸走向精細化路徑,例如對積極品質(zhì)的量化評估、積極品質(zhì)形成與發(fā)展特點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簡單的描述,而是更注重借鑒數(shù)學、心理學等其他學科的理論方法進行細致的科學分析。最近幾年研究的精細化程度越來越高,例如在積極品質(zhì)的影響因素研究中,分別將校園文化、宿舍文化、體育文化、網(wǎng)絡環(huán)境等作為專題進行探討,對象上也細化到女大學生、貧困大學生、大學生志愿者、有留守經(jīng)歷的大學生等不同群體分別進行實證研究。
從目前掌握的文獻資料來看,主要的研究內(nèi)容可以概括為5個方面:其一是積極品質(zhì)的現(xiàn)狀與對策研究。這類研究所占比例最大,相關文獻基本上是通過問卷調(diào)查的方法了解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的狀況,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其二是積極品質(zhì)的評估研究。這類研究在思想政治教育領域注重評估指標體系的構建,典型成果有閔永新的大學生思想品德量化評估指標體系[4]、許文蓓的多維度大學生品德評價體系[5]等;而積極心理學、品格教育學領域更注重積極品質(zhì)評估量表的開發(fā),如孟萬金[6]、李自維[7]、蓋笑松[8]等編制了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總量表,其他學者編制了諸如感恩、樂觀、希望、抗逆力等積極品質(zhì)量表。其三是積極品質(zhì)的形成與發(fā)展機制研究。這類研究一部分集中于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形成與發(fā)展的影響因素,探討較多的外部因素有教養(yǎng)方式、社會政治、校園文化、社會實踐、同齡群體、網(wǎng)絡及大眾傳媒等;內(nèi)部因素有人生觀、世界觀、情緒狀態(tài)、自我認知、思維方式、生理條件等。另一部分研究集中于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的內(nèi)化過程,特別是大學生積極道德品質(zhì)的內(nèi)化,如董天菊的大學生道德內(nèi)化過程研究[9]、沈江的高校德育促進大學生道德內(nèi)化的思考[10]。其四是積極品質(zhì)的結構研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與成果有孟萬金的大學生積極心理品質(zhì)6維度[6]、蓋笑松的大學生積極發(fā)展10品質(zhì)[8]、王新波的大學各年級積極心理品質(zhì)[11]。另外還有對特殊大學生群體積極品質(zhì)結構的分析,如大學生志愿者的積極品質(zhì)[12]、留守大學生的積極心理品質(zhì)[13]。其五是積極品質(zhì)的培養(yǎng)研究。在培養(yǎng)理念的構建研究方面,目前已經(jīng)形成了生活教育觀、積極教育觀、自我教育觀、社會家庭和學校聯(lián)合教育觀等積極品質(zhì)培養(yǎng)觀;培養(yǎng)方法的探索與實踐研究注重團體輔導、個體心理輔導、體驗式訓練、體育教育與活動、閱讀活動等對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的干預。
(三)研究方法從傳統(tǒng)研究范式主導向多樣化研究范式轉型
早期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研究主要采用傳統(tǒng)的思辨法和經(jīng)驗總結法。以思辨法開展的研究所占比重最大,幾乎涉及了積極品質(zhì)研究的所有主題。以經(jīng)驗總結法開展的研究數(shù)量僅次于思辨法,其研究往往是對國內(nèi)外已有研究成果的進一步總結和提煉,研究主題涉及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存在的問題、培養(yǎng)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及現(xiàn)狀等。
近10年來質(zhì)性研究和量性研究范式日益受到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研究者的青睞。質(zhì)性研究方面以使用訪談法為主,如周嵚通過深度訪談形成了大學生積極特質(zhì)的評價指標體系[14]。量性研究方面,早期主要是翻譯并使用國外的量表 (如優(yōu)勢行動價值問卷[15])來測評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隨著研究本土化的進展,國內(nèi)學者也開發(fā)了一些測評工具,較有代表性的有 “中國大學生積極心理品質(zhì)量表”[6]“當代大學生主要積極品質(zhì)問卷”[7]“中華美德問卷”[16]“大學生積極發(fā)展問卷”[8]等。一些社會科學研究的新方法也被應用于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研究,如運用實驗法設定實驗組和對照組前后所測的等組實驗設計,開展團體輔導以對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進行教育干預,運用跟蹤研究法探索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的培養(yǎng),等等。
三、我國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研究的主要局限
(一)概念缺乏統(tǒng)一
對積極品質(zhì)概念的理解關乎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研究的未來發(fā)展。目前國內(nèi)學術界還未形成 “積極品質(zhì)”的統(tǒng)一定義,許多學者的研究仍然局限于大學生的道德品質(zhì)、品德、品格、積極心理品質(zhì)、積極人格等,實際上這些詞匯對積極品質(zhì)的表達都不全面,有重復之處。比如道德品質(zhì)、品德、品格主要指道德層面的積極品質(zhì),而積極心理品質(zhì)、積極人格主要指心理層面的積極品質(zhì)。由于概念表述的不統(tǒng)一和內(nèi)涵的片面性,使得對積極品質(zhì)結構、現(xiàn)狀及培養(yǎng)策略的理解出現(xiàn)差異,影響了積極品質(zhì)研究的進展。綜合國內(nèi)各學科領域對積極品質(zhì)的研究,從積極道德品質(zhì)、積極心理品質(zhì)、積極行為模式的整合來研究大學生的積極品質(zhì),有望提煉出統(tǒng)一的積極品質(zhì)概念,彌補當前在概念界定方面的研究局限。
(二)學科間缺乏整合
不同學科領域的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思想政治教育領域對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的培養(yǎng)意義、價值和路徑的理論成果;積極心理學領域對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結構、量化評估、培養(yǎng)方法的實證成果。然而這些研究成果尚未實現(xiàn)整合,而且不同學科的研究還存在簡單重復的現(xiàn)象,使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的質(zhì)性和量性研究、理論和實踐檢驗的成果不能相互補充,更不能對教育實踐起到有效的指導作用。另外,這些學科領域的新研究成果本可以對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研究發(fā)揮引導作用,但目前尚未被引入。如思想政治教育領域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研究,可以為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內(nèi)容的分析提供參考;積極心理學領域對主觀幸福感、自我決定理論、積極心理的認知研究等,可以幫助設計和修訂適合中國大學生的積極品質(zhì)測量工具;品格教育領域對6E途徑、道德敘事、回歸社群的研究等,可以提供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新的培養(yǎng)路徑。
(三)研究的發(fā)展性和長期性缺乏
國內(nèi)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研究以現(xiàn)狀研究或橫斷面研究為主,一般采用在某個時間點收集相關資料,對積極品質(zhì)的現(xiàn)狀、問題及對策進行研究,但是這些研究完成之后普遍缺乏后繼研究,即研究缺乏發(fā)展性和長期性。從研究對象來看,大學生正處于從青春期后期到青年發(fā)展再到成人的過渡期,既有對上一階段身心發(fā)展的承接,又有本階段自身的特點,大學生的積極品質(zhì)也會表現(xiàn)出高低年級不同的特點,而以往的積極品質(zhì)研究往往忽視大學生發(fā)展性的特點。雖然王新波曾根據(jù)已有全國大學生積極心理品質(zhì)測量的相關成果,提出了以年級為序大學各年級需要重點培養(yǎng)的關鍵期品質(zhì)和控制性品質(zhì)[11],但仍然缺乏后續(xù)理論探索和實證檢驗。從研究時間來看,以往的積極品質(zhì)研究很少進行長期追蹤性研究,缺乏對理論成果的實踐檢驗,其外部效度較差。雖然張高產(chǎn)曾進行了為期6個月的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追蹤研究,探索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對網(wǎng)絡成癮預防作用研究[17],但該研究的對象僅限于大一學生,研究數(shù)據(jù)僅來源于相隔半年的兩次心理測評,研究的長期性和外部效度上還不夠。
四、我國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研究的未來展望
縱觀國內(nèi)學者30年來在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中的進展與局限,未來的研究期望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
第一,加強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基本問題的整合研究。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研究蘊含一系列基本理論問題,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者就其內(nèi)涵、結構、影響因素等已作過一些探討。但如何從學理上進一步整合這些研究成果,以更清晰、更明確的脈絡回答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的相關問題,仍有深入探討的必要。對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如何定義,如何將幾個不同學科提出的諸如道德品質(zhì)、品德、品格、積極心理品質(zhì)等概念整合,特別是如何將大學生的積極道德品質(zhì)和積極心理品質(zhì)整合進當代大學生的積極品質(zhì)范疇內(nèi),以及作為中國人具有的傳統(tǒng)優(yōu)秀品質(zhì)與作為現(xiàn)代公民具有的積極品質(zhì)如何整合。這些相關問題都有待進一步研究。
第二,開展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發(fā)生發(fā)展的比較研究。古羅馬學者塔西陀曾說:“要想認識自己,就要把自己同別人進行比較。”要科學準確地把握當代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的發(fā)展狀況,需要開展比較研究,積極借鑒古今中外積極品質(zhì)研究的有益經(jīng)驗。然而在現(xiàn)有成果中關于中外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的比較、國內(nèi)不同時代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的比較、不同年級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的比較、不同大學生群體之間積極品質(zhì)的比較、大學生與其他群體積極品質(zhì)的差異等研究寥寥無幾,這些比較研究將成為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未來研究的重要走向。
第三,深化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培養(yǎng)路徑的實證研究。目前國內(nèi)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培養(yǎng)路徑的研究大多側重于理論闡述,只有很少學者開展實證研究。然而,只有經(jīng)過實證檢驗的培養(yǎng)路徑,才是具有針對性和現(xiàn)實可操作性的。未來的研究需要整合相關學科的各種實務工作方法,如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個體心理咨詢、心理健康課程教學,社會工作中的個案工作、小組工作、社區(qū)工作法,以及隱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實務工作方法,將這些方法應用到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培養(yǎng)中,并以實驗法、測量法、個案法等研究方法獲取第一手材料,指導教育工作者以客觀務實的態(tài)度來培養(yǎng)大學生的積極品質(zhì)。
[1]李義天.當代國外美德倫理學研究綜述[J].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07(6):119-122.
[2]James Leming.Social Studies Research and theInterest of Children[J].Theory and Research in Social Education,1997(4):16-20.
[3]Park N,Peterson C.Positive Psychology and Character Strengths:Application to Strengths-based School Counseling[J].Professional School Counseling,2008(2):85-92.
[4]閔永新.大學生思想品德量化評估指標體系的設計與操作[J].中國高教研究,1996(2):69-70.
[5]許文蓓.構建多維度大學生品德評價體系的思考[J].高校理論戰(zhàn)線,2008(3):47-49.
[6]孟萬金,官群.中國大學生積極心理品質(zhì)量表編制報告[J].中國特殊教育,2009(8):71-77.
[7]李自維,張維貴.當代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探析——基于積極心理學視野下的調(diào)查分析[J].河南社會科學,2011 (6):119-121.
[8]蓋笑松,蘭公瑞.大學生積極發(fā)展問卷的編制[J].心理與行為研究,2013(6):786-791.
[9]董天菊.大學生道德內(nèi)化問題研究[J].教育與職業(yè),2009(5):82-84.
[10]沈江.新時期高校德育促進大學生道德內(nèi)化的思考[J].中國高教研究,2006(2):78-79.
[11]王新波.大學生積極心理品質(zhì)培養(yǎng)研究[J].中國特殊教育,2010(11):40-45.
[12]嚴太華.大學生志愿者服務、愛心和責任三種積極品質(zhì)的分析[J].高校輔導員學刊,2013(10):74-79.
[13]羅滌,李穎.高校留守大學生積極心理品質(zhì)研究[J].中國青年研究,2012(8):83-87.
[14]周嵚.大學生積極特質(zhì)結構的驗證性因素分析及影響因素的研究研究[D].河北師范大學,2008.
[15]段文杰.優(yōu)勢行動價值問卷(VIA-IS)在中國大學生中的適用性研究[J].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2011(4):473-478.
[16]Duan W J,Bai Y.Factor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Virtues Questionnaires[J].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2012(6):680-688.
[17]張高產(chǎn).積極心理品質(zhì)對大學生網(wǎng)絡成癮的預防作用的研究[D].華東師范大學,2005.
[責任編輯:慶來]
G641
A
1674-3652(2016)03-0119-04
2015-12-20
教育部2014年度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專項任務項目“跨學科視野下的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研究”(14JDSZ2042);2015年度廣東省高校德育創(chuàng)新項目“大學生積極品質(zhì)培養(yǎng)的心理健康教育‘發(fā)展’模式”(2015DYYB096)。
鞠鑫,女,山東泰安人。博士,副研究員。主要從事心理健康教育與比較道德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