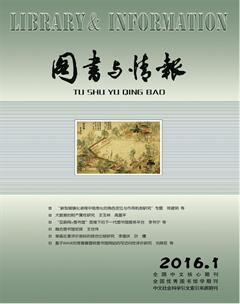公共文化服務網絡治理:一個基于契約的視角
羅云川 阮平南



摘 要:文章對公共文化服務網絡治理中契約的內涵、關系、構成進行了研究,并對公共文化服務的社會化購買與PPP模式進行了探討。提出在公共文化服務網絡治理中,多元主體的參與使公民與政府之間的“委托-代理”關系發生了轉移,產生了第二級的“委托-代理”關系,認為公共文化服務中的契約治理由精神、行為和分配三個層面構成。
關鍵詞:公共文化服務;網絡治理;治理;契約
中圖分類號: G24 文獻標識碼: 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16016
Governance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Net-work in Perspective of Contract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connotation of contract in the governance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network, relation, and structure was studied 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to buy and PPP model are discussed. In the governance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network, multi-subject participation made the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izens and the government shifted, and a second level of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 was produced. The contractual governance i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is composed of three aspects: spirit, behavior and distribution.
Key word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network governance; governance; contract
1 引言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確定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并指出“必須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加快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1]公共文化服務作為由政府主導的,旨在保障社會公民基本文化權利的一項國家基本公共服務,推進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應是題中應有之義。
治理理論興起于上世紀90年代。根據治理理論主要創始人羅西瑙的定義,治理是指一種共同的目標所支持的一系列活動,這個目標未必出自合法的以及正式規定的職責,而且它也不一定需要強力克服挑戰而使別人服從[2]。盡管眾多學者對治理一詞的解釋不一而足,但其核心思想是基本相同的:治理是多元主體為有效達成某一目標,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協同開展活動的過程、制度及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