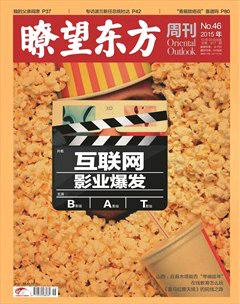《喜馬拉雅天梯》的院線之路
陳莉莉
電影界的人一般說投資中國電影有三個禁區,也就是如果你想有不錯的票房收入,就不要碰動漫、紀錄片、文藝三個題材
一個伊朗人去法國開出租車謀生。但他告訴乘客,開出租車不是他生活的意義。
乘客問:什么是你生活的意義?他回答,唱歌。應乘客要求,他準備開唱,掏出已被翻卷得很舊的歌詞本,上面有諸多筆跡。
“唱完以后,他羞澀地笑了笑,就是那羞澀的笑。”蕭寒回想那個細節,極力找到合適的詞語,來表達那個笑帶給他的意義。
這部成于2006年的荷蘭紀錄片《永遠》讓蕭寒記憶猶深。于是,在履行浙江工業大學副教授社會角色的同時,蕭寒試著通過紀錄片進行更多表達。
2015年10月16日,蕭寒擔任聯合導演的《喜馬拉雅天梯》正式走進院線,喜馬拉雅山脈腳下的登山向導第一次以這樣的方式呈現在世人面前。
到11月初,他在微信那頭“唉”了一聲。此時,《喜馬拉雅天梯》票房收入600多萬元,剛剛在2015南山國際山地電影節開幕式領了獎,這是它獲得的眾多獎項之一。
另一部以珠峰為題材的英國電影《絕命海拔》正在北京宣傳,不久后,韓國團隊制作的珠峰題材電影也要在中國上映。
關于珠穆朗瑪峰的電影故事還沒結束,誰也不知道屬于它的時代到底有多長。其中一個主線,就是如何讓它更真實和貼近地走進內地人的視野。
影院經理的忠告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雷建軍與蕭寒是多年朋友。同好紀錄片,或許是原因之一。
2010年,雷建軍要從拉薩去珠峰,一位名叫次培的當地登山向導問他:“能幫我帶幾本經書給我的父親嗎?”
次培的父親在5800多米的絨布寺里當喇嘛。那里距離珠峰頂不過20多公里,既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寺廟,也是前往珠峰大本營路上一處令人難以忘記的風景
路途遙遠,捎帶幾本經書,這樣的觸碰,讓有紀錄片制作經驗的雷建軍特別想呈現這位登山向導的生活方式。
他找到一些在讀研究生作了長時間的田野調查,希望了解登山向導的一切:他們為什么爬山?職業生涯是怎樣的?他們的命運將會怎么?等等。
雷建軍將這個想法說給蕭寒,那時雷建軍已經談了好幾家機構,但是沒有人愿意投資拍攝。
蕭寒對《瞭望東方周刊》回憶,“當時我一拍大腿說,我來拍。”后來遇到一系列的困難,“我先投資200多萬元,錢很快就不夠了,又賣了房子,繼續拍。也收到過各種扶持,包括政府和社會力量的。主要是資金、政策、還有物資。這些對我們來說確實非常重要。”
拍攝2011年正式啟動,目標就是進院線。
雷建軍依然擔任制片人。之前他也曾嘗試過把學生的作品送進電影院,不了了之。
雷建軍告訴《瞭望東方周刊》,他剛開始計劃是跟拍一個藏族小孩,從他初中畢業一直跟到登頂珠峰,但是發現時間長、費用實在是太高了。后來就決定展示一個群像。即使如此,也遠遠超過原計劃一年的周期。
這種“無奈”,讓《喜馬拉雅天梯》被認為“沒有主線、故事性不強”。雷建軍則說,“它有那么多的唯一性。目前唯一一部漢族攝像進入海拔7000米的紀錄片。另外相比眾多的南坡題材,這是珠峰北坡。”
各種困難、唯一,和國際知名團隊,共同的4年時光,構成了《喜馬拉雅天梯》的88分鐘。
接下來就是找電影院。
蕭寒“都是面對面很誠懇地聊”,卻得到一位影院經理的忠告:花多少錢都沒有用,別浪費錢了。
蕭寒問雷建軍:“還往下談嗎?”后來他們發現,聊30家還是這個結果。
但是還有一個可能性,就是“你們自己組織觀眾。讓更多人知道,驚動院線。”
只有大屏幕才配得上
幾乎2015年整個夏天,北京、南京、深圳、廣州等城市與戶外、旅游、體育有關的主題展覽上,蕭寒都要去。
有時就在露天的地方,先把片花放出來,“拿著話筒扯著嗓子喊。哪怕我面前只有三個人,甚至這三個人中還有一個剛買菜回來包里露著一根大蔥的阿姨。”蕭寒回憶。
事實證明,不是人們不愿意看西藏和珠峰,而是他們不知道還有什么可以看,“當我說了一些話,介紹這是一部什么樣的片子,我們在做什么樣的事情時,很快就能聚攏很多人。”
蕭寒稱這個為“擺攤賣藝”,這種最直接的告訴別人自己在做什么的方式,贏得了掌聲。
蕭寒接著問:“你們愿意去電影院看它嗎?”獲得眾聲肯定的回復。
人們圍過來加蕭寒的微信,并保證說一定會幫他傳播,“其實人們內心深處總有一些東西是相通的。”
蕭寒建立一個微信群,微信公眾號文章的閱讀量也有幾十萬,“原來我的心里是沒底的,雖然剛開始就是抱著要進院線的想法,但是商業院線里充斥著紀錄片零排片、一日游的現象。”蕭寒告訴本刊記者。
但是對于他們來說,“只有電影院寬闊的大屏幕才配得上這部紀錄片。如果只能在自己家里,通過電腦、電視來看它,對我來說像自己的孩子沒被尊重。”
蕭寒覺得,“我們希望院線里有不同的生命個體。即使三線、四線城市或者小鎮青年,也能看到文藝片、紀錄片,至少他們有這個選擇性。”
登頂過珠峰,或者喜歡西藏文化的名人也被列入了目標:企業家王石和黃怒波、演員陳坤、主持人魯健以及楊瀾等。他們在一個月的時間里紛紛被找到,錄了推薦影片的視頻,活躍在互聯網平臺。
還有眾籌,等等。這些方法,《大圣歸來》也用過,路偉是它們共同的出品人。
如果能有1000萬元的票房
“電影界的人一般說投資中國電影有三個禁區,也就是如果你想有不錯的票房收入,就不要碰動漫、紀錄片、文藝三個題材。前兩個題材,我都已經做了,現在看來還不錯,接下來還真要投一部文藝片。”路偉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路偉覺得,總投資2000多萬元,希望票房能過1000萬元,這在中國電影市場上就是很好的案例了,“對于中國紀錄片的發展來說,它是一次試水。”
上映以來,票房穩定,沒有猛量增加,也沒有突然減少。上座率高,不過排片太少,路偉想申請延期,讓它在院線里的時間更長一些。路偉總結,“通過這次試水發現,中國缺乏藝術院線,而且相比商業片,紀錄片的價格太高了。”
路偉認為,他們希望能針對不同類型的片子有不同的定價機制。投資2000多萬元的紀錄片,肯定不能去跟投資上億元的商業片定一樣的價格。
雷建軍的感受是,電影只有宣發到達的人群足夠才能引起影院經理的注意,才會給排片,才會有人進影院。發行一定要引入商業的機制。中國不缺好紀錄片,就是缺好的放映渠道。那么好的紀錄片只能往國外送,這偏離了拍紀錄片的本質。
蕭寒說,如果能有1000萬元票房,就是成功了。這樣給紀錄片創作者們帶來希望,給那些用商業方法來評估更小眾的事情以希望。否則,如果有一天他們徹底失望了、不做了,大家的生活里就失去了選擇。
“這有點像堂吉訶德大戰風車,”蕭寒說,“我們都是堂吉訶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