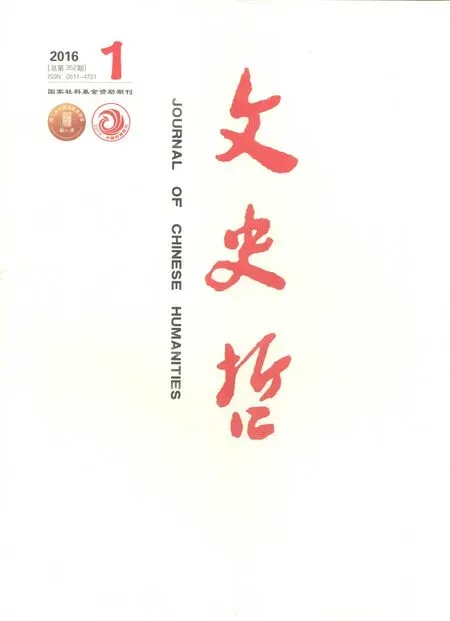人性善惡與民主、專制關系的再認識
?
人性善惡與民主、專制關系的再認識
方朝暉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北京 100084)
關于儒家人性論及其與民主、專制的關系問題,目前存在許多嚴重的誤解。這里想重點澄清如下幾個重要事實:
第一,性善不等于性本善,性惡不等于性本惡。很多人從現代漢語的習慣出發,認為:儒家的性善論主張人性本質上是善的,相反,性惡論則主張人性本質上是惡的;前者以孟子為代表,后者以荀子為代表。這一說法嚴格說來并不成立。
首先,無論孟子還是荀子,都沒有使用過“性本善”或“性本惡”這樣的表述。孟子的典型說法是“性善”,荀子的典型說法是“性惡”。須知,“性善”與“性本善”、“性惡”與“性本惡”一字之差,卻有著非常重要的含義之別。因為“性本善/惡”很容易被理解為“人性本質上是善/惡的”,“本”在現代漢語中極容易被理解為“本質”。
筆者在其他地方曾指出,古漢語中沒有“本質”一詞,現代漢語中的“本質”一詞嚴格說來來源于希臘哲學。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說法,“本質”一詞指存在于事物背后、代表一事物成為該事物的屬性(“是其所是”,to ti en einai等)。在希臘哲學中,“本質”代表變化不定的現象背后永恒不變的實體。然而,在古漢語中,“本”有兩個基本含義,均與西方的“本質”概念差別甚大:一是指根本,甲骨文中相當于樹的根部;二是指開端,比如“本來”、“原本”之類。因此,雖然古人后來也有了“性本善”的說法,但是古漢語中的“性本善”卻是指“開端是善的”。比如《三字經》中的“性本善”,如果聯系上下文來看正是這個意思,絲毫沒有“人性本質上是善的”意思。
其次,古漢語中的“性”,雖有很多定義,但大體上是指人天生就有的屬性;由于天生的屬性很多,所以“性”不能理解為“本性”,或者說,不是指本質。《孟子》中有“山之性”、“水之性”、“牛之性”、“犬之性”、“杞柳之性”、“食色性也”之類的用法,《荀子》從生理機能(如“目可見”、“耳可聞”)、生理欲望(如“饑欲飽”、“寒欲暖”)、好利疾惡和好聲色等角度理解“性”。從這些用法可以發現,孟、荀所講的“性”均不是指現代人所謂的本質或本性。這一點,英國學者葛瑞漢(A. C. Graham)早在20世紀60年代末就已明確指出,并特別強調用現代英語中的human nature來翻譯先秦漢語中的“性”存在片面性,其后夏威夷大學安樂哲(Roger T. Ames)一再論證不能用西方語言中的human nature來翻譯古漢語中的“性”。他們的看法正是基于古漢語中的“性”不代表本質或本性這一點。
換言之,既然“性”在孟子、荀子那里不是指人的本質或本性,而只是指生來就有的一些屬性,那么,所謂“性善”、“性惡”也就只是指這些屬性之善惡,而涉及不到人的本質或本性是善還是惡。把“性善/惡”理解為人的本性善/惡,或人性本質上是善/惡的,并不符合古人的原意。把性善論理解為人性本質上是善的,很容易得出結論說,這是對人性過度理想化的認識。
第二,性善論是否儒家人性論的基本立場?由于宋明理學在元代以降居于官方統治地位,在宋明理學中性善論又得到極高的推崇,很多人認為,過去兩千多年來性善論代表儒家人性論的基本立場。現在需要追問的是:在孔子以來的儒學史上,性善論是不是一直處于主流地位?中國歷史上的絕大多數儒生都主張人性善嗎?只要我們認真考證一下即可發現,所謂性善論代表儒家人性論主流的說法恐怕是成問題的,至少在多數歷史時期并不成立。
首先,沒有證據表明,在先秦儒學中,性善論占主導地位。孔子本人主張“性相近,習相遠”,沒有說過“性善”。根據王充《論衡》介紹,先秦儒生周人世子碩、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皆主張“性有善有不善”。荀子也明確批評孟子性善說。在先秦儒學中,恐怕只有思孟一派支持性善論。
其次,漢代儒生基本都不主張性善論,甚至明確反對之。董仲舒、荀悅、王充皆明確批評孟子的性善論。揚雄明確提出“人性善惡混”(《法言·修身》)的主張,影響甚大。從漢代到唐代,沒有文獻證明多數儒者主張性善論。即使是被公認為后世理學道統說之祖、對孟子評價極高的韓愈,也在《原性》中明確提出性三品說,顯然并未完全接受孟子的性善論。
其三,宋代可能是明確批評孟子性善論最多的一個朝代。早在北宋時期,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皆對孟子的性善論提出明確批評。雖然程朱理學在宋代開始興起,但是他們所代表的“道學”并不占統治地位,甚至還是官方打壓、禁止的對象,所以不能說性善論是宋代的主流觀點。即使在宋代程朱理學譜系內部,也沒有形成支持性善論的明確共識。相反,程朱理學譜系內反對性善論的人并不少,比如胡安國、胡宏、黃震等與葉適一樣明確反對性善論。
其四,有清一代,雖然支持性善論的人仍不少,但由于漢學大明,在乾嘉漢學內部,恐怕也不能說性善論就很穩固。嚴格說來,從王夫之到戴震、阮元等人,荀子式人性觀反而成為理解孟子人性論的基礎。其中,孫星衍、俞樾就明確反對性善論,清末三大儒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均明確表示不接受性善論。康有為傾向于認為人性有善也有惡(接近于揚雄),梁啟超更傾向于接受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說,章太炎認為孟、荀人性論各執一偏,皆不如孔子“性近習遠”之說為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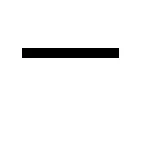
第三,關于人性善惡與民主、專制關系的問題。還有一種常見的觀點認為,性善論更有利于專制,性惡論更有利于民主。理由是:性善論對人性持過于樂觀的態度,因而不注重從制度上限制權力,由于一味寄望于道德而容易成為專制的幫兇;相反,性惡論對人性持相當懷疑的態度,因而注重從制度上制衡權力,由于一直寄望于制度而容易促進民主的發展。然而,歷史的事實卻正好相反。在中國歷史上,主張性善論的孟子、程朱理學家都是反對專制、獨裁的急先鋒,主張性惡論的韓非子、李斯等法家人物莫不成了專制、集權的倡導者。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西方歷史上。我們都知道,西方主張性惡論的馬基雅維利、霍布斯明確支持君主專制。相反,西方提倡民主政治的洛克、孟德斯鳩、盧梭等人皆從“自然狀態”說出發,持一種近于人性善的立場。
霍布斯認為,人類最初的愿望是互相征服,這是不合理的。權力和統治的思想是由許多其他的思想所組成,并且是依賴于許多其他的思想的,因此,不會是人類最初的思想。
霍布斯問:“如果人類不是自然就處于戰爭狀態的話,為什么他們老是帶著武裝?為什么他們要有關門的鑰匙?”但是霍布斯沒有感覺到,他是把只有在社會建立以后才能發生的事情加在社會建立以前的人類的身上。自從建立了社會,人類才有互相攻打和自衛的理由。*[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張雁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年,第4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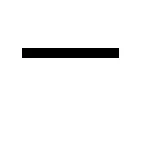
但是,如果像時下流行的那樣,硬要把人性善惡與專制、民主聯系起來,則會發現:歷史上多數主張君主專制的學者主張或傾向于人性惡,多數主張自由民主制的學者主張或傾向于人性善。為什么會這樣呢?根源在于:從人性善的立場更容易推出反對專制的政治制度來,這是因為它相信并尊重人的自我主宰能力。這就是洛克、盧梭、孟德斯鳩等人皆從人的自由是天賦且神圣不可侵犯的角度來為其自由民主制立論的原因。相反,從人性惡出發,固然會想辦法用制度限制權力,但是一種靠丑陋反對丑陋、陰暗限制陰暗來運行的制度,是沒有生氣和希望的。其對人性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更容易給獨裁、集權以理由,因為制度終究必須靠人來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