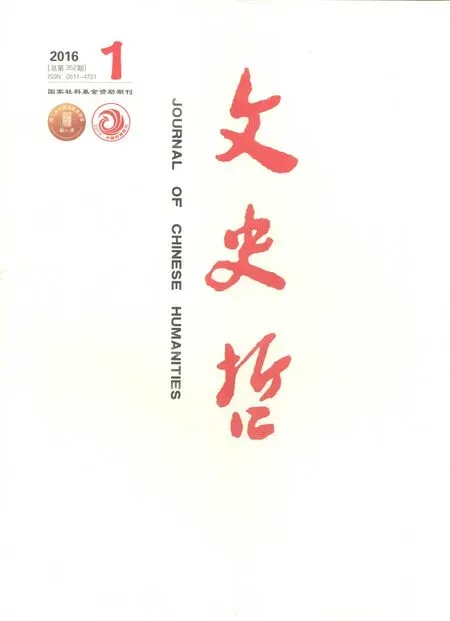自由主義的人性論問題
?
自由主義的人性論問題
高全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北京 100191)
很高興能夠參加《文史哲》編輯部召開的這個有關人性論與自由主義和儒家的對話會。說起來,這是一個大問題,古往今來,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目前也還沒有了結。我想《文史哲》發起這個論壇,未必是打算在理論上對此有一個總結,而是拋出一個話題,引發諸位的爭鳴,由此活躍一下中國思想界的氛圍。確實,人性論本身就是一個話題,再加上把自由主義和儒家思想糾纏在一起,置于當今中國的特殊政治語境下,舊調新彈,頗值得玩味。我想從兩個方面簡單表述一下對此問題的看法。
第一,流俗觀點的再認識。《文史哲》首先提出了一個看法,即自由主義一般主張人性惡,儒家思想大多主張人性善,由此把兩家召集在一起,相互作個辯駁。作為雜志這樣做,當然沒有問題,理論爭鳴嘛,越辯越清晰。但是,這個基本預設,似乎并沒有得到多少認同。大家在發言中都認為,前些年關于自由主義和儒家傳統思想的認識,存在一定的教條主義謬誤。那種認為自由主義主張人性惡、儒家主張人性善,所以兩派的政治觀、社會觀等兩廂對立的看法,是一種流俗之見,可能具有相對的合理性與論辯價值,但肯定存在重大偏頗。例如,儒家對于人性的看法,并非只有性善論這一派。告子、荀子,乃至孔子,就從來沒有把人性善視為社會觀、政治觀的出發點和歸結點。
自由主義就更是如此了。自由主義主要是一種政治、經濟與法制理論,屬于社會科學的范疇。它們集中關注制度層面的事務,尤其關注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方面的個人與秩序之間的關系問題。其價值訴求是政治自由與規則之治,采取的主要是個人主義的方法論。自由、民主、憲政是其核心價值。這些制度方面的理論分析和價值訴求,與哲學人性論之間并沒有太多的因果關系,也不必然主張人性惡。例如,蘇格蘭啟蒙思想作為自由主義思想理論譜系的一支,就與法國啟蒙思想(自由主義思想譜系的另一支)關于人性的看法大有不同,其與德國啟蒙思想就更不同了。而即便是在英國(包括蘇格蘭)思想譜系中,曼德維爾、邊沁與哈奇遜、亞當·斯密、休謨,關于人性的看法,也有重大分歧。此外,關于自由主義,還有古典自由主義與現代自由主義的差別。這些我都不細說了。總之,那種認為自由主義主張人性惡,因此才需要法制、憲政和市場經濟的看法,是非常簡單與片面的。以此來與儒家人性善思想辯論,認為儒家主張善治、德政、王道等是基于性善論,等等,諸如此類的看法,大體上屬于流俗之見。
不過,在討論了與會學者的上述共識以后,我倒是想再回過頭來重新分析一下這個問題,即流俗之見僅僅是流俗?如果僅僅是就哲學認識論來分析,那么上述的流俗看法是流俗的、不得要領的。但是,如果就政治事務來說,尤其是就如何構建一個正義的社會制度來看,預設人性惡就是必要的,至少要比預設人性善更助益于建立一個正義的制度。或許,這個制度只是一個較不壞的制度,不是一個美好的社會制度,但它要比那些沉迷于人性善而冀望于圣王明君開萬世太平的奢想,更為現實和可靠。這也就是現代自由主義與古代的哲學王之類的古典美德主義的根本區別。在這一點上,東西方皆是如此。性善德性論陳詞太高(萬世太平的理想國),其結果是專制主義,自由憲政論只求底線(最不壞的制度),其結果反而是“三代之治在英美”。
如此看來,關于人的性善性惡,在此就不是哲學的認識論問題,不是真與假的求真問題,而是預設問題。也就是說,自由主義如果主張人性惡,那也只是一種預設,而且這個預設還有嚴格的限定,即:僅僅就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法律制度的人間秩序構建來說,要追求一種正義的制度,那么預設人性惡比預設人性善,更有益于建立一套正義、自由,甚至美好的社會制度。英國保守主義思想家奧克蕭特曾經指出,人性論問題只有置于政治理性的范式下才有意義。或者說,在政治領域,且僅僅在政治領域,人性惡的假設才是成立的。如果我們把自由主義視為一套政治理論,那么預設人性惡就比預設人性善在理論上更為可欲。至于哲學、倫理學、道德學層面的關于人性問題的探討,則是另外一回事了。不過,上述人性惡的預設只是自由主義的一種理論方式,自由主義還有其他論述政治的方式,例如,基督教神學上的原罪論,以及歷史主義的關于人性的演變論,甚至來自古典亞里士多德的德性論,等等,都可以成為現代自由主義政治理論的思想淵源。
第二,中國自由主義與儒家思想接榫的可能途經。在筆者看來,在社會政治領域,人性論的觀點并不占有核心地位。即便是試圖構建一整套學說的思想流派,其關于人性善惡的觀點,一旦涉及社會法政領域,其內在的邏輯理路也不是平鋪直敘、一竿子到底的,而是需要一種方法論的重大轉化。政法事務是人類共同體要處理的一個特殊事務,不同于道德乃至倫理領域中的人際關系事務,其中制度設置具有重大的作用。一個優良的政體可以讓惡人變成好人(至少在行為層面),一個敗壞的政體可以讓好人做出諸多惡行。翻檢中外歷史,這一點隨處可見。
其實,思想家們對此早有洞察,并沒有多少固執一詞的教條主義。說起來,自由主義有多種形態,儒家也有多種形態。就人性論而言,各家各派固然有不同的偏重點,但相同之處也很多。例如,英國的自由主義的主流思想理論,與傳統的儒家思想多有契合,有關社會事務的看法多有一致之處。相形之下,中國先秦乃至漢代儒家的思想與德國的哲學思辨,反而隔膜甚遠。至于宋代理學,雖然接引佛老,與德國思想旨趣有些相投,但其義理之辨的形而上背景還是大為不同的。德國思想中的歷史主義有一個神學超驗論的大帽子,而中國儒家的歷史主義則是文史之道,超驗論色彩并不凸顯。總的來說,中國儒家一脈,從周孔之道直至晚清公羊學,就其呈現出來的經驗論、不可知論、文明演進論、良善社會論,等等,與英國的自由主義,例如洛克、穆勒,尤其是蘇格蘭思想一脈,有著很密切的相關性和契合性,它們之間有著相當多的思想理論的公約數。
就人性預設來看,例如,休謨和斯密,就持有與孔子相似的看法:人性中有同情、仁愛的種子,但人性中也有自私自利的成分。但在社會政治領域,最重要的是如何塑造社會秩序,如孔子所謂的周禮秩序,使得人性的光輝得到發揚,人性的卑鄙受到約束。這就不是單純的人性善惡本身所能解決的了,而是需要另外一些東西。在英國自由主義看來,這另外的東西就是文明的演化,尤其是經濟、法律、道德等方面的規則與習俗的擴展,它們形成了一個抽象的大社會,在其中,每個人的德性和動機之良善與否,并不至關重要,遵循規則、尊重他人,才是最為根本性的。在其中,方法論的個人主義與方法論的集體主義也并非你死我活地非要斗爭,這里的關鍵是不能以道德優勢驅使公權力強迫他人,當然,更不能為惡人提供使用公權力滿足私欲的空間。所以,這個抽象社會,必然是一個公共社會、法制社會、憲章社會,其最大的敵人,是公權力的私用。
或許,就是在這個方面,儒家思想與自由主義出現了差別。儒家沒有發現這個關于人性論的政治領域的方法論轉型,而還是一竿子到底的邏輯,以為圣徒、明君或士君子可以以德治天下。在古典社會或許還有部分的可能性,因為那時的社會大體是小社會、熟人社會,或親緣關系遞減的小型共同體。但對于一個擴展的大社會來說,德治以及人性善的政治觀,則是要出問題的,因為約束公權力恣意妄為的制度難以建立。周孔之道與英國自由主義,都認同文明的力量,認為文明可以使社會政治實現昌明和廉潔,人民福祉得到保障。但是,文明的力量要擴展起來,靠的是什么?僅僅是教化嗎?僅僅是大學之道嗎?英國自由主義并不這樣認為。他們認為,更為關鍵的是相信每個人獲取自由的訴求與努力,這些或許在圣賢眼里是微不足道的,但正是這些力量塑造出來一個正義的擴展的秩序結構,其中包含憲制秩序、經濟秩序和法制秩序。上述這些秩序,與人性論的善惡預設并不對峙,可以接納德政,接納人性中蘊含的仁義禮智信,給它們足夠的發揚空間,同時也接納人性惡,但可以抵制這種惡通過驅使公權力或秩序力量來實現自己的私利企圖。
這便是保守的自由主義的思想觀點,它們是自由主義社會政治理論的核心,來自英美思想譜系,例如,英國的普通法傳統、蘇格蘭啟蒙思想、美國立憲主義等。正是在上述基點上,筆者認為自由主義與儒家思想是可以找到接榫之處的。這種自由主義,對于儒家思想和儒家傳統,大致是贊同的,是可以合作的。在當今中國社會的大轉型中,自由主義與儒家,應該合作,相互吸收、相互融匯,共同建立中國的自由主義政治理論。所謂中國,其實就是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型,換個角度看也即自由主義包容中國傳統,共同構建中國的憲制國家、法制政府與公民社會。
總的來說,自由主義需要中國化,需要進一步置身于中國傳統,在傳統中國的變法維新、移風易俗中獲得生命的根基。而儒家思想也要與時俱進,不能固守古代舊制,拘泥于章句鉤沉,而是必須面向中國社會的大轉型,實現方法論的轉變,從人性論的一竿子到底的邏輯定式中走出來,尋求復古更新之路。而英美自由主義則是儒家最有助益的拐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