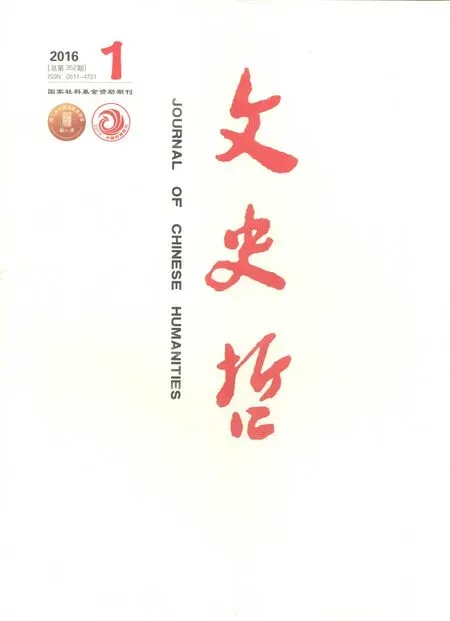儒家烏托邦傳統與近代中國的激進主義
?
儒家烏托邦傳統與近代中國的激進主義
蕭功秦
(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上海 200234)
我要說的第一個問題是,中國文化中的性善論導致了用道德主義解決一切問題的政治哲學。西方文明與儒家文明對人性的預設確實有所不同。西方基督教文明主張性惡論,這是關于人性的悲觀主義的理解。既然人性是惡的,就不可能單純通過道德教化來改造,西方文明因而發展出一整套基于歷史經驗的制度與法律,來約束人性中的惡。相反,儒家文化中的性善論則是關于人性的樂觀主義預設。儒家相信人性本善,認為通過道德的涵育與教化,就可以把人內在的善的潛質(即儒家所謂的“性”)顯揚出來,通過“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就可以讓人皆有之的內在的善的資源充沛于全身。如果全社會的人都能通過修養與教化,修煉成具有完善人格的君子,那么,理想社會就會到來。
儒家執著于道德治國。儒家經典中的“三代”,實乃由儒家所肯定的道德原則建構起來的烏托邦世界,它與夏、商、周的歷史事實相距甚遠,只是儒家知識分子心目中的道德理想國的投影。儒家根據德治的原則,建構起一系列理想化的古代制度,并把這種制度附麗到“三代”上去。這種烏托邦建構的過程,類似于現代建構理性主義的思維過程。在后者看來,良好的制度可以經由人的理性,根據“第一原理”與道德原則設計出來。這一建構過程是純理性的,與經驗事實無關,與人在適應環境挑戰過程中的經驗與試錯無關。這種思維方式也可稱為“儒家道德建構主義”。
儒家通過它所描繪的“三代”告訴世人,先人曾經生活在非常完美的過去,只要按“三代”的制度去做,什么問題都可以解決。自秦漢以來,人們真以為歷史上的“三代”就是曾經出現過的理想社會。儒家的這種道德建構主義,如同人類各民族的烏托邦理想一樣,像黑暗世界的一盞明燈,確實起到了用理想世界來批判不公正的世俗生活的作用。然而,這種建構主義思維模式,也成為中國烏托邦主義的根源。西漢末年的王莽與那個時代的人們一樣,對三代美好社會信以為真,于是他力圖運用自己取得的至高權勢,在現實生活中復古改制,結果造成了社會的大災難。王莽的悲劇是烏托邦理想付諸實踐而形成的悲劇。20世紀30年代,著名思想家蕭公權先生認為,王莽改制是最古老的社會主義試驗。同時,我們也可以說,它是中國烏托邦主義政治實踐最早的慘痛失敗。
我要說的第二個問題是,康有為的樂觀主義的人性論導致了烏托邦主義。康有為的大同思想,其深層的思維句法結構,可以說與儒家文化中的道德建構主義一脈相承。在《大同書》中,家庭、私有財產、國家、階級、婚姻等等,舉凡一切在適應環境挑戰過程中形成的集體經驗的產物,都被認為是罪惡的,或至少是不完美的。康有為認為有必要憑著人類自己的理性,按照他心目中的道德理想的原則,去設計一些人造的完美制度。在康有為看來,既然人類憑自己的理性可以發明精美的機器,為什么就不能發明適合于人性的好的社會制度?用完美來取代不完美,用無缺陷來取代罪惡與缺陷,被認為是毋庸置疑的天經地義。康有為大同思想就是以這種樂觀主義的邏輯為基礎的。
在康有為看來,作為千百年來人類在現實生活中形成的國家、家庭、婚姻及種種傳統習俗既然充滿缺陷,那么,最理想的、最適合人類生活的社會就應該取消這些東西,而代之以他頭腦中想象出來的、沒有缺點的人造新制度。康有為在《大同書》里認定,因為國家之間會發生戰爭,所以要取消國家,代之以“世界政府”。因為階級制度會導致社會不平等,所以要取消階級。因為家庭導致婆媳爭吵、兄弟打斗,是自私的溫床、罪惡之源,只會帶來無窮的痛苦,所以可以而且有必要取消家庭,代之以“公養”、“公教”、“公恤”。又因為婚姻造成事實上的女子不平等地位,所以要取消婚姻,代之以一個月至一年為期的男女合同制,等等。
康有為的自信,源于他的理性萬能信念。他認為,經驗會犯錯誤,理性則如同公理幾何,不會出錯。但事實上,康有為在運用他的理性時就出了問題。他把黑人診斷為“劣等種族”,繼而主張:采用“黑白雜婚之法”,男性黑人必須與女性白人結婚,女性黑人必須嫁給男性白人,以便在“七百年至一千年”內,使黑人化為白人。這一荒唐的例子足以證明,觀念人所信托的理性本身具有缺陷。
毫無疑問,這種以性善論為基礎的政治邏輯勢必導致一種烏托邦傾向。康有為正是基于這一傾向,建構了通過對人進行教化以達到無私社會的政治哲學。
這種理想主義的社會藍圖,必然導致政治上的激進主義。譚嗣同的“沖決網羅”是20世紀激進反傳統主義的先聲。在他看來,傳統就是“網羅”,就是束縛人性的東西,要實現一個符合人性與道德的社會,就必須沖決這些“網羅”,用觀念中的完美主義世界取代現實。可以說,譚嗣同是中國近代以來第一個把傳統“妖魔化”的知識分子。當然,傳統中有許多必須批判的東西,但“沖決網羅”則把傳統符號化,使之被解釋為沒有積極意義與正面社會功能的東西。“五四”以后,全盤反傳統主義取得優勢話語權。譚嗣同的“沖決網羅論”為20世紀中國觀念人的大量出現開辟了道路。
更嚴重的問題還在于,對“善”的理解是因人而異的。不同的時代、教養、性格、經歷,特別是經受過不同挫折與痛苦的人們,會在自己頭腦中形成不同的“善”的世界愿景。人們會以自己所理解的主觀的“善”為標尺,對世界現行秩序進行重新建構。受這種烏托邦理念與思維模式支配的人們,存在著一種強大的重構人類新秩序的道德沖動。由此而產生的道德優越感、斗爭意識與正邪兩值分類,是激進主義政治哲學的基礎。
事實上,用自己有缺陷的理性,去設計社會改造的藍圖,強行挑戰人類千百年的集體經驗——這種行事模式,正是近代以來激進主義的巨大悲劇之一。對康有為的《大同書》進行深入分析,有助于理解20世紀激進主義的哲學基礎與內涵。
我要說的第三個問題是,古代、近代知識分子與現代知識分子具有深層同構性,都是用道德建構主義重建世界。孔子、康有為、“五四”以后的中國知識分子,雖然時代不同,價值觀不同,但在思維方式上,卻存在一脈相承的“道德理想國”傳統。在儒家那里,道德王國在過去,即三代;在康有為與“五四”以后的中國激進知識分子那里,道德王國則在未來。這三者具體取向不同,但思維方式卻頗具深層的同構性與延續性。他們都崇尚人類經驗世界中并不存在理想王國,都不承認現實中的社會是人類集體經驗的產物,不承認這種歷史產物是一方水土上生活著的人們在適應自身環境挑戰中形成的。并且,他們都相信,可以用自己體認的道德理性原則來重塑新世界,前者的榜樣在過去,因此趨向于復古,后者的榜樣在未來,因此趨向于激進地反對傳統。
以道德建構主義為基礎的中國知識譜系,本能地拒斥經驗主義思維方式。雖然中國民間文化中也有樸素的經驗主義傳統,但作為精英主流文化的儒家思想,卻缺乏西方意義上的那種以人類集體經驗為基礎的經驗主義政治哲學。美國學者墨子刻曾這樣評論道:“在西方經驗主義者看來,歷史始終是一個神魔混雜的過程,社會中始終有著很多與人類理想相矛盾的成分。人類的生活一方面并不完美,另一方面也還是很有價值的,這個世界還是很值得留戀,是有趣味的。世界既不完美也還值得活下去,人們還有希望使世界變得比它原來的樣子更好一些。既然人們對生活的要求既不太高,又不滿足,這就不會走極端,就能心平氣和地考慮這個世界的種種問題,如果人們認同這樣一個前提,那么,無論是要保守傳統,還是要改革傳統,都是對方可以理解與體諒的。”*參見蕭功秦:《一個美國保守主義者眼中的中國改革》,《中國的大轉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年,第307頁。
墨子刻還認為,在保守主義者看來,“改革傳統,是因為傳統并不完美,保守傳統,是因為傳統值得我們留戀。它既不壞到哪里,也不好到哪里,這樣,知識分子與國民就會形成一種保守主義與改革主義之間的持續的對話”*蕭功秦:《一個美國保守主義者眼中的中國改革》,《中國的大轉型》,第307頁。。這就是西方意義上的保守主義。西方的保守主義并不反對變革,但反對以人的理性去設計建構一個新社會,反對以這種想當然的“新社會”模式來取代現實社會。而儒家的道德建構主義卻相反,以道德理想國設計為好社會的藍本。到了近代,這種思維模式與思維“句法結構”,自然而然與激進主義合流。一切激進主義都采取經驗的反叛者姿態,以自己心目中的道德意象為楷模,試圖從根本上顛覆、否定現存秩序。
我要說的第四個問題是,對極左思潮的反思:烏托邦主義為什么在中國盛行?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國的大災難,這場災難的發生有政治、歷史與文化多方面的原因。在這里,我們可以從與本文有關的角度,對“文化大革命”極左思潮的觀念邏輯作大概的解析。這種極左思潮鼓吹“斗私批修”與“靈魂深處鬧革命”,這種觀念背后隱含著一種特殊的“道德建構主義”邏輯。這種建構主義的邏輯是:現行體制下之所以仍然出現“官僚主義”,問題不在所有制,因為所有制改造已經完成了;人的“私心”不是來自所有制這一經濟基礎,而只能來自“腐朽的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筑”,因此只有進行“上層建筑的革命”,才能解決“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的問題。而在極左思潮的觀念中,“上層建筑革命”的核心就是“斗私批修”,就是“在靈魂深處進行革命”。而要推行極左的道德教化,那就要“破私立公”,就要在“靈魂深處”進行“狠斗私字一閃念”的革命。只有這樣,才能造就“新人”,只有當這樣的“上層建筑革命”完成了,革命才能實現最終的目標。
意味深長的是,早在七百年前的元代理學家吳澄的文集中,我們赫然發現“破私立公”這四個字。這種字句上的巧合并非偶然,而是表明極左思潮的道德建構主義,與理學家的道德建構主義之間,存在深層次的邏輯同構關系。正因為如此,當我們研究儒家思想時,提倡儒學的學者一定要注意到這些層面的問題。儒家的道德建構主義有著發展為文化浪漫主義的潛質。
中國的自由主義學者與中國的新左派學者,其價值取向雖然各異,思維方式中卻都不自覺地存在著我所說的道德建構主義。這或許與人們不自覺地承繼了傳統文化的深層結構有關。要克服思想中的片面性,還是要回到經驗主義上去,限于篇幅,對此就不再展開了。
要之,性善論具有多面性。必須承認,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缺乏制度性宗教信仰的民族,性善論在歷史上也曾起到社會道德標尺的作用,它有著激勵社會成員通過合理教化,獲得積極向上的人生價值的社會功能。性善論與道德建構主義的關系,以及道德建構主義與烏托邦的關系,是思想史研究中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在這里初步提出一些看法,供大家思考。從儒家文化中獲取積極的精神資源,揚棄儒家傳統中的烏托邦主義,是值得當今中國思想界關注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