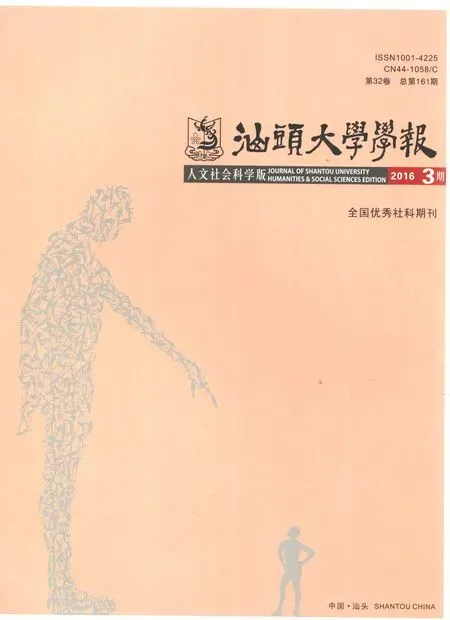《老子》之“身”辨:“有身”“無身”與“為身”
張艷艷
(汕頭大學文學院,廣東 汕頭 515063)
?
《老子》之“身”辨:“有身”“無身”與“為身”
張艷艷
(汕頭大學文學院,廣東汕頭515063)
摘要:在老子以氣構生的有機身體觀及身物關系格局中,甄別形軀之身與精神之身并非是老子論身的關鍵;在目、心、志與腹、骨、氣的對照關系中,老子有著對身體主體構成及其價值指向的貞認。以“無身”為身,勘破現實之身在形塑過程中的失真狀態,消解形塑現實之身的價值屬性,以回復身體之自然原初狀態為終極訴求,建構老子理想之身;以“無身”為身所實現的消解與構建揭示出老子身體觀的價值旨趣。
關鍵詞:目;腹;氣;圣人;有身;無身;為身
基于《老子》文本中圍繞“身”展開的話語富有含混性,自古以來注家釋義便爭訟不已,尤其以13章的釋義最為顯著,見出對老子貴身與否迥異其趣的見地。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13章》)
一說強調“無身”,以河上公本釋義為始作俑者,“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有身則憂其勤勞,念其饑寒,觸情縱欲,則遇禍患也。使吾無有身體,得道自然,輕舉升云,出入無間,與道通神,當有何患。”[1]所要無的“身”顯然是形軀之身,這倒貼合兩漢之際成仙問道方式對老子的宗教式演繹。后世成玄英疏義:“執著我身,不能忘遣,為身愁毒,即是大患。只為有身,所以有患,身既無矣,患豈有焉?故我無身,患將安托?所言無者,坐忘喪我,墮體離形,即身無身,非是滅壞,而稱無也。”[2]401已是援莊釋老,又入莊老出玄佛,所要無的“身”是執著于一己欲念心志之身,若“無己”、“喪我”則可無身,忘身養神則得道之大清明。此論后繼者眾,不一一陳說。
一說強調“貴身”,司馬光之論:“有身斯有患也,然則,既有此身,則當貴之,愛之,循自然之理,以應事物,不縱情欲,俾之無患可也。”[3]110李榮的注更說得直接:“身形是成道之本”,[2]672顯然形軀之身不獨只是生命的載器,所貴之身當亦包含對形軀之身的持守與肯定。陳鼓應在辨疑此章時說:“這一章頗遭曲解。前人多解釋為‘身’是一切煩惱大患的根源,所以要忘身。一個‘貴身’的思想卻被誤解為‘忘身’。造成這種曲解多半是受了佛學的影響,他們用佛學的觀點去附會老子。肉體和精神這兩個部分是構成人之所以為人的充分而且必要的條件,也即是構成人的生命的充分而且必要的條件。有些人把‘身’視為‘肉體’的同義字,再加上道學觀念和宗教思想的影響,認為肉體是可卑的,遂有‘忘身’的說法。”[3]112-113陳氏此論亦是在肯定形態之軀的前提上,在形神一體的格局中強調老子對“身體”的珍視。
然而僅就形神關系的向度言說老子之身以及由此引發的“無身”與“貴身”之爭是否就得老子論身之要領?如是的思路又如何解釋圣人“為腹不為目”?故此,要論說此意,恐怕要先對老子的身體觀做一統和式體認,首先甄別形軀之身與精神之身是否是老子論身的關鍵?繼而在目、心、志與腹、骨、氣的對照關系中,辨析老子對身體主體構成及其價值指向的貞認,何以圣人“為腹不為目”、又何以要為天下“渾其心”?在更闊達的視域中,由老子之道來看宇宙間與人世間所開顯的物身關系格局,并以此審視老子對“身”之定位與期許,老子貴身與否的爭訟本身實則可以統和。雖然老子圍繞“身”所展開的話語表述本身是以含混的面貌出現的,卻有著清晰的方向指向性,以“無身”為身,是以損卻的方式消解基于自我本位立場對一己之身的執著,同時亦勘破起于身對物(也包括他人)的對象性關系的僭越實質,在恢復物之自在本性的同時,亦恢復身之“歸本復初”的狀態,由此可見要損卻的“身”是被對象性關系粘滯著的自我本位立場之身,當然是不應貴的,損卻此身獲得的身是自在而富有生機的,當然是老子珍視的。以“無身”為身所實現的消解與構建,當是老子之身的價值旨趣。
一、《老子》中涉及到“身”的關聯性表述
(一)以身喻道:“母”
首要的問題是何者為老子之身的確切落實?此問初看是明知故問,但是在追問的求索之途可以見出微妙旨趣,也只有厘清這一前提之后,方可細論老子對身體主體構成及其價值指向的貞認。事實上《老子》全文與“身”關涉的關聯性表述各自承載的價值屬性與角色設定皆不同。母、嬰兒、圣人、民,何者才是老子之身的承載者、是老子思想格局中真正的身體主體呢?
縱觀《老子》全文,“母”凡5見,皆與“道”相關,取“母”的功能性隱喻義,開顯“道”為萬物生成之根本的生成論本體地位。“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老子·1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老子· 25章》)無論是“天地母”、還是“萬物母”都是對不可坐實向具象形跡的核心概念“道”的隱喻性表述,基于隱喻認知源域向目標域的投射,借助“母”這一身體意象的具象特質——蘊育生命的生殖性功能和“生”而不有的角色屬性——在人的認知格局中實現格式塔式整合,目不可見、耳不可聽,無法落實向形跡的“道”體,在我們這里獲得異質同構的具象體認。所以“母”雖為身體意象,卻不具有身體主體向度上的意義,“母”作為概念隱喻,在其它章節中,甚至直接指代“道”本身。“我獨異于人,而貴食母。”(《老子·20章》)“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老子·52章》)堅守吸納自母而來的滋養和對“母”的持守其實都是人不離道、以道為本。有鑒于老子話語生態與隱喻思維的內在親緣,不獨“母”為概念隱喻以喻道,川谷、橐龠等自然器物意象亦然,以此也可輔證“母”雖為身體意象,但是實質上與道更為關涉,并不具有身體本體意味,在身體論的視域中“貴食母”之論可暫時擱置。
(二)以身喻道及圣人:“嬰兒”
與之相應“嬰兒”也是身體意象,但是與老子之“身”則更多牽絆,我們可否說老子所論之身就是嬰兒呢?還是老子以嬰兒為用、作為言說憑介見出老子之身的真諦?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鑒,能如疵乎?愛國治民,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老子·10章》)
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嬰兒之未孩;累累兮,若無所歸。(《老子·20章》)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為天下溪,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于樸。(《老子·28章》)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老子·55章》)
何謂嬰兒?高亨說:“人性未漓為嬰兒”,[3]179“含德之厚”、“常德不離”都是對于嬰兒生命狀態的描述,在道物關系的格局里“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老子·51章》)諸家釋義:德為道之“功”、“見”、“用”,[3]148綜合王弼所述:“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4]可以說:“德是踐履著的道,是道向有形之物的落實,德是生命之為生命的本質所在,生命之本性所在,也是道的顯現”。[5]27如是可見,嬰兒是葆有老子之道的具象身體形態,55章中我們看到老子所推崇的嬰兒之身的具體狀態,他“精氣充足”、“元氣淳和”、雖然“骨弱筋柔”卻飽富有生命力,終日號哭嗓子卻不黯啞,毒蟲、猛獸與禽鳥都不會攻擊他。何以如此?恐怕這些特性都導向同一個因由:因其“未知”所以不起欲,尚無一“己”的貞認,當然不知“牝牡”之事,也當然不會有我與物的分界,既然尚不知物我的分界,對于毒蟲、禽鳥猛獸亦無所謂畏懼與不畏懼,所以兩相自在。結合老子多處“樸”之為喻,“道常無名樸”(《老子·32章》)、“敦兮其若樸”(《老子·15章》),高亨說:“木質未散為樸。”[3]179-180,強調的也是本在原初的狀態,可見老子是借助樸與嬰兒的自然自在狀態來譬喻老子之道的境界,現實境遇中的具體生命體也當以自然性為道境的終極訴求,以“復歸于”嬰兒與樸為修身之理想狀態。于是我們看到老子說“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我“沌沌兮,如嬰兒之未孩”,顯然“我”與嬰兒有分界,所以才說“如”,句式關系清晰,嬰兒是對“我”修身理想境界的具象表述,是道境的隱喻化表達,卻不是老子所有語境中實際行為主體,所以老子是憑借“嬰兒之身”為喻,見出“我”等身體主體養成的境界。“我”既然是老子之身的真正落實,那么“我”為何人呢?
(三)身體主體的分鑒:“圣人”與“民”
統觀《老子》全文81章,在社會現實境遇中的個體生命大致呈現出圣人與民對應的兩個序列,作為圣人序列的行為主體表述有:圣人(24章次)、我(吾,5章次)、侯王(2章次)、善為道者(2章次)、善攝生者(1章次)、君子(2章次)、大丈夫(1章次)、士(1章次),涉及君子、大丈夫、士各章所論皆無關要旨,另外修身工夫諸章及其他省略主語的章節,雖未明確言出其行為主體亦在圣人序列。作為民序列的行為主體表述有:民(13章次)、百姓(3章次)、眾人(3章次),人(作為“眾人”之人,5章次)。如果我們取圣人與民各代之,則發現兩者各自代表不同的身體狀態與價值取向,同時各自承載的角色定位亦不同。我們列舉部分章節如下: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老子·3章》)
荒兮,其未央哉!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嬰兒之未孩;累累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馀,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且鄙。我獨異于人,而貴食母。(《老子·20章》)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鎮之以無名之樸,夫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老子·37章》)
圣人在天下,歙歙焉,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老子·49章》)
顯然圣人與民的對應關系至少包含如下兩個面向:其一,圣人與民分別代表不同的生命情態和價值取向,現實境遇中的民熙熙攘攘、縱情使欲,為聲色、貨殖、名利所蠱惑,自然的天性受到損傷,陷入與道背馳的境地。而圣人則無欲、不爭,守道靜定,顯然圣人才是老子心目中自然道境的持守者與踐履者,是其價值指向的貞認者。其二,圣人與民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施動與受動關系,因為圣人處身為世的姿態,最終決定民的生存狀態。圣人(侯王)若能持守自然無為之道,損卻好惡、賢愚、貨殖的分辨,則民自然葆有自化、自正的原初素樸狀態,于圣人而言是自覺主動的行為選擇,于民而言是自然被動的結果。雖然兩者都是《老子》中具體的身體主體構成,但是民并不具備切實的主體性,他們的生存狀態只是圣人踐履自然之道的結果,所以圣人才是自省、自覺的身體主體,而民只是自然自在的生命狀態。因此,我們所要談論的老子之身及其由此帶來的爭辯當是以“圣人”這一身體主體為本。
二、《老子》中的身體主體構成及其價值指向
(一)禮樂建制對身體主體構成的形塑:《老子》的言說語境
中性意義上有關五官感知生理屬性與功能意義的描述,是軸心時代所有論說展開的前提,正所謂:“目辨白黑美惡,耳辨聲音清濁,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荀子·榮辱》)身體器官各有其生理功能是生就如此的自然屬性,在禮樂對身體主體的形塑過程中,基于感官知覺的自然屬性卻生發出其價值屬性,為禮樂建制提供身體論依托。
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國語·周語下》)
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役也。(《五行· 45- 46簡》)
目者,心之浮也。言者,事之指也。作于中,則播于外矣!(《大戴禮記·曾子立事》)
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國語·周語下》)
誠在其中,此見于外;……初氣主物,物生有聲……心氣華誕者,其聲流散……聽其聲,處其氣,考其所為,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以其前占其后,以其見占其隱,以其小占其大。此之謂“視中”也。(《大戴禮記·文王官人》)
“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先秦的身體觀,感官感知與血氣心知為一體貫通關系,兩者之間呈現雙向互滲、交流溝通狀態。《國語》中的論說強調由表及里的顯發,耳目感知是心的樞機關鍵所在,耳和視正、耳目聰明才能導致思慮純固。口辨味道,耳聽聲音,聲音和味道產生精氣,精氣顯現于口為人的言語,滲透于目是人的觀察,如果所視所聽出了問題,不僅是對耳目的損害,同時也意味著損傷了人的精氣,從而整個身體失去和諧。可見此時已貞認感官感知對于體氣心知的塑造影響之功。在雙向互滲的另一向度,也強調體氣心知對于感官感知的滲透,是由里及表的顯發。不同身體主體的內在“心氣”不同,那么其聲色自然有異,可以憑借他的“溫好”之聲,判斷此人心氣“寬柔”;也可以憑借一人“其聲斯丑”,判斷此人心氣“鄙戾”。這便是“誠在其中,此見于外”的“視中”之法。“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役也”、“目者,心之浮也”,意思非常清楚,感官感知是對于心知的執行,是其外在顯現,心的絕對主導地位到孟子、荀子的文本中進一步確立,所謂心為大體、為君之論,所謂胸中正,眸子才可以正。總括來看此一體兩面,感官感知與體氣心知之間的雙向溝通互滲關系清晰,各種文本都見出對表里內外互通關系的肯定。故此整個先秦時代的身體觀是一體觀而非二元論,耳目-心氣是一體貫通的,同時非常重要的是,也未見將心與氣對立起來表述的情況。
春秋時代的文本中時見這樣的表述:視聽味之正與不正、和與不和。從生理屬性的層面來看,這個問題是不存在的;但是在幾乎所有的文獻中,這個問題是如影隨形的。如此可見在辨析身體主體內在構成的同時,身體的價值屬性一并被構建起來了,甚至可以說,對身體觀的確立是為禮樂建制提供身體基礎。
《左傳》中,“氣”首先是宇宙天地氤氳的自然之氣,所謂“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是也。萬物有機體尤其是人作為生命有機體,他的好、惡、喜、怒、哀、樂皆源于此,在天人感應互通的關系格局中人的六種情緒變化分別對應天地自然之氣的六種狀態,可見身體之內的氣息流轉與天地自然之氣是一體互通關系,而后者為本源。“五味”、“五色”、“五聲”皆為氣之顯發,如果它們“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所以對于氣所生發之聲色味必須有所整飭,才能保證“哀樂不失”、“協于天地之性”。由此“禮”的正當性、自然性、必要性呼之欲出,于是趙簡子心悅誠服,“甚哉,禮之大也!”禮樂建制變成了天經地義之事,聲色味便“為禮以奉之”,制定六畜、五牲、三犧是五味所要遵循的,制定九文、六采、五章是五色所要遵循的,制定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使五聲有所遵循。中性意義上的聲色味有了等級的分界,在該與不該的區隔中,何目視何色有了清晰的層級規定,位階關系有了具象的感性體現,基于感官感知的身體基礎,禮樂建制將新的社會秩序確立于容動聲色、舉手投足間,此其一。其二,中性意義上的聲色味有了善惡的價值分界。何者為正、順、善、和,何者為奸、逆、惡、淫,并不取決于聲色味自身的特質,而取決于與禮樂建制的社會秩序的呼應。就個體生命而言,體氣心知的塑造源于聲色味的滋養,所謂“以鐘鼓道志,以琴瑟樂心”,所以視之正與不正、聽之和與不和是根本所在,只有呼應禮樂建制的聲色味才是正的與和的,才可以由“耳目聰明,血氣和平”,而“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美善相樂。”(《荀子·樂論》)諸上兩點我們已清晰可見禮樂建制對于身體主體構成的規定性與形塑軌跡,所以中性意義上的生命體僅只是潛在狀態的人,要想“成人”則必是要“能自曲直以赴禮者。”
(二)老子論身體主體構成及其價值指向
在厘清老子之身的真正落實者是圣人的前提下,在《老子》文本生成的整個時代語境中,我們來看老子對身體主體構成的分辨及其蘊含的價值指向。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圣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老子·3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圣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 12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為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老子·59章》)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老子·55章》)
圣人常無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老子·49章》)
在諸上涉及到身體主體構成的各章中,目/腹、心/腹、志/骨、心/氣,具體所示雖有差異,但是前后的對照關系明晰確定:耳目五官感知、心志在一個序列,而腹、骨、氣則構成另一個序列,兩個序列代表不同價值取向,前者被老子否定,后者則被老子肯定。對照之下,《老子》對于感官感知與心志的關系表述并未發生變化,但是其“氣”卻與“心”分離,同時骨、腹從中性意義上的軀體感知中區分出來,進入與氣順應的序列。這是表層面上術語的使用差別。更進一步,“目”、“心”與“腹”、“氣”在老子視域中的價值屬性又當作何解呢?
老子處身的時代語境有其雙重性:一重自然是禮樂建制對于身體主體構成的形塑,及在此基礎上構建起的社會秩序。但是此一重是以理想狀態存在的,哪怕是以“先王”皆尚之的姿態回望其曾確實存在。另一重則是禮崩樂壞的失序現實。單穆公與伶州鳩對景王的勸諫是如此脆弱,對聲色味之禮制構建在其文本語境中便顯反諷意味。孔子說:“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論語·八佾》)。自候王到官宦僭越之義日顯,禮樂建制對于個體感官感知的形塑在現實社會境遇中面臨全然崩塌的危機。
這是老子言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的雙重語境。五色、五音、五味表面來看是現實狀態中人人不可遏制地追求縱情聲色。究其因由,老子卻以為起于禮樂建制的等級分界與善惡附會。這與原始儒家的訴求無疑有著本質差異。原始儒家是做出善惡、美丑、順逆、莊淫的分辨,貞認其一極;在忍無可忍之后,用心良苦以求禮樂文明之重建,并嘗試建構禮樂建制之學理基礎。而道家則勘破分辨本身,反思禮樂建制本身所弊。“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老子·38章》)莊子將禮樂建制對于身體主體構成的形塑之弊說得更為具體:“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莊子·馬蹄》)又“駢于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于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莊子·駢拇》)這兩段可做老子上述所論極為恰切的注腳。真正損傷耳目心知的并不是中性意義上的聲色味,而是被禮樂構建了的聲色味,是禮樂建制對目、心的蒙蔽與傷害。老子說“絕圣棄智”、“絕巧棄利”,甚至描述“小國寡民”的社會圖景都是在試圖消解禮樂文明讓耳目心知失真的努力。既然如此,《老子》文本中的“心”、“目”便不在中性意義上使用,而是指在禮樂文明的建構與失序雙重格局中,被形塑又陷溺的身體感官與心志。林語堂說:“‘目’指外在自我或感覺世界。”[3]107此解在先秦語境其實可見淵源,孟子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五官感知與物為接,所以容易為外物蒙蔽,不免陷溺。當然孟子所論有截然不同的旨趣,因為接下來他說“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孟子·告子上》)顯然是強調心性本體的路向,而《老子》文中的心性與耳目五官一樣早已被禮樂建制所形塑,并因此被挑逗起無窮盡的欲望而最終讓禮樂建制失序。所以老子才說圣人之治,“不為目”,虛其“心”、弱其“志”、“渾其心”、不能“心使氣”,所要損卻的都是被禮樂建制所附著的“心”與“目”。“‘虛’不是去本在自然之心,而是清除附著于其中的人文化成之后滋生出的種種欲念心志,清除之后回復到自然自在的本心狀態。”[5]58只有去禮樂建制對于身體的形塑之弊,心才可以復本心、目才可以復明。
老子對“腹”、“骨”、“氣”的肯定態度十分顯著,不同于先秦文獻中“心氣”并置的表述,“氣”在老子文本中意義非凡。“氣”凡三見,一處論氣為萬物之本:“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老子·42章》)一處論修身成圣的工夫:“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老子·10章》)再就是“心使氣曰強”,集合三處之義,以氣為身體之本的觀念已顯出端倪。“治人事天”,要在于“嗇”,高亨注:“天,身也。”[3]295河上公本注:“治身者當愛其精氣不放逸。”[3]295兩相結合,更進一步佐證老子以氣為身體之本的論說。所以持守身體本在之精氣,才是真正的“長生久視之道”。
圣人之治,“實其腹”、“強其骨”、“為腹”,蔣錫昌說:“‘為腹’即為無欲之生活”[3]107,林語堂則說:“‘腹’指內在自我(the inner self)”。[3]107因為“無欲”是《老子》中高頻度出現的表述,并不在中性意義上使用,“為腹”與“無欲”并置有點兒同義反復,以“內在自我”與“感覺世界”相對解釋“腹”與“目”又無法撇清“腹”可能與“心”發生的混淆。就其字面意思上講,很多人將“為腹”視為對基本生理需求的滿足,又有生物本質主義的嫌疑。
五官感知與心志皆與物為接,試若“為目”,目之所欲為周遭情景所浸染而不易察,同時耳目感官彼此連覺、感通,很多時候感知的愉悅并不真正來自這一感官本身。舉例來說,所謂“活色生香”便是在對象性關系中感官感知本身的失真狀態。習語常說“口腹之欲”,其實不同,尤其在老子看來,口之愉與腹之適有著本質的不同。味覺快感與腹部舒適之間的差異從生物醫學的角度是很容易分清的,然而這一不同經常被深切的混淆,區分這一不同是理解老子深意的生物基礎,腹與骨的感受不會因對象性關系而與物為接,也不會在禮樂建制中被形塑。要知老子的身體并不出離具體的社會情境,他還是談境遇中的身體,但是身在境遇中,卻“不知有之”,老子推崇的最高妙的姿態,是“太上”之境,對境遇中的物與身抱持一種兩相自在的狀態,為何是“為腹不為目”,恐怕有這樣的寓意。承上所論,境遇中的“目”不免受制于具體情境中的“色”,而境遇中的“腹”、“骨”卻似絕緣體,不為所動。以“腹”、“骨”為喻,可以更具象的引領大家體認身體主體構成本然自在的狀態,而對身體主體構成本然自在狀態的追求也才是老子要提領出的生命境界。
至此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目/腹、心/腹、志/骨、心/氣的兩個身體構成序列意義不同:“這個‘腹’指的不是生理形軀,從根本上說,是指身體的自然性,這個‘目’(心)指的也不是人先在的感知意識能力,而是指身體被社會化之后滋生出的非自然性。”[5]58對自然性與非自然性的界定作為價值甄別,以自然性為其人文訴求。依然是在社會境遇中的身,但身自為身。
在理想的身體主體狀態中,兩個序列將統和為一,耳目、心志、骨腹、氣一體貫通。那么以肉體、精神二元對分的觀念分辨其貴身與否明顯不恰切。同時老子的兩個價值序列中雜糅肉體與精神,若依肉體與精神對分,談老子貴此賤彼,還是賤此貴彼,實在都不得就里。
由現實格局來看,圣人“治身”皆始于自覺,是自覺自為的行為主體,民從“注其耳目”到“心不亂”的“處身”狀態則得益于圣人之治,是圣人自覺自為的后果。若就整個思想氤氳滲透而言,圣王又內轉為生命境界層面的內圣,于是人人皆可以此為生命境界之高標,修身以成圣。成圣之途亦見出圣人之身的微妙意趣。
三、以“無身”為身的消解與構建
(一)成圣之途的“損”與“復”
圣人的姿態首先以一系列否定式的行為顯現:“去甚,去奢,去泰”(《老子·29章》);“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老子·3章》);“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老子·22章》)。河上公註:“甚謂貪淫聲音,奢謂服飾飲食,泰謂宮室臺榭。”[3]186已是非常具體的直陳,可見圣人對陷溺于禮樂建制鼓蕩而起又無可遏制的淪喪于其中的耳目感官與心志欲念的消損與否定。老子不斷告誡彼時之候王:“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老子·26章》)再看44章:“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名、貨與治身對應,都可見老子對于理想生命情態的訴求:對陷溺于物的耳目五官感知之欲的消損;對陷溺于物的心志欲念的消損;對執著于一己之身,以自我為核心,充分凸顯一己之欲的消損。
圣人的自我修煉表現為:“欲不欲”、“學不學”、“為無為”,“行不言之教”、“處無為之事”,“無知”、“無欲”、“無為”,“不爭”、“守道”。如何才是守道之本?“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無為而無不為。”(《老子·48章》)圣人的“無為”并非指被動、放棄無所作為的行動狀態,仔細留意會發現,所有否定狀態的行為其實都包含主動選擇的前提,于是所有的否定、棄絕都不是中性意義的,而是彰顯老子明確的價值指向與觀念意圖。為的是“無為”,而同時“無為”帶來“無不為”、“不爭”帶來“天下莫能與之爭”的極大利好后果。所以錢鐘書說此為“盡人之能事以效天地之行所無事耳”[3]66。可謂一語中的。
由此我們看到圣人之治身與治世顯現出卓然不群的態勢。郝大維將“無欲”譯為“無對象的欲望(objectless desire)”,并說“這個譯法與我所解釋的‘無知’和‘無為’相呼應。非原理性的認知和非強加的行為都不會造成對世界及其組成部分的對象化。同樣,與‘無欲’相聯系的欲望不需要通過占有、控制使我們所‘欲望的’東西對象化。”[6]218老子警告現世中的候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不可執也。”(《老子·29章》),所以圣人處理與這個世界的關系是“無執”、“無為”,王弼注:“萬物以自然為性,故可因而不可為,可通而不可執也。”[3]184可見圣人治身與治世皆“尊重那種內在于自然的方式”[6]222,任物自然。當然這個“物”不只包括外于己的物,也包括內于己的身。這是非自我-對象二元論的路向,不以自我為核心本位立場,世界是一個多元并在的有機融生體,不執著于一己本位立場,便不會抱持我與他者有根本分界與等差地位的體認,“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復。”(《老子·16章》)一己與他者都是世間萬物之殊相,若可任物為物,任民(在候王與民的位階格局中)為民,則不僅物與民得以復其本性,“萬物自化”、“民自樸”。自己也從對象性關系中解放出來,獲得自然本在的身體情態,耳目感官與心知從聲色貨殖之物的陷溺中回復本心、本目,成就一氣貫注、筋柔骨健、自然狀態中耳聰目明的生命體。
(二)從修身格局看以“無身”為身
行文至此,我們亦可以明了《老子》的文本語境中“身”至少有三種分辨:原初之身、現實之身、理想之身。原初之身作為理想之身的隱喻,以嬰兒的身體意象為標示。在成就理想之身的修身工夫中常常出現:你的含德之厚能如嬰兒嗎?你不為物擾、不為欲惑能如嬰兒嗎?你的身體情態一氣貫注能如嬰兒嗎?……現實之身用來指耳目心知被對象性關系牽絆,其占有之欲念而喪失本真狀態的身體。眾人“熙熙”、“察察”,“注其耳目”如此,侯王“多藏”、“甚愛”、“尚顯”、“貴生”者也是。理想之身作為老子的理想生命情態,勘破現實之身在形塑過程中的失真狀態,消解形塑現實之身的價值屬性,以回復身體之自然原初狀態為終極訴求,借助原初之身的隱喻,建構起老子理想之身的價值旨趣。
來看涉及無身與有身之辯的其他章節: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老子·7章》)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老子·26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老子·44章》)
首先可以肯定老子是貴生的,所謂貴生,當然不是現實之身對于生之厚的執著,而是珍視生命的意思,“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的追問中,珍視生命之義已然顯著,而現實之身在具體的社會境遇中卻難免陷溺,所以老子發出這樣的警告。珍視生命之義在大量的篇章中,也都可找到支撐的依據。老子反復提到“長久”之道、“長生久視之道”,如何可以“無遺身殃”、“善攝生者”怎么做等等皆是。
蔣錫昌釋26章“以身輕天下”,“言人君縱欲自輕,則失治身之根”[3]173,可見此身是指現實之身,7章“后其身”之身、“外其身”之身,13章“所以有大患”之身都是指的現實之身,此時的身體主體沉浸于聲色、貨殖、賢愚、貴賤、高下的分辨中,其實已喪失生命原初的生機,當然是應當消解、損卻的,所以老子才說要“后”之、“外”之、“無”之。消解掉現實之身對于對象性欲望的執著,則身體的原初生命狀態得以復現,這是老子對于理想之身的描述。所以“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得以“先”和“存”的便是理想之身,而以此理想之身治世處天下,才放心可以把天下交給他。呂洞賓以“先天之身”與“后天之身”、“道身”與“凡身”分辨,“是存道身,外凡身”[7]。而劉笑敢則捻出“真身”與“世俗利益之身”[8]對照,諸上都是近似的意思。相形之下,我們以現實之身與理想之身對照,再輔之以原初之身為參照,旨在凸顯老子對身體主體的構建之義,老子視域中的身體主體并不真正落實向原初之身,而是以原初之身為隱喻,表達其對理想之身構筑的價值旨趣而已。如是便可窺見老子以“無身”為身的內在消解與構建理路。
參考文獻:
[1]王卡,點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M].北京:中華書局,1993:48- 49.
[2]蒙文通.道書輯校十種[M].成都:巴蜀書社,2001.
[3]陳鼓應.老子注譯及評介[M].北京:中華書局,1984.
[4]樓宇烈,校釋.王弼集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1980:137.
[5]張艷艷.先秦儒道身體觀與其美學意義考察[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6]郝大維.從指涉到順延:道家與自然//[C]安樂哲,等,道教與生態.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8.
[7]呂巖,釋義.呂祖秘注道德經心傳[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26.
[8]劉笑敢.老子古今:五種對勘與析評引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180.
(責任編輯:李金龍)
中圖分類號:B2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 4225(2016)03- 0005- 08
收稿日期:2016- 01- 13
作者簡介:張艷艷(1978-),女,山東濱州人,文學博士,汕頭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先秦儒道身體觀的美學意義再考察”(10CZX049);廣東省高等學校優秀青年教師培養計劃“先秦環境美學思想研究”(Yq2013075);汕頭大學“基督教、生命教育與宗教文化”研究專項資助(STUCCS2013-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