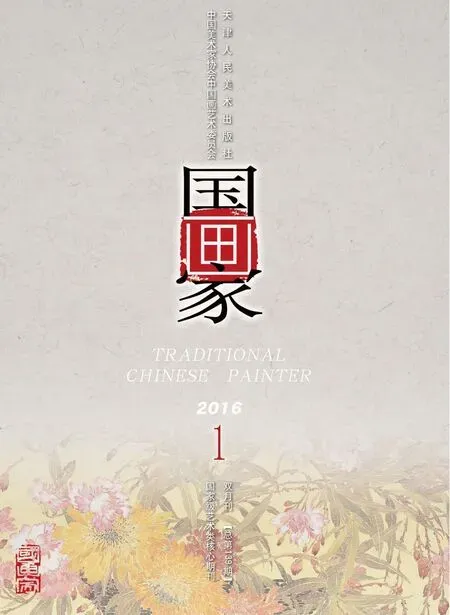從“河山紀行”太行篇談當下山水畫寫生熱問題
璞者
?
從“河山紀行”太行篇談當下山水畫寫生熱問題
璞者
太行山縱貫中華大地八百余里,它重巖疊嶂,林泉掩映,氣勢磅礴,素有“太行天下脊”的美譽,代表著華夏北方山水獨特的雄渾魅力。在古代,它是中原文化與草原文化交會的通道;在現代,它是抗戰時期的主戰場,凝聚了不朽的太行精神。在美術史上,太行山水孕育了荊浩、關仝、范寬等一代宗師,他們的藝術成就一直影響著后繼者,影響著今天的中國畫壇。此次由杭州木工堂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贊助開設的“河山紀行”欄目,就將視野投向了太行山。
近年來,全國各地來太行山寫生的院校及畫家可謂人數眾多,太行山也成了寫生的熱點,對推動當下山水畫壇寫生熱起了相當大的作用。應當承認,在此番寫生熱潮中,的確也出現了許多優秀的寫生作品,把寫生的難度和學術水準提高到一個新層面。但是,大家也認識到,在這股寫生熱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使得本該正常的寫生卻顯得不那么正常。在許多人特別是初學或初入畫壇者的觀念中,似乎誰要是不寫生或不會寫生就不是山水畫家似的。在這樣的行動與思維推動下,又形成了唯寫生才能論山水畫、唯寫生才能論創作的不良傾向,寫生似乎成了中國山水畫的代名詞,寫生又似乎可以代替臨摹,可以代替創作,可以代替中國山水畫學習,成為中國山水畫的“總代理”,并且這種唯寫生論論調目前仍有繼續蔓延之勢。更為麻煩的是,我們的寫生觀念和把握方式,大多是受了西方繪畫的影響,潛意識中的寫生觀是立足于西方的。而以西方繪畫寫生觀的立足點和以西方繪畫的觀察方式所畫的寫生,往往會與中國山水畫的觀物方式和把握方式產生齟齬,最終對中國山水畫的語言表現有多大推進就成了問題。因為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從學習外語中尋求漢語自身的全面發展。
西方的寫生是學習西方繪畫的入門基礎,而中國繪畫的入門基礎則是臨摹,雖然西方繪畫也有臨摹這個環節,但重點是在寫生。西方繪畫的寫生是從現實寫生中尋求此時此地解決問題的辦法,中國山水畫的寫生則是進一步印證古人畫法和法式與自然的和諧關系,進而以陰陽、虛實、剛柔等文化道理,讓傳統的筆墨活起來,完成書寫性靈的課題。
對西方繪畫來說,學習繪畫直接從寫生開始也未嘗不可,而中國山水畫則舍臨摹無由入門。沒有對傳統的深入體悟,所謂的寫生只是徒有形骸的輪廓而已,無法深入到用中國畫造型結構和皴法語言去表現的層面。看來,寫生對東西方繪畫都很重要,只是著重點有所不同,中國繪畫是沒有高水平臨摹基礎的寫生就沒有多大意義,而西方繪畫是沒有高水平寫生基礎的創作也沒有多大意義。當下中國山水畫的麻煩是把寫生當成了學習入門處,畫家、學生的熱情都集中在寫生這個關節點上,從而忽視了對傳統的學習和把握。
中國山水畫寫生,大致分為四種類型。第一種是將傳統山水畫的造型結構形態通過寫生向現實結構與形態轉化,把過去傳統的變為當下應用。第二種是對所到之地、所見物象用鋼筆或鉛筆之類,進行寫生素材的收集,以備日后創作之用。第三種是用水墨直接對景寫生,此類寫生在藝術水準上就要求高些,畫家的筆墨功夫會在寫生作品中顯現出來。第四種是在對傳統、對寫生已全無問題的前提下,悟對山川進行觀察,體會自然山川的陰陽、虛實和剛柔,體會大自然內在的生命意圖,不拘于形象的記錄,而是心識目記、了然于心。
應該說,上述四類寫生方法,所解決的問題是有區別的,是一種相對完整的山水畫寫生訓練,其目的仍然是為以后的創作打下堅實的基礎。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許多山水畫家只是對水墨寫生情有獨鐘,對其他的寫生訓練方法全無興趣。實際來說,水墨寫生并不簡單,它已超出收集素材的功能,是畫家對傳統認識和寫生能力以及筆墨把握的試金石。在近年的寫生熱中,我們的確看到了許多高水準的寫生作品,山川形質、筆墨韻味都有著絕佳的表現。不過,我們也要指出,水墨寫生雖然有著相當的難度要求,但它也最易“糊弄”人,許許多多傳統功夫很弱的畫家就愛畫水墨寫生,畫不出結構了就留空白是為用虛,畫亂套了反復遮蓋是為積墨,畫得不像中國畫了就說中西借鑒,畫得軟弱無力就說松靈淡逸,水墨寫生成了遮蓋功夫欠佳的“萬金油”。誰都可以畫兩筆,誰都可以涂幾下。
如此一來,我們就把水墨寫生從完整的寫生訓練中孤立出來,似乎不會寫生就不會畫中國畫了,中國山水畫寫生就在這樣的情形下出現了偏差。從大的方面,我們把寫生從臨摹、寫生、創作的鏈條中孤立了出來,進而又把水墨寫生從各種功用方式的寫生中孤立出來,形成了當下山水畫寫生的畸形發展,也影響了中國山水畫的健康發展。
此次參加“河山紀行”太行寫生活動的畫家們,雖然對寫生都有著自己的理解,也有著自己的寫生方式,但都認識到不能過度夸大寫生在中國畫創作中的作用,寫生是一個重要的環節,但不能全盤代替,更不能凌駕于臨摹和創作之上,更不能以寫生代替中國山水畫的學習。這一點,我們從他們的山水畫作品中就能有所體會,體會出他們從寫生中生發出的創作激情和對自然山川的熱情,體會出他們對山水筆墨表現的純化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