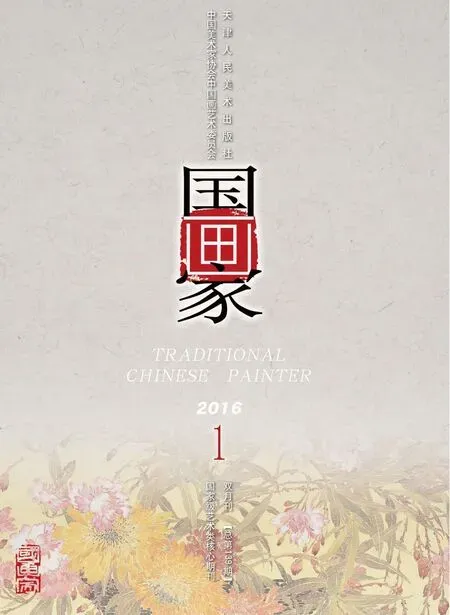中國道教和俄羅斯東正教的繪畫藝術
李一帥
?
中國道教和俄羅斯東正教的繪畫藝術
李一帥
在璀璨的中國歷史中,道家思想是集社會、人生為一體的思想。道教是道家思想的神化形式,道家思想自然發展成了宗教體系,道教也成為發源于中國本土的宗教。不管道教還是佛教,都講究參禪悟道的靜修方式,相似的是,在東正教中也存在靜修主義。儒家也是中國千年文化的精髓,儒家學說更傾向于一種倫理學說,道家學說似乎更形而上,更具有宗教性。道家思想中所建立的中國之“道”,是一種通達自然的態度,其精神的自由解放達到至樂和天樂。《淮南子·修務訓》有道:“故為道家,皆托之于神農、黃帝,而后能人說。”如果遵循此說法,把黃帝尊為道家鼻祖,道家思想的起源可謂源遠流長。
俄羅斯的國教東正教是基督教三大分支之一,在信奉東正教之前斯拉夫人長期信奉多神教:太陽神、風神等等。公元4世紀,君士坦丁堡成了羅馬帝國的國家教會首都,直到11世紀東西教會的分裂,徹底形成了東羅馬正教會。15世紀,羅馬帝國因君士坦丁堡戰役敗亡,君士坦丁堡成為奧斯曼帝國首都,改名為伊斯坦布爾。當今以希臘正教會和俄羅斯正教會為首的東正教會體系確立。在公元988年,時任大公的弗拉基米爾派特使赴希臘找到了他們的國教——東正教,并以自己受洗的方式宣布東正教在斯拉夫土地上的確立。“俄國人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苦修主義,也就是仿效基督的貧窮、溫順和愛,認為這才是得救的道路。”[1]
為何把道教藝術和東正教藝術做對比?道家能代表中國人的心性,這種心性具有民族特征,而我們從俄羅斯的文學、繪畫中可知東正教是他們的精神傳統的基礎,這種精神傳統能代表俄羅斯的民族特征,把兩種藝術做對比,反映出的是兩個民族的精神特征的異同。和中國道家思想講的靜修不同,俄羅斯更講苦修,中國思想中講的是飄遠,那么俄羅斯思想中講的則是悲切,這些思想中的特點都反映在兩個國家、兩個民族的繪畫特點當中。宗教影響繪畫,而繪畫中的宗教實際上同宗教本身具有同樣的功能,即體現人的寄托和理想。
道教藝術受道家思想影響,從宇宙精神這一本質上去設定美,從宇宙精神與人的精神的對話、交流、融合中去確定美,這不同于東正教的美學基礎。東正教把美理解成崇高的東西,比如:“在民間壯士歌中贊嘆勇士的美和體魄,欣賞神話英雄的勇敢、智慧和幸運,為堅毅精神的美和‘圣徒’的道德面貌所傾倒。”[2]而在道家思想中的美,更講究“和”。《樂記》說:“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莊子·知北游》稱:“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世界上最美的人,在道家那里為“真人”“圣人”和“神人”,其精神是“以天合天”,美就在于“與道同體”。
據記載,“《太平經》有《乘云駕龍圖》《東壁圖》《西壁圖》。《乘云駕龍圖》有天尊、仙宮、仙童駕龍在云天遨游的形象”[3]。也就是說,早在東漢時期,就出現了和道教相關的繪畫。在公元3—4世紀,東正教還沒有傳到俄羅斯,但是東正教藝術已經在拜占庭開始繁榮,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建造了氣勢恢宏的索菲亞圣母大教堂,被視為當時最輝煌的藝術典范。
首先,我們從“圣人之像”來看道教與東正教的藝術。道教中的“圣像”要從《老子化胡經》說起,《老子化胡經》著于西晉惠帝時期(290—306),這部經書曾經引起了道教和佛教之間的激烈沖突,唐高宗、中宗都曾下令禁止。起因是天師道祭酒王浮每與沙門帛遠爭邪正,杜撰《化胡經》一卷,記述老子入天竺變化為佛陀,教化之事,以謗佛法。后人陸續增廣改編為10卷,成為道教徒攻擊佛教的依據之一,借此提高道教地位于佛教之上。后到13世紀,出現了《老子八十一化圖》,是根據《老子化胡經》繪制,成為老子化胡說在金末元初新的傳播形式。老子的“圣像”是從什么時候出現?現在考證眾說紛紜。據袁宏《后漢紀·桓帝紀》記載,桓帝于延熹年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祠老子”[4],也就是桓帝在位時期(146—167)就可能出現過老子像。藝術史家、芝加哥大學教授巫鴻認為:“自2世紀中期以降,雖然存在廣泛的老子崇拜,但老子像卻僅僅在250至300年之后才出現,在老子像出現之前,‘華蓋之座’被用來象征‘老子的存在和神性’。”在東正教的源頭基督教里,“圣像”一詞起源于希臘語,意思為“形象”“圖形”。在最初的幾個世紀,教會是禁止為圣者畫像的。公元1—3世紀,古埃及開始盛行遺像“法尤姆肖像畫”,“法尤姆肖像畫”主要是用蠟畫法畫在木板上,形象刻畫鮮明生動,用色飽滿,畫法不同于古希臘和羅馬的肖像畫。這種肖像畫應該屬于拜占庭最早期的宗教繪畫源頭。3世紀開始,耶穌基督逐漸從俄耳普斯(古希臘神話中的形象,他的父親是太陽神阿波羅,母親是司管文藝的繆斯女神卡利俄帕。他被稱為音樂之神)轉換為面部修長留著胡子的形象,就是與我們當今看到的中世紀及以后創造的耶穌形象相同。到了10世紀東正教傳入俄羅斯,俄羅斯又開始出現了和拜占庭圣像畫類似,但是又融入了俄羅斯民族自己風格的圣像畫。
《老子八十一化圖》被認為是宋末出現的,“當時《老子八十一化圖》的流傳形式應該有以下幾種:版刻經本、雕塑、壁畫、石刻等”[5]。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傳播力還是相當廣泛的。在《老子八十一化圖》的《第四化-秉教法》中寫道:“夫道不可無師資,教不可無宗主,故老君師玉晨大道君‘靈寶天尊’焉。大道君即元始天尊之弟子也。天尊生億劫之前,為之祖,所以道君為天尊之弟子也。二圣既立,即老君嗣焉。而曰‘老’,處長之稱;‘君’者,君宗之號。以老君先億劫而生,后億劫而長,天天宗奉,帝帝師承,故賜以‘太上老君’之號。三圣相承,千古垂則。且道君、老君,皆具至圣之德,動息合道,豈假師承耶?蓋以圣傳圣,理自玄同。然起教之端,必資授受,為今昔之筌蹄,人天之鴻范也。”圖中三位圣者分別描繪的是元始天尊(玉清)、靈寶天尊(上清)、太上老君(太清),構圖突出元始天尊的位置,因為元始天尊為萬物之主,靈寶天尊和太上老君緊隨左右,護佑元始天尊。三圣者相輔相成,乃是道教中開天辟地的師祖們。
無獨有偶,在東正教繪畫中,也同樣存在表現三位圣者的身影,只是圣者的人物不同。俄羅斯圣像畫大師安德列·魯勃廖夫的《三位一體圣像》是15世紀俄羅斯宗教圣像畫的杰作,這幅作品畫于1423年左右,是俄羅斯宗教畫中第一次出現的和諧而有抒情意味的形象和畫面,描寫的是《圣經》中天父向亞伯拉罕顯圣而化成的三位天使的形象,從構圖上看同《老子八十一化圖》的《第四化-秉教法》相似,都是三位圣人達成三角的穩定結構,突出中間一位,這幅畫在色彩的處理上,以輕巧、柔和的中間色調為主,色彩明朗、淡雅。魯勃廖夫說,他創作這幅畫的目的是為了讓人們凝望三位神靈的統一,戰勝分裂世界的惡魔和仇恨,這幅畫是東正教三位一體觀念的體現,而三位一體的精髓在于它是一個整體,反對分裂,主張團結,要像三位天使一樣堅固地融為一體。
道教藝術中還有永樂宮壁畫可以算是中國古代壁畫中的經典,也是世界繪畫史上罕見的巨制,其繪畫目的是為揭示教義和感召人心。整個壁畫共有1000平方米,分別畫在無極殿、三清殿、純陽殿和重陽殿里。三清殿的《朝元圖》被譽為是永樂宮壁畫中的重中之重,表現的是玉皇大帝和紫微大帝率領諸神來朝拜元始天尊、靈寶天尊、太上老君的情景,也就是原來分散的諸神全都集合起來朝拜最高主神了,反映了道教的完整體系,而近三百身群像,行色各異,動靜相宜,疏密有致,在變化中達到統一,在多樣性里展現了和諧。壁畫中,帝君的神情多肅穆,玉女端莊秀麗,武將披金戴甲,高士風度儒雅,面目表情描寫得十分生動。以壁畫的南墻為例,在兩側的青龍白虎星君引導下,神龕后的三十二天帝為后護衛,從東、西、北三面及神龕左右側諸神圍繞八位主神依次排列,氣勢恢宏的是兩側的人物分三至四層排列開來。其中涉及的諸神眾多:南極長生大帝(南極)、東極青華太乙救苦天尊(東極)、中宮紫微北極大帝(紫微)、勾陳星宮天皇大帝(勾陳)、玉皇上帝(玉皇)、三官(天、地、水)、四圣(天蓬、天酞、翊圣、真武)、八卦、五行、二十八星宿等等。
在俄羅斯東正教教堂,宗教壁畫種類繁多。以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報喜教堂為例,報喜大教堂是擁有俄羅斯最古老風格的圣像壁畫之一的教堂,安德烈·魯勃廖夫也參與了這座教堂圣像壁的繪畫。墻壁上有5排圣像,自下而上來看:“第一排是本地圣者像,即最受尊崇的莫斯科圣者像;第二排是德厄西斯(眾使徒祈禱像);第三排是節日圣者像,即教會規定的紀念耶穌基督和圣母的東正教十二大節圣像;第四排是先知圣像,圣母圣嬰位于本排中心位置;第五排是祖先圣像,新約中的三位一體圣像位于本排中心位置;圣像壁的頂部中心位置插著一個十字架,它象征著耶穌基督被釘死的地方——各各他。第六排圣像壁,也叫補充圣像壁,畫面內容是耶穌基督受難歷程,或其他與此相關的傳說故事。”[6]我們從東正教的圣像中,找到了《朝元圖》的影子,一排排人數眾多的序列,人物都是各自宗教里的重點人物,《朝元圖》里有各種星神,報喜大教堂里有各類天使,他們存在于教義中,同時也被書寫于歷史上諸多文學作品之中。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宗教繪畫是相似的,它們的作用都是感召人心,起到教化作用;強調教義,用繪畫的方式讓教徒理解教義,同時加深印象。它們來自不同的國家、區域,在交通不發達的過去,不太有可能得知彼此宗教的訊息,但是當它們被揭開于這個時代,放于歷史之中再去審視,連構圖都驚人的相似:同樣的二維圖畫,同樣的三角構圖,同樣的繪制形式。但是,它們又是如此的不同,因為它們產生于不同的宗教、文化背景,中國的“‘道’具象于生活、禮樂制度。道尤表象于‘藝’。燦爛的‘藝’賦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給予‘藝’以深度和靈魂”[7]。可以說,道決定了中國繪畫和中國傳統藝術的精神特質和美學觀念。受道家思想的影響,亦受老莊思想啟示于“道”的繪畫藝術性的反省,還是東漢末年、南北朝時期。繪畫進入道家精神之內的客觀世界,常是自然世界。所以中國繪畫中更喜歡繪畫自然之境。俄羅斯繪畫創作理念是圍繞穩坐高臺的“正神”上帝的偉大與榮耀開始,畫家描寫的自然不是顯出自然的偉大與美麗,而是歌頌耶和華的神力與偉大,因為自然的一切都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安排的(包括繪畫)。描寫事件、四季、山川、曠野、風暴、雷聲都旨在稱頌上帝的榮耀,畫筆主要是為了表現上帝,許多體現東正教意義的畫都把自然視為上帝的化身來歌頌。
綜上,中國傳統繪畫的根系深扎在中國社會和中華文化的沃土之中,中國繪畫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獨特的風格和審美情趣以及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體現了悠遠的東方神韻。同樣,在俄羅斯畫壇上,畫家通過油畫的藝術形式所表現俄羅斯民族信仰的追溯,是我們在探討跨文化審美比較中值得注意的。兩國繪畫可謂是“外師造化,中得心源”,這“造化”和“心源”是合二為一的精神顯然,是“以天合天”的精義所在,是俄羅斯畫家向往的天堂氣息,是中國畫家夢寐的天籟氛圍。如果說中國繪畫是作者內省的寂照與至美,那么俄羅斯繪畫就是畫家心靈的救贖和寄托,中俄繪畫的藝術精神是朝霞與彩虹的比較,二者是悟道與祈禱的不同心祭。
注釋:
[1]華萊士《俄羅斯的興起》,葉倉譯,紐約:紐約時代公司,1979年,第96頁
[2]奧夫相尼科夫《俄羅斯美學思想史》,張凡琪、陸齊華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14頁
[3]劉仲宇《道教對中國繪畫影響述評》,1988年Z1期宗教學研究,第93頁
[4]晉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后漢紀校注》卷二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11頁
[5]胡春濤.博士論文《老子八十一化圖研究》,第18頁
[6]Т.С.格奧爾吉耶娃《文化與信仰》,焦東建、董茉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2年,第124頁
[7]宗白華《藝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168頁
(作者系浙江大學美學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