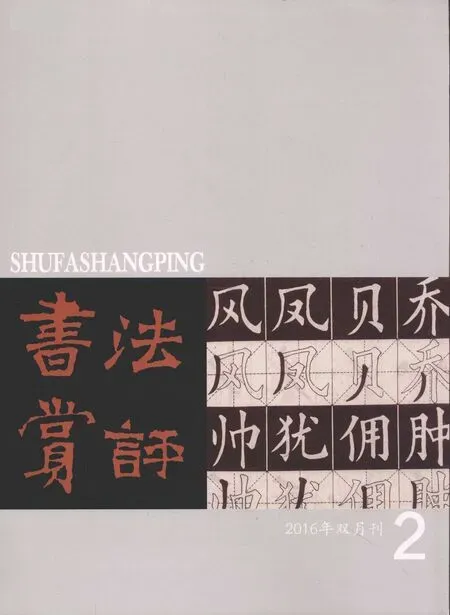從草書史立場看當代草書的創變空間
■李亞杰
?
從草書史立場看當代草書的創變空間
■李亞杰
草書史上,“二王草書、唐代狂草、黃庭堅草書、晚明狂草以及民國碑系草書是最具學術價值的五種創變形態。作為草書史嬗變的五個轉捩點,其價值意義不僅是風格創新問題,同時也是歷史空間拓展問題。從書法史的高度去分析這些現象,通過對草書流變的梳理,明確當代草書的創變空間,才能彰顯草書創作的學術地位與歷史意義。
一、草書史的嬗變
1、經典的“二王”帖系草書
魏晉時期是一個分水嶺,因為自魏晉始,風格取代書體成為書法發展史的基本趨向與理想,并與魏晉以前非自覺的書法史作了徹底的劃分。在此轉型過程中,王羲之、王獻之作為草書新體風格的創立者,把漢代以來草書的無序與野俗進行理性的書體規范,初建了草書的法度,提升了草書品味。“改變了來自民間書法小傳統的草書境遇,確立了草書的文化完型。” (姜壽田 《羲、獻妍媚風格辨》)而“二王”之間又有差別,張懷瓘在 《書儀》中說:“父之靈和,子之神駿,皆古今之獨絕也。”沈尹默在 《二王書法管窺》中說:“若大王是內擫,小王則是外拓。試觀大王之書,剛健中正,流美而靜;小王之書,剛用柔顯,華因實增。”王羲之草書筆法老練、結構精嚴,把嚴肅與飄逸、法則與自由、理智與情感和諧地熔于一爐,自然混成,開啟了后世“中和”的書法審美類型。王獻之將王羲之的“中和”型草書發展成為一種詭譎奇肆的表現型草書,把王羲之內擫筆法轉化為外拓的大草筆法,并且成為唐代狂草的核心筆法,筆致放縱,圓通而奔逸。“二王”草書確立了中和與表現的兩大派系,是經典帖系草書的濫觴,是歷代書家汲取養分的源泉。
2、理性的唐代狂草
盛唐張旭、懷素為代表的草書家進一步深化“二王”筆法,尤其是王獻之的外拓筆法,是表現型草書的推進。二人都有當眾揮毫的史跡,借助酒性,去破壞理性的束縛,在草書史上留下了瘋狂的印跡,熊秉明稱之為“狂醉派”。但是二人雖然以“顛”“醉”名世,事實上二人狂草卻法沒有突破法的限制,書寫極具理性。劉熙載《書概》評旭素草書云:“旭、素書可謂謹嚴之極,或以為顛狂而學之,與宋向氏學盜何異?旭、素必謂之曰:若失顛狂之道至此乎?”他們的狂草雖風格迥異,而其用筆都十分謹嚴,形態雖狂,狂而不怪。他們的草書在連續不斷的筆觸中,完全可以清晰地尋檢出各個獨立的點畫,在高速的運筆過程中,不離法則而隨意驅動法則。二人草書的“表現”性是外在的,而由于對草書技法的理性把握則是內在的。所以,二人把草書推到了理性的巔峰,也可稱為表現的理性化。
3、黃庭堅理性兼抒情的哲理型草書。
宋代的草書高峰,完全是由黃庭堅個人造成的,筆法與空間營造是黃庭堅超越旭素,開拓草書風格的路徑。黃庭堅草書筆法一反唐代狂草流暢圓融的使轉,點畫極力向外拓展,如長槍大戟,運筆漸行漸按,形成“抖擻”筆法,遲澀而復雜。在空間營造方面,他有意放棄線條的連續而著意于空間的擺布,單字內部空間與字字銜接頗具匠心。如果說,唐代狂草講求筆勢的奔放,連綿不絕,黃庭堅則追求空間結構體勢的挪騰與銜接。宋人論書強調“意”,強調書卷氣,因為宋代書法家同時是詩人、散文家、畫家、政治家。蘇軾說:“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反推求。”黃庭堅也說:“幼安弟喜作草,求法子老夫,老夫之書本無法也。”所以,黃庭堅草書“無一畫之違于理”,但又“意態橫出,不主故常”,充分說明了其草書的理性的控制與“尚意”的追求。而且黃庭堅受禪學思想影響甚深,草書中蘊含豐富的哲理與禪機。所以說,黃庭堅的草書是理性兼抒情的哲理型草書。
4、晚明的表現型狂草
因為社會文化背景的變化,晚明草書大放異彩,出現了以倪元璐、徐渭、傅山等為代表的狂草書家,把旭、素草書中的表現主義成分推向高峰,為了表現而表現,成就了真正的表現型狂草。他們的草書雖然面目各異,但風格深處保持十分相似的基因:焦慮、叛逆、狂傲、掙扎。就個性而論,倪元璐草書表現出峻刻、偏激、壓抑的情緒,用筆圓勁爽利,字法風格強烈;徐渭草書將一己的悲憤盡情宣泄,故意的反秩序、反統一、反和諧,在項穆所謂“醉酒巫風”的筆致中顯示出憤世嫉俗的情緒;傅山草書求“丑”求“拙”,所謂“寧拙毋巧,寧丑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直率毋安排。”無所謂法,一任自然,大氣磅礴,雖有扭曲過度之嫌,但絕無一點兒塵俗氣,外表飄逸,內涵倔強。當然,晚明狂草由于之前草書技法的極大成熟,明代“心學”哲學思潮以及士人心態的大自由、大解放,使得晚明草書家成為古代草書史的殿軍。表現型狂草也因不可預期為后人留下諸多創新空間。
5、民國碑系草書的兩個極致
清代由于碑學盛行,帖學式微以致草書創作衰退,碑學背景下的草書創作異常艱難。引碑入草的創作理念經過鄧石如、趙之謙等人的多次嘗試,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隨著碑帖融合的進一步發展,于右任的碑系草書探索才取得一定成功。但其探索終止于小草領域,并把小草推向標準化,也就是推向了理性書寫的極致,其意義正如旭、素的理性帖系草書一樣,實難超越。章草方面,沈曾植、王世鏜、鄭誦先等人的章草實踐為王蘧常章草的形成提供了創變思路。王蘧常用筆以中鋒為主,側鋒為輔,筆畫厚實凝重,結體雍容大方。其碑與帖的互用,終于蛻變出他的章草風格。“他將凝重的北碑與流暢的章草有機結合起來,并且有效地解決了章草的碑化問題。”(楊吉平 《二十世紀草書四家評述》)是民國以來唯一可以作為取法對象的草書家 。如果說于右任把碑系小草推向了理性的極致,那么王蘧常則把碑系章草推向理性的極致。
二、當代草書的創變空間
梳理草書發展中的轉捩點,理清草書發展基本脈絡的同時也能明晰創變的可能性。結合當代草書的創作現狀,筆者分析了四種創變的可能:古典式草書、表現型狂草、碑系大草、表現型章草。當然,所列空間并非創變的唯一途徑,只是這些領域有足夠大的創變空間,有潛在的無限可能性。
1、古典式草書
為了區別“二王”及“二王”之后的草書體系,本文姑且把在“二王”經典草書形成之前的草書統稱為古典式草書。“二王”經典草書是永恒的取法對象,現代以來沈尹默、吳玉如、潘伯鷹、白蕉等在“二王”草書的創作領域做出重要探索后日漸衰微。當代“二王”草書創作又陷入偏執狀態。創作群體規模大甚至呈泛濫狀態,但面目趨同,取法過于單一,這是對“二王”古法的誤讀并且機械強化而形成的一種唯技術論風尚,是一種“偽二王書風”。在“二王”草書創變日益狹隘的同時,古典式草書卻無人涉及,這將成為當前草書創變的一個重要方向。古典式草書由于其原始性、初發性、朦朧性極具生命力與想象空間,而大多逸筆草草,結構散漫,有一定的整合難度。所以,古典式草書創作,一方面需要對草化簡帛、草隸書、草化銘刻書、樓蘭殘紙等原始草書進行筆法的提純并且有機糅合“二王”草書經典筆法尋求筆法新創;一方面又要對各類書風歸類比較,深入分析應該繼承什么,摒棄什么,不致于糟粕與精華混為一談。若能探索成功,古典式草書在草書領域將是一個全新的創作路徑。
2、表現型狂草
晚明草書家把狂草提升到相當高度,但并沒有終結。傅山之后,現代書法史上出現了毛澤東與林散之兩位表現型狂草大家,并且二人的草書都在晚年臻至化境。晚年毛澤東狂草,以 《七律·長征》詩卷為代表,此卷使筆如疾風暴雨,飛騰迭宕、峻健壯觀、字體大漲大落如河水湍急,一瀉千里,章法如行軍征戰,氣勢恢宏、情緒激昂,有來勢不可擋,去勢不可遏之勢。毛澤東狂草根基在旭素,表現性則超越晚明諸家,在現代草書史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當然與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博大的胸襟、恢弘的氣勢,非常人能達性情不無關系。與毛澤東的恢弘不同,林散之草書表現的是一種蒼勁清潤的虛靈氣質。其草書的創變基于筆法與墨法的獨特,林散之以漢隸筆法入草,線條潑辣滯澀、沉郁頓挫,筆勢多變。墨法得自黃賓虹傳授的畫法用墨,林散之移用于書法,其用墨往往拖泥帶水、模糊凄迷、帶燥方潤、將濃遂枯,于無墨中求筆,在枯筆中取潤,獨到的墨法水法和玄妙的用虛用白,使得林散之草書散淡玄遠,贏得了“當代草圣”的桂冠。
雖然,二人的草書各有千秋,但留給我們的空間卻很大。應該說,毛澤東走到了表現化高峰的邊緣,但草書技法有待提高;林散之草書整體氣象偏向柔媚,陰柔有余,陽剛不足,雖以漢碑入草,卻并沒有把碑骨、碑意有機融入草書。二人的這些缺陷給當代表現型狂草留下了很大的創變空間。
3、碑系大草
于右任和王蘧常分別把碑系小草與碑系章草推向理性的極致,碑系大草領域涉足者甚少,因為將團團使轉的大草與棱角分明的魏碑相打通,不論在技術上還是理論上都沒有可資借鑒的原型。相對而言,晚晴蒲華、現代陸維釗、衛俊秀對碑系大草的探索顯得尤為可貴。蒲華以繪畫稱著,書名不顯,其在何紹基、趙之謙碑體行書基礎上進行碑系大草創作,以篆隸、北碑為體,黃庭堅草書為面,厚而不滯,漲墨淋漓。但其書作夾雜大量行書,碑系大草面目不凸顯,嚴格來說蒲華屬于碑系大行草的范疇。陸維釗先生以篆隸名世,草書并非其所擅長,他筆下的草書結體倔強,食碑未化,生硬欠自然。衛俊秀碑系大草面貌比較純粹,他將傅山狂草與北碑的古拙剛勁熔鑄一體,書風沉著,大氣盤旋。但是筆者認為衛俊秀只是在精神氣質上逼近碑系大草,而在技法層面,比較草率,只見“氣”不見“法”。
所以,碑系大草的創變難度在于:將碑學系統與草書系統在筆法、字法、章法上的二級分治混化無間,將碑學古質精神與草書寫意精神對接升華。此難題倘若解決,將是草書領域最偉大的成就。
4、表現型章草
作為學者型書家,王蘧常把碑系章草推向了理性的極端,創變余地小。但是,表現型章草卻有無限的創變空間。與王蘧常同時的豐子愷、沙孟海在章草表現性方面的拓展為當代章草嬗變提供了兩個可能發展的思路:一是把章草與畫法結合,把畫法多變的筆觸,皴擦點染的語匯糅入章草,追求活潑爛漫如豐子愷;二是走章草與今草結合之路,把章草的古拙、厚重與今草流動、暢達結合起來,端莊雜流利,剛健含婀娜如沙孟海。但是二人都沒有走向極致,對于表現型草書來說,沒有最高,只有更高。若能沿著二人的方向繼續前行,章草領域將變會得異常輝煌。
三、結語
草書一直是書法諸體中最困難的一種,它對書家主體的學養、才情、技術、心態諸因素要求極高。草書是天才的藝術,不具草書性情與襟抱斷難在草書領域有所作為,故中國書法史上草書大家屈指可數,當代草書創作也最為欠缺。但通過對草書流變的梳理發現草書依然擁有巨大的創變空間,本文所列的古典式草書、表現型狂草、碑系大草、表現型章草遠遠不能涵蓋所有創變維度。如對楊凝式、楊維楨、張瑞圖、黃慎等草書家的開掘依然有空隙。《論語·子張》中講:“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從這個意義上說,草書之道未絕,草書大家必然會涌現,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草書經典也必然會誕生。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作者單位:河北美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