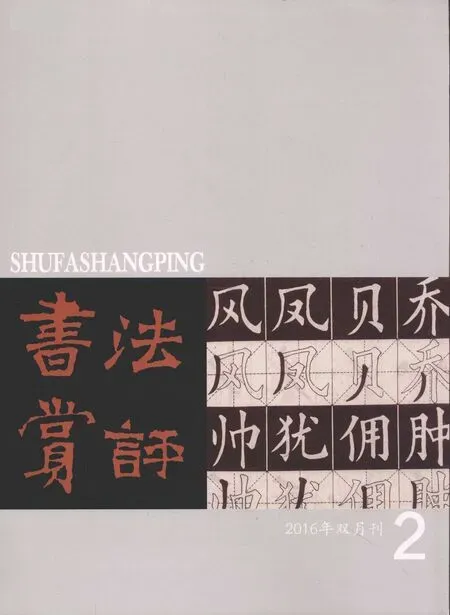驚人的相似
——談館閣體與展覽體
■梁厚能
?
驚人的相似
——談館閣體與展覽體
■梁厚能
近些年來,隨著書法賽事和展覽日趨頻繁,于是書壇催生了一種新體,即“展覽體”,“展覽體”三字無疑也成為書壇的一個熱詞。展覽體,是當今書法展覽機制的產物,這不由使我想起科舉制度衍生的“館閣體”。我將兩者稍作比較,發現竟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體”的含義相似。我們知道,書法的“體”是指書法的樣式與風格,書法樣式有篆隸楷行草,就書法風格來說,書法史公認的有顏柳歐趙諸體,當然也有“板橋體”“瘦金體”“毛體”“啟功體”等之說,它是對某一書法家的書法風格而言的,是肯定性的。能夠稱得上體的,不僅書法風格獨特,而且對書法發展有著巨大的促進作用。館閣體 (明代稱臺閣體),是明清在科舉試場上使用的書體,強調的是方正、光潔、烏黑而大小齊平的共性,千人一面,而不強調書法家的個性。清洪亮吉 《江北詩話》一書記載:“今楷書之勻圓豐滿者,謂之館閣體,類皆千手雷同。”沈括 《夢溪筆談》亦云:“三館楷書,不可不謂不精不麗,求其佳處,到死無一筆是也。”展覽體,目前還沒有一個權威的解釋,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不是指某一書法家的書法風格,而是指一種書法想象,一種共性,或者說是無數書法家的書法風格。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展覽體與館閣體含義的相似之處,一是兩者均不是指書法史上所稱的反映書法家個人風格的“體”;二是兩者反映的是一種書法風格的共性想象;三是都沒有褒義。
產生機制相似。館閣體是中國科舉制度的產物。科舉制度是中國歷史上的考試選拔官員的一種基本制度,從隋朝大業元年 (605)的進士科算起到光緒三十一年 (1905)正式廢除,整整綿延了1300年。在漫長的科舉考試中,曾產生出700多名狀元、近11萬名進士、數百萬名舉人。科舉考試的內容和形式,雖然各朝都有不同的規定,但對應試者的書法要求都十分嚴格。特別是在明清兩代,更是達到了頂峰,以致產生了館閣體 (臺閣體)。評卷關鍵往往在應試者的書法,甚至到了“抑文重字”的程度,字寫得欠佳者,即使滿腹經綸,也會名落孫山。士子為了應試,不得不迎合考官的口味,不得不苦練館閣體,以期一朝奪魁,譽滿天下。現在的書法“國展”,類似于古代的科舉考試。“國展”,是中國書法家協會主辦的全國書法篆刻作品展覽的簡稱,作為我國書法界四年一度最高規格的綜合性展覽,被譽為書法界的“奧林匹克”。自1980年以來,迄今已舉辦了十一屆。每屆展覽所展出的1000件左右的書法作品,遴選自全國幾萬件參選作品,可謂是百里挑一,其競爭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據報道,2015年舉辦的全國第十一屆書法篆刻作品展覽,共收到來自32個省、市、自治區的書法作品42572件,經過嚴格評選,入展作品作者公示名單703人 (其中書法623人,篆刻60人,刻字20人),其中優秀作品作者公示名單42人 (書法37人、篆刻4人、刻字1人)。入展獲獎名單如此之少,而參賽作品又如此之多,可以想見“國展”的巨大吸引力。可以說“國展”是廣大書法愛好者的最高夢想,猶如古代讀書人的科舉考試,一旦入展,特別是獲獎,便一朝成名天下知。“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僅有豐厚的獎金,具備加入中國書法家協會條件,更是奠定其在書壇的正統地位。要想進入“國展”,就必須要適應“國展”的機制,迎合評委的口味,這樣展覽體也就出現了。也像館閣體是科舉制度衍生的產物一樣,展覽體是“國展”機制催生的產物。
技法含量相似。館閣體,其特點是字體方正、光潔、烏黑,大小一律,要求規范、美觀、整潔、大方,寫得就像古代木版印刷體,現在的電腦體。館閣體在技法要求上是特別高的,能夠寫得出一手館閣體的人,必須經過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刻苦訓練。觀看中國歷史上最后一位狀元劉春霖的館閣體書法,一幅書法從頭看到尾,筆筆精到,字字漂亮,幾乎發現不了任何敗筆。再看當下的展覽體書法,其技術含量絕不亞于館閣體,作者均經過了嚴格的技法訓練,傳統功夫個個了得。這筆是王羲之的,那筆是蘇東坡的,或者是趙孟頫的,都能見到古人的影子,有的單從技法來說,還超越古人,“比王羲之還王羲之”。能夠入展獲獎的作品,都經過了評委的大浪淘沙般的層層篩選,亂涂亂抹的拉下了,丑字、爛字、孩兒體、老干體被拉下了,有錯別字的拉下了,文詞不通的拉下了,擺在展廳里的作品,符合了規范、美觀、整潔、大方的審美需求。就是一些篆書、隸書、草書作品里,看似隨意,實則精心摻雜的小楷字,黑字里面摻雜的朱砂字,以及一幅作品堆積幾千字,等等這些都無疑在炫技,有人稱之為“技術密集型”。從技法角度來看,館閣體與展覽體的技術含量,筆者看來難分高下,都是出于技法層面,而不是藝術層面。
書寫內容相似。館閣體的書寫內容是八股文,而八股文就是指文章的八個部分,文體有固定格式:由破題、承題、起講、入題、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組成,題目一律出自四書五經中的原文。八股文雖由士子自己創作,屬于今天所說的原創詩文,但因其范圍狹窄,形式陳腐老套,不能真正的抒情達意。而縱觀展覽體,其書寫內容大多陳腐老套的,不是唐詩宋詞,就是四書五經,以及前賢書論,雖然提倡自作詩文,但精彩的少之又少。
產生影響相似。館閣體書法是書法藝術史的一種特殊現象,千人一面,一字萬同,毫無生機,使書法走向工整化、程式化的極致,它對于書家的才華、性情無疑是一種無形的束縛,是對書法抒發情性本質的悖反,因而成為書法發展的桎梏。館閣體對書法的規范性書寫,技法的基礎性訓練,是有積極意義的,但這種積極意義十分有限,它更多的是負面影響,對阻礙書法發展也是致命的。展覽體是最近幾年才興起的,相對于興盛于明清兩代達500多年的館閣體,其時間尚短,但因當今信息的高度發達,其對書法發展影響之廣、程度之深,已不亞于明清的館閣體。展覽體作為展覽機制下的“新生事物”,它的出現,是書齋文化向展廳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慢生活向快生活發展的必然結果。試想,在數以萬計、堆積如山的參展作品中,在偌大的展廳內,如果不瞬間抓住評委或觀眾的眼球,哪怕你的作品內涵再豐富,作品馬上被評委槍斃,更不用說留下觀眾的匆匆腳步。展覽體,對引領書法走入傳統、走入經典,其意義無疑是正面的,是值得肯定的。但其過度強調形式而忽視內涵,過度強調技法而忽視書家內心的表達,將書法從“藝”的層面帶入了“技”的層面,這無疑是倒退,是對書法發展的阻礙和傷害。
以上找出了館閣體書法與展覽體書法的五大相似之處,有的是形似,有的是神似,這只是筆者的膚淺認識。其實兩者是有很大區別的,最本質的區別是,館閣體是為了實用 (如寫公文),而展覽體是為了藝術;在書體上,館閣體只指楷書,而展覽體包含了篆隸楷行草諸體;在幅式上,館閣體一般較小,而展覽體追求大幅,甚至超大幅;在用紙顏色上,館閣體一般為素色或單色,而展覽體追求的是花色,各種顏色紙都敢用,不惜挖空心思用染色或拼接來達到此效果;在用墨上,館閣體是用黑墨,而展覽體不僅用黑墨,有時還用紅墨、黃墨、綠墨,而且敢于顏色混雜等等。
在明清館閣體盛行的年代,不僅有大量書奴,也有以獨特的風格名世的書法大家,如明代的董其昌、徐渭、張瑞圖、倪元璐、祝允明、王鐸、傅山等;清代的鄭板橋、八大山人、金農、劉墉,鄧石如、康有為、何紹基、趙之謙、吳昌碩等。筆者認為,作為一名真正的書法家,我們不能被展覽體時風牽著鼻子走,要有自己的獨立思考和追求。時代呼喚著創新,書法也將在繼承和創新中得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