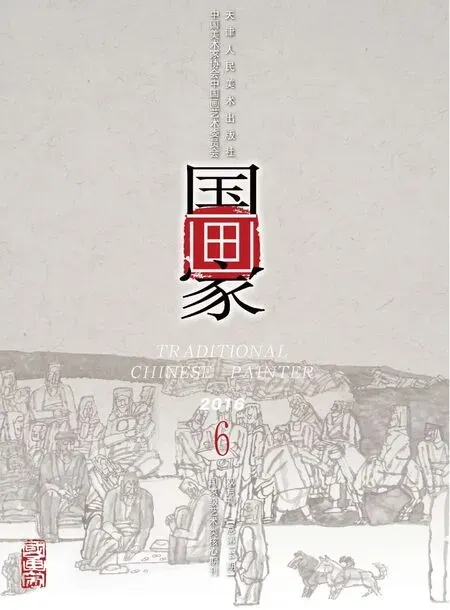中國文人畫淺談
周鐵寧
中國文人畫淺談
周鐵寧
何謂文人畫?近現代美術史家陳衡恪先生在其《文人畫之價值》一文中開篇道:“即畫中帶有文人之性質,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畫中考究藝術上之功夫,必須于畫外看出許多文人之感想,此之謂文人畫。”1
欲理解文人畫,必先了解文人。國學大師錢穆先生說:“有文人,斯有文人之文。文人之文特征,在其無意于適用。”
中國封建帝制時期,“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大批有著人文修養、富有創造性和思想性的讀書人前仆后繼,以文弱之軀投入到無限熱情的科舉考試之途。他們通達順暢之時,自然能夠進入整個國家行政系統之內,實現自己兼濟天下的宏圖偉業,但是學而優則仕于龐大的泱泱中華官僚系統中畢竟是少數的。對于大多數的讀書人來說,嵌入帝國官僚的內部仍然是一個極為艱難的過程。但是不可否認的是,自隋朝開始的科舉制度造就了一個在之后中國浩浩蕩蕩的歷史進程中極為重要的階層——“文人士大夫階層”。
人類的情感自古便有許多種方式寄托。《詩經》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2但是對于文人士大夫來說,這一切還遠不足以表達他們的至高追求,這就是老莊思想中的“道”,是一種可以臥而游之,可以無盡玩味的摹山范水。在他們眼中“以形寫形,以色貌色”,窮神變,測幽微,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借天地萬物淘泳乎也,才是更為經常的表達情感的方式。所謂“畫者,文之極也”。文人士大夫進入繪畫領域,不僅僅極大地拓寬了繪畫的題材,豐富了繪畫功能,也使得存乎勸誡的繪畫逐漸成為個人怡情悅性、抒懷明志的手段。這樣文人士大夫不僅獲得了極大的精神慰藉,同時也為中國的藝術審美開啟了一片燦爛的天地。正是由于文人對繪畫功能的改觀,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文人士大夫投身于繪畫領域。
追根溯源,最早明確提出文人畫的是宋代大文豪蘇東坡。《又跋漢杰回山》蘇軾品評宋子房畫時曰:“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許便倦。漢杰,真士人畫也。”3蘇軾以有無“意氣”作為文人畫和畫工畫二者差異的關鍵,所謂意氣者,神韻者也。
以蘇東坡為代表的文人畫理論主張當然不僅僅是他個人藝術見解和美學思想的單方面認識,其實也是整個宋代多數文人畫家藝術的貼切表達。“南北兩宋,文運最隆,文家、詩家、詞家彬彬輩出,思想最為發達,故繪畫一道亦隨之應運而興,各盡其能。歐陽永叔、梅圣俞、蘇東坡、黃山谷對于繪畫皆有題詠嘆,皆能領略;司馬君實、王介甫、朱考亭在畫史上皆有名,足見當時文人思想與繪畫相契合。……至文湖州竹派,開元明志法門,當時東坡識其妙趣,文人畫不僅形似于山水,無物不可寓文人之興味也明矣。”4宋代的文人畫奠定了后世文人繪畫的最基本的底色,即使在文人畫藝術理論成就和繪畫創作鼎盛的元代及其之后,我們大都可以看到宋式文化的強烈的審美情懷,和對文人意識強烈的感染力。明人王世貞說“文人畫起自東坡,至松雪敞開大門”。元以前的文人畫運動主要表現為理論和美學概念上的鋪墊。而元入主中原,傳統文人士大夫失去了向上攀升的救命稻草,于是他們隱居山林,優游林下,以畫自娛,運筆丘壑,妙而不工,聊寫胸中逸氣,雖是無意,卻佳作迭出。“不管六朝興廢事,一樽且向圖畫開。”“飽則讀書,饑則賣卜,畫室室竹,飲梅花泉,一切富貴利達,屏而去之。”元代文人對繪畫的無意選擇,正是在王朝異代之際,文人士大夫游心于藝,托身于畫,在“獨行,獨住,獨坐,獨臥,獨吟,獨醉,獨往,獨來”的人生大寂寞中體會天地萬物大道的絕佳途徑。
“不落棲經,謂之士氣;不入時趨,謂之逸格。其創制風流,昉于二米,盛于元季,泛濫明初。”5明清文人繪畫更加高速發展,一躍成為繪畫主流。人品、學問、才情、思想四要素完美具備,詩書畫印四體兼備的綜合性,這也成為中國文人繪畫區別于西式繪畫的極大差異。
文人畫在長期的發展中,自然形成了一套自己獨特的審美規范和技法標準,以筆取氣,以墨其韻。虛實相生,疏密相用。題材雖不過梅蘭竹菊、高山流水、漁隱歸棹,這些大自然中平常的景致卻都是文人士大夫內心或者豪邁或者抑郁,表達自身清高文雅,不拘時尚的絕佳載體。正如清初花鳥畫家惲南田在《南田畫跋》中所言:“其筆墨,則以逸宕為上,咀其風味,則以幽淡為工,雖離方遁圓,而極妍盡態,故蕩以孤弦,和以太羹,憩于良之上,泳于穴寥之野,斯可想其神趣也。”6
及至近代以來,西方的堅船利炮打開了緊閉的大門,中國人似乎從天朝大國的夢中驚醒,“落后就要挨打”似乎成為懸掛在每一個中國人頭頂之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生存還是毀滅,這是個問題。于是,開明之士高歌猛進,從技術層面到制度層面都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自強運動。伴隨著時代的不斷演進,最后一個封建制帝國清王朝的落幕,使得中國文人士大夫階層永遠失去了賴以存在的最堅實的土壤。對于中國文人畫來說,失去創造主體——文人的文人畫是否還能夠稱作“文人畫”?文人畫是否應該被更為精細、更為寫實的西洋繪畫所取代,似乎成為那個大時代極其重要的選擇。
但是從更為長遠的視角來看,文人畫是中國幾千年傳統河流上不斷流淌的河流,它在不斷向前流動之時,也在不斷地接納其他水流以補充和更新自己。社會的變革,歷史進程的演進,傳統意義上的文人或早已不存,但傳統文化不是一潭絕望的死水,中國人文精神仍在不斷地向前發展,中國藝術一脈相承的“寫意”精神仍然存在,所以新時代文人畫依然是一個真實的存在,比如對“新文人畫”不斷追尋正是對傳統文人繪畫的繼承和發展。雖然在追尋的過程中免不了伴隨著爭議和誤解,但這也都是正常的。
山水畫家黃賓虹先生認為“凡是能蓄道德,能文章,讀書余暇,寄情于畫者,就可以列入文人畫家的行列”。所謂“士夫之畫,渾厚華滋,秀潤天成,是為正宗。得胸中千卷之書,又能泛覽古今之跡,錘爐在手,矩矱從心。展觀之余,自有一種靜穆之致,撲人眉宇,能令睹者矜平躁釋,意氣全消”7。
“一味霸悍”之潘天壽則更為寬容,認為“畫家須重視內心修養,游歷名山大川,畫無有不氣韻,然畫有氣韻,不應定其人品格高、思想好、學問優也”8。
其實他們都意識到文人畫的真正精髓在于文人對繪畫所持有的那種出入不物、得失隨緣的價值態度,并不會因為傳統文人畫歷史背景的脫落而終止其發展,所以文人畫始終是個理論問題,而不是社會問題。
陳師曾認為文人畫首精神,不貴形式,故形式有所欠缺,而精神優美者,仍不失為文人畫。“所謂不求形似者,其精神不專注于形似,如畫工之鉤心斗角,惟形之是求耳,其用筆時,另有一種意思,另有一種寄托,不斤斤然刻舟求劍,自然天機流暢耳。”9
“中國藝術的妙境,就在那形式之外妙香遠溢的世界中,形只是走向這個世界的引子”。因此無論是舊時代的文人士大夫,還是新時代的讀書人,文人畫作為中國一種獨特審美的繪畫樣式,都是創造主體的藝術家對人自身存在和他所生存環境的一個審美觀照,都是創造主體的中國人借以表達內心真實情感——喜怒哀樂的視覺呈現。因此在新的形勢之下,筆墨當隨時代,文人畫繼承與創新,并不是一句扯大旗幟的美好口號,更是迫切的現實問題。近些年中國藝術界也興起了對傳統文化回歸的強勢勁頭。對傳統文人繪畫,包括對吳門、浙派、四王、四僧的再認識,都在某種程度上提示今天的我們,雖然當代中國藝術走向現代,走向世界,多元文化爭鳴、發展的態勢已是不可逆轉,但是作為當代中國藝術家如何從人文傳統中汲取更多、更好的基因和元素,從筆墨技法到精神內涵等各個層面豐富中國繪畫仍然是一“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艱苦卓絕的過程。
注釋:
1.陳師曾著譯:《中國文人畫之研究》,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年。
2.王秀梅:《詩經》,中華書局,2006年。
3.周積寅編著:《中國歷代畫論》,江蘇美術出版社,2013年。
4.周積寅編著:《中國歷代畫論》,江蘇美術出版社,2013年。
5.惲壽平著,張曼華注解:《南田畫跋》,山東畫報出版社,2012年。
6.惲壽平著,張曼華注解:《南田畫跋》,山東畫報出版社,2012年。
7.趙志鈞編:《黃賓虹論畫錄》,浙江美術學院出版社,1993年。
8.徐宇:《文人畫淺說》,藝術科技,2014年第12期。
9.陳師曾著譯:《中國文人畫之研究》,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