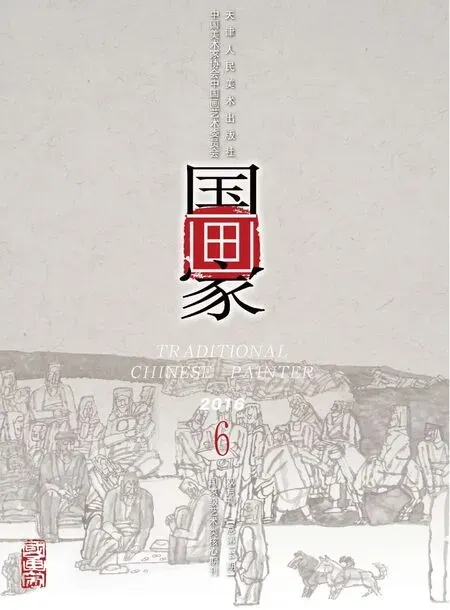現代工業題材寫意人物畫筆墨藝術語言的實踐與探究
王春濤
現代工業題材寫意人物畫筆墨藝術語言的實踐與探究
王春濤
筆墨是一個矛盾的兩個方面,一方面筆要靠墨色來體現,另一方面墨沒有筆法也是不存在的,筆墨既是對客觀物象的反映,也是作者才情、修養、閱歷的主觀展現,是畫家個性藝術語言的載體,在優秀畫家的藝術生涯中筆墨是終身錘煉的重要基本功之一,筆墨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和造型、色彩、構圖、情感、意境等諸因素有機融合,因此筆墨在中國畫藝術語言中,始終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有時甚至凌駕于其他語言和整個藝術形式之上,對筆墨的認識程度標志了對中國畫的認識程度。
在時代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中國城鎮化建設和工業化進程發展迅速,農民工、產業工人、自由職業者這些勞動群體新名詞隨之產生,研究表明,21世紀的中國要建設和實現新工業化戰略,只有走工業化道路才能促進經濟發展。縱觀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無處不在的工業化建設場面,無時不在我們身邊,這些建設者們常年默默無聞、甘于奉獻,他們是社會的基石,社會離不開他們,對這些群體應當予以尊重、關注和謳歌。產業工人和特定的勞動建設場景共同構成新時期寫意人物畫表現內容的新視野,新的表現領域隨之給畫家在表現內容上拓展了空間,在筆墨語言、構圖、色彩、意境等方面帶來創新和突破的契機。特別是在中國畫筆墨藝術語言方面,豐富、改善了傳統人物畫描繪現實生活的能力,對促進傳統繪畫語言產生積極推動作用。本來筆墨是中國畫的一種表現語言,它單純為造型服務,“以合乎內容的形式為形式”。內容決定形式,表現現實生活中的景和人物。但死守傳統筆墨程式,忽略形式對內容的反作用,講究一筆一線的傳統意味而忽略了現代的表現對象和目的,只會導致陳陳相因,了無生氣,流于形式。

王春濤 濱海鉆工
一、新的表現內容,建立與之相適應的筆墨藝術語言
當今社會遠不是古人小橋流水、長袍馬褂的時代了,人們的視野和活動范圍擴大,發現前人沒有表現或鮮有表現的新題材、新內容,嘗試新技法是豐富發展傳統的必然趨勢,符合藝術發展規律。如用寫意技法表現難度較大的工業題材、異國風情、現代化工業設備,各種筆墨藝術語言的運用極大豐富了中國畫的感染力。任何藝術的表現形式都要基于表現內容的需要而產生,新時期產業工人的精神氣質、服裝道具、機械工具有別于六七十年代,如石油工人與建筑工人在精神氣質、工業設施、勞動環境等方面也存在明顯不同;現代工業題材內容的多樣化自然產生新的表現題材,畫家在該方面的探索也引領人們的審美觀趨于多元化與個性化,工業題材場面中除了構成畫面的人物之外就是大型工業現代化設備,其富有視覺沖擊力的造型給人以感官上的新鮮,這些設備以直線造型為主,橫縱交叉,層次錯落,構成獨特的視覺秩序,這使得善于表現文人高士、水墨淋漓自由滲化的傳統筆墨語言在表現此類物象時自然受到造型的制約,從而在筆墨表現技法上產生很大局限性,縱觀近現代中國畫傳統在工業題材特別是寫意工業題材的運用上,借鑒的東西并不多,這也是目前鮮有人問津此類題材的原因之一,因此畫家必須把傳統筆墨語言進行“變異”與“嫁接”,才能賦予其新的生命力。如筆墨與造型、筆墨與情感、筆墨與意境、筆墨與思想等,具體與之適應的技法有揉、皺、噴、拓、貼……各種畫面肌理的制作以及一些抽象筆觸型用筆和一些非書法性用筆的出現,提高了筆墨語言的表現力。但一種語言的變化可在自身傳承的范圍內進行,形式語言創新但意趣還是傳統審美內涵,這是在表現工業題材寫意人物畫探索中豐富發展筆墨語言所特別要注意的。
二、現代工業題材寫意人物畫筆墨的寫意性
“精而造疏,簡而意足”,雖然說是宋代的審美趣味和審美理想,但它可以代表中國繪畫藝術的審美原則。張彥遠的《論畫體》有一段文字對我們了解“寫意”這一審美原則,對理解中國畫的重“意”很有幫助。他說:“夫畫物特忌形貌彩章,歷歷具足,甚謹甚細,而外露巧密。所以不患不了,而患于了。”面面俱到基于照相式的繪制只能是“能品”,上升不到“神品”和“逸品”。中國畫從本質上是寫意的,工筆的內涵也是寫意,只是表現形式不同,寫意精神是中國畫區別于西方繪畫的本質所在。中國畫與其他畫種存在的主要區別就是筆墨對意境的表達,“寫意”既是中國繪畫的繪畫觀,又是創作方法。中國畫筆墨具有多重屬性特征,既是一種繪畫的工具材料,又可作為一種繪畫方法,同時又是一種重要的鑒賞標準和繪畫語言形式。寫意性作為中國畫中獨特的藝術觀,在中國畫筆墨的多重屬性特征中都有具體體現。寫意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中國畫筆墨的本質內容,只有寫意才能將中國畫特有的審美趣味和藝術美感呈現出來。千余年來,深厚的傳統積淀造就了國畫的博大精深,國畫的筆墨程式化語言雖然確立了中國畫藝術特征,但畫家們在注重這些傳統特征的同時卻很容易忘卻自我,如基于禪道基礎上的筆墨語言,經多年積淀形成世人感官接受的筆墨程式,在表達超遠、淡泊、孤高、虛靜的古代文人心境上獨具特色,但在表現大工業題材面前明顯不適合,傳統的筆墨模式難以表達當今工業題材人與物的感受,因此筆墨要在人物與景物之間尋求一種契合,即塑造物象同時更要講求自身的筆墨語言,筆墨式樣要服從畫面總體氣氛與意境的需要,使工業題材寫意人物畫具有很強的寫意性。
三、色墨相生豐富筆墨語言形式
現代工業題材中大型設備、流水線、人物服裝的色彩純度高,色相明確,體現了一個時代的造物特征,有些勞動場面采用自動化生產線,機械化取代了過去的人山人海、人拉肩扛的勞動方式,從而構成具有時代文明烙印的畫面,這些都是表現構思中的亮點所在,中國畫歷來講求“墨分五色”,“水墨為上”的筆墨審美觀念占據意識主流,長期以來,重程式的中國畫給我們帶來表現上的便利,其中有消極的一面,也有傳統精粹的一面,其中有很大潛力可以挖掘,但傳統筆墨程式如“十八描”不太適合表現新時期工業題材“人與物”強烈的視覺感受,用傳統筆墨套用新的表象物象顯然是不合時宜的,眾所周知,傳統是需要創新的,當然要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沒有傳統的創新是立不住的。“我之為我,自有我在。古之須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代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腸。我自收我之肺腑,揭我之須眉。”三百多年前石濤在繼承傳統和個性創新方面闡述得很清楚,在筆墨與色彩的對比中尋求工業題材表現的突破口,是“隨類賦彩”的延伸,是氣韻生動的再造,不僅是工業題材寫意人物畫筆墨語言的創新點,而且在提高畫面色彩與筆墨視覺感受從而豐富中國畫筆墨語言方面容易出特色、見效果。如入選慶祝建黨95周年全國美展的作品《舞臺》,其題材屬于常見的現代建筑工地,但作者卻在紅墻與腳手架上的勞動者之間找到了創作支點,正如羅丹所說:“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美的眼睛。”該作品在內容與形式、色彩運用與筆墨符號、具象寫實和抽象元素的運用等方面都體現了探索意識、創新精神,其中“以意用色”,色彩與筆墨的黑白灰使用恰到好處,使該作品個性鮮明、真實可感、時代性強。
四、筆墨與黑白虛實的轉化
素描光影和筆墨有機結合的手法在當今現實主義為主的寫意人物畫中技法成熟,成績斐然,實現了20世紀畫壇先驅徐悲鴻、蔣兆和當初完善改良傳統人物畫的初衷,在此首先要正確理解黑白虛實的概念是什么。如在現代工業題材寫意人物畫中,人物身后一塊大的墨塊不能理解為光線的投影,一個人物被處理成黑色塊也不能理解為人在投影之中,如此看來中國畫中的虛實內涵不僅是素描中的明暗表象,而且體現強烈的主體意識,雖然筆墨與自然明暗虛實有緊密關聯,但更主要的是畫家在畫面中通過筆墨結構形成畫面“虛實”與“黑白陰陽”的節奏對比,如果筆墨只是一味照相般的臨摹對象而形成的虛實,那是表面的筆墨觀。縱觀李伯安頗有震撼力的人物造型,可以看到畫家駕馭筆墨、塑造形體的能力,筆墨善于從結構入手,形成經概括、抽象、凝練而成的大黑大白的塊面沖突,黑白虛實塊面關系轉化為絕對自由的畫面構成需要。李可染的山水也是成功地把素描光影轉化為黑白虛實關系的水墨山水獲得成功,從而推動山水畫在傳統的基礎上發展。在現代工業題材寫意人物畫創作中,筆墨與虛實的處理往往體現畫家觀察生活的細致和創作理念的成熟與否,如入選慶祝建黨90周年全國美展的作品《濱海鉆工》,該幅作品取材于天津大港油田,在寒風凜冽的冬日,四個采油工人正在緊張作業,畫家大膽創新,采用中國人物畫很少運用的俯視構圖,形成畫面別具一格的視角,表現了當代石油工人特有的工作環境。鉆機與油管等環境用沒骨手法概括處理,淋漓的筆墨既表現了現代化設備的厚重又突出了主體人物,整個畫面充滿動靜、黑白、線面、繁簡等對比因素,筆墨與虛實轉化得當,畫面厚重而不失空靈,勾勒,意在筆先,點染,起伏凹凸,有著獨特的視覺美感,這些顯然是畫家對生活的觀察與體驗,也體現了畫家對筆墨與虛實關系的精準把握。
“墨非蒙養不靈,筆非生活不神”,實現現代工業題材寫意人物畫筆墨語言的創新首先離不開深入火熱的生活,在生活中發現、汲取靈感是其基礎,其次,挖掘具有傳統內涵、探索富有時代特色的個性化筆墨語言是其關鍵。工業題材的探索雖然具有難度,但具有廣闊的前景,在提倡藝術貼近生活扎根人民、推出時代精品的今天,人物畫家肩負著更多的社會責任,在全面提高自身藝術修養的同時,注重筆墨藝術語言的創新在創作中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王春濤 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