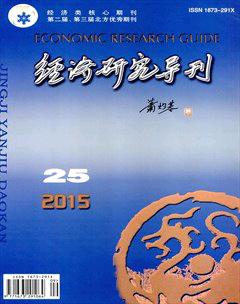鎮江科技服務支撐體系與高新產業協同治理及其構建意義
凌峰 朱冬林 費傳寶
摘 要:由鎮江市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現狀與問題出發,界定高新產業科技服務支撐體系的內涵。運用高新產業集群相關理論與弦振動模型,詮釋高新產業與科技服務支撐體系協同治理的形成機理,并明確構建當地高新產業科技服務支撐體系的戰略意義。
關鍵詞:高新產業;科技資源;協同治理;戰略意義
中圖分類號:F26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5)25-0041-03
引言
黨的十八大堅定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將科技創新放在國家發展核心位置。蘇南長三角地區社會經濟較發達,推進產業結構升級,實施創新驅動戰略,是貫徹習總書記視察江蘇講話精神,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建設“經濟強、百姓富、環境美、社會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蘇”之切實行動。鎮江在長三角城市群中居一席之地,是蘇南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的組成部分。搶抓機遇,加快步伐,融入國家“一帶一路”整體戰略,成為當前切實而緊迫的任務。作為產業技術升級最具活力板塊,鎮江市高新技術產業長足猛進,成為推動當地經濟、促進區域產業調整與產品檔次提升之重要增長點。本文通過分析鎮江高新產業現狀與問題,運用區域經濟相關理論,闡述科技服務支撐體系與高新產業協同治理模式和機理,并簡述構建高新產業服務體系的戰略意義。
一、鎮江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現狀與問題
(一)鎮江經濟發展與高新產業概況
鎮江地處長江三角洲北翼,滬寧杭都市圈,長江與大運河在此交匯,京滬高鐵、滬蓉高速等通達全國,長江第三大航運中心——鎮江港通江達海。作為新興工業城市,是蘇南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組成部分。改革開放以來,深入實施科技創新工程,扎實推進“創新創業行動計劃”。2013年全市高新技術產業產值3 432.2億元,同比增長20.32%,占全市規模工業產值46.8%,民企與三資企業日漸成為高新產業發展主力。全市共有省級及以上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等企業研發機構212家,其中國家級5家、省級207家;擁有兩個國家級開發區、6個省級開發區、5個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基地;擁有省級科技公共服務平臺11家,建成國家、省級孵化器21個,孵化面積超240萬平方米,在孵企業914家。世界主要錨鏈生產基地、全球單廠規模最大高檔銅版紙生產基地、中國最大汽車發動機缸體和醋酸生產基地陸續落戶。鎮江正逐步成為集機械、化工、造紙三大主導產業,電子信息、新材料、交通設備、食品、電力五大優勢產業,船舶及船用設備、五金工具、眼鏡、香醋等十大產業集群為主體的長三角地區制造業基地。
(二)鎮江高新技術產業面臨的問題
鎮江市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面臨的問題主要有:增長勢頭不足,自主創新能力較弱,產業內部不均衡,集聚優勢不明顯,未能形成更好的互動態勢等。具體看,各城區高新產業發展主導方向與核心能力不同,面臨難題各異。如:京口區單靠文化創意產業較難形成很強的積聚效應,相比周邊城市,扶持政策單一。京口歸國博士園面積小,難以產生規模集聚效應;潤州區可供發展用地少,“零土地”招商困擾該區。軟件人才流失嚴重,人員住宿困難;個別項目技術高端,卻難進入尋常百姓視野,市場推廣較難打開局面。未與當地大學和科研機構有更緊密聯系,產學研合作待深入;科技新城產學研互動運轉效率不高,區際或市際某些產業發展同質化傾向初現端倪,人才爭奪日趨激烈;政策調節一定程度無序化與政府中長期規劃間矛盾難以完全避免,光伏、LED等產業已現過剩。如何在公共服務方面刺激企業長久發展態勢,是政策層面亟待解決的問題。
(三)鎮江市科技服務支撐體系內涵界定
當地高新產業發展固然有起步晚,基礎弱,產業發展欠均衡,科技孵化、加速器培育待深化,產學研互動融合不足等原因。但與之配套的科技服務業目前存在水平相對滯后、層次有待提升、支撐效應不明顯、資源優勢待發揮等問題,以致對高新技術產業支持力度不夠,針對性不強,是制約高新技術產業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鎮江市科技服務支撐體系是立足于本市服務業現有各項軟硬條件,結合區域經濟優勢,遵循高新產業鏈發展規律,致力于支撐、引導、輔助、配合鎮江市高新技術產業整體發展,旨在提高和改善與高新產業相關信息、研發、產學研合作、商貿物流、人才培育、金融支持、公共服務等各項科技資源配置方式與水平,并使自身在這一融合過程中不斷優化、提高并逐步融入更多高科技含量,與當地高新產業高度相融的本地現代服務業體系子系統。這一服務支撐體系與傳統科技服務業求同存異:首先,科技服務支撐體系對高新產業服務針對性更強;再者,科技服務支撐體系形成自洽融合系統,體系所涵蓋的各項理念、政策、方法、制度、措施、手段等要有機融合,并行不悖;繼之,服務體系構建從鎮江高新產業面臨實際問題出發,對癥下藥,量體裁衣,提出一攬子支撐方案與措施整合。
二、區域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理論基礎與服務支撐體系協同治理模式
(一)區域高新技術產業集群發展理論基礎
王緝慈在《創新的空間》中對高新技術產業集群做了相關論述,認為:增長極與新產業區理論對區域高新技術產業集群發展研究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增長極理論闡述區域內嵌入高新產業后,會通過乘數效應帶動其他產業發展,從而促使域內經濟增長的動態機理。然而該理論較理想化,實踐表明若當地有高新企業是跨地區垂直一體化公司的分支機構,與本地企業后向關聯小,則對本地企業帶動作用不大。甚至高新區一些較大型企業利用了本地出臺的優惠政策,提供的基礎設施、人力資源等要素,其產生的經濟增長卻主要在區域外,成為事實上的“飛地”。高技術活動在當地對促進就業的作用也有限,同時,由于大量使用稅收優惠政策,弱化了對本地財政支持[1];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高新區真正價值是創造當地良好孵化環境,促使區域供應商、制造商、客商、大學與研發機構、信息平臺、人才交流等日益頻繁相互作用,減少交易費用,產生整體協同效應,由此新產業區理論應運而生。該理論認為,高新區對當地影響程度取決于其自身發育,發育成熟的重要標志在于區內高新企業繁衍及區內各要素機構間相互聯系[1];美國硅谷、東京大田、臺灣新竹、印度班加羅爾等地科技園發展歷程向我們昭示:起先政府對高新產業引領作用很快為區內眾企業自身發展迅速的技術與人才聯系所取代。當地創新網絡與文化環境建構主體間相互依存的學習環境、組織、制度創新及上述共同形成的協同治理“軟環境”,隨著高新企業群內成長而形成日益頻繁的相互聯系。這才是吸引更多高新企業加盟并杜絕“飛地”的重要條件。甚至有的專家認為,政府干預會影響高新區企業間上述配合之默契。
應理性看待上述理論,我國許多高新區發展正處于增長極階段向新產業區過渡時期。即便這一轉變在各地尚未完成,如鎮江部分高新區依然由某些主導產業帶動。但根據相關理論與發達國家既往發展歷程:高新產業發展的增長極階段必將成為歷史。增長極模式弊端在于:易引起本地經濟對某類單一產業過度依賴,而新產業區模式強調當地各產業間整體協調互動,系統性協同治理本身不斷培育與加強形成了本地特有的產業群落特征,當地整體產業結構由引入型向帶動型,向自身形成不斷協同強化的優質經濟生態群落轉變。將發展優勢融于本地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促使各種科技資源合理配置,不會因一兩個重要企業搬遷而影響當地整體經濟水平與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然而,新產業區理論對提供公共服務的最大主體——政府的作用較為忽視,在城市和區域直接參與全球化激烈競爭的今天,稍縱即逝的機會窗口與眾多根植于本地制度與文化特色相互交織,使各地從此步入各自發展軌跡。為此,政府在植根本地社會經濟網絡,強力發動服務創新引擎,整合各種科技服務資源,引領當地高新產業發展路徑,推動本地各機構及要素集聚,通過技術與信息交流達成協同,從而形成當地特有生產服務系統的過程中至關重要。高新產業集群在新產業區階段與政府、科研和金融等機構形成具持久活力的協同創新網絡,這一作用本身即增強了當地生產與經濟系統整體實力,從而吸引更多企業不再囿于各地日趨同質化的優惠政策,而更多關注當地高新產業整體性協同網絡的輻射誘惑而加盟。這也啟發政府將招商引資戰略航船逐步引領出單純依靠區際優惠政策博弈的“紅海”桎梏,利用政府公權力及對于公共服務的強大供給能力,整合區內優質服務資源,推動新產業區發展,駛入逐步形成的具有自組織功能,自成長機制,具地方特色的高新產業戰略“藍海”。
(二)區域高新技術產業與科技服務支撐體系協同治理模式的形成
高新產業集群與當地科技服務體系是相互融合、互動共贏的兩大體系,由于這兩大體系間的和諧共振導致其協同治理格局的出現。共振要因在于相互間頻率和諧。服務支撐體系不是與區域內幾個龍頭企業發生共振,而是與這些企業及其他機構所形成的協同網絡的群體效應相互反饋。世間物理、生理、心理、事理、管理等皆相通,比如聲音在物體中的傳播由聲音頻率、物體致密度和內部應力等因素共同起作用。服務支撐體系對高新產業群的調節作用如同波在高新產業群內傳播。在此利用弦振動模型,省去推導過程,有下列方程:
在(4)式中,等式左邊是縱向位移加速度,即科技服務體系對高新產業群影響的加速程度,這取決于等式右邊兩項的變化。顯然若高新產業群內企業彼此聯系程度T越緊密,同時政策初始影響f0越強,則此種影響對高新產業的促進愈發加速。這是一把雙刃劍,即不合適的政策對于高新產業群的整體影響也同樣會加速。高新產業群內部的企業密度函數p(x)值越小,越有利于公共服務政策在高新產業群內的影響加速傳導。這與人們平時的感觀不相符,提醒人們:盲目追求高新區企業的數量是不足取的,最要緊的是新引進企業是否能帶來高技術含量和高附加值,并且與區域內現有高新企業建立起廣泛有效,協同驅動的相互聯系。橫向位移x方向對于縱向位移u上的高階導數提醒我們政策及其他科技相關服務驅動高新產業過程中存在拐點,這是否為科技服務運行中的調控預示了空間,有待進一步研究。外部政策與商業服務對高新產業群形成了持繼而有力的驅動,這些驅動傳播的效果又有賴于高新產業群內部聯系與密度分布,這一和諧共振機理有力促進了高新產業與科技服務業本身相融,長效和持久發展,從而逐步形成了高新產業群與科技服務這兩大動態系統的協同治理模式。
三、構建高新產業科技服務支撐體系的戰略意義
高新技術產業持續競爭力的獲取須依賴域內整個產業價值鏈群系統效率提升,針對特定產業設計的服務支撐體系,作為具有區域和時代特征的公共管理工程的一部分,將保障產業鏈條各環節有效銜接,促使高新產業整體價值實現過程在鏈群有機運行中順暢進行,在對高新產業的規制協調和引導管控下,實現其系統效用優化和價值穩步增值,從而產生區域產業聯動效應。科技服務支撐體系是地區高新技術產業價值鏈群中各環節有機結合的黏合劑、各子產業動態磨合過程中的潤滑劑、系統整體效用實現過程中的整合劑、產業鏈核心價值增值得以穩固達成的催化劑。
鎮江高新產業科技服務支撐體系不是單項研究成果、方法措施、管控手段、引導政策的簡單裝配,也不應成為各種適用技術、業務流程、組織管理、法律制度的草率“拼盤”,而是具有特定輔助手段、協調對象、合理方法體系,可促進產業鏈群發揮長效機制,各利益相關方和諧共贏的系統工程。推動鎮江市高新產業融入整個蘇南示范區建設,著力打造產業化、市場化、現代化、國際化的科技服務支撐體系,不斷擴大高新技術產業規模、加快產業內部結構調整,逐步引領鎮江高新技術產業群成長為蘇南長三角示范區建設的現代標桿。
收稿日期:2015-05-18
基金項目: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指導項目“協同治理視域下江蘇科技資源市場化配置研究”階段性成果(2015SJD775);鎮江市2015年社科應用研究課題(ZSK2015034);鎮江市2014年軟科學課題階段性成果(YJ2014013)
作者簡介:凌峰(1974-),男,江蘇鎮江人,講師,博士后,從事區域經濟與科技創新研究;朱冬林(1964-),男,江蘇丹陽人,書記,從事科技創新管理研究;費傳寶(1956-),男,江蘇淮安人,教師,從事科技創新管理、區域科技人力資源配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