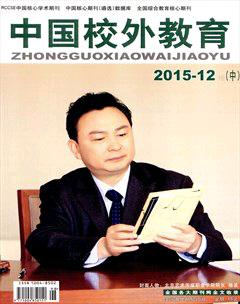從語義到詞義
席洋 張芳
摘要:從認知語義學的基本觀點出發(fā),首先闡明了語義、詞義、概念之間的內(nèi)在區(qū)別與聯(lián)系。其次透過對語義主要特征的描述,詞義的概念意義與文化意義的解析,表明詞義的變化是認知機制的體現(xiàn),理解原型范疇理論思維模式的變化對詞義的提取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認知語義學 語義 詞義 原型范疇理論
語義和詞義的研究一直是認知語義學的重要內(nèi)容,尤其是關于詞義的解釋及提取過程都與認知機制下的語義分析密不可分。范疇化與概念化作為認知語義學的基本原理,運用于詞義研究,其本質(zhì)揭示了語義下的詞義并非建立在一組充分必要條件下;語義與概念的區(qū)別和聯(lián)系,及其語義自身的特征決定了詞義的不確定性、可變性、動態(tài)性、相對性和多樣性等。因此,建立在概念意義的基礎上,在認知機制的作用下,運用原型范疇理論整合出恰當合理的文化意義,對于詞義的提取具有重要意義。
一、概念、語義、詞義的區(qū)別與聯(lián)系
1.概念與語義的區(qū)別
概念是反映對象的本質(zhì)屬性的思維形式。人類在認識過程中,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把所感知的事物的共同本質(zhì)特點抽象出來,加以概括,就成為概念。詞匯是表達概念的語言形式,不同的語言對于同一概念的表達形式不同。
概念不同于語義。語義是語言學或語義學所重點關心的對象;而概念是指思維的基本單位,主要屬于邏輯學和認知科學。
語言是音,形,義,意結合的符號系統(tǒng)。語言的意義包括:詞匯意義,語法意義,修辭意義,這三部分構成了龐大的語義體系。詞匯作為語言的外在形式的直觀表達,承載著該語言使用者的認知基礎和言語社團群體共識,這便是我們說的語言的“義”。而“意”則指語言使用者的交際意圖,表達“意”的過程是一個構建的過程。因此,詞義是語義的一個組成部分,語義是建立在詞義的基礎上的,語義是遠大于詞義的。
2.概念與語義的非對應性
概念具有普遍性,而語義則會因語言而異。不同民族用語言表達概念的方法,即詞匯化方法會有很大的差異,因而概念與語義不是一一對應的,自然概念與詞義也非一一對應。
在二語習得的過程中不難發(fā)現(xiàn),同一事物或概念,在英漢兩種語言中并非能找到完全對應的詞來。譬如,英語中opera一詞,對應在漢語里有歌劇,戲曲等義項,而我們都知道中國的戲曲和西方的歌劇無論在藝術形式和內(nèi)涵上都存在著較大的差別,而這也并非是一本雙語詞典能解決的問題。語言中出現(xiàn)的詞匯意義的差異只是語義差異的一個方面;上文中談到的“義”的認知基礎便是我們說的這種語義差異,也就是語義的“分裂”。而另一方面為了達到交際的需要,表達出恰當?shù)摹耙狻保覀儽仨氉龊靡饬x的“整合”。
二、語義的主要特征
1.語義是處于動態(tài)與靈活變化中的
意義的變化與我們對于世界的認識有關,我們必須要面對一個處在變化中的世界。在環(huán)境中新的體驗與變化要求我們采用我們的語義范疇對不同場景做出轉化,及對細微差別和異端例子留出空間。
2.語義百科觀與非自治性
語言意義并不是與我們所擁有的關于世界的其他知識所分離的,它所涉及到了已經(jīng)滲透于我們的其他認知能力的知識。比如,我們對于方位介詞behind/in front of的理解,就基于我們運用身體方位概念化,這種自然定位定義了什么處于我們前方,什么在后方,并將這種定位投射到其他和視線所產(chǎn)生的自然定位的個體上。
3.語義的體驗性
Paul Kay關于色彩詞的研究結果發(fā)現(xiàn),盡管各種語言的色彩詞不盡相同,個人對色彩范圍的界定也不相同,但對于某種特定的色彩,所有受試者認定的最典型或最具代表者完全一致。進一步研究表明,這種一致性來源于人類相同的生理構造。語言是代表客觀世界中的事物,事物結構,及事物關系的符號,因此語義也是客觀獨立的存在,語義是體驗性的。我們必須通過對進行認知活動的生物體的身體構造和經(jīng)驗的研究來理解意義。
三、詞義的概念意義
概念意義是語言符號意義的核心部分,是以語言概念為基礎的意義。概念意義主要運用基本范疇分析法來界定事物的非此即彼,通過范疇化,強調(diào)邏輯意義。范疇化是概念和詞義形成,以及語言運用的出發(fā)點,也是認知語言學的核心內(nèi)容,我們知道之前的經(jīng)典范疇理論是無法解釋一詞多義現(xiàn)象的。原型范疇理論是認知語義學的重要理論,原型是范疇中最典型的成員,是人們對世界進行范疇化的認知參照點,其他成員圍繞原型構造,呈現(xiàn)具有家族相似性的邊界模糊的輻射狀結構。值得一提的是,這里我們說的原型成員或原型范疇詞,并非僅是以往學界提到像cry,cup,water,fire諸如此類的簡單中性詞,或是穩(wěn)定性較強的基礎詞,像本文前面提到的諸如opera這樣的文化性原型范疇詞,更能反映出語義的百科觀與體驗性,也更應該在詞匯習得中引起關注。
四、詞義的文化意義
詞義的文化意義體現(xiàn)在其民族性,地域性,特殊性方面。Eleanor Roasch做過一個關于“鳥類”(bird)的原型范疇成員的時間反應調(diào)查,受試者被要求在規(guī)定時間內(nèi)描述出一個帶有鳥的句子,Roasch根據(jù)不同的句子給出T或F的分類(T屬于范疇內(nèi),F(xiàn)屬于范疇外),并且記錄下了每個受試者給出答案的時間。結果豐富多彩:其中有人給出了麻雀,有人給出了知更鳥,還有人給出了企鵝,甚至有人給出了公雞的答案等。
由于不同地域,文化,甚至個人經(jīng)驗的差異導致人們對“鳥”,這個本身較穩(wěn)定的范疇詞匯的原型成員產(chǎn)生了千差萬別的認知體驗。那么問題是:究竟在英語當中“bird”的原型成員是什么呢?對于中國北方大部分地區(qū),無疑麻雀是比較的常見鳥類,又因為習性近人,又耐寒冷,世界大部分寒帶,亞寒帶地區(qū),麻雀均普遍可見;而對于我們比較陌生的知更鳥,大多數(shù)歐洲人則習以為常,這種鳥兒善于鳴叫,它更是英國人的國鳥,因此我們能在英國文學作品中常看到它的身影;對于大洋另一端的美國人,傳統(tǒng)感恩節(jié)餐桌上的壓軸大菜便是一道“A big bird”,實則就是一只火雞。因此有人把公雞看作是鳥就顯得并不古怪了。
世界各民族的共同文化通常由概念意義反映出來。但是不同民族,文化區(qū)域決定了各自語言的伴隨義的色彩和不同側面的文化意義。語義是個開放的系統(tǒng),體現(xiàn)在概念與詞義的非對等原則上。應該看到,在詞匯習得中,詞義本身的概念意義僅反映其處于靜態(tài)當中的詞典意義,而不同認知模型下的原型范疇成員絕非是一成不變的,它所反映的原語言符號特有的文化意義才是我們正確提取詞義的關鍵所在。
五、結語
考慮到語義本身的屬性和特征,結合詞義的概念意義和文化意義,在詞匯習得的過程中就必須將具體的詞匯納入到一定的語義范疇中,運用認知原型范疇原理來構建合理有效的語義網(wǎng)絡,進而提取正確的詞義信息。
參考文獻:
[1]王寅.認知語言學[M].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