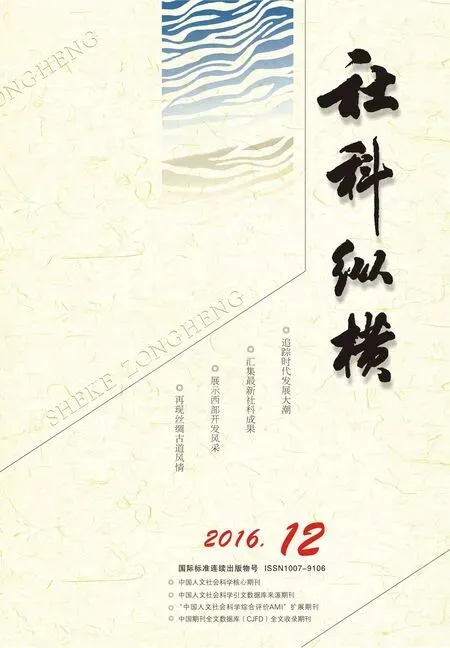網絡“惡搞”與大學生網絡道德素養教育研究
何茂昌
(蘇州健雄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太倉 215411)
網絡“惡搞”與大學生網絡道德素養教育研究
何茂昌
(蘇州健雄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太倉 215411)
本文從網絡“惡搞”的起源開始分析,深入剖析了它的實質以及在大學生中廣為流行的深層次原因,指出了網絡“惡搞”給傳統大學生道德素養教育所造成的困境和挑戰,提出了網絡監管部門和學校教育者的責任。
網絡“惡搞”網絡道德素養教育網絡環境
隨著計算機和移動互聯網的普及,“惡搞”之風風行網絡世界,大有蔓延之勢。[1]如何看待“惡搞”文化,如何引領“惡搞”文化,如何在這個“惡搞”時代對大學生進行網絡道德素養教育,這正是監管者和教育者必須面對的新課題。
一、網絡“惡搞”文化的源流
“惡搞”一詞來源于Kuso(庫索),日本的網絡游戲用詞。kuso在日文里面做名詞時,可以翻譯為“糞”,其意等同于中文網絡用語里的“爛”或“挫”;做動詞時,意思是不懷好意的“搗亂”,基本等同于中國俚語“往死里整”的意思。“惡搞”一詞首先在日本的游戲界源起,原意是指游戲玩家購入了一個“不好玩”的游戲時,使用“惡搞”的做法,仍然可以達到“好玩、搞笑”的目的。后來,傳到臺灣后,Kuso(庫索)就逐漸發展成為認真地“搞笑、搞怪”,并成為一種流行的網絡文化。后來,“惡搞”一詞經由網絡再從臺灣傳到香港,不知不覺擴散至大陸,成為一種經典的網絡用語,成為了青少年網民的口頭禪,甚至被貼上了代表網絡文化的標簽。
二、網絡惡搞文化的實質
作為青年人所推崇的一種網絡亞文化,網絡惡搞具有鮮明的反叛性和冷漠性。正如邁克爾·布雷克指出:“對青年亞文化的兩個重要反應形式,不是反叛,就是冷漠。”總之,青年網民們推崇網絡惡搞的初衷,是為了解決他們所共同面臨的種種社會矛盾,這是他們對抗社會矛盾的文化策略。那么青年們反抗的又是什么呢?
首先,從惡搞文化的創作主體來看,多是二十歲上下有些叛逆的年輕人,采用這種非傳統的方式來愚弄老一輩的思想。諸如惡搞紅色經典就是屬于這種類型的詆毀型“惡搞”,這主要是針對傳統價值觀、特別是主流價值觀進行的“惡搞”,如對《地雷戰》、《閃閃的紅星》、《劉胡蘭》等經典紅劇的“惡搞”,對已深入人心的人民英雄形象的“惡搞”,對經典紅歌的“惡搞”等等。[2]可見,惡搞者旨在反抗傳統和經典。
其次,從遭遇惡搞的對象來說,他們多是走精英路線的人或物,可見他們反抗的是以權威自稱的精英路線。比如較早在網絡上掀起惡搞狂潮的《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惡搞了電影《無極》,主要原因在于《無極》居高臨下的“導師式”敘事方式,正如電影史學家陸弘石教授所評論的那樣,電影《無極》“最大的問題是概念化,內涵直白寡味,主題先行”。同樣,以權威著稱的中央電視臺也難逃惡搞的“厄運”:從主播糗事到播出事故,甚至連頻道名稱都成為被惡搞的對象。與此類似的還有《三國
演義》、《西游記》等一大批優秀的傳統文化代表作品被“惡搞”。可以說,通過網絡“惡搞”解構精英文化,似乎已經成為“家常便飯”,甚至不可避免。原因就在于以青年網民為代表的“草根”階層對精英文化存在厭惡、質疑甚至反抗心理,而網絡給他們提供了話語權,于是他們借助這一平臺開始以“惡搞”的方式,無所顧忌地愚弄、嘲笑、諷刺精英們的作品,以狂歡的名義構建起一種非官方的、草根的民間文化形態。
最后,從惡搞的內容來看,他們多采用幽默夸張的形式來消解傳統文化的慣例,嘗試和玩弄另類的時尚。比如說,芙蓉姐姐和鳳姐的走紅,就顛覆了人們對傳統文化中審美標準的信仰。在這個“偶像泛濫”的時代,一些顏值高、身材好的明星,經由大眾傳媒的的包裝,成為家喻戶曉的“男神”、“女神”,然而,當正統的“偶像文化”被媒體推到極致后,觀眾普遍產生了“審美疲勞”。于是,一些當紅的花旦頻頻被黑,甚至被網友要求“滾出娛樂圈”,而“芙蓉姐姐”、“鳳姐”這樣為人詬病的人反倒成了“網紅”。一個所謂的“反偶像”時代在“娛樂至死,惡搞成風”的風氣下應時而生了,“大眾開始有意識地消解傳統觀念、顛覆傳統意義上的經典[3]”。
雖然網絡惡搞在網絡世界中有蔓延之勢,但它是否像某些人所說得那樣:已經顛覆了傳統文化的霸權,是一種庶民追求民主的勝利嗎?
確實,網絡惡搞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優秀文化、主流價值、法制觀念,使人們得到了心靈的解壓、情緒的宣泄,張揚了個性,得到了嘩眾取寵的機會。但是,惡搞作品并未能撼動主流文化權威的地位,草根作者也并未獲得與文化精英平等對話的權利。網絡惡搞使人們更加堅定《西游記》、《三國演義》等優秀傳統文化作品的價值,對紅劇、紅歌和英雄人物的惡搞,引發了民眾的不滿……由此可見,網絡惡搞并沒能厘清虛擬和現實的邊界,致使人們錯誤地把這種所謂的民主(其實是“烏托邦”)當成了真正的民主。[4]可見,網絡惡搞是處于民主饑渴狀態的草根階層用來發泄情緒、獲得快感的一種最經濟的策略,它并不能動搖傳統文化的霸權地位。正像光明網所認為的那樣:“‘惡搞’是完全以顛覆的、滑稽的、莫名其妙的無厘頭表達來解構所謂‘正常’,是文化虛無主義思潮一種新的表現形式”[5]。而這種“惡搞”和周星馳的無厘頭還是有很大區別的,比如周星馳最新電影《美人魚》已是通過“無厘頭”來表達一種嚴肅主題。
三、網絡惡搞文化在校園盛行的深層次原因
網絡惡搞能夠在校園迅速風行,除了互聯網提供了交互的平臺之外,目前我國文化的發展局面和文化氛圍、文化制度等對校園的影響也與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第一,多元文化在校園共榮。一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變革以及網絡技術的不斷提高,世界各國之間文化交流和信息傳播不斷提速,大學生接觸到的訊息更加多樣,他們的思想也更加開放、自由和包容,過去因為文化差異被視為奇怪甚至是異類的文化現象如今已經能夠被中國大學生所接納。
二是,在信息爆炸的時代,魚龍混雜的信息獲取渠道必然造就多元化的思想觀念、價值標準和行為特征,對大學生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帶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對傳統文化、權威觀念、主流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帶來一定的挑戰。而網絡的交互性則為多元文化的共同流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平臺,讓長期處于被動地位的某些大學生獲得了主動的權利,使他們有了自主的選擇權利,同時也可以自由地表達他們的意見和心聲。
三是,目前我國處于社會轉型期。轉型期最主要的特點就是社會階層進一步細化和分化,不同階層的價值觀念和文化取向日趨多元。[6]這也是我國由大眾傳播時代進入分眾傳播時代,各媒體紛紛開設專業頻道吸引特定受眾的原因,網絡媒體因為其可以通過發揮交互性博得了渴望發出自己聲音的年輕一代的關注。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網絡惡搞才有其在校園風行的土壤,才能在這樣多元文化共榮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第二,娛樂文化的盛行對校園的影響。這是一個“娛樂至死”的年代,娛樂制造產業向縱深發展,政治、經濟事件甚至也常常被娛樂消費。正如美國學者波茲曼在他的《娛樂至死》一書的前言中提到的赫胥黎的預言那樣:“這是一個娛樂之城,在這里,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并成為一種文化的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7]”正是在這樣浮躁的社會風氣影響下,惡搞也已經從最初純粹的“笑與詼諧”演變成網絡世界中的“肆無忌憚”。加上缺乏相應的監管,
網民們甚至綁架了道德規范、民族信仰乃至國家的苦難歷史,并借此“惡搞”以嘩眾取寵。涉世不深的某些大學生,是非觀和價值觀受到了沖擊,容易導致價值觀陷入混亂。
第三,傳統文化教育存在不足,尤其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明顯滯后。網絡“惡搞”之所以能夠對大學生的思想觀念造成較大的影響,與高校當前“說教式”、“灌輸式”、“被動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不無關系。不能將晦澀的理論語“寓教于樂”,不善于將純政治性話語進行轉換,教學形式單一、說教、呆板,不能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會造成學生求助于網絡信息的獲知,這就給大學生接觸網絡“惡搞”以可乘之機。從惡搞的參與者來看,大多數是80后、90后,他們具有較強的反叛精神和自主意識,他們往往對這種落后教育模式進行積極或消極的抵抗,通過惡搞來實現表達自我的需要。
四、如何正確引導網絡“惡搞”文化,對大學生進行網絡道德素養教育
雖然網絡惡搞文化并沒有從根本上動搖傳統文化的主導地位,但是它對于傳統文化尤其是紅色經典和名著名篇的惡搞不僅傷害了作者和相關創作人員,而且也傷害了一些觀眾和讀者,特別是那些對紅色經典和名著懷有深厚感情的觀眾和讀者,尤其會影響大學生形成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榮辱觀,更為嚴重的是,會造成他們法律意識淡薄,認為網絡世界可以為所欲為。因此,要積極引導網絡惡搞文化,發揮其正向作用,加強對大學生進行網絡道德教育。
第一,高校應探索傳統文化教育的新模式、新思路、新途徑。網絡惡搞的出現,從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大學生對傳統文化,尤其是對校園文化的不信任狀況。著名教育家葉圣陶先生認為教育者要以平等的心態對待受教育者,必須尊重受教育者的主體地位。在教育教學中,要變“教”為“導”,變“教”為“學”,實現教是為了不教的目的。這就要求教育者摒棄把大學生當做客體的教育方法,而采用主體性的教育方式,充分肯定大學生的主體性和能動性。[8]在這種情況下,教育者要充分重視學生的主體地位,熟悉和掌握大學生的心理特征,與時俱進,投其所好,及時探索出能夠緊跟時代發展的教育方法和模式,多采用大學生喜聞樂見的討論式、啟發式、教練式等生動活潑型的教育形式,吸引大學生主動參與,積極互動,以傳統文化的感召力,提高大學生的網絡道德水平,增強他們的網絡自律意識。
第二,網絡監管部門應加強網絡監控體系建設,確保法律法規的嚴肅性。為加強對“惡搞”行為的監控,監管部門需要利用更先進的網絡技術讓“惡搞”行為在網絡中傳播的難度更大,成本更高;同時,要加強法律執行,嚴肅查處網絡違法案件,懲戒網絡違法行為,真正做到“依法治網”。尤其是對網站出于商業利益不斷炒作、推廣造成的惡性結果進行嚴厲懲罰。
第三,媒體要承擔起傳播“正能量”、正確引導社會輿論。信息時代造成的多元文化盛行,使社會輿論呈現出更加多樣、多變和復雜的特征。這就要求媒體遵從傳播學的規律,不跟風,不媚俗,主動承擔起宣揚傳統文化、傳統價值觀和主流意識形態的職責,及時屏蔽、批判甚至聲討網絡“惡搞”行為,彰顯媒體的社會責任。在娛樂經濟風行的年代,能夠挖掘出更多充滿理性和具有實在意義的信息提供給廣大的受眾,從一定程度上遏制出于娛樂目的嘩眾取寵引發的網絡惡搞行為。
總之,要對網絡惡搞行為進行正確的引導和對大學生進行網絡道德素養教育,確保其在參與惡搞獲得快樂和釋放時,能正確區分良莠,把握好“人生觀、價值觀、榮辱觀”的方向盤,使網絡惡搞在帶來幽默和快感的同時,不至于對傳統文化,尤其是大學生的思想道德造成不良影響。
[1]馬明輝.網絡惡搞對大學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影響分析[J].高教論壇,2011(7):21-23.
[2]嚴瑞.網絡惡搞的反思及對策[J].渤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6):137-140.
[3]彭興庭.“芙蓉姐姐”與泛偶像時代[N].珠江晚報,2005-6-22.
[4]劉邦凡.網絡困境的價值哲學思考[J].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2014(5):63-65.
[5]傅海.網絡惡搞是非談.[EB/OL].http://media.people.com. cn/GB/5378779.htm l.
[6]傅宏波.網絡惡搞與大學生媒介素養摭談[J].湖北科技學院學報,2015(6):85-87.
[7]尼爾·波茲曼著,章艷譯.娛樂至死[M].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8]何茂昌.葉圣陶主體性德育思想在新媒體時代的價值研究[J].教育探索,2015(10):8.
G641
A
1007-9106(2016)12-0159-03
*本文為江蘇省教育科學“十二五”規劃葉圣陶專項重點課題“基于葉圣陶主體性德育思想的高職‘三三三’德育模式研究”(編號yz/2015/01);蘇州市教育科學規劃課題(高職高專類)“基于教練技術的高職活動性德育課程的研究與實踐”(編號:16000Z028);江蘇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課題“培養現代職業人——高職院校職業素養課程體系建設的研究與實踐”(編號:2015JSJG513)的階段性成果。
何茂昌(1982—),男,碩士,蘇州健雄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