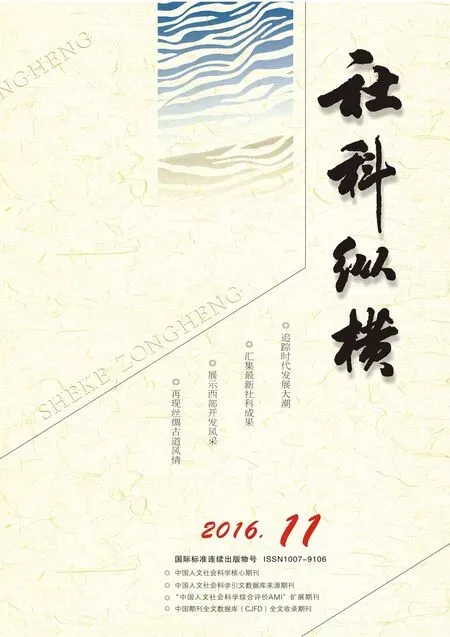馬克思論“消滅哲學”及其批判進路
盧文忠
(廣東警官學院思政部 廣東 廣州 510230)
·哲學研究·
馬克思論“消滅哲學”及其批判進路
盧文忠
(廣東警官學院思政部 廣東 廣州 510230)
馬克思在早期思想發展中不斷亮出“消滅哲學”的利劍。從歷史語境來看馬克思首次提出的“消滅哲學”具有五層意蘊,其實質上意指人們只有用現實的物質力量(而非純粹的理論批判)來變革現實的社會制度,才能揚棄源自這種現實制度的哲學。馬克思早期思想形成過程中前后兩個階段的“消滅哲學”是在唯物史觀批判和超越舊世界觀中不斷深化和提升的哲學批判,唯物史觀的形成成為馬克思推進“消滅哲學”的邏輯主線。在唯物史觀形成的基礎上,馬克思實現了從意識形態維度、物質經濟維度、歷史主體維度、革命實踐維度來推進“消滅哲學”。
馬克思 “消滅哲學” 哲學批判 唯物史觀 實踐
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寫出了膾炙人口和意味深長的最后一條提綱:“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1](P57)這句革命箴言鮮明地展露了馬克思在哲學問題上的批判性和實踐性的思維方式和行動取向,是馬克思早期思想形成過程中在哲學領域進行批判和斗爭的集中表達。作為用科學理論指導實踐的無產階級革命者,馬克思與其它哲學家的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馬克思不僅要用哲學來解釋世界,更要用實踐來改變世界。曾經的哲學家們過多地糾纏于理論上的解釋世界,即便有改變世界的意愿和沖動也不免被其把持的舊哲學所阻礙和幻滅。“傳統哲學只是在解釋世界,實際上,傳統哲學一直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維護現實世界的秩序,而改變世界的立場必然是‘批判'的態度,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制度,是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2]因此,真正的哲學家應該做到實踐基礎上的解釋世界和改變世界的統一。馬克思奮斗終身的就是要解決改變世界的問題。在這一過程中,馬克思對形形色色的哲學發起批判,用哲學批判作為武器來回應改變世界的問題,在與舊哲學的交鋒和對舊哲學的批判中特別是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提出“消滅哲學”的獨特觀點,并在唯物史觀形成中不斷推進“消滅哲學”,亮出了哲學批判和哲學革命最銳利的鋒芒。馬克思關于“消滅哲學”的觀點和論述,是馬克思哲學批判的核心命題和表現形式之一,也是備受爭議的焦點問題。因此,為了全面深入地把握馬克思“消滅哲學”的真實意義(消滅什么哲學)和“消滅哲學”的實現方式(怎樣消滅哲學),有待于從馬克思早期思想的發展歷程來深入研究“消滅哲學”及其批判進路。
一、馬克思提出“消滅哲學”的歷史語境
馬克思生于具有厚重哲學氛圍的普魯士德國,早年深受德國哲學、西方哲學的熏陶和感染,積極投身于哲學研究和哲學批判,致力于否定和揚棄舊哲學,在早期思想發展中不斷亮出“消滅哲學”的利劍。早在1841年其博士論文《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就已初見鋒芒。在這篇博士論文中,馬克思就曾發起過帶有“消滅哲學”意蘊的哲學批判:“世界的哲學化同時就是哲學的世界化——哲學的實現同時就是它的損失,哲學向外斗爭的東西也就是它自己特有的內在的缺陷,正是在斗爭中它自身陷于它所反對和斗爭的那種錯誤,而且只有當它陷于同樣的錯誤時,它才揚棄了這些錯誤。”[3](P65)其中的“實現”、“損失”、“揚棄”展露了馬克思消滅舊哲學的否定性和批判性的內在維度。
隨著在哲學領域的研究和斗爭的深入,馬克思在繼承黑格爾哲學中告別黑格爾哲學并走進了青年黑格爾派對黑格爾唯心主義體系的哲學批判行列之中。正是在哲學的批判和交鋒中,促進了馬克思與青年黑格爾派分道揚鑣,并對青年黑格爾派的自我唯心主義發起了哲學批判。此時擺在馬克思面前的理論任務是要批判和否定這些哲學。同時,德國實踐政治派也發起對德國哲學的否定。但是,“該派認為,只要背對著哲學,并且扭過頭去對哲學嘟囔幾句陳腐的氣話,對哲學的否定就實現了”。[1](P8)對此,馬克思認為該派全然顛倒了哲學與現實、理論與實踐的關系,針鋒相對地指出:“你們不使哲學成為現實,就不能夠消滅哲學。”[1](P8)
從《〈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的歷史語境來看,馬克思這一“消滅哲學”的觀點有五層意蘊:第一,對哲學的否定是正當的,或者說消滅哲學是正當的,人們應該提出這個要求。那是因為,在馬克思看來,德國哲學已經是為德國制度作辯護的“卑劣事物”,對德國制度開火就必然與否定德國哲學緊密關聯。第二,前半句的“哲學”和后半句的“哲學”的意義不完全相同,前者是意指“哲學批判”,即是那些局限于純粹理論性質的哲學家所進行的哲學批判;后者是意指“黑格爾哲學”。第三,消滅哲學,并非要完全取消哲學,廢棄一切哲學,“消滅”實為揚棄之意,即對哲學的否定中要有所拋棄,也要有所保留。因此,馬克思消滅哲學的那句話可以表達成:“你們不實現哲學,就不能夠揚棄哲學。”[4]第四,要消滅哲學,就要使哲學成為現實。這就是說純粹理論意義上的哲學批判要上升社會現實意義上的物質力量,才能消滅哲學。第五,哲學所要成為的現實包括市民社會、革命、無產階級。馬克思認為,市民社會成為德國革命的物質基礎,無產階級成為德國革命的現實主體,“哲學把無產階級當作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作自己的精神武器”。[1](P15)綜上所述,馬克思“消滅哲學”這句文本意義上的話可以概括表達為:德國實踐政治派必須把黑格爾哲學歸入德國的現實范圍,在市民社會中只有被帶上徹底的鎖鏈的無產階級用徹底的德國革命來推翻德國制度,就可以消滅黑格爾哲學了。換句話說,在一般意義上,人們只有用現實的物質力量(而非純粹的理論批判)來變革現實的社會制度,才能揚棄源自這種現實制度的哲學。從“消滅哲學”的真實意義來看,馬克思在關于哲學批判的問題上論述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主體作用和社會革命的物質現實根源,逐步形成唯物史觀的觀察視野和理論基礎,構建起推進“消滅哲學”的邏輯主線。
二、馬克思推進“消滅哲學”的邏輯主線
“消滅哲學”是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首次提出和論述的,但其“消滅哲學”的哲學批判并非就此完成,而是隨著其早期思想的形成發展而不斷推進,同時“消滅哲學”也正是馬克思早期思想形成發展的具體展現。“我們一般習慣于把從馬克思的博士論文到他與恩格斯合寫的《共產黨宣言》這一段思想歷程作為馬克思的早期思想。”[5](P3)在馬克思早期思想歷程中貫穿著一條邏輯主線:唯物史觀的形成。唯物史觀形成前后的分界線是《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其標志著馬克思哲學思想的變革。據此,馬克思在唯物史觀形成前后對某些具體問題的觀點和論述是有差異的和不斷革新的,只有從思想發展的動態意義上才有全面準確地把握馬克思關于某些具體問題的真實意義。就“消滅哲學”而言,唯物史觀的形成成為推進“消滅哲學”的邏輯主線,馬克思在唯物史觀的形成過程中不斷推進自己曾經提出和論述的“消滅哲學”。馬克思“消滅哲學”的觀點論述及其批判進路是馬克思唯物史觀形成過程中進行哲學批判的具體體現。因此,“對馬克思在這兩個階段(1845年為界)所提出的‘消滅(或否定)哲學'應該作分別的研究。”[6]必須緊跟唯物史觀形形成這條邏輯主線來把握馬克思“消滅哲學”的觀點論述及其批判進路。
第一,馬克思唯物史觀形成前對“消滅哲學”的提出。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之前,馬克思思想中仍不免帶有他曾信奉過的黑格爾唯心主義哲學和費爾巴哈人本主義哲學的理論殘余,仍或多或少在傳統的哲學批判意義上來“消滅哲學”,尚未能完全用唯物史觀的科學武器來進行批判和否定舊哲學。當然,馬克思不斷通過清算自己曾經的哲學信仰來消滅這些殘余,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集中批判黑格爾哲學,在《神圣家族》中集中批判青年黑格爾派,實際上,馬克思這一系列的哲學批判即是對哲學家們的錯誤觀點的消滅同時又是對自己的舊哲學的理論殘余的消滅。因此,馬克思在這一時期對“消滅哲學”的論述,是對自己原有的哲學立場和觀點的否定和超越。正是如此,馬克思所做的“消滅哲學”已超越了其他哲學家對哲學的批判和否定,彰顯了一種徹底的哲學革命的取向,最重要的是已經論及從根本上“消滅哲學”的物質經濟、歷史主體、革命實踐等現實維度。在這一意義上看,馬克思關于“消滅哲學”的觀點,用馬克思關于改變世界的革命箴言的話語方式來表達就是:哲學家們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批判哲學,問題在于消滅哲學。這種“消滅哲學”促進了唯物史觀的形成,又在唯物史觀的形成中推進“消滅哲學”。
第二,馬克思唯物史觀形成后對“消滅哲學”的推進。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之后,馬克思確立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哲學的貧困》、《共產黨宣言》中進一步發揮了“消滅哲學”的觀點,把曾經使用的哲學批判建立唯物史觀的基礎之上,把哲學批判提升到對社會經濟規律的科學分析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實踐促成。“馬克思的哲學批判不單純是從哲學的意義、原理、概念去批判舊哲學,而是在對舊哲學的揚棄中形成新的哲學觀、世界觀和社會歷史觀,將哲學批判轉化為革命性的實踐批判,不斷把批判的武器上升為武器的批判。”[7]正是這種新的哲學觀、世界觀和社會歷史觀,為“消滅哲學”真正落實到“成為現實”指明了道路。在這一意義上看,馬克思關于“消滅哲學”的觀點,再用馬克思關于改變世界的革命箴言的話語方式來表達就是:哲學家們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消滅哲學,問題在于消滅現實。
因此,馬克思早期的前后兩個階段的“消滅哲學”是在唯物史觀批判和超越舊世界觀中不斷深化和提升的哲學批判,后階段的“消滅哲學”在唯物史觀基礎上對前階段“消滅哲學”的繼續和完成,構建了“消滅哲學”的批判進路。
三、馬克思實現“消滅哲學”的多維進路
在唯物史觀形成的基礎上,馬克思實現了從意識形態維度、物質經濟維度、歷史主體維度、革命實踐維度來推進“消滅哲學”。
第一,意識形態維度:就是馬克思從哲學內容的廣度和深度上來推進“消滅哲學”。一方面,在唯物史觀形成之前,馬克思“消滅哲學”所要消滅就是德國哲學,在唯物史觀形成之后,馬克思“消滅哲學”所要消滅的不僅是德國哲學,“從根本上講就是消滅那種把哲學視為科學之科學,視為凌駕于各門科學之上,把自己臆想的聯系強加于各門實證科學的形而上學的思辨哲學的傳統”。[8]馬克思此時要消滅的是舊哲學中的思辨傳統,擴大了要消滅的范疇,這是唯物史觀所具有的科學性的內在要求。另一方面,馬克思絕非簡單地終結一切哲學,絕非一概否定哲學的歷史功績,而是消滅舊哲學中的功能缺陷。“從哲學的功能來說,消滅哲學講的是根本改變以往哲學只是解釋世界而不是著重改變世界的缺陷。”[8]馬克思以此倡導一種解決改變世界的問題的新哲學,深化了要消滅的對象,這是唯物史觀所具有的實踐性的內在要求。當然,在意識形態層面上對哲學的否定、批判、消滅并非馬克思的根本取向,畢竟意識形態上的斗爭并不能從根本上體現唯物史觀之“物”的特殊意義。事實上,馬克思最注重的是從物質經濟、歷史主體、革命實踐等“物”的現實層面來推進和實現“消滅哲學”。
第二,物質經濟維度:就是馬克思從社會物質生產交往的現實基礎來推進“消滅哲學。對物質經濟的考察是為了強有力地顛倒已被哲學家們顛倒了的理論與現實的關系,證明理論只是現實的反映和表達而非相反。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指出:“經濟范疇只不過是生產的社會關系的理論表現,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學家蒲魯東先生把事物顛倒了,他認為現實關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疇的化身。”[1](P141)馬克思要用活生生的經濟現實來駁斥和消滅這種顛倒的哲學。更重要的是,在馬克思看來,哲學是人們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分工的產物,是源自社會物質現實的意識形態,哲學批判是源自社會生產矛盾的精神活動。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馬克思指出如果哲學和“現存的關系發生矛盾,那么,這僅僅是因為現存的社會關系和現存的生產力發生了矛盾”。[9](P26)也就是說,只有消滅現存社會的物質生產、勞動分工、社會關系才能從根本上“消滅哲學”。
第三,歷史主體維度:就是馬克思從無產階級歷史主體的地位和作用來推進“消滅哲學”。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神圣家族》中馬克思就已經把無產階級、工人群眾作為革命主體來看待。此后馬克思則更加明確地把無產階級的主體作用與意識形態革命聯系起來,把消滅哲學當作無產階級瓦解資產階級社會的舊生活條件和舊思想來理解。正如他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無產階級,現今社會的最下層,如果不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就不能抬起頭來,挺起胸來”。[10](P39)馬克思所要消滅的哲學,正是無產階級所要炸毀的官方社會上層的一部分,無產階級是消滅哲學的歷史主體。“消滅哲學”在主體意義上意指無產階級在改變資產階級舊社會的歷史進程中通過徹底的哲學革命和意識形態革命來克服舊哲學對自身的統治和奴役從而實現自身的精神解放。
第四,革命實踐維度:就是馬克思從無產階級反對現存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運動來推進“消滅哲學”。在馬克思看來,其它哲學家依靠純粹理論的批判來否定和消滅哲學是徒勞的,最根本的方式在于用直接的現實的革命實踐消滅這些哲學賴以產生的社會物質基礎。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意識的一切形式和產物不是可以通過精神的批判來消滅的,不是可以通過把它們消融在‘自我意識'中或化為‘怪影'、‘幽靈'、‘怪想'等等來消滅的,而只有通過實際地推翻這一切唯心主義謬論所由產生的現實的社會關系,才能把它們消滅;歷史的動力以及宗教、哲學和任何其他理論的動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9](P36)可見,此時馬克思已立足于唯物史觀的高度把“消滅哲學”當作革命實踐來理解,把對觀念形態的哲學的批判與對物質形態的經濟關系的革命緊密結合起來,而且更深入和具體地把對經濟關系中的所有制關系(資產階級私有制)的變革作為哲學革命和消滅哲學的現實基礎。“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10](P48)因此,要把傳統的觀點(傳統的哲學)消滅,就要用消滅既存的私有制的共產主義革命。
結語:總之,“馬克思把哲學的實現與對現實生活的批判性改造活動本質地關聯在一起,因此才提出通過‘在現實中實現哲學'的辦法去‘消滅哲學'。”[11](P93)在唯物史觀形成的基礎上,馬克思從意識形態、物質經濟、歷史主體、革命實踐的維度來構建“消滅哲學”的實現方式,使“哲學成為現實”。從這一意義上說,此時馬克思已深化和超越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消滅哲學”的意義,直至《共產黨宣言》的論述,“消滅哲學”的真實意義已提升為:只有無產階級通過革命實踐來改變資產階級舊世界的物質生產和社會關系才能從根本上揚棄作為社會意識形態的哲學。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孫大志.論馬克思主義文化思想的哲學意蘊[J].社科縱橫,2015(12).
[3]馬克思.博士論文[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4]俞吾金.“消滅哲學”還是“揚棄哲學”?[J].世界哲學,2011(3).
[5]衣俊卿.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6]何麗野.馬克思要“消滅”和“實現”的是什么哲學[J].哲學動態,2014(5).
[7]劉卓紅,盧文忠.唯物史觀創立進程中的馬克思早期文化批判研究[J].馬克思主義研究,2013(8).
[8]陳先達.哲學中的問題與問題中的哲學[J].中國社會科學,2006(2).
[9]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節選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0]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1]鄒詩鵬.激進政治的興起:馬克思早期政治與法哲學批判手稿的當代解讀[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B0-0
A
1007-9106(2016)11-0082-04
*本文為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二五”規劃項目“馬克思文化批判思想及其當代價值研究”(GD13CMK01)的階段性成果。
盧文忠(1985—),男,廣東警官學院思政部講師,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文化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