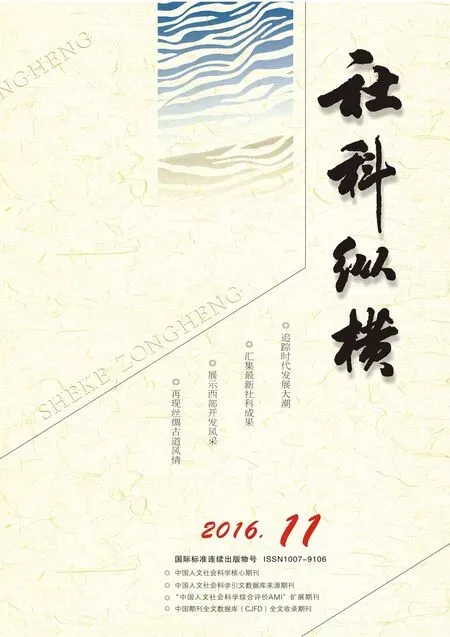再談庭審中心主義
韓紅俊 薛少峰
(西北政法大學 陜西 西安 710063)
·法學探討·
再談庭審中心主義
韓紅俊 薛少峰
(西北政法大學 陜西 西安 710063)
庭審中心主義對于提高訴訟效率,保障獨立審判,增強訴訟權威性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庭前準備不充分、當事人訴訟能力欠缺和法官釋明不足等原因,導致庭審混亂、效果不佳。因此,應完善庭前準備程序,取消庭審階段的劃分,提高法官的庭審駕馭能力,從而保證訴訟的正當性。
庭審中心 庭前準備 程序保障
庭審中心主義是上個世紀80、90年代審判方式改革的過程中,為確保司法的去行政化、司法公開、法官職權為主向當事人參與轉變提出了“證在法庭、辯在法庭、判在法庭”,確立了未經法庭質證的證據不能作為定案依據的規則。在司法改革的進程中,為保障法庭成為訴訟的中心,法官成為法院的核心起到了積極的推進作用。但由于配套機制的不健全,庭前準備工作的不充分,過分強調當事人主導,淡化法院的主導,庭審往往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
一、庭審中心主義的程序保障功能
庭審是固定爭點、查明事實和正確適用法律的基礎,是訴訟活動的關鍵環節。“庭審中心主義”強調開庭審理在整個民事訴訟中的重要作用,其主要體現在,證據的認定,案件事實的查明,應當在庭審過程中,同時庭審活動決定判決的形成。這體現了現代訴訟的一般原理,開庭審理是法院解決民事糾紛的基本方法,而庭審程序是民事訴訟獲得正當性的最重要的環節。[1]
(一)庭審中心主義增強了判決的權威性
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未經質證的證據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法律依據。旨在防止法官的突襲審判,更重要的是尊重當事人的程序主體性,調動訴訟雙方當事人參與到庭審中來。在庭審中,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負有舉證責任。同時在反駁對方當事人的主張時也應當提供必要的證據和理由。這就在很大程度上調動了當事人的積極性,因為裁判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當事人自己的行為。由于程序的進行蒙受了不利結果的訴訟當事人,因為自己已經被給予了充分的機會提供證據,行使各項訴訟權利,所以該當事人對結果的不滿就失去了客觀的依據而只能接受。這體現了程序上的公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和吸收當事人內在的對審判結果的不滿,增強了判決的權威性,由此實現了服判息訴的目的。
(二)庭審中心主義排除了外部干擾
庭審過程中訴訟各方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積極進行攻擊防御,合議庭需要對案件的事實是否清楚、證據是否充分,法律責任應當如何分配以及訴訟費用如何分擔依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作出裁判。庭審資料成為合議評判的依據、審判委員會研究討論的依據和制作判決的依據,任何形式的研究決定和裁判制作,均不能違背庭審查明的事實和認定采信之證據。裁判結果需要在判決理由及依據方面對當事人雙方進行的主張和舉證作出回應,這能使判決更具有說服力,其他人很難參與其中。因此,庭審中心主義可以從某種程度上排除外部干擾。
(三)庭審中心主義提高了訴訟效率
在臺灣、日本的法庭審理中,庭審超過1個小時的很少見,一個法庭甚至一天開了8個庭,這是由于大陸法系許多國家和地區規定“未確定爭點前法庭不得調查證據”,大大節省了庭審時間,提高了訴訟效率。現在法院普遍面臨著案多人少的矛盾,實行立案登記后法院受理的案件不同程度增加,為了盡快結案,法官都希望能在一次開庭中審結案件,尤其是二審案件。但只有在開庭審理前作好了充分的準備,庭審才能夠順暢且富有效率的進行。庭審中心主義要求法官庭前對案件的情況有基本的了解,梳理案件的訴訟爭點;在庭審中引導指導雙方當事人及訴訟代理人圍繞訴訟爭點展開辯論;裁判以庭審為基礎而作出。庭審中心主義在強調規范庭審程序的同時也注重強調要建立相應完備的庭前程序,提高庭審效率,加快訴訟進程,由此來減輕法官的工作量,提高司法公信力。
二、庭審中心主義在司法實踐中的問題
庭審是訴訟的關鍵環節,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案件審理的質量、效率和效果,對于這一點已經達成了共識,各級法院也逐步重視庭審中心化。但在司法實踐中,庭審中仍存在著一些問題。
(一)庭審前準備不足
從當事人的角度看,法律沒有要求必須庭前答辯。從法官的角度看,當事人不答辯,案件數量多,導致無法準備。當然,不會準備也是一個原因。法學院沒教過,立法和司法解釋沒做規定,怎樣才叫“準備好”?標準很模糊,會不會準備過頭了,又被批“先定后審”?因此,無答辯、無證據交換、無爭點的“三無”庭審,以及訴請不明確、審理對象不明確、審理范圍不明確的“三不明”庭審,是當前庭審方中存在的普遍問題,爭議焦點歸納不清晰,當事人舉證和辯論沒有針對性,以至于庭審功能紊亂,庭審效果不佳。
(二)當事人訴訟能力欠缺,法官釋明不夠
我國未實行強制律師代理制,很多案件當事人沒有律師代理,當事人訴訟能力較低,不知如何提出訴訟請求、或者訴訟請求不適當;只知道追求客觀真實,不知道要提供證據,更不知如何提供證據、質證。因此,需要法官在不違反中立性的基礎上,需要進行釋明。釋明有助于防止突襲性裁判,為當事人就作為判決基礎的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充分發表意見提供機會,使程序更加充實和透明。在當事人訴訟請求不明時,法官詢問和提示較多,但在事實主張不清、證據材料不充分時,法官的釋明較少。甚至部分庭審存在舉證責任分配不當的情況。
(三)庭審的實質效果不佳
庭審中的突襲答辯和舉證普遍存在,被告庭前提交答辯狀的案件不足20%,大多是當庭表達,庭前原、被告未能交換意見,造成補充證據不斷;法官對證據關聯性重視不夠,放任無關聯的信息進入訴訟,不僅降低了訴訟效率,而且常常誤導法官的判斷;由于缺乏交叉詢問技術,法官對人證無法識別真偽,很多證人不出庭,當事人陳述也很少發揮證據作用,大大削弱了庭審的實效。
(四)庭審的混亂
在實際的庭審過程中,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的刻意分立也造成了庭審效率的低下。立法將開庭審理分為以下幾個步驟:宣布開庭、法庭調查、法庭辯論和最后稱述。法庭調查的目的和任務是在經過上述程序后,全面而客觀的揭示案件事實,為之后的法庭辯論做準備。法庭辯論則是民事訴訟法中辯論原則的集中體現,主要目的是,通過雙方當事人的辯論進一步查明案件事實,分清是非責任,以便做出公正的裁判。但事實上,在司法運作中很難將法庭調查與法庭辯論區分開來。因為,在法庭調查階段涉及到舉證責任的分配、實體法律關系的認定和待證事實的確定;在質證階段需要對證據的客觀性、合法性和關聯性進行爭辯,這些都需要在法庭辯論中展開。同樣在法庭辯論階段也會涉及到法庭調查階段的內容,根據我國法律的規定,法庭辯論是在法庭調查已經充分揭示案件事實的基礎上進行的,但實際上在法庭辯論中有關法律問題的辯論與事實有著內在的聯系,法律問題與事實問題經常相互交織在一起。由于證據問題與事實問題存在著內在的聯系,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也存在著內在的聯系,而立法上將法庭調查與法庭辯論的刻意分立,使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被打亂,這就造成了在法庭調查階段經常出現的情形,即當事人在發表有某些針對性的反駁意見時被法官打斷,告知其現在是法庭調查階段而不是法庭辯論階段,不要進行辯論,到了法庭辯論階段自然會讓雙方當事人進行充分的辯論。從而這就容易致使當事人在表達某些辯論意見時,在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兩個階段的交錯中落空。此外,在法庭辯論中當事人雙方在辯論中就可能因為提出新的觀點,而又將涉及新的法律事實。我國民事訴訟法允許在開庭審理階段提出新的事實和證據,此時法庭需要對新提出的事實和證據進行質證、認證,這就必然使法庭終結已經開始的法庭辯論程序,重新開啟已經結束的法庭調查程序。這種情形會導致對一個案件的多次開庭以及庭審效率的低下。
(五)庭審的形式化
由于開庭審理是一審的必經步驟,現在有的法庭,庭審程序一步不落,但問題卻沒有解決,法官的精力主要放在審判程序有無遺漏,而不是如何解決紛爭上。結果一個庭開下來,當事人稀里糊涂,法官也稀里糊涂。要防止庭審中的形式主義,有必要重新強調開庭的目的是解決問題,而不是機械地走程序。法官在辦案時不應當將其主要精力放到庭外詢問當事人和反復進行調解的活動上,而是應當主動向當事人釋明其在庭前所享有的權利和義務,積極推動庭前的證據開示、總結案件的訴訟爭點,由此才不會導致庭審功能的弱化即庭審程序的虛置。此外,實踐中的將案件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和請示匯報制度也弱化了庭審功能。
三、庭審中心主義的推進措施
庭審中心主義可以防止突襲裁判,提高司法的權威和當事人對生效裁判的接受度。欲使庭審發揮應有作用,須有配套制度和相應措施。
(一)庭前準備程序的完善
充分的庭前準備,是優質高效庭審的基礎和保證。在開庭審理前,雙方當事人在法官的主持下,對案件的爭點及相關證據進行整理,以明確爭點及法庭調查的證據,為正式的開庭審理做準備,這是審前準備程序最具實質性的內容之一。
1.強制答辯制度的建立
被告的答辯是整理案件爭議焦點的前提,是法院組織雙方當事人進行證據交換的基礎,如果被告在審前不提交答辯狀則不僅會使整個庭前程序處于虛置狀態,從而導致庭審效率低下,而且還會增加的訴訟成本,浪費了司法資源。[2]從程序公正的角度出發,訴訟中注重的是雙方當事人的武器平等,即在攻擊或防御方法上強調在對方知悉的情況下進行,反對繼續進行證據的突襲,強調訴訟效益以及要求庭審應當在雙方有充分準備和在法庭組織的有秩序的情形下進行集中審理。因此,有必要建立相應的強制答辯制度,明確規定被告在接到起訴狀后必須提交答辯狀,并給予相應的時間規定,同時規定在被告逾期沒有提交答辯狀的情況下,除非有足夠的免責事由,否則產生直接承認原告訴訟主張的法律后果。
2.案件訴訟爭點的整理與固定
在庭前準備程序中最重要的是案件訴訟爭點的整理和明確。司法實務中往往是一邊進行案件的證據調查,一邊整理案件的爭議焦點,這無疑就造成了案件審理的拖延,弱化了庭審功能。
爭點整理,是指對民事訴訟當事人間就證據、事實問題、法律問題和訴訟標的存在的爭議予以總結、固定的行為。我國2012年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4項和最高人民法院新頒布的司法解釋中第224條至第229條都規定了開庭準備程序的內容,強調了在答辯期屆滿后應當進行證據交換、組織庭前會議、通過庭前會議明確案件的爭議焦點以及就法官歸納的爭議焦點征求當事人的意見。但是其對案件的爭議焦點歸納的規定還較為概括,沒有設置詳細的規定來進一步細化整理案件的爭議焦點的程序。
對爭點的整理應該遵循邏輯順序,訴訟標的確定,蘊涵于其中的法律爭點才能明確;只有法律要件明確,待證事實才能被確定;而只有待證事實確定,證據爭點才能呈現出來。考察實踐中法官們的思維,他們有時是在事實與法律間進行“來回穿梭的觀察”,一方面,法官們須依案件的法律爭點去探尋事實與證據爭點;另一方面,法官須從展現出來的事實與證據爭點重新去探討已歸納出來的法律爭點,作一些擴充與限縮,之后,再返回事實與證據爭點補充分析。實踐中,法官們所進行的是一種相互闡明的思考過程。
此外,對案件爭點的整理主要是法官的職責,沒有規定當事人可以自行進行案件爭點的整理,未能充分調動當事人的積極性。[3]若能對庭前準備程序的效果也沒有做出相應的規定,即在庭前準備程序中沒有主張的事項在庭前準備程序之后開庭審理中不得進行主張,則當事人會積極參與到爭點的整理進程中來。
(二)庭審階段劃分的取消
庭審的主要功能應當是在法官的主持下,當事人圍繞著案件的爭議焦點展開充分的舉證、質證和辯論,查明案件事實、分清是非責任。民事訴訟將開庭審理程序劃分為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兩個互不重合、各自運行的階段,其不僅硬性地割裂了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的聯系,致使其在庭審過程中審查了許多與案件事實不相干的證據,而且弱化了庭審程序中的言詞辯論。例如在一起陰雨天發生的一起交通事故案件,在庭審中一方當事人提供了許多與天氣相關的證據,其想證明當時的天氣情況是是如何的惡劣,出借人不應該在明知天氣狀況不好的情況下出借自己的摩托車。而本案的實質焦點應當是出借人在出借自己摩托車時是否盡到了自己的審慎義務,即承租人是否具有駕駛資格,而非什么天氣因素。由此可見,對這種與案件并無太大關系的證據的審查不僅會影響庭審的效率而且對案件事實的查清并無太大幫助。而弱化庭審中的言詞辯論則主要表現為,正是由于過多的審查了一些與案件不甚相關的證據從而影響到對那些與案件相關的重要事實和證據沒有得到充分和質證和辯論,最終致使案件的全部事實沒有查清。因此有必要取消這種過于僵硬的兩階段的劃分。《司法解釋》第230條規定,法官在征得當事人的同意后,可將兩階段合并進行。由此可以看出對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的劃分正朝著取消的方向發展。此外,國外的民事訴訟法也未將法庭審理劃分為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兩個階段。例如在法國的民事訴訟程序中,其辯論程序為庭審程序。在辯論程序之前還有事前的準備程序,準備程序主要是對案件的爭議焦點和證據進行整理,為辯論程序做準備。辯論程序是民事訴訟的核心程序,原告關于訴訟請求的稱述、有關的證據評價,被告的抗辯以及雙方之間關于各焦點的辯論都在該程序中進行,其沒有將辯論程序再進一步的劃分。
(三)建立庭審的程序性保障
庭審程序中主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對案件事實的認定。強化對案件事實認定的其最主要的是要加強對庭審制度的程序性保障。現代民事訴訟程序保障對庭審程序的基本要求是直接言詞原則,直接言詞原則是由直接審理原則和言詞原則的合并。
直接審理原則要求對案件作出裁判的法官應該直接對證據進行審查,未親歷證據審查的法官不能對案件事實作出裁判。法官對個案的處理必須親歷其境,直接審查證據和事實,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形成對案件事實的內心確信。對證據與事實的親歷性即直接感知,能夠使事實判斷者掌握豐富與生動的信息內容,而這些信息內容是形成合理心證最重要的保證。言詞原則,意味著訴訟不再以卷宗為中心,是指法庭審理須以口頭陳述的方式進行。包括當事人要以口頭進行陳述、舉證和辯論,證人、鑒定人要口頭作證或陳述,法官要以口頭的形式進行詢問調查。除非法律有特別規定,凡是未經口頭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定案的依據采納。這必然需要加強庭審的舉證、質證、辯論環節,落實證人、鑒定人出庭等。
直接言辭原則的另一個核心內容就是事實上的審理者與裁決的作出者在主體上應當保持同一性,把審判者以外的司法人員和機關排除在認定案件事實的主體之外。因此,應盡量限制直至取消我國現行司法實踐中審判委員會對案件的討論以及下級人民法院向上級人民法院的請示匯報行為。
(四)提高法官的庭審駕馭能力
庭審中,法官的言行會給當事人、旁聽群眾留下深刻的印象,是社會大眾直接感受法院形象的重要途徑,庭審能力強,司法的公信度也會隨之提高。[4]庭前準備階段,法官要及時對雙方有爭議和無爭議的事實和證據進行歸納總結。庭審中,法官認真聽取當事的訴請和抗辯意見,是法官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關鍵,再次確認有爭議事實和無爭議事實;對于當事人的質證,法官要能引導當事人針對證據的三性和證據能力進行;要認真聽取當事人關于證據和待證事實關系以及適用法律的辯論意見,以便能將裁判限制在當事人提出的范圍內;在合議階段,法官應當具備分析判斷、法律適用和裁判說理能力。
[1]吳澤勇.論我國民事訴訟庭審程序的正當化建構[J].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04(2):7.
[2]畢玉謙.對我國民事訴訟審前程序與審理程序對接的功能性反思與構建——從比較法的視野看我國民事訴訟法的修改[J].比較法研究,2012(5):20.
[3]許士宦著.新民事訴訟法[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201-202.
[4]蔣惠嶺.重提庭審中心主義[N].人民法院報,2014-4-1.
D925.2
A
1007-9106(2016)11-0112-04
韓紅俊,西北政法大學教授,法學博士;薛少峰,西北政法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