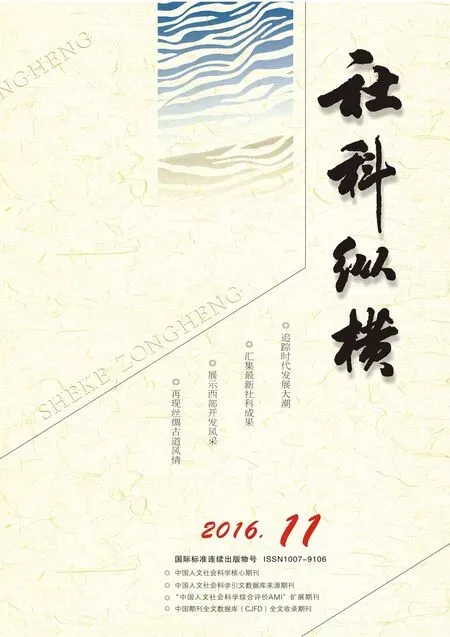客家商幫的形成演變及歷史影響
閆恩虎
(嘉應學院;“客商”研究所 廣東 梅州 514015)
·史學研究·
客家商幫的形成演變及歷史影響
閆恩虎
(嘉應學院;“客商”研究所 廣東 梅州 514015)
客家商幫是明清時期廣東四大商幫(潮商幫、廣府商幫、客家商幫、海南商幫)之一。因為強有力的社團組織以及海外網絡的延伸,在近現代社會劇烈變革中它不僅沒有消失,反而不斷演變壯大。目前客家商幫(簡稱“客商”)已經超越傳統商幫的內涵,演變為全世界客籍實業家的組織,是華商網絡的重要成員和積極組織者。客家商幫及其成員在近現代史上有重要影響,對其形成演變以及歷史影響的研究有助于當前商業文化建設和儒商文明的弘揚,對國家安全體系的構建也有積極作用。
客家商幫 形成 演變 歷史影響 研究意義
一、客家人及其悠久的商業傳統
客家人是西晉永嘉年間黃河流域的一部分漢人,因戰亂南徙渡江,逐步南遷形成。根據羅香林先生研究,分五次大規模遷徙:公元317—879年間、880—1126年間、1127—1644年間、1645—1843年間、1866年以后。[1](PP59)目前南中國省區及南太平洋主要國家都有客家人,尤以粵東(梅州、河源、惠州)閩西(汀州、龍巖)贛南(贛州)三省交界處最為集中。客家人在遷徙中將中原文化和先進的經濟組織方式帶到南中國邊遠山區及南太平洋各國,為當地的社會經濟發展作出重要貢獻。客家人是廣東三大民系之一。梅州號稱“世界客都”,是客家人的核心聚居地,下轄梅江區、梅縣、興寧、平遠、蕉嶺、五華、豐順、大埔等八個縣(區、市)。本文的例證主要以梅州地區為主。
客家人崇文,但不蔑商輕商。因為在遷徙定居中,一般只能選擇偏僻的山區。山區土地資源有限而且貧瘠,隨著族群的繁衍,人口越來越多,脆弱的農業經濟不能支撐他們的生存與發展,經商成為客家人謀生發展的重要途徑。粵閩贛客家聚落圈有著悠久的商業傳統。南北朝后期到唐末,梅縣水車窯聞名遐邇,其青瓷是當時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商品。《舊唐文》記載,唐代德宗時期(公元780年),有“波斯”、“古暹本”(古時泰國的附屬地方)的大型船舶從海上順風到達潮州進行青瓷貿易。1980年,泰國北部清邁地區發現荷葉式四瓣口青瓷大碗,海南省陵水縣的海灘上也發現成捆的同類青瓷大碗。經考證,都為唐代梅縣水車窯的產品。福建連城客家人雕版印刷業在明清時期名聞天下,與北京、武漢、江西許灣并稱為中國古代四大雕版印刷基地。鼎盛時期“刷就發販幾半天下”、“壟斷江南,行銷全國”。據《范陽鄒氏族譜》載:明末鄒保初“貿易于廣東興寧縣,頗獲利,遂娶妻育子。因居其地,刊刻經書出售。至康熙二年辛酉,方搬回本里,置宅買田,并撫養諸侄,仍賣治生。閩汀四堡書坊,實公所創也”。[2](P65)宋代,以鹽業為中心的潮州海販業及糧食貿易促成跨粵閩贛的潮汀贛梅貿易區繁榮。
宋鄭強《移創州學記》說:“汀在(閩)西南境,介于虔(贛)梅之間,銅鹽之間道所在”。明清時期的《潮州府志》載:“(大埔)高陂瓷僅追蹤于江西省景德鎮”。其產品遠銷東南亞,號稱“南國瓷鄉”。汕頭開埠以后,大埔瓷器更是一直居于大宗商品出口的前列。明清時期,梅縣松口是著名的商埠,舟楫往來、商賈云集,以至于客家山歌從這里傳到四方。而客聚地之一的贛州,在宋時已是南北商貿匯聚的中心。粵東的興寧,在民國時期,一直有“小香港”之稱。
二、客家商幫的形成演變
客家商幫(簡稱“客商”)的形成在明末清初時期,以外拓為主,商跡遍布國內,縱橫南洋。其演變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大多是地域性組織;第二階段是在客家意識覺醒后,冠以“客家”“客屬”名;第三階段是全球“客商”網絡的形成。
(一)早期客家商幫地域特征明顯,多以省或州縣冠名
商幫的三大特征:會館、章程和活動區域。客家人崇文,客家商幫所到之處一般都建有會館。“凡都會之區,嘉屬人士,足跡所到者,莫不有會館”(《光緒二年建筑省城嘉屬會館碑記》)。早期客家商幫在國內建立的會館多以“廣東會館”“江西會館”或州縣冠名,是一個地域商人組織。據劉正剛教授研究,在清代前期(1644—1840),不少客家幫商人隨移民入四川經商,在重慶、瀘州及各縣城建立會館者有17個。[3](P358-361)四川成都的洛帶古鎮是清初客家商幫在華西的重要商務會聚中心,那兒的“客商”會館都是地域性的命名:廣東會館(南華宮)、江西會館(萬壽宮)、湖廣會館等。
據《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輯》統計,嘉慶年間(1796-1820),蘇州就有嘉應會館修建的碑記17塊之多,反映了清代前期客家幫商人在江蘇經商十分活躍和會館活動興旺。[4](P251-253)嘉慶十八年(1813)《嘉應會館碑記》載:“我嘉一郡五屬,來此千里而遙,坐賈行商,日新月盛。性向未立會館,咸以為缺事,泰(董事)等托足此地二十余年,承各位鄉臺及先達來往者。盛不以為不才而囑倡其事”。[5](P350)道光年間,廣東的廣府商人、潮州商人和客家商人在蘇州城外蓮花兜共建“海珠山館”。[6](P208)
清代潮州城已經成為潮汀贛梅經濟中心,商人紛紛云集,客家商人建有“汀龍(福建汀州、龍巖)會館”、“鎮平(蕉嶺)會館”等。意溪鎮是客家商人集中的地方,有眾多的客家會館,其中和平館為建筑規模最大的一個客家會館,由福建連城人創辦,廣東、福建二省共管,專做杉木貿易;金豐館由福建永定客家人創建,除作為貿易中介之外,有時還直接收購轉賣貨主的杉木板;銀溪館由大埔銀江人創建,專做銀溪河的大杉生意;豐埔總館由豐順、大埔兩縣聯合創辦的竹館,免費為豐順、大埔兩縣的貨主和放排工人提供食宿,同時按2%的比例向貿易雙方收取中介費,用于支付館內的日常開支。在意溪,還有橡埔、鄞江等會館。這些會館都是地域性組織,大多是潮籍商人、客籍商人和福建籍商人共同組織的。
在康雍乾時期(1662—1795),客家人到東南亞國家經商貿易定居者有300多萬。[7](P178)到了清代后期,客家幫商人到外國經商而建立會館為數不少,計新加坡、馬來西亞就有21個,美國舊金山2個,加拿大維多利亞1個。[4](P251-253)越南堤岸的“義安會館”是客家商幫和潮州商幫共同建立的,始建與明末,義安在東晉轄今天粵東潮梅地區、閩南的漳浦、云霄、詔安等縣。同治五年(1866)重修、光緒二十八年(1902)大規模改建,留下幾塊碑記。其中《重修義安會館碑記》開頭第一句:“我堤岸義安會館,依隋代古郡以立名,合潮循道(今潮梅地區)屬而共建”。并在《重建義安會館序》中對“義安”二字做了特別的解釋:“為鄉情而適義,會梓誼以問安”。在碑記中寫到:“會館之建設久矣。其初為潮客兩幫諸商董協力同心,創成基址。凡吾兩幫人等來南者,皆得賴以聯絡鄉情,會議商務。即今左右門楣,懸掛公所,潮客兩幫,相對輝映,所以壯會館之觀瞻也”。[8](P20-21)
可以看出,早期客籍商人基本上是沿襲中國傳統的地域幫屬,并未強調民系或族群的理念。
(二)客家族群自覺的加強與客家商幫的獨立
客家人是不斷遷徙的,地域觀念本來淡泊。但客家人在遷徙過程中一直受到其它族群的歧視。“粵人”的記述中對于客家的記載大部分是負面的,如崇禎《東莞縣志》(1639年)稱客家人“獠”,在許多地方志中客家人還經常被稱為“匪”。而無法避免的“土客之爭”更使客家人生存面臨巨大威脅,族群必須團結。僅清一代,兩廣地區“土客之爭”的武裝械斗就有幾百次,死亡一百多萬人,曾一度使人口劇減。清咸豐年間,廣東平興縣內“土客”械斗曾將城坪民居“夷為平地”。清咸豐(1854年)至同治年間(1867年),在廣東的開平、恩平一帶發生大規模“土客大械斗”事件,驚動一時,破壞程度極大,死者達數十萬人,田屋財產毀壞更是無計。清政府為了平定械斗,曾一度“逐客”。劉坤一任兩廣總督時,曾設“土客永安局”以防“土客械斗”。[9](P234)在南洋各地,客家人與當地土著及其他族群和商派的沖突也愈演愈烈。當時吉隆坡的開拓者客家人葉德來“遣子弟回嘉應,幕義勇,葉氏舉族萬余人,皆度海助戰,而鄰近村落應之者亦奪,他邑之流寓其地者皆從”。[10](P132)1907年,順德籍著名學者黃節在編著《廣東鄉土地理教科書》時,將客家人劃在“漢種”之外,更是將對客家人的排擠上升到意識形態。當時客籍學者立即予以批駁。20年代末,歷史學家羅香林教授撰寫了《客家研究導論》,科學地證明了“客家為漢族里頭的一個支系”,有力地批駁了將客家誣為“語言啁啾不甚開化”、“野蠻的部落,退化的人民”等種種論調。其后他推出了《客家源流考》,系統闡述了客家的源流和系統、客家的分布及其自然環境、客家語言特征等,全面有力地證實客家人是華夏正脈。“獨憶30年前,我客屬人士,僑居香港,以無統屬團體,常遭意外歧視”。[11](P5)由此,客家認同由族群團結上升到文化凝聚。“語言是思維的外殼”,是文化的直接征象。客家話是他們認知的重要紐帶。“在民系認同標準中,文化方言是第一位的,其次是血緣關系(裔承與體格),地緣關系是第三位的”。[12](P478)
客家商幫的獨立組織最先是在南洋形成。1795年,廣東客家商人和福建客籍商人共同在檳榔嶼組織廣汀會館。這是第一個打破區域觀念的純客屬商幫組織,但當時并沒有冠名“客”字。其后在1840年前后,檳榔嶼的永定籍客家人和大埔籍客家人結盟,成立永大會館。隨著客家人聯系的日益廣泛,在19世紀,客家人的這種聯合會館在東南亞分布極廣,遍布新馬各地。[13](P95)這些客屬會館的會員除廣東、福建的客家人外,還有廣西、湖南、湖北天門籍客家人。但大多沒有以“客籍”或“客家”冠名。
最早以“客”冠名的客籍會館是1865年在印尼成立的客屬總義祠。“客家人在東印度之團體組織,其歷史較長者,當以巴達維亞之客屬總義祠為最著”。[14](P4)梅州籍印尼的客家商人1882年在吧城成立客屬總義祠,以后泰國的客家商人成立“合艾客屬會館”等;旅居馬來西亞的梅州籍客家商人也組織了各地的客籍會館。上個世紀初,梅縣籍旅泰國“客商”僑領伍佐南以團結客屬同胞為己任,將泰國兩個客籍會館于1910年合并,正式組成“暹羅客屬會所”,并向暹羅政府立案,成為合法社團。以后,美國的舊金山、非洲的南非、毛里求斯以及南美洲等地先后出現各種客家會館或客屬聯誼會。
(三)客屬公會成立——全球“客商”網絡的形成
文化認知的推動作用,使世界各地的“客商”組織普遍認為必須有一個統一的組織,溝通團結,更有利于事業發展,更有利于與祖國的聯系。“本洲屬僑雖眾,然向乏聯絡,無共同組織也”。[14](P4)進入20世紀20年代,“客人南來日眾,人事交接日繁,分布區域日廣,社會關系日密,非作有組織之大團結,不足以聯絡感情,互通音問,及收團結互助之效”。[15](P16)廣泛地團結客屬華僑力量,維護華商的合法權益,影響殖民當局的各項政策,被“客商”領袖視為一項緊迫任務。“自合群組織發達以來,團體構成,指不勝屈,或以地方為區別,則感于疆域之不廣,或以姓氏為依歸,則感于群道之不足,若崇正總會,則以語言為系統,為客族之集團,橫貫數行省之地區,綜合百家姓氏之群眾,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兼收并蓄,團結精誠,其集思廣益之功,較之同鄉同姓之團體,實更巨大”。[16](P72)
1921年,當“客商”領袖胡文虎在香港設立第一家永安堂分行時,就參與香港崇正總會的建立活動。1928年當選為會長,繼而成為該會永遠名譽會長。
1923年,胡文虎等“客商”領袖籌建南洋客屬總會,1929年8月23日,南洋客屬總會正式在新加坡舉行開幕典禮,胡文虎被推選為會長,并歷屆蟬聯,成為新馬華僑社會的著名領袖。南洋客屬總會不僅是團結新馬客屬人士的核心組織,而且也是聯系東南亞各地客家同鄉的唯一紐帶,南洋客屬總會經常與世界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之客屬僑團保持聯系,發揮溝通聲氣和團結互助之橋梁作用,對加強各地客屬僑胞之間的聯絡、協作,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抗戰爆發后,胡文虎以南洋客屬總會會長名義,推進客家社團組織的發展,特派代表到南洋各地宣傳發動組建客屬公會,“各地同僑,應起而組織客屬公會,以符合先有小組織,而后有大組織,先有小團結,而后始能大團結之主旨”。[14](P8)遇到籌備費用不足時,胡文虎則資助重金,因而南洋各地的客屬公會紛紛成立。在短短的一年中,共有53個客屬公會成立,分布在馬來亞、沙撈越、印尼、緬甸等地。這些客屬公會在組織關系上都隸屬于客屬總會,并直接由總會領導,形成了系統的客家社團聯絡體系。[17](P21)1946年,“暹羅客屬會所”更名為“泰國華僑客屬總會”,制訂有為僑胞服務的“生有所養,長有所教,病有所治,死有所歸”的福利措施,提出了擴充華僑校舍、籌辦公立醫院、增設新的“義山”(指無依無靠的華僑去世后安宿之地)的計劃。
1971年9月,世界各國和地區近50個客屬團體及代表數百人,在香港發起成立世界客屬總會,創會宗旨為:宣揚客家精神,加強屬人團結,凝聚屬人力量。推動并傳達全球客屬人士的工商業和文化活動,使各地客屬人士能進一步了解和團結,使客家人的優良傳統,果敢、剛毅、刻苦耐勞的精神,在全世界形成一股受人尊重的組織力量。
至此,以“客商”為核心的全球客屬網絡正式建立。“客商”也由早期的行商、傳統商幫演變成為具有全球網絡的客籍實業家組織。
三、客家商幫的歷史影響
(一)客家商幫是近現代“實業救國”和“實業興國”的重要力量。近現代化,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工業化。興辦實業,發展民族工業,和西方列強競爭,是近現代愛國興國的根本,是愛國實業家的歷史使命。“客商”是近現代高舉“實業救國”的愛國商幫。僅廣東大埔籍“客商”張弼士一人,就是中國葡萄酒制造業、農業機械制造業和玻璃制造業的創始人,也是中國近代海運業、鐵路業、金融業和海外華文教育的奠基人之一。廣東梅縣籍“客商”張榕軒張耀軒兄弟是近代鐵路業發展的積極推動者。廣東平遠籍“客商”姚德勝回國定居后,銳志建設家鄉,投資創辦印刷廠、紡織廠,開客家地區農村發展近代工業之先河。據統計,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在香港及海外被稱為行業大王的“客商”,僅梅州市就有十多個。
近現代史也是中國走出“天朝大國”迷夢,融入國際競爭的歷史。經濟實力的角逐,是國際競爭的核心和基礎。發展實業,提升民族工業的競爭力,不僅是實業家的職責,更重要的是需要政府的保護和支持。晚清和北洋政府的腐敗,使愛國實業家“實業救國”的理想屢屢受挫。呼吁社會引導政府重視支持民族實業的發展,是當時先進實業家的積極舉措。張弼士在清末首倡設立商部,保護華商利益。他在擔任清商部考察外埠商務大臣、太仆寺正卿以及北洋政府的總統府顧問、工商部高等顧問和南洋宣慰使期間,多次倡議政府興辦實業,振興民族工業,積極保護民族工業利益。1910年,江南開勸業會,張榕軒張耀軒兄弟帶頭捐資20萬光洋,用于倡導“實業救國”。1911年的“保路運動”,廣東的帶頭人就是張弼士,他強烈要求清政府收回出賣的路權,呼吁保路權在于“奪外蔑視之奸膽,申張正義以絕阻謀”。中國第一個具有比較系統的改良主義思想的實業家、一代“儒商”鄭觀應對張弼士尊崇備至,譽其為“商務中偉人”,并親自撰寫《張弼士君生平事略》,書中感言:“所最難者,擁厚資不自暇,晚年已垂老,不憚焦勞,無非欲提倡實業,遂其救國救民之志”。[18](P98)
改革開放后,當代海外“客商”不僅攜巨資回國興辦實業,振興民族工業,而且“客商”領袖還利用參政議政的機會,為政府出謀劃策,改善引資環境,支持實業發展,同時還利用海外中華商會的組織功能,團結海內外華商,積極開拓民族品牌,為“實業興國”作出杰出貢獻。著名的有曾憲梓(原全國人大常委、香港中華商會會長、“領帶大王”)、田家炳(著名慈善家、“人造革大王”),熊德龍(美國中華工商團體聯合會會長、美國熊氏集團主席)、余國春(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國貨大王”)等。國內“客商”也在改革中迅速崛起,繼承先賢的優良傳統,在“實業興國”方面成績顯著。著名的有洗滌業巨子梁亮勝(全國政協委員、絲寶集團董事長兼行政總裁)、地產巨子朱夢依(合生創展董事局主席)、印刷業巨子林光如(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星光集團董事局主席)等,梅縣雁洋鎮在上個世紀末崛起一個客籍實業家群體,名震廣東,極大地壯大了國內“客商”的聲勢,其中有著名的現代農業典范模式——“雁南飛模式”的創造者、寶麗華企業集團董事長葉華能等。[19](P3)
(二)“客商”為中國傳統“儒商”文化的現代轉型作出杰出貢獻,是現代“儒商”文化的積極踐行者。在中國傳統商幫體系中,“客商”和“徽商”是儒商文化的積極代表。徽州是朱子故里,有其他地方不可比的儒學傳統。徽人廣建書院,崇儒重道,形成了“儒風獨茂”的地方風情。在這種文化氛圍中,形成徽商“賈而好儒”的特征。[20](P96-102)客家人是衣冠南渡的中原詩禮縉紳后裔,歷來“崇文重教”。在這種社會文化環境下,形成“客商”文化深厚的“言商向儒”本質。“客商”追求或儒商合一或先賈后儒。前者如廣東梅縣籍“客商”謝逸橋謝良牧兄弟、謝樞泗(廣東梅縣人,泰國“宜發父子有限公司”的創始人,合艾市的開埠者)等,他們本身就是學者;后者如張榕軒張耀軒兄弟等。張氏兄弟在商事之余,不忘讀書修身,于1901、1911年先后出資輯錄刊成嘉應五屬的《梅水詩傳》共13卷,并捐資支持翰林院檢討溫仲和總纂編成《光緒嘉應州志》。張榕軒著有《海國公馀輯錄》6冊和《海國公馀雜著》3卷。張弼士初到南洋時,曾發過這樣的感慨:“大丈夫不能以文學致身通顯揚名顯親,亦當破萬里浪,建樹遐方,創興實業,為外國華僑生色,為祖國人種增輝”。[21](P70-75)這是對“客商”儒商本質的概括。
由于社會的劇烈變革,時代背景已經不同,現代儒商文化的內涵不同于傳統。傳統的“儒商”概念比較抽象,仁義為本、知書達禮,就是“儒商”,本質是個人修養的內涵。現代意義上的“儒商”,不再是知書達理舞文弄墨而已,而是一個社會意義的具體范疇,是在誠實守信的傳統儒商精神基礎上,具有愛國濟世的人文情懷。愛國,在近現代具體對商人而言,就是振興民族工業,支持發展教育事業,弘揚民族文化;濟世,就是熱心公益事業、造福人類。在這幾個方面,“客商”都走在時代的前列。
在弘揚誠實守信方面,比較中國傳統商幫文化,相對于“晉商”“徽商”的“重義”,“客商”更表現的是一種“崇仁”。“崇仁”在社會層面,表現為扶危濟困、修橋鋪路、興學救世;在經營層面,則表現為誠實守信。
在支持發展教育事業、弘揚民族文化方面,“客商”歷來是支持國內教育事業的重要力量,“客商”是近現代海外華文教育的開拓者和積極推動者。以張弼士為代表的近代“客商”領袖曾出巨資在廣東各地創辦學校,現中山大學有張弼士紀念堂。1902年,張耀軒以張榕軒的名義捐獻8萬兩銀給廣州一所高級中學作基金。他們兄弟捐贈10萬元給香港大學,并捐建嶺南大學“耀軒樓”。“客商”領袖胡文虎在20年代就捐巨資規劃在全中國每個縣設立現代中學,他先后在國內捐助過上海大廈大學、中山大學、嶺南大學、福州福建學院、廈門大學以及廣州仲愷農工學校、上海兩江女子體育專門學校和十二所中學。香港大學也于1951年初設立“胡文虎婦產科病系獎學金”。他的女兒胡仙繼承父志,在廣州、梅州、福建等地捐贈了6所小學。1993年10月,胡仙在福州注冊成立“胡文虎基金會”,將國內資產收益全部用于捐贈。她到處奔波,專事扶持教育事業。僅在江蘇泗洪縣就捐建了26座教學大樓,在福建興建15所學校,捐資達4000萬元以上,獲得“捐贈興辦公益事業突出貢獻獎”。令人矚目的是她把祖業廣州永安堂捐贈給廣州市人民政府作為廣州少年兒童圖書館館址。曾憲梓專門創立曾憲梓教育基金會,鼓勵中國高等師范院校的教師敬業重教和資助品學兼優的在校大學生。田家炳先生堅持自己“中國希望在教育”的信念,全力支持國內教育事業,甚至不惜賣掉自己在香港的豪華別墅,實現“中國每個省的師范大學都有田家炳教學大樓,廣東省每個市,梅州市每個縣、大埔縣每個鎮都有田家炳學校”。朱夢依設立的“合生珠江教育發展基金”市值約有10億元港幣。而海外華文教育則是在“客商”領袖張弼士、姚德勝等的倡導推動下發展的。1923年,中國駐緬甸臘戍領事梁紹文在其《南洋旅行漫記》一書中評道:“在南洋最先肯犧牲無數金錢辦學校的,要推張弼士為第一人。”“檳榔嶼的中華學校,相傳為華僑學校最先創辦,最有成績的,就是弼士所建筑的。中華學校客廳之中,供一尊泥像,只有兩尺高,坐在一張椅子上,手執雕毛羽扇,身穿長衫馬褂,態度雍容,面圓耳厚,眉間表露忠厚長者的神氣,安放在一個玻璃龕內,校內的職員早晚焚香供奉,這就是檳榔嶼教育界人士追念張弼士恩德的紀念品了”。[22](P32)據梅州電視臺《客商》專題片攝制組在馬來西亞的采訪報道,目前馬來西亞共有華文學校60多間,其中54間是“客商”興辦的。
在興辦社會公益事業方面,“客商”是當之無愧的優秀代表。近現代中國由積貧積弱遭列強宰割到獨立自主的發展中國家,期間充滿艱難辛苦,中國人民為國家和民族復興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熱愛人民、支持社會公益事業是近現代儒商優秀品質的體現。張弼士當年在汕頭市購置物業,設置汕頭育善堂,堂產用于國內福利基金和資助外出學子讀書。1900年,黃河決口成災,張弼士一次募集白銀百萬兩。他的慈善行為深得光緒皇帝的稱譽,清庭為其賜建“樂善好施”牌坊。姚德勝在這次賑災中一人一次匯出6萬銀元支援災區,光緒皇帝賜給他“樂善好施”圣匾一方。“客商”領袖除積極賑災救濟外,還在家鄉等各地捐款辦醫院、修橋鋪路。到“客商”的主要家鄉——廣東梅州參觀,到處可以看到他們捐款冠名的公益建設。曾憲梓是中國體育事業發展的重要資助人。姚美良(廣東大埔人,馬來西亞太平局紳、南源永芳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多次捐款支持文化事業,僅紀念黃遵憲誕辰105周年書畫展就囊括當時海內外最著名的華人書畫家作品,并在全國各大城市展出,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和整合。
(三)“客商”是近現代“華商”網絡的倡建者和積極推動者。由于持續移民遷徙的特殊歷史原因,客家人有著強烈的自組織意識。這種積極的組織意識和國家觀念相結合,使“客商”成為華商網絡建立和發展的積極推動者。華商網絡的核心組織——海外中華商會首先是在“客商”領袖張弼士的倡導組織下成立的(新加坡中華商會)。差不多與張弼士同時,姚德勝在馬來西亞怡保組建馬來西亞中華商會。以后,不僅海外各地的“客商”領袖積極成為華商網絡的組織者和領導者,而且“客商”的組織機構——各種客屬會館也成為華商網絡的主要機構,為海外華商和祖國建設的聯系作出杰出貢獻。
(四)“客商”是近現代民主革命和國家建設的積極支持者。從1893年至1911年的十九年里,清廷委任的六任五位的駐檳城領事(張弼士、張煜南、謝春生、梁碧如、戴欣然)都是當時的“客商”領袖,他們不僅冒著風險保護孫中山,而且還捐款支持,甚至讓子女參加革命。張弼士一次通過胡漢民捐款30萬兩白銀,還讓兒子參加同盟會。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客商”及其子弟就有16個,紅花崗四烈士就有兩個。辛亥革命以后,張弼士多次捐款支持國防建設。張弼士去逝,孫中山敬送花圈和挽聯,挽聯曰:“美酒榮獲金獎,飄香萬國;怪杰贏得人心,流芳千古”。[23](P337)謝逸橋謝良牧兄弟傾其家產支持追隨孫中山革命,是同盟會的早期組織者,1918年5月,孫中山親自到松口探望在家養病的謝逸橋,在謝家“愛春樓”住了三天,并為愛春樓題聯:“博愛從吾好,宜春有此家”;“愛國愛民,玉樹芝蘭佳子弟;春風春雨,朱樓畫棟好家居”。兩聯均嵌入“愛春”兩字,可見孫中山對謝氏兄弟感情之深摯。孫中山還閱讀了謝逸橋的詩抄,欣然命筆填寫一曲《虞美人》。姚德勝捐巨款資助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孫中山特頒發給他“一等嘉禾勛章”。張榕軒兄弟積極支持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后,革命黨人經濟拮據,張耀軒在同盟會會員謝逸橋的發動下,以其本人的名義捐了一大筆資金。1912年建立民國后,孫中山先生特為張耀軒親筆題贈“博愛”大字一幅,以表彰其對革命之貢獻。著名革命家鄭士良、廖仲愷、葉劍英及抗日名將葉挺、謝晉元、黃琪翔、羅卓英、范漢杰等都是“客商”子弟。抗戰爆發后,輟商回國參加抗戰有華僑抗日義勇軍大刀隊隊長周輝甫、鐘若潮等,而“客商”領袖蟻光炎則是抗戰第一個獻出生命的愛國僑領。胡文虎領導的南洋客屬總會,明確提出以抗日救亡為宗旨,“以團結的精神,一致的動作,在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下,表現吾屬人士救亡進行的熱烈”。在短期內籌得國幣30余萬元,成為籌款最多的南洋華僑團體。胡文虎本人僅在“七·七”事變至1939年4月間,所獻義捐及認購國民政府發行的抗日公債即達300余萬元。1941年回國慰勞義軍時又慨捐國幣200萬元,至于在不同時期所捐獻的物資、藥品等更是不計其數。廖安詳(廣東梅縣人,香港“香港亞洲貿易公司”的創辦者),在抗日戰爭期間,積極參與廖承志領導的港九“秘密大營救”,掩護搶救陷落香港的何香凝、柳亞子、茅盾、鄒韜奮、胡繩等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這些文化知名分別以丹青翰墨酬贈廖安詳。同時,廖安詳開辦“源吉行”籌集華南抗戰經費和物質。抗戰后,他在香港創辦“香港亞洲貿易公司”,支持中國的革命和建設。當代海內外“客商”領袖捐資支持國家建設的報道已頻見與各種媒體。1994年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臺將新發現3388號和2886的小行星報經國際小行星命名委員會審議核準,分別命名為“曾憲梓星”、“田家炳星”。
四、“客家商幫”研究的意義
(一)以“客商”個案深化中國商業文化和商業倫理研究,促進當前商業文化學和商業倫理學學科建設。目前我國商業理論領域的基礎研究嚴重滯后,國內高校尚沒有商業文化學和商業倫理學學科體系,只有個別論著和泛論的教材,有些甚至以營銷學代替商業文化,這是目前我國高等商科教育的重大缺陷。在經濟全球化競爭的背景下謀求發展,對有中國特色的商業文化學和商業倫理學意義重大。以“客商”研究作為個案,系統探索中國傳統商業文化和商業倫理,促進我國商業文化學和商業倫理學學科建設,以堅實的基礎研究推動商科教育的發展,培養學養深厚視野開闊的經濟管理人才和企業家人才。
(二)強化中國參與國際商業規則的制定和演化力度。長期以來,國際商業規則主要由歐美國家主導,成為“地中海文明”的專利。中國有著悠久的商業文明和商業傳統,從春秋時期齊桓公的“葵丘會盟”就可以看出當時完善的對外貿易規則體系。通過“客商”的實證研究,深化中國商業文明和商業倫理的研究整理,以令人信服的學術成果強化中國參與國際商業規則的制定與演化。
秦暉先生根據近期歐洲學者的研究成果認為歐洲早期也不存在什么“重商主義”,古希臘古羅馬一樣是重農抑商的。“所謂‘古代的重商主義'被認為是一種神話,無論希臘還是羅馬都以重農抑商為國策,以貴農賤商為正統價值觀,商業的發達只不過是一種‘末世'的腐敗現象(就像中國歷史上的王朝末世那樣?!)。在這一代學者筆下,過去的‘現代主義'者用以宣揚工商業重要性的種種論據幾乎都被一一否定;科路美拉開列的農場主經營賬只不過是寓言式的虛構,與實際狀況不相干;羅馬人消費的埃及小麥以及其他舶來品也不是商品,而是征服者勒索的貢賦;羅馬發達的公路系統主要不是用于工商業運輸,而幾乎完全是為軍事與行政服務的;羅馬的葡萄酒風行高盧,這并非由于生產葡萄酒的羅馬‘企業'通過技術、成本或價格上的競爭而贏得了市場,而僅僅是因為當地富豪出于‘本地的姜不辣'的心理,為炫豪夸奢擺闊氣才形成了這種時髦;等等。總之,這里不存在過去被視為西方‘傳統'的那種理性的‘經濟人',所謂市場的刺激只不過是今人臆想出來的‘烏托邦',成本、利潤、競爭、投資、需求之類的概念也從未為古希臘羅馬人所有”。[24](P305)
(三)弘揚“儒商”文化,進一步提高民族企業家素質。在經濟全球化競爭的背景下,發展壯大民族實業,積極的先進的商業文化是重要的促進因素。研究“客商”、“客商”文化,弘揚優秀儒商文化,積極改革和充實民族企業文化,提高企業家素質,增強企業競爭實力。正如著名歷史學家李約瑟、黃仁宇所言:“中國商人不缺乏積極主動、誠實、節儉、精打細算、機敏靈活的品格。這已經充分表現在他們作為商人的成功上在19世紀中國人僑居的所有海外國家,中國商人的成功遠遠超過當地人。但是,其他中國人所關心的只是政府以及它的難處。這些背景真正反映的是,中國問題的解決方案更可能要從傳統主旨的調整中去尋找,而不是模仿外面的世界”。[25](P15)
(四)有利于促進鞏固國家安全。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中國正在成為海洋大國。由于能源的現代傳輸體系,國家安全的重心(特別是主權安全、經濟安全)已經推移到海洋領域,尤其是南海(歷史上的南洋)。由于“客商”在南洋開發中的杰出歷史貢獻,東南亞各國政府和人民對“客商”領袖充滿尊重和懷念,至今,仍以各種形式紀念他們。歷史上“客商”領袖擔任東南亞國家領導人的有很多,目前正在東南亞主要國家擔任國家領導人的“客商”及其后裔也有多人(泰國的他信兄妹、新加坡的李光耀父子、菲律賓的阿基諾母子等)。東南亞各國是目前我國經濟貿易與合作的重要伙伴,也是關系我國國家安全尤其經濟安全的重要和敏感區域。進行“客商”與南洋開發的歷史研究,對于加深友誼,促進我國與東南亞各國的友好往來,抑制錯誤的“排華”意識有重要的意義。同時,對于增強東盟“10+3”合作中中國的參與力度有積極的作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公報》在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重點強調“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維護國家文化安全任務更加艱巨,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要求更加緊迫”。
(五)加強華商網絡的聯系,促進中國的對外貿易。歷來的海外中華商會,尤其是以新加坡、香港為代表的東南亞各國的中華商會中,“客商”有重大的影響。海外中華商會是目前華商網絡的核心組織,是發展我國對外貿易的重要橋梁,研究“客商”領袖,對于了解海外中華商會的歷史和貢獻、增強當前華商網絡的團結發展有積極作用。尤其是客籍商會領袖對祖國民主革命和經濟社會建設的貢獻,對于增強海外華商的愛國精神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1]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影印本),1992.
[2]陳日弟.淺談閩西四堡坊刻[J].福建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3(2).
[3]劉正剛.廣東會館論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4]黃啟臣.黃啟臣文集(二)[M].北京: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07.
[5]蘇州歷史博物館等.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
[6]范金民.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7]廣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廣東省志·華僑志[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
[8]黃挺.潮商文化[M].北京:華文出版社,2008.
[9]閆恩虎.客商概論[M].上海:文匯出版社,2009.
[10]李長傅.南洋華僑史[M].上海:上海書店,1991.
[11]陳承寬.香港崇正總會30周年紀念特刊序[A].崇正總會.崇正總會30周年紀念特刊[C].香港:崇正總會,1950.
[12]黃淑娉.廣東族群與區域文化研究[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13]顏清湟.新馬華人社會史[M].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1.
[14]元一.客屬海外各團體之組織與發展[A].崇正總會.崇正總會30周年紀念特刊[C].香港:崇正總會,1950.
[15]許云焦.胡氏事業史略[A].關楚璞.星洲十年[C].新加坡星島日報社,1939.
[16]羅平山.崇正總會三十周年紀念祝詞[A].崇正總會.崇正總會30周年紀念特刊[C].香港:崇正總會,1950.
[17]張侃.從社會資本到族群意識:以胡文虎與客家運動為例[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01).
[18]鄭觀應.張弼士君生平事略[A].沈云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75輯[C].臺北:臺灣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6.
[19]閆恩虎.廣東“客商”[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20]王世華.也談“賈而好儒”是徽商的特色[J].安徽史學,2004(01).
[21]商鳴臣.鄭觀應與張弼士經濟思想及實業經營管理之比較[J].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1997(2).
[22]梁紹文.南洋旅行漫記[M].上海:中華書局,1924.
[23]田辛墾,張廣哲.張弼士[A].黃偉經.客家名人錄(梅州地區第一大卷)[C].廣州:花城出版社,1992.
[24]秦暉.文化決定論的貧困——超越文化形態史觀[A].學問中國[C].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
[25]李約瑟,黃仁宇.中國社會的特質——一個技術層面的詮釋[J].Journal of Oviental Studies(Hong Kong),12;1/2(1974).
G127
A
1007-9106(2016)11-0123-08
*本文為廣東省人文社科省市共建重點研究基地——客家研究院2009年度招標課題“‘客商'與近現代中國”(課題批準號:09KYKT04)階段成果。
閆恩虎(1968—),男,嘉應學院經濟學教授,嘉應學院縣域經濟研究所所長,“客商”研究所所長,研究方向為發展經濟學、商業文化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