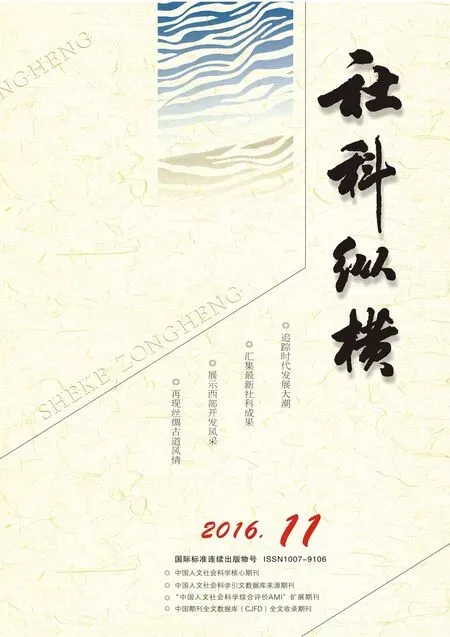傷痕書寫的閻連科模式
艾翔
(天津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天津 300191)
傷痕書寫的閻連科模式
艾翔
(天津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天津 300191)
通過對作家情節模式、人物設置、思想資源、身份特征、立場態度等方面的分析,確認其人其作透露出的強烈“曖昧”特質,而這種特質正是一些特立獨行、不偏不倚的優秀作家共有的稟賦;這一特質融入在小說所處理的社會歷史背景中,其實也就確立了閻連科的文學史位置,即對過去那個過于草率、未經充分發展及被中斷的傷痕文學傳統的深化和拓展,不但體現在對現代派技巧的征用,更克服了傷痕小說“脫歷史”的短板,建立起有效的歷史對話機制。但同時作家仍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這一思潮的前定,這是值得注意之處。
閻連科 曖昧 傷痕文學
根據自己近年所做的當代文學歷史化的研究工作,程光煒教授反復強調“文學史研究,并不完全認同一個作家對自己創作千奇百怪的解釋。針對復雜紛繁的創作現象,它要以文學思潮、流派、經典的顯微鏡做杠桿,去冷靜衡量和評估一個作家的意義,也不會相信批評家那些‘前所未有'的結論。”[1](P58)對閻連科這個似乎趨于完成經典化的作家的研究也應秉持這種立場。近年來該作家多次受到國內外矚目,2012年獲得馬來西亞華文文學最高獎“花蹤文學獎”,2013年獲得英國國際布克獎提名,2014年獲得卡夫卡文學獎,都迫使我們重新認真閱讀他的作品。
“曖昧的繾綣”
曾有論者將閻連科的《堅硬如水》同王蒙的“季節系列”作比較,認為紅色語言的洪流早已出現在王蒙筆下,并且透露出鮮明的理性批判色彩,然而閻連科不但了無新意,更“不可饒恕”的問題是“應該決絕的離開,閻連科卻投下了留戀的目光。暖昧的態度消解了批判的力量,作家立場的混亂最終導致了作品的混亂和讀者的無所適從。”[2](P40)似乎從《堅硬如水》里嗅出了某種不祥的氣息。
當然,我們可以從笑的角度對閻連科和王蒙做一區分,從中得到關于前者獨特性乃至獨創性的證明,但不能否認的是論者敏銳的感知力。《堅硬如水》并非“一邊倒”地拆解“革命話語”,這是相較指認作家的反抗立場更具穿透力的洞察,更重要的是對閻連科小說“曖昧”特點的提示,可謂切中肯綮。
閻連科寫作中的曖昧首先表現在細節設置上,如《受活》中帶領村民“退社”的茅枝婆的“紅四”身份及1936年這個年份的選取、《堅硬如水》中高愛軍宣布程天青“罪狀”時“上綱上線”的“虛判”,還有多部小說中出現的人鬼對話和多聲部敘述包括“絮言”結構造成的敘事線索的遲疑等等。此外還有態度和技術上曖昧手法,比如他贊賞馬爾克斯曖昧的半因果,使用普遍性的寓言化效果時仍然保持卡里斯馬人物的主體地位,將達到極限的苦難殘忍敘事與笑的風格捏在一起,熱衷于寫卑微人物的崇高美感,尋求荒誕與真實的辯證法,在同一口鍋里倒入強攻擊性、弱攻擊性、言此意彼的轉涉式攻擊性的笑和無攻擊性的民間純笑等口味不同的調料,混雜使用白話書面語、文言和民間俗語,偶然性因素被大量融合進歷史必然性等等。
寄托在這些技藝層面之上的則是思想上的曖昧:借鑒革命的思想資源卻不完全信任革命、理解烏托邦邏輯但懷疑烏托邦思維模式的普遍有效性、厭棄卻又留戀傳統文化、與毛傳統多處吻合卻拒不委身、對農民和農村的批判揭露與親近融洽、對失落的軍人英雄主義的嘲弄和哀嘆等等。
甚至作家本人的身份也透露出某種曖昧:同時兼具精英知識分子和農民的雙重特點,其中知識分子身份有耿直和怯懦兩種性格特征,作為農民則既樸實忠厚又不失狡黠機智,仍是體制內的學者和一定程度上疏離體制的作家,所有這些造成其頑強的斗士和軟弱的妥協者的雙重人格。可以說,閻連科作品的接連問世,其曖昧性為小說理論家和美學家們提供了糾纏不清的麻煩和可喜而充沛的談資。閻連科正是這么一個不左不右、不中不西、不知不農又亦左亦右、亦中亦西、亦知亦農的“曖昧”的作家。
但筆者并不認為閻連科的曖昧令其失色,相反由于這種猶豫不決或左顧右盼令其獲得了更超脫客觀的立場,對歷史事件不妄下判斷,而是盡可能呈現原貌,進而能夠比其他人更逼近混沌不清或機關重重的歷史現場,更能理解歷史發生的玄奧,這似乎是一種更為睿智的歷史態度。作家在一次講座過后的互動環節透露:“如果一篇小說你看它有意義,你想得很清楚、說得很清楚,我覺得那確實就不用去寫了,隨便寫個散文、寫個隨筆、寫個言論、寫個雜文把它講清楚就完了,不要去寫小說。我特別煩一部小說30塊錢、50塊錢,35萬字、55萬字,結果看起來就和《南方周末》的一篇報道一模一樣的意思,你叫我看它干什么?這是浪費大家的時間。所以我認為寫作的意義,首先是作家說不清的,你必須意識到它有,但是你又說不清,這個時候你可以寫給讀者,否則你就是對讀者的不尊重。你說了清清楚楚的30萬字,那讓一個哲學家寫一行字就完了。我想,文學的豐富一定要超過哲學的豐富,哲學能把它講清楚,你就不要去講它。”[3](P97)正是曖昧含混的寫作姿態和謙虛謹慎的做人品格,賦予了閻連科小說既不同于傳統現實主義的某些自居歷史闡釋者的心態,又不同于“新時期”后諸多文學流派各不相同的對歷史和政治態度的片面與武斷。
其實從閻連科本人的性格來說,他更想做的并不首先是反抗,而是清晰地表達自己的立場:“現實主義可能有很多種,你有你的現實主義,我有我的現實主義,但是文學史上形成了一種觀念,認為只有符合這個的才是現實主義。就是這種現實主義,影響著中國的發展。”[4](P35)或許是作家感受到的“傳統”的壓力已經令作家無法承受,才會有某種帶有反抗色彩的行為。
如果以史為鑒,不難發現其實今天看來勢力龐大根基深厚的“傳統現實主義”也經歷了如閻連科一般的調整變革階段:“在五四時期,‘現實主義'是作為一場更為宏闊的中國現代化和文化變革運動的一分子而被熱情接受的。然而,1920至1930年間,每一個主要的參與者都發現現實主義其實無力回天,無法兌現它所承諾的社會影響。為了擺脫這種可見的宿命,中國作家有時會另辟他途,……這樣一來,現實主義模式的局限在遭到質詢的同時,它的表現型潛能也得到了開掘。”[5](P184)現實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歷程中,作家們從未停止協調現實主義創作模式與現代化目標、民族獨立任務、服務人民的目的和同政治實踐的相處姿態等內外因素的關系。再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這種協調的任務再度被提出,可以說閻連科所謂“神實主義”的出現有歷史的合理性,閻連科所做的只不過是接過了以往歷代前衛作家或者進步作家的歷史責任,畢竟他并沒有像之前更多作家那樣放棄現實主義,而是本著修補、規正現實主義的愿望扎扎實實地開墾歷史與現實的原野。
這樣理解閻連科的曖昧,就會發現“曖昧”其實為作家和文學發展提供了一個緩沖地帶,退回到這個地帶讓各種想法在這里碰撞,以期找到現實主義既延續又拓新的發展前路,曖昧實際是化解僵局的途徑:“用教條主義的尺度一貫地拋棄一切不是表現‘現實'的東西,是嚴格和縮小現實主義,特別是模糊了藝術發展的一個基本問題:像通常所說的文化繼承問題。……在一個專橫強權企圖帶上科學的面具、教條主義企圖擺出藝術面孔的世界上,羅杰·加洛蒂的書是一件大事。正是作為現實主義者——不要弄錯,是作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者——我要向他的那種從容不迫的大膽致敬。”[6](P89)在這一點上,閻連科表現出了與卡夫卡一定程度的相似:“他絕不是樂觀主義者,因為他在消除異化的根源時,看不到也拿不出改變世界的手段。他也絕不是悲觀主義的,因為他任何時候都不甘心忍受世界的荒謬和厄運。他也決不是一個屈從者。……卡夫卡不是一個革命者。……卡夫卡也不是一個反革命:他對壓迫人的當局和他們掌握近乎上帝的權力的奢望感到狂怒,他認清了資本家們在虛偽的箴言或機構的掩飾下的利益。……卡夫卡不是一個無神論者,……然而卡夫卡也不是一個神秘主義者。”[7](P145-147)因此大概可以認為,“曖昧”是閻連科超越之前現實主義作家作品并獨樹一幟的最精當的概括。
“重審傷痕文學歷史敘述的可能性”
閻連科用“曖昧”的寫作姿態對他認為已經束縛住他和文學發展的傳統現實主義模式進行超越,在作家的理解里,“超越”不等于“跨過”。比如他說要超越意識形態,超越政治,但明確表示不能回避政治;要超越主義,超越現實主義,但仍然給予現實主義很多溢美之詞①。
孫郁不無洞見地認為閻連科依據的仍是“寫實的傳統”,“現實主義的理論在中國流行多年了,已經成為窒息創作的僵死的模式。他的詛咒現實主義,其實是對流行的話語解釋權的疏離,而本質上與傳統的理念差異甚微。所以在闡釋這一美學觀時,他顯得有點概念混亂。”[8](P21)程光煒同樣富于雄辯地指出:“如果說趙樹理逼真的寫實給他帶來了極大的現實麻煩的話,而閻連科的超現實手法則是一種掩飾現實的修辭手段,他的精神世界事實上是一直與趙樹理骨肉相連、血氣相通的。……閻連科的‘超現實'小說其實不是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而是立足于充滿鮮活生命力的中國特色上的。說到底,他只是一個口頭上的馬爾克斯,卻是一個徹底的趙樹理主義者。由此反觀二十年來中國的鄉村題材寫作,雖然搬來了福克納、馬爾克斯、略薩、卡彭鐵爾,還有沈從文、孫犁等等,他們所書寫、重提并深化的原來不過是趙樹理式的那些中國農民的話題。作為文學史的一個元話語,趙樹理的意義也許并不是他狹義的小說所能代表的,他的意義在于農民與現代中國的矛盾是始終存在的。”[1](P61)
數年之后再次確認了閻連科的這一文學史價值:“我們今天再讀傷痕文學的時候,我們每個人經歷過的歷史并沒有放到傷痕文學里面來。因為傷痕文學是一個預設的、事先規劃好了的文學地圖,所以很多東西都沒有進來。……那段歷史沒有被裝到文學里,傷痕文學在今天看它的局面就非常小了。傷痕文學是一個起點——30年文學的一個起點過早的結束了。……我覺得曉明老師說的很好——有各種各樣的現實主義,但它有個基本功能不變,就是幫助我們認識生活。”
程光煒教授得出如此結論,與其之前厚重的研究積累密不可分。在論及1980年代文學的發生中的“主流作家”的巨大作用時,程光煒分析道:“由于上述寫作者的文學教育、題材記憶、寫作經驗和敘述方式大多來自‘十七年'的緣故,盡管出現了文學觀念、主張的‘轉型',但文學創作不可能在短時間就告別自己的‘歷史記憶'和‘文學記憶'。因此,在80年代的最初幾年中,人們對當代文學‘轉型'的理解,明顯停留在對‘十七年'時期一度被壓制的‘現實主義文學'的理解水平上。”因此,傷痕、反思小說的公眾影響力與其“回收十七年”的特征緊密關聯。進入1985年后,“文學的重心開始由傳統的‘現實主義'轉向受到西方現代派文學和拉美魔幻現實主義作品影響的‘先鋒文學',后者的文學觀念和敘述方式,對文學創作產生了越來越大的‘示范'作用。”[9](P56)閻連科的文學經驗和知識結構與尋根、先鋒小說有同構的一面,即拉美文學的深刻影響,但可以辨明作家的拉美記憶不像后者那樣奉之為精神內核,而更多只是作為外在的創作出發點,真正的神髓是俄蘇文學的神性和崇高。
十七年文學是奉俄蘇文學為圭臬的,后來又被新時期發軔的傷痕文學“回收”,故而閻連科小說從內涵來說距傷痕文學更近而較先鋒小說更遠。或者說,閻連科和傷痕文學都是始于同一個起點。此外,對于閻連科來說,傷痕文學技巧上的如下特征或許可以被挪用:“在作者的創作中,社會‘問題'是壓倒了人物‘形象'的,……換言之,題材大于藝術那種傳統的創作模式,在作者的潛意識中是根深蒂固的。”[10](P22)閻連科找到了一套與歷史展開對話的機制,并且他對問題的關注取消了傷痕文學的那種“時效性”或者說政治上的策略性,因此擺脫了后者的“問題小說”模式,成為發展了的傷痕文學。
包括程光煒在內的一些學者日益透露出對傷痕文學的不滿足,后者根源于“大膽揭露才有光明”的社會情緒激化,“這嚴重阻礙了從另一方面對這一成規的過分濫觴加以必要約束和警覺的力量的存在和發展”,同時也與政治上的“撥亂反正”同步,“如果說,‘十七年小說'是因為‘為工農兵服務'的宗旨才這樣的,那么,新時期小說為‘傷痕'服務的目的同樣也是露骨的。既然有服務的意識,當然就會有對成規的不自覺地追求。”[11](P199-200)成規不但限制了藝術形式的多樣化,更扼殺了作品思想的深刻化,傷痕文學便只能作為某種情感化的記錄,而不能為歷史發展脈絡提供某種解答或啟示。閻連科在一個更有距離優勢的時代進行了不倦的思考和探索,重新撿起傷痕文學未盡的歷史責任并且沖破了傷痕文學成規,甩開了先入為主的偏見,克服了“脫歷史化”的慣式,以極大的勇氣解剖歷史推演,正是作家創作活動的重要歷史意義。
“寫作應該有一個限度”
在認可閻連科在理論上對現實主義的開拓和文學史視野中對傷痕文學的深化這一雙重價值的同時,不能忽視往往被視為“迂腐”或“教條”的蘇契科夫的表態:“如果我們徹底地把‘無邊的現實主義'應用于藝術的話,那就不得不將任何藝術作品都看作是現實主義的,其理由是在它里邊哪怕只反映出一丁點的現實性也行,從而取消了藝術認識現實和概括現實的必要性,即藝術成為真正的現實主義藝術的必要性。”[12](P257-258)
還是不得不提到前文多次討論過的《為人民服務》。王德威認為:“《堅硬如水》的出版,代表‘文革'記憶和‘文革'敘事的又一重要突破,也已經引起熱烈討論。不論《為人民服務》如何鬧得風風雨雨,小說的成績只能說是平平,在議題的發展上,并未超過《堅硬如水》。”[13](P26)一直關注閻連科作品的梁鴻也曾坦言相告:“你的《為人民服務》被禁了也好,因為它的故事重復了《堅硬如水》。”[14](P123)與作家私交甚好的李洱也認為:“(《為人民服務》)這是閻連科最差的小說,這是閻連科影響最大的小說。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無論在海內還是海外,閻連科都將因此備受困擾。不說也罷。”[15](P481)正如各位論者的敏銳覺察,這部小說雖然有值得肯定之處,但其在藝術上、技巧上和思想上的貧弱乃至失當,足以引發我們思考。
楊慶祥表示《四書》的殘酷敘事引起了他的不快感:“歷史書寫應該在哪個地方止步,寫作應該有一個限度,用另外一種方式拯救歷史虛無主義。畢竟文學是要給人希望的,竹內好講過,文學是要讓人活的,而不是讓人去死。”[16](P58)這應當是對閻連科小說發展方向的最好勸誡,無論是對待革命、民間資源還是在殘酷敘事、方言寫作等方面,“限度”都是一個不得不考慮的問題。這些是閻連科獨樹一幟、為文壇引來新風的關鍵因素,如果程度不足則難免流于庸常,但如果突破限度,則無非是傷痕文學的“再現”或“加劇”,而不是“重述”。如果說《日光流年》等作品為閻連科贏得巨大聲譽的原因在于“曖昧”的技巧和“傷痕”的動因令其最大程度呈現了歷史的復雜性,那么《四書》等近作雖然進行了驚心動魄的藝術嘗試保持了自身獨特性,但多少因為概念化的歷史觀削弱了過去作品中歷史議題多向度的理解空間。
在作家主要涉足的兩大領域中,相比占主導地位、引起主要關注的農村題材(主要是“耙耬系列”),軍事題材(“和平軍旅系列”)在結構、語言、思想性方面的探索較少②,著力點放在對“五四”個人主義的還原:“把‘軍人'降到了‘人'的一個最基本的位置上,給作為軍人的人,寄予了最起碼的理解與尊重。其中,它對英雄主義的解構,對理想主義的反叛,……都體現的十分明確。”[17](P52)很難想象這一系列與充斥著英雄主義色彩、由卡里斯馬人物支撐起的“耙耬系列”出自同一作家之手,我們當然要為作家創作的豐富性和探索勇氣鼓掌,但不能不反思,即使不考慮受眾的閱讀期待,也不考慮“五四”時期鼓吹個人主義的具體時境,僅就這種個人主義與軍事題材的嫁接及發展前景就值得商榷。
在短篇作品《兵洞》中主人公戰士堅決保衛不敢絲毫怠慢的山洞倉庫最終被無意打開,發現里面空無一物,戰士“堅決保衛”的行為也就被消解。在和平年代,除個別國家還存在直接的軍事打擊,軍隊的各種行為很大程度上帶有一種象征意義,但不能因為“主權”這類范疇的虛空便去否定行為的意義。另外雖然每一個體必須應當被尊重,但集體或國家更大層面上的利益是否絕不能凌駕于個體和群體之上可以討論。對于國家和軍隊的大戰略是不適合用個人主義的價值觀來判斷的,個人主義只能用作對可能產生的壟斷性霸權進行勸諫的刺激機制。當然軍隊作為國家暴力機構和等級制森嚴的組織,內部可能甚至已然產生病變,這就需要閻連科這樣的作家直言諷諫,但矛頭指向不應是批判縹緲的價值觀、回歸個人主義,而是應該落實到具體的這些病變進行手術切除。可以說,閻連科的軍旅題材的價值和缺失都在于對“寫作限度”把握的成功與否。
同樣應該遵循限度的是作家別致的理論:“由懷疑‘十七年'歷史的真實性,發展到懷疑‘十七年文學'經典的藝術價值”[11](P197-198),其中潛在的邏輯或許仍是反映論模式。如果我們大膽一些,將十七年文學看成樣板戲那樣前衛的實驗藝術、浪漫主義或表現主義作品——因為按照“神實主義”的部分意見它們也是反映了當時作家心目中的真實——那么是否歷史之間便不存在決絕的矛盾?筆者的意思是,閻連科從其創作實踐中萃取的獨創性理論對撬動文學的慣性思維意義重大,但也不能將此意義無限度予以拔高。簡單地說,這種理論的意義更大程度上在于“理論上”的意義。無論是荒誕的創作風格還是“神實”的創作理念,都應該為作家驅使自如,而不應反受其治,束縛住創作的自由,以免最終導致自我標簽化。
程光煒教授分析了傷痕文學的成規后著意提出:“這一文學成規在規劃新時期初期的文學面貌的時候,也在孕育著文學創作的單一化傾向,和文學敘述的某些雷同現象,是應該指出來的。”[11](P201)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傷痕文學的成規不僅僅是一種歷史遺跡,“由于文學批評在有些年代的地位過高,文學批評的作用就被無形地放大,會過分‘干擾'文學史更為理性化的過濾、歸類和反思性的工作。”[18](P5、P90)即使及時更換了研究手段,“用‘新方法'得出‘舊結論'”的現象也屢見不鮮,這就意味著當時的文學成規很有可能經過未經沉淀的批評化的文學史結論繼續殘留在我們看待歷史的眼光中。
筆者擔心的是,這種“活化石”似的文學成規再次借助傷痕文學的復蘇和推進而沉渣泛起,或操縱作家創作思維,進而強化并合法化這種成規,或操縱部分批評尤其是以占據市場為企圖的媒體批評的思維,進而對作家創作形成不良導向。如果只看到閻連科“大膽揭露才有光明”的果敢一面,卻無視其“曖昧”中體現的對政治、歷史乃至政治哲學的高明見解,不但是對作家創作實績的嚴重低估和對作家思想的矮化,更重要的是可能會將原本出現生機的文學生態重新拖入單質化的歷史泥潭,而非螺旋式發展。本文撰寫的意圖,正是為了呈現這種“曖昧”,展示出作家反傳統的另一面即對傳統現實主義的某種謹慎的親近,以期還原作家的多層次性,并希望避免歷史上成規的回卷。
注釋:
①在提出“超越主義”的著名文章里閻連科就表達出對某一階段或內心深處的現實主義的推崇,后來解說“神實主義”時再次強調不排斥現實主義。見其《尋求超越主義的現實》(《受活》代后記)、《我的現實我的主義》和《發現小說》。
②如祝東平認為“從小說題材看,ABB型形容詞的新構,鄉土題材多于軍事題材”,《閻連科小說語言ABB型形容詞的新構》,《長春大學學報》2000年第4期,第59.當然這只是泛論,如軍旅系列的《寂寞之舞》容納傳統全知敘事、第三人稱限知敘事和二人對話等敘述方式。
[1]程光煒.閻連科與超現實主義——我讀《日光流年》、《堅硬如水》和《受活》[J].當代作家評論,2007(5).
[2]翟業軍.曖昧的繾綣——評閻連科《堅硬如水》[J].書屋,2001(11).
[3]閻連科.小說與因果:文學中的“小歷史”思考[J].名作欣賞,2011(19).
[4]閻連科,劉汀.“神”的橋梁與“實”的彼岸——閻連科訪談錄[J].中國圖書評論,2012(9).
[5][美]安敏成.姜濤譯.現實主義的限制——革命時代的中國小說[M].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
[6][法]路易·阿拉貢.論無邊的現實主義·序言[M].百花文藝出版社,2008.
[7][法]羅杰·加洛蒂.吳岳添譯.論無邊的現實主義[M].百花文藝出版社,2008.
[8]孫郁.日光下的魔影——《日光流年》、《受活》、《丁莊夢》讀后[J].當代作家評論,2007(5).
[9]程光煒.當代文學在80年代的“轉型”[J].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6).
[10]程光煒.“傷痕文學”的歷史局限性[J].文藝研究,2005(1).
[11]程光煒.經典的構筑和變動[A].文學講稿:八十年代作為方法[C].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12][蘇]Б·蘇契科夫.胡越譯.關于現實主義的爭論[A].羅杰·加洛蒂.吳岳添譯.論無邊的現實主義[C].百花文藝出版社,2008.
[13]王德威.革命時代的愛與死——論閻連科的小說[J].當代作家評論,2007(5).
[14]閻連科,梁鴻.行走在現實與學理之間[J].當代作家評論,2008(5).
[15]李洱.閻連科的聲母[A].張燕玲主編.能不憶南方——《南方文壇》年度優秀論文獎文集(2001-2009)[C].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
[16]見程光煒,邱華棟等.重審傷痕文學歷史敘述的可能性——閻連科新作《四書》、《發現小說》研討會[J].當代作家評論,2011(4).
[17]閻連科,梁鴻.巫婆的紅筷子——作家與文學博士對話錄[M].春風文藝出版社,2002.
[18]程光煒.當代文學學科的“歷史化”[A].文學史研究的“當代性”問題[A].文學史的興起[C].河南大學出版社,2009.
I207.42
A
1007-9106(2016)11-0143-05
艾翔,天津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文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