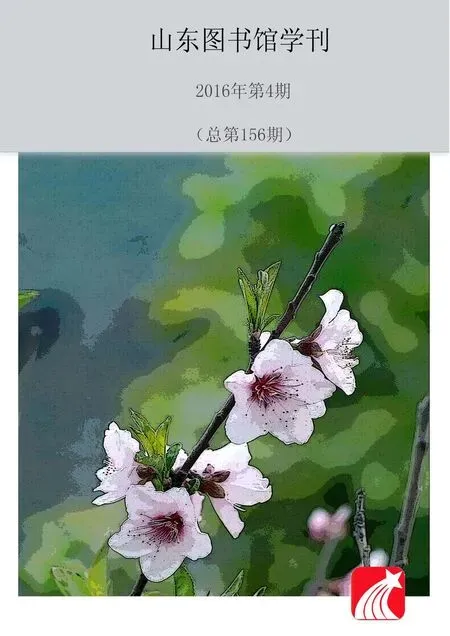我國文化管理體制改革的背景、問題及對策*
張 窈 黃先蓉,2
(1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2武漢大學信息資源研究中心,湖北武漢 430072)
?
專題研究山東圖書館學刊2016年第4期
我國文化管理體制改革的背景、問題及對策*
張窈1黃先蓉1,2
(1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2武漢大學信息資源研究中心,湖北武漢 430072)
我國文化管理體制改革的開展具有一定的歷史和現(xiàn)實原因。從2002年黨的十六大做出文化管理體制改革的戰(zhàn)略部署至今,我國的文化管理體制改革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如:“樹結(jié)構(gòu)”事業(yè)體制根深蒂固、中央頂層設(shè)計與地方實踐錯位、政府與市場關(guān)系不順、文化政策法規(guī)體系不完善等。因此必須加快體制改革的步伐,從文化管理體制的頂層設(shè)計入手,厘清政府管理職能,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guān)系,完善政策法規(guī)體系。使我國文化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突破體制障礙,實現(xiàn)社會主義文化的大繁榮和經(jīng)濟的快速發(fā)展。
文化管理體制改革政府市場制度政策法規(guī)體系
制度是在一定環(huán)境的刺激下發(fā)生反應(yīng)的一種習慣方式,雖然在某一時期具有相對的穩(wěn)定性,但是由于其本質(zhì)上要與一定社會環(huán)境下的行為、組織及程序相適應(yīng),所以制度必須隨著社會環(huán)境的變化而變化。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實踐充分證明,制度建設(shè)和制度創(chuàng)新是推動我國社會發(fā)展、經(jīng)濟增長的重要力量。文化軟實力作為當前國際競爭的重要方面,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國家對文化建設(shè)的關(guān)注度不斷提升。黨的十五大以來,確立了“大力發(fā)展文化產(chǎn)業(yè)”的方針政策;2012年,十八大報告從實現(xiàn)“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高度,提出建設(shè)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zhàn)略任務(wù);2015年,《中共中央關(guān)于制定國民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第十三個五年規(guī)劃的建議》明確將文化建設(shè)作為“五位一體”建設(shè)中的關(guān)鍵一環(huán),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文化管理體制改革作為當前我國體制改革的重要方面,是實現(xiàn)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文化強國戰(zhàn)略目標的重要途徑。
1 我國文化管理體制改革的背景
文化管理體制規(guī)定著一個國家的文化制度,對文化的發(fā)展起著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所以了解我國文化管理體制的發(fā)展過程及運行特征是把握改革力度及進度的前提,也是找出改革過程中存在問題的關(guān)鍵所在。從歷史發(fā)展來看,我國的文化管理體制本質(zhì)上是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和管理文化及意識形態(tài)的一整套方針政策、組織機構(gòu)和運作機制,“同權(quán)分割”是其基本的組織原則。隨著全球化和科技的發(fā)展,歷史遺留的體制問題越來越成為妨礙文化市場發(fā)展壯大的絆腳石,市場參與者對健康有序的市場環(huán)境的呼聲愈來愈大。近年來,中共中央在戰(zhàn)略部署上不斷深化文化管理體制改革。歷史和現(xiàn)實、內(nèi)部和外部兩組動因同時推動著改革前進的步伐。
1.1歷史原因
所謂文化管理體制,是指國家管理文化事業(yè)、文化活動的組織體系及其運行機制[1]。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參照蘇聯(lián)模式并在結(jié)合具體國情的基礎(chǔ)上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jīng)濟體制。在這種經(jīng)濟體制下,黨的一元化領(lǐng)導(dǎo)體制使得文化管理權(quán)集中在中央、在黨委。統(tǒng)一的行政命令成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20世紀50年代中國逐漸建立起了比較完備的國家文化事業(yè)體系,包括文化藝術(shù)系統(tǒng)、文物系統(tǒng)、廣播電視電影系統(tǒng)、新聞出版系統(tǒng)等,在國家宏觀層面上形成了一種以“同權(quán)分割”為組織原則、以“樹結(jié)構(gòu)”為基本形態(tài)的事業(yè)體制,并一直延續(xù)到了21世紀初期[2]。為了適應(yīng)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了文化管理體制改革的目標、任務(wù),將深化改革同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相結(jié)合。十多年來,市場機制和非國有的產(chǎn)權(quán)制度的不斷完善,文化領(lǐng)域的體制管理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作為一種“邊緣突破”[3],外層制度改革和基層文化單位的改革似乎未能觸動到體制的核心問題。歷史遺留的體制局限性使得文化領(lǐng)域政出多門,黨政不分、管辦不分等問題仍然存在,政府和政策的執(zhí)行力被限制,經(jīng)濟發(fā)展受到了阻礙。
1.2現(xiàn)實原因
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要進一步解放文化生產(chǎn)力,以適應(yīng)當前文化經(jīng)濟一體化的大潮,推動國家經(jīng)濟發(fā)展。政府作為文化管理體制改革的主體,在改革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管理制度的安排和相關(guān)文化管理政策的制定,無不影響著改革的內(nèi)容與前進的方向。因此,無論是從經(jīng)濟還是政治角度,文化產(chǎn)業(yè)發(fā)展現(xiàn)實環(huán)境的不足與日益增長的發(fā)展需求的矛盾,使得文化管理體制的改革既需要從內(nèi)打破,又需要外部推力。
1.2.1經(jīng)濟原因
在信息化、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經(jīng)濟發(fā)展越來越需要一個更加自由、開放、有序的市場環(huán)境,這對我國現(xiàn)有的管理體制形成了一種倒逼。
一方面,我國當前文化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是從計劃經(jīng)濟體制下政府文化行政管理模式中演變而來。文化領(lǐng)域內(nèi)最初的行業(yè)分工和專業(yè)分類,是被當做一種文化意識形態(tài)在產(chǎn)業(yè)形態(tài)上的表現(xiàn)形式,而并非作為一種可以創(chuàng)造經(jīng)濟效益的產(chǎn)業(yè)形態(tài)。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當前我國“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布局不合理,傳統(tǒng)文化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比重過大,制約科學發(fā)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較多”,因此要“調(diào)整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突破體制障礙”。調(diào)整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前提是調(diào)整產(chǎn)業(yè)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因此文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無疑是管理體制改革的核心。
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文化領(lǐng)域內(nèi)新興行業(yè)隨科技的進步不斷涌現(xiàn),文化企業(yè)不斷增多。截止2014年末,全國文化單位為28.74萬個,文化市場經(jīng)營單位(含互聯(lián)網(wǎng)上網(wǎng)服務(wù)營業(yè)場所、娛樂場所和民營藝術(shù)表演團體)22.00萬個[4]。媒介融合時代,社會分工更加專業(yè)化,交易范圍不斷擴大、交易層次逐漸增加,原有的管理體制使得市場交易成本不斷增加,管理更加復(fù)雜。因此急需建立一套適應(yīng)市場經(jīng)濟和當前文化領(lǐng)域發(fā)展現(xiàn)實的管理制度。
1.2.2政治原因
2002年黨的十六大做出了文化管理體制改革的戰(zhàn)略部署,將“保障公民文化權(quán)利”視為文化工作的重要目標,我國文化管理體制改革正式進入試點推動階段;2005年,“十一五”規(guī)劃建議中正式提出“公共文化服務(wù)體系”的概念;同年,《關(guān)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指出“要深化文化體制改革,以體制機制創(chuàng)新為重點,形成科學有效的宏觀文化管理體制”、“要加大公益性文化事業(yè)投入,逐步構(gòu)建公共文化服務(wù)體系”,文化管理體制改革全面展開;2011年,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guān)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2年11月,十八大報告從實現(xiàn)“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高度,提出建設(shè)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zhàn)略任務(wù)。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深化文化管理體制改革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作出部署;同年12月,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lǐng)導(dǎo)小組,主要負責“改革總體設(shè)計”“統(tǒng)籌協(xié)調(diào)”“整體推進”“督促落實”;2015年,“十三五”規(guī)劃建議中指出要“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完善公共文化服務(wù)體系、文化產(chǎn)業(yè)體系、文化市場體系”等。黨中央、國務(wù)院這一系列的政策和行動明確了我國公共文化服務(wù)戰(zhàn)略,政府由管制型向服務(wù)型過渡。根據(jù)“兩分法”的構(gòu)想,新的文化管理體制應(yīng)該兼顧公共文化事業(yè)和文化產(chǎn)業(yè),以此為依據(jù)制定發(fā)展目標、政策,構(gòu)建起符合我國現(xiàn)行市場經(jīng)濟體制的文化行政管理體制是黨和政府的政治職責所在,也是實現(xiàn)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2 我國文化管理體制改革進程中應(yīng)解決的主要問題
深化文化管理體制改革就是要掃清改革進程中的障礙、解決改革問題,而這關(guān)鍵就在于理順各方面的關(guān)系。簡而言之,就是政府與黨委關(guān)系、中央與地方的關(guān)系、政府與市場的關(guān)系,而維持這幾方關(guān)系的平衡有序必須要法律來保駕護航。由于歷史原因,我國長期以來形成的“樹結(jié)構(gòu)”事業(yè)體制根深蒂固,使得改革在推進過程中并不順暢;文化管理體制改革自上而下的特征決定了中央的頂層設(shè)計與地方實踐在現(xiàn)實對接中存在錯位的現(xiàn)象;此外,政府在文化市場管理中的行政干預(yù)和部分文化政策法規(guī)的缺失也是我國文化管理體制改革進程中急需解決的主要問題。
2.1“樹結(jié)構(gòu)”事業(yè)體制根深蒂固
我國文化管理體制一向具有高度的行政依附性,其特點是:在中央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下的“條塊結(jié)合,以塊為主,雙重領(lǐng)導(dǎo),分級管理”[5]。條、塊分別代表各級文化管理機構(gòu)和該機構(gòu)所在的當?shù)攸h政部門。這種管理體制使得我國文化事業(yè)中既有從中央到地方縱向的條條管理,又有屬地的塊塊管理。職能設(shè)計交叉,部門間的博弈使得權(quán)力與責任之間存在錯位、越位與缺位現(xiàn)象。這一方面使得市場無法自由地在資源配置中起到?jīng)Q定性作用,降低了資源使用率和市場運行效率;另一方面,條塊分割、各自為政造成的行政壁壘阻礙了公平競爭市場體系的形成。從2004年《關(guān)于文化體制改革綜合性試點地區(qū)建立文化市場綜合執(zhí)法機構(gòu)的意見》的出臺到2013年《國務(wù)院機構(gòu)改革和職能轉(zhuǎn)變方案》的頒布,我國行政管理的組織結(jié)構(gòu)從頂層設(shè)計上不斷優(yōu)化,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成立加快了我國大部制改革的步伐。但是歷史遺留的文化領(lǐng)域內(nèi)管理組織的條塊化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大部制改革的本意并不是機構(gòu)合并下管理職能的簡單歸并,而是實現(xiàn)政府文化管理職能的有效整合。如何構(gòu)建與市場經(jīng)濟體制相適應(yīng)的大文化管理職能與機構(gòu)體系仍需不斷探索。
2.2中央頂層設(shè)計與地方實踐錯位
不同于“自下而上”的經(jīng)濟體制改革,文化管理體制改革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復(fù)雜性和艱巨性。從管理學角度來看,某個行動必定由一定的動機引起。因而“自上而下”的文化管理體制改革模式就決定了文化單位在改革中的被動地位,內(nèi)在動力不足也就不足為奇。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由于我國文化管理體制改革漸進性道路的限制,使改革呈現(xiàn)出“非均衡”的特點,文化領(lǐng)域內(nèi)的區(qū)域差異、行業(yè)差異和層級差異持續(xù)擴大[6]。這使得中央無法實行整齊劃一的管理,轉(zhuǎn)而采用一定的“制度彈性”辦法。于是中央簡政放權(quán)、鼓勵地方充分發(fā)揮主觀能動性逐漸取代了中央統(tǒng)一的集中管理。政策目標的彈性策略落實到各行業(yè)、地方就轉(zhuǎn)化為具體實施路徑選擇的多樣性。這一方面給地方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立足自身探索地方改革的特色道路提供了土壤;另一方面,這種“政策縫隙”使得地方政府在利益的驅(qū)使下和中央產(chǎn)生“不良博弈”。由于我國文化領(lǐng)域的政策法規(guī)并不完善,文化績效的考評未成體系,公共資源和財政支持有限等,使得“彈性政策”成為地方政府謀取利益、推卸責任的“避彈衣”,地方化、部門化、小團體化屢見不鮮。中央與地方的“不良博弈”嚴重阻礙了文化管理體制改革的進程。
2.3政府與市場關(guān)系不順
深化文化管理體制改革的目標之一就是形成統(tǒng)一、開放、競爭、有序的文化市場體系,更大程度地發(fā)揮市場在文化資源配置方面的基礎(chǔ)性作用[7]。我國政府對文化的管理歷來是以單一的行政管理為主。新制度主義學者拉坦認為“組織與其環(huán)境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的變化是引起制度變遷的原因之一”。改革開放后,傳統(tǒng)高度整合的“一體化社會”開始向國家、市場和社會三元分立格局轉(zhuǎn)化[8]。外部環(huán)境的改變使重新調(diào)整政府組織和市場組織、社會組織之間的關(guān)系成為文化管理體制改革的“重頭戲”。近年來,在文化管理體制改革不斷推動下,政府力圖從事無巨細的“辦文化”管理方式中解放出來,走向“管人、管事、管資產(chǎn)、管導(dǎo)向”的間接管理模式。但是從現(xiàn)實的發(fā)展情況來看,文化領(lǐng)域內(nèi)產(chǎn)業(yè)集團的建立并不是市場自覺的資源配置,而是政府在壟斷政策下強制干預(yù)市場的結(jié)果。這一定程度上擠壓了其他性質(zhì)的經(jīng)營性文化生產(chǎn)單位的生存空間,擾亂了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由于市場失靈(主要有三大類:進入壁壘、外部性與內(nèi)部性)是政府管制介入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所以文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目標應(yīng)該是放松管制與優(yōu)化管制的并重[9]。將政府主動介入的范圍控制在市場失靈的范圍內(nèi),厘清政府與市場的管理邊界是實現(xiàn)深化體制改革目標的重要途徑。
2.4文化政策法規(guī)體系不完善
新制度經(jīng)濟學家諾斯認為,制度是由社會認可的非正式約束、國家規(guī)定的正式約束和實施機制三個部分組成[10]。其中,正式約束就是指人們有意識創(chuàng)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規(guī)。從我國的歷史來看,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在思想層面極具價值的東西并不比西方少,但是傳統(tǒng)的“經(jīng)驗習慣”使得我們在歷史上更加依靠約定俗成、倫理道德等非正式約束,而將價值層面的東西轉(zhuǎn)化為法律、制度較少,不少學者認為這或許是我們落后于西方國家的原因。
目前,我國文化領(lǐng)域的管理以政策規(guī)章為主,法制建設(shè)較薄弱。隨著改革的深化和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文化立法不足的問題日益突出。如法律的層級較低,部門地方法規(guī)多,國家立法少;法律法規(guī)不健全,立法盲點較多;立法內(nèi)容多偏重于管理而不是服務(wù)等。2014年10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將文化法治建設(shè)作為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方面作出部署,文化領(lǐng)域的法制建設(shè)被提上國家戰(zhàn)略日程。政治規(guī)則決定著經(jīng)濟規(guī)則,健全的法律制度是市場經(jīng)濟有序運行的有效保證,更加適應(yīng)現(xiàn)實發(fā)展需要的文化政策法規(guī)體系需要不斷被完善。
3 深化我國文化管理體制改革的對策
針對上述我國文化管理體制改革進程中的主要問題,我們需要通過大部制改革來整合、厘清政府管理職能,厘清政府與黨委、以及政府各部門之間的關(guān)系;通過加強文化管理體制的頂層設(shè)計,把握好過渡路徑來改善中央與地方的關(guān)系;通過轉(zhuǎn)變管理方式,放松管制與優(yōu)化管制并重來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guān)系;通過加強文化立法,完善政策法規(guī)體系,使我國文化管理有法可依。
3.1大部制改革背景下整合、厘清政府管理職能
加快大部制改革步伐是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國改革政府管理組織、優(yōu)化職能的一個有效途徑。但是作為一項復(fù)雜而又艱巨的任務(wù),大部制改革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循序漸進。首先要處理好黨政關(guān)系。有學者把當前實際運行的各種文化職能分為三種基本類型,即文化政治管理職能,文化經(jīng)濟管理職能、文化社會管理職能[11]。在此基礎(chǔ)上可以對相關(guān)管理機構(gòu)的管理方向做出大致的區(qū)分。由于文化的特殊性,使得文化領(lǐng)域內(nèi)的企事業(yè)單位必須堅持黨的領(lǐng)導(dǎo),因此有關(guān)社會輿論的引導(dǎo)控制和意識形態(tài)的宣傳教育應(yīng)該與黨委宣傳部門的管理對接,而有關(guān)經(jīng)濟管理和社會管理的職能應(yīng)交由政府部門承擔,優(yōu)化“黨委領(lǐng)導(dǎo)、政府管理”文化管理模式;其次要處理好部門之間的關(guān)系。大部制改革下機構(gòu)調(diào)整并不是由原來多個文化行政部門單獨行使的職能改為同一機構(gòu)下各內(nèi)設(shè)部門單獨行使。這種換湯不換藥的做法與改革的初始目的背道而馳。整合機構(gòu)設(shè)置、科學合理界定各部門的職能范圍、理順權(quán)責關(guān)系,有利于突破原有的條塊限制,降低政府管理成本,提高體制機制的運行效率。
3.2加強文化管理體制的頂層設(shè)計,把握好過渡路徑
體系的構(gòu)建是一個長期性、系統(tǒng)性的工作,需要從頂層設(shè)計、宏觀布局角度予以思考。雖然在中央向部門、地方讓權(quán)的過程中仍存在不少問題,但是由于中國國情復(fù)雜,統(tǒng)一格式化的管理并不能均衡地方的發(fā)展,所以依然要堅持中央簡政放權(quán)、地方增強主觀能動性這條道路不動搖,在此基礎(chǔ)上找到優(yōu)化管理的辦法。彌補改革內(nèi)源動力不足、改善中央與地方的“博弈”關(guān)系,就必須創(chuàng)新文化管理體制改革的辦法,用“系統(tǒng)推進”取代“邊緣突破”。相關(guān)的文化政策、財政支持要與體制改革同步推進,使地方改革單位由被動轉(zhuǎn)為主動。統(tǒng)一的文化管理的考核應(yīng)盡快建立,形成誰管理誰負責的工作模式,拒絕在權(quán)利占有情況下的責任轉(zhuǎn)移。
3.3轉(zhuǎn)變管理方式,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guān)系
改革是發(fā)展的動力,管理是發(fā)展的保證。要厘清市場與政府的制度邊緣,優(yōu)化政府的管理方式,充分發(fā)揮政府和市場這兩股力量。在具體實施中,政府一是要從管微觀向管宏觀轉(zhuǎn)變。減少中央對具體事物的把控權(quán),如各類行政審批,增強地方的自主性,從事無巨細的管理角色中走出來,著重進行大方向的把控;二是要從直接管理向間接管理轉(zhuǎn)變。計劃經(jīng)濟體制下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統(tǒng)一管理嚴重影響了市場主體創(chuàng)造財富的積極性,要改變單一的行政管理方式,學會用法律去規(guī)范、政策去引導(dǎo)調(diào)節(jié);三是要從管直屬向管社會轉(zhuǎn)變,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體制下,市場才應(yīng)該是政府管理的中心,要轉(zhuǎn)變把企事業(yè)單位作為重點對象的管理方向,切實扮演好市場監(jiān)管的角色,為文化單位的經(jīng)營發(fā)展提供良好的環(huán)境。市場、政府應(yīng)充分發(fā)揮作用,實現(xiàn)文化市場管理中的多元共治。
3.4加強文化立法,完善政策法規(guī)體系
道格拉斯·C·諾斯認為:由于缺少進入有法律約束和其他制度化社會的機會,造成了現(xiàn)今發(fā)展中國家的經(jīng)濟長期停滯不前[12]。所以要實現(xiàn)經(jīng)濟穩(wěn)定持續(xù)增長,就必須建立與文化管理體制改革相適應(yīng)的政策法規(guī)體系,實現(xiàn)文化市場秩序的法制化。首先要加強文化領(lǐng)域基本法的建立。由于我國構(gòu)建“公共文化服務(wù)體系”戰(zhàn)略目標的設(shè)置,使文化產(chǎn)業(yè)和公共文化成為我國文化領(lǐng)域并駕齊驅(qū)的重點項目。“十三五”規(guī)劃建議中明確提出要推動文化產(chǎn)業(yè)與公共文化融合發(fā)展。因此需要《公共文化服務(wù)保障法》和《文化產(chǎn)業(yè)振興法》這樣的基本法來清楚界定文化領(lǐng)域內(nèi)的一些基本問題,為構(gòu)建完善的文化法律體系和實現(xiàn)二者融合發(fā)展保駕護航。其次,要提升立法層次、均衡地方立法。除了《著作權(quán)法》《廣告法》《文物保護法》等少數(shù)法律出自全國人大,文化市場內(nèi)大部分現(xiàn)行的規(guī)章制度都是由各部委制定,法律層級和效力均不高,各地方、部門立法的成果參差不齊。最后,完善文化市場中的單行法。信息技術(shù)帶來了大媒體、大融合時代,也使文化市場上涌現(xiàn)了一批新興行業(yè)。由于法律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滯后性”,使這些新興的文化產(chǎn)業(yè)領(lǐng)域還存在一定的立法空白。所以必須健全文化立法的類別,保證政府管理有法可依。
〔1〕蒯大申,饒先來.新中國文化管理體制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
〔2〕傅才武.中國文化管理體制:性質(zhì)變遷與政策意義[J].武漢大學學報,2013(1):69
〔3〕楊步國.傳媒體制創(chuàng)新研究[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45
〔4〕文化部財務(wù)司.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2014年文化發(fā)展統(tǒng)計公報[EB/OL].[2016-1-24].http://zwgk.mcprc.gov.cn/auto255/201505/t20150525_30342.html
〔5〕蒯大申,饒先來.新中國文化管理體制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63
〔6〕傅才武,陳賡.論文化創(chuàng)新戰(zhàn)略的確立與文化管理體制的轉(zhuǎn)型[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10(11):108
〔7〕劉克利,欒永玉.中國文化體制改革與建設(shè)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127
〔8〕楊立青.中國文化營理體制改革與“制度變遷”[J].中國文化產(chǎn)業(yè)評論,2014(2):104
〔9〕郝婷,黃先蓉.我國文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背景、問題及對策[J].信息管理資源學報,2014(1):95
〔10〕沈陽.比較制度經(jīng)濟和產(chǎn)權(quán)理論[M].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3:27
〔11〕陳世香.大部制視角下中部地區(qū)政府文化管理體制改革戰(zhàn)略思考[J].中南大學學報,2010(12):19
〔12〕盧現(xiàn)祥.新制度經(jīng)濟學能統(tǒng)一社會科學嗎?[J].中南財經(jīng)大學學報,2005(1):22
Background,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Reform in China
Zhang YaoHuang Xianrong
The reform of 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in our country has certain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reasons. In 2002, the Sixteenth National Party Congress made a strategic plan for the reform of 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So far, the reform of 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in our country has made some achievements,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deeply rooted “tree structure”, the dislocation of central top-level design and local practice, the contradicto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and the incomplete cultural policy and regulation system. Therefore, we must insist on deepening the pace of administrative reform and clarifying the government management functions, straightening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and improving the policy and regulation system from the top-level design of cultural system management. As a result,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in China can break through the barriers of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achieve the socialist cultural prosperity and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Reform of 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Government; Market; Administrative system; Policy and regulation system
*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專項任務(wù)項目“文化管理體制與經(jīng)營機制創(chuàng)新研究”(15Z003)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G120
A
張窈,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2014級碩士研究生;黃先蓉,管理學博士,武漢大學信息資源研究中心研究員,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