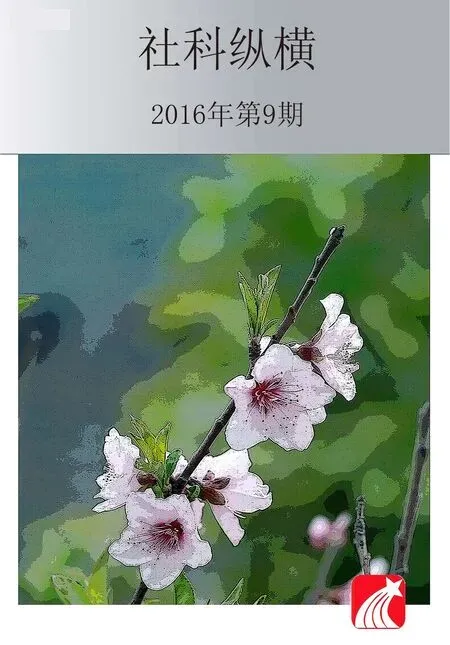陜南蘇區在川陜革命根據地建立過程中的基礎性作用
尹行創
(安康學院政治與社會發展學院陜西安康725000)
陜南蘇區在川陜革命根據地建立過程中的基礎性作用
尹行創
(安康學院政治與社會發展學院陜西安康725000)
從鄂豫皖根據地進行戰略轉移的紅四方面軍為策應中央紅軍在川陜建立了革命根據地,這其中先于陜南建立了一塊陜南蘇區,陜南蘇區一方面使紅四方面軍有了穩定的落腳地,一方面支撐了川陜革命根據地的創立,盡管陜南蘇區存在時間不長,卻在這中間起著基礎性作用。
川陜革命根據地陜南蘇區基礎作用
川陜革命根據地(1933年2月—1935年3月),是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于1932年12月戰略轉移到四川、陜西邊界地區,在川陜邊區黨組織和廣大勞動群眾的配合支持下建立的一塊蘇維埃區域。“是中華蘇維埃共和的第二個大區域”。
從鄂豫皖到川陜革命根據地,期間需越過千山萬嶺,這個千山萬嶺就是陜西南部,紅四方面軍在長途跋涉中經過陜南時,在陜南臨時建立一塊蘇區,即陜南蘇區,它是川陜革命根據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組成部分主要是與四川接壤的鎮巴、寧強、西鄉、勉縣、南鄭五縣,陜南蘇區始于1932年12月底,止于1935年4月,歷時二年四個月。
那么,紅四方面軍為何在陜南去開辟蘇區和根據地呢?陜南蘇區作為川陜革命根據地建設前的落腳點在川陜革命根據地建立過程中又起著怎樣的作用呢?
首先是陜南的自然地理條件方面符合那個時候建立蘇區和根據地的基本要求。陜南蘇區地處于中國東南和西北的結合部地區的秦巴山區,位置偏僻,山高林密,國民黨統治力量較弱。對于革命力量相對弱小的紅軍來說有利于站穩腳跟,開展土地革命活動,當時的眾多蘇區包括中央蘇區也基本上選在這樣的地方。
其次是陜南有一定的革命基礎。陜南的革命斗爭早在清末就已開始,革命者曾積極參與了清末陜西的辛亥革命活動,之后,部分先進的知識分子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下,轉向了共產革命的道路,積極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經受過革命風暴洗禮的陜南籍在外地參加中國共產黨或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青年學生,陸續回到陜南,又在家鄉掀起了新的革命高潮。
為便于統一開展革命,1929年中共陜西臨時省委就派員來到陜南,組成陜南共產黨小組并與各縣聯系。1930年春,省委又在陜南成立中共陜南特別委員會。在特委領導下,南鄭、城固、洋縣和漢中五中、女師、城固中學相繼建立起了基層組織。同時,還建立了學生自治會、討逆宣傳委員會等群眾性的外圍組織,進行革命活動。并以“抗捐稅,減田賦”相號召,發動群眾運動。
隨著形勢的發展,1931年陜南特委將工作方向由城鎮轉向農村,領導農民打擊土豪劣紳,建立工農武裝,開辟革命根據地。1931年12月,成功的說服了漢中西鄉縣私渡、廷水、駱家壩一帶當地的一股武裝力量,使其轉向革命方面,這是陜南農民武裝之始。
陜南革命基礎的堅實還可從主力紅軍來到后陜南人民的表現得到佐證,當紅軍一進入陜南商洛時,為支援配合紅四方面軍的斗爭,中共陜西省委即時發出《為歡迎紅四方面軍來陜宣言》。號召全陜一切勞苦群眾,“在工廠里、在兵營里、在學校里、在街頭上,全體動員起來,歡迎紅四方面軍來陜”。要求工人罷工,“不替國民黨制造一槍一彈去進攻紅軍”,農民“武裝起來,攻白軍,圍剿民團,不繳租,不納捐”;知識分子“罷課罷教來歡迎紅四方面軍”,白軍士兵“嘩變起來殺死你們的官長,帶槍械投到紅軍中去”[1]。當紅軍進駐漢中城固縣上元觀地區后,該地黨組織發動群眾,張貼標語,歡迎紅軍。良好的基礎是以后發展壯大的根本。
再有一個重要因素是與當時中國革命的政治發展局勢有關: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在漢口召開了“八·七”緊急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接到指示的中共陜西省委迅速調整斗爭策略,全部黨員轉入地下,革命的重心由城市轉到農村,原在北京、上海、武漢、廣州等大城市的一些陜籍黨員陸續調回本省,加強了農村地方上黨的領導力量,并具體側重于農運和武裝斗爭工作。
陜南革命的發展正是在此背景下深入的,到1927年9月,僅漢中地區約回來共產黨員30余人,在他們的帶動下,陜南民眾的革命重新燃燒起來,地方黨組織先后在寧強、城固、南鄭建立了支部,開展學運、農運,發行進步刊物。1930年2月,陜西省委派梁益堂到漢中,恢復建立了陜南特委,轄城固、洋縣、寧強等縣委,并在褒城、鳳縣、西鄉、勉縣等地發展黨員,建立組織。在此基礎上,11月在南鄭城西南的龍崗寺召開了陜南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了陜南特別委員會,創辦了特委的機關報《前驅》,翻印了一批馬列主義書籍。在宣傳上揭露和抨擊地方封建勢力和反動勢力,使黨的影響重新擴大,群眾運動穩步推進。
陜南黨組織另一個重點工作是在白軍中做兵運工作。1932年3月,陜南特委根據省委關于深入武裝割據的指示,陳淺倫在西鄉,和早在那里開辟農村工作的劉傳壁、陳明倫一起,發動農民抗糧抗捐,隨后著手組織武裝,重點是改造地方民團,變其為革命武裝,并卓有成效,不久成功地組織起七百余人的農民武裝,這為陜南游擊隊和以后的紅29軍的成立打下了基礎,極大地策應了紅四方面軍進入陜南和在陜南開辟蘇區的斗爭。
另外一點就是基于上述因素基礎上紅四方面軍正確的戰略移向:紅四方面軍全稱是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是中共在以大別山為中心建立的鄂豫皖根據地發展起來的一支人民武裝力量,是中國紅軍主力部隊之一,為革命的發展建立了赫赫戰功。但由于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影響,在面對蔣介石國民黨于1932年8月到10月的大規模第四次圍剿中,苦戰不利,不得不撤離鄂豫皖根據地,尋找新的立足發展之地。起初紅四方面軍主力沿鄂陜邊境奮戰,于11月初到達鄂皖陜邊界鄧縣之南化塘,擬在鄂豫陜邊界創建新的根據地。但敵優勢兵力尾追而至,并三面圍逼,此計劃遂之放棄。
之后紅四方面軍決定經鄂陜邊之漫川關入漢中,建立陜南根據地。不久紅軍按計劃經鄂北、豫西到達陜南,可這時在張國燾的主張下轉向北出秦嶺,于11月27日,進入關中平原,到達西安以南和西南數十里的王曲鎮、子午鎮地區。盡管給西安造成了壓力,但敵又增派了力量,反而阻斷了紅軍的前進道路,對紅軍威脅更大,逼迫再次翻越秦嶺改向漢中前進,紅軍廣大指戰員對這樣盲目的逃跑政策極為不滿。1932年12月9日經6個日夜急行軍的紅四方面軍在小河口舉行會議。這是西征以來紅軍總部舉行的第一次師以上干部會議,對張國燾推行王明路線,以及第四次反“圍剿”失敗后不明不白地無止境向西轉移進行了尖銳批評,并建議恢復軍委會,集體討論和決定重大問題。“會議的具體成果是組成了前敵委員會,委任曾中生為西北軍事委員會參謀長。雖然沒有也不可能糾正張國燾的錯誤,但也起了某些抑制作用,使張國燾獨斷專行、飛揚跋扈的軍閥作風有所收斂,對以后川陜根據地迅速創建起了積極作用”[2]。
小河口會議是一次重要的決定紅四方面軍去向的關鍵性會議,在紅四方面軍的歷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它確定了在陜西建立根據地的根本方針,停止了盲目西進,軍事上獲得了很大的主動權。敵人追擊部隊已被拋在遙遠的關中和安康地區。至此方面軍結束了歷時兩月,行程三千里的長途跋涉,擺脫了西進以來的被動局面。
在陜南建立蘇區后不久,1933年2月紅四方面軍又挺近川北,開辟了區域更大的川陜革命根據地,陜南蘇區在這其中的過渡性作用十分顯著。它使紅四方面軍迅速站穩腳跟,贏得了寶貴的喘息時間,并擴大了影響,補充了力量。正是有了這樣有力的基礎性的支持,才有以后開拓更大蘇區根據地的可能。
“紅四方面軍在川陜蘇區發展那么快,和陜西地下黨的支援是分不開的”。“川陜革命根據地及其陜南蘇區的創立與發展,也為黨領導下的陜西其他地區的革命斗爭的深入發展,提供了甚為有利的政治軍事條件。中共陜西省委和陜南特委,充分利用這一有利形勢,特別加強了黨對陜南國民黨反派統治區革命斗爭的領導,積極地支援配合整個川陜革命根據地的斗爭。”[1]
這種基礎性的支持主要表現在中共陜西省委和陜南黨組織對紅四方面軍在情報上、宣傳上、人力物力上、軍事上的全力配合。就在紅四方面軍翻越秦嶺抵達漢中時,陜南地下黨組織及時給紅軍總部送去了急需要的軍事地圖,同時發動群眾,張貼標語,宣傳共產黨的主張,紅軍的性質和政策。散發“歡迎紅軍的宣言”,以告市民告兵士書的小傳單形式—千余件,大力號召當地青年參加紅軍。城固縣委為保護紅軍安全過境,在自身武裝力量薄弱的情況下出擊,牽制敵人主力。洋縣縣委也把支持落到實處,開展“一雙草鞋運動”,在地下黨的領導下,當地群眾積極投身其中,編織草鞋、背心,捐出糧食、肉類等物資。在紅軍的幾次大戰役中,陜南地方黨組織發動人數眾多的擔架隊、運輸隊、洗衣隊,救護傷員,運送物資,洗衣補服,體現了深厚的軍民魚水情,成為戰役取勝的重要因素。陜南人民還踴躍參加紅軍,壯大了紅軍的力量,據漢中地區有關縣在建國初期的不完全調查統計,“陜南蘇區建立前后共有4370多人參加了紅軍”[3],出現了許多父子、夫妻、兄弟以至全家幾代人同時參軍的動人情景,而這在陜南一帶山地多,耕地少,經濟十分落后的情況下是非常不容易的,從中可見陜南人民的傾力革命熱情。
以后紅軍發展的事實證明在陜南去開辟蘇區和根據地是非常正確的,紅軍在陜南迅速壯大,工農民主式的革命政權在十幾個村建立,從政治上經濟上打擊了封建地主階級,倍受國民黨反動派和封建地主階級殘酷壓迫和剝削的陜南山區的農民一經解放,他們的革命積極性空前高漲,在與反動派斗爭中,紅軍始終受到陜南人民的熱情支持。每當有戰斗發生,當地群眾“沿途送茶水、抬提架、運糧草,風云涌地支援紅軍。”“人們把戰士們攙扶到家里,換下了破爛不堪的衣服,端出了熱氣騰騰的飯菜,又眼中含著淚水給我們洗腳上藥。到了這時,我們這些挺過了那樣艱難困苦的硬漢子,也都不禁流下了熱淚。”[3]。正是這魚水相融的建設,使紅四方面軍擺脫了困難,為以后更好更大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陜南蘇區對川陜革命根據地建立的作用還體現在對紅四方面軍進軍川北給予了密切而有效的配合,可以說解除了其后顧之憂。因為陜南蘇區的蓬勃發展,嚇壞了國民黨反動派,蘇區建立不久,蔣介石就急令在陜的十七路軍孫蔚如部,川軍劉湘、田頌堯等部在四川,圍攻紅四方面軍,紅四方面軍面臨敵優勢兵力在擊破幾次圍剿后審時度勢,根據四川境內軍閥混戰方酣,無暇北顧,川北防務空虛,經濟和地理條件較之陜南更為有利的實際情況,于12月15日在陜南西鄉縣鐘家溝召開團以上干部會議。討論了“進軍川北建立川陜革命根據地”的方針、政策和意義。此后,紅四方面軍開始了向川北的大進軍。
陜南蘇區隨之堅決地予以了配合:中共陜南特委發出《為歡迎紅四方面軍發動群眾斗爭開展游擊運動創建漢南新蘇區》的緊急通知,明確提出“動員雇農分配豪紳地主糧食、土地,游擊隊積極解除豪紳地主武裝,組織攻擊白軍小部隊,破壞敵人交通運輸,搶奪敵人糧秣,配合紅四方面軍軍事行動”[3],發動群眾在西鄉、城固、洋縣、褒城、南鄭、勉縣、寧強開展游擊戰爭。1933年1月6日,紅軍解放通南巴后,中共陜南特委為更好地配合紅軍行動,作了《擴大西鄉城固邊新蘇區創建紅29軍的決議》。2月24日,以川陜邊區游擊隊為基礎,正式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29軍,陳淺倫為軍長、李艮任政治委員,在和敵人進行頑強的斗爭中,開辟了面積達250平方公里的根據地和400多平方公里的游擊區,紅29軍以后與地方武裝合編成“陜南游擊隊”,堅持開展游擊斗爭,減輕了川陜根據地的壓力,有力地保障了川陜革命根據地北線邊境的安全。
正是這種強有力的后方支持,紅四方面軍出陜南不到一個月時間,就解放了川北通江等重鎮,迅速在川北打開了局面。不久建立了規模更大、更具影響力的川陜革命根據地。可以說陜南蘇區在川陜革命根據地建立過程中是個十分必要的過渡,起著基礎性的作用。
[1]傅鐘.陜南黨組織在創建川陜革命根據地中的貢獻.
[2]許世友.紅四方面軍經陜入川經過[A].中共陜西省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川陜革命根據地陜南蘇區[C].1987.
[3]陜西黨史專題資料集(六)[A].中共陜西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川陜革命根據地陜南蘇區[C].1987.
K263
A
1007-9106(2016)09-0126-03
*本文為四川革命老區發展研究中心立項項目(編號:SLQ2015A-03)的前期成果。
尹行創(1967—),男,安康學院政治與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