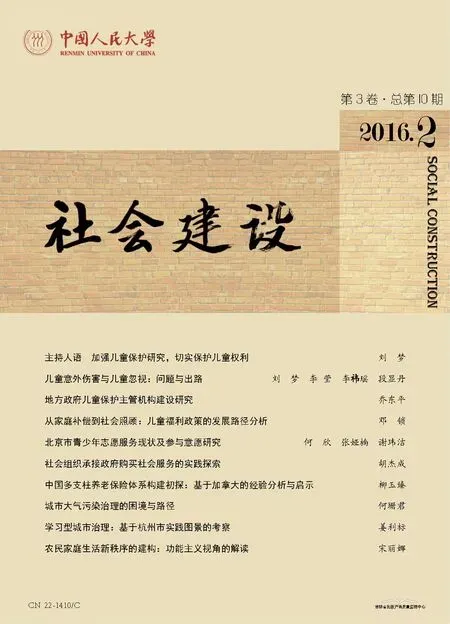農民家庭生活新秩序的建構:功能主義視角的解讀
宋麗娜
?
農民家庭生活新秩序的建構:功能主義視角的解讀
宋麗娜
摘 要:以往人們對于家庭的認識多是從感情、倫理和道德等層面展開的,不過現實經驗卻越來越復雜。從功能主義的視角來看,農民的家庭生活新秩序正在被建構成型。本文從家庭分工、家庭關系和家庭意義三個層面來具體闡釋農民家庭生活新秩序建構的實踐機制。本文認為,代際分工構成了家庭分工重塑的核心內容,引起了家庭關系的結構性變化,進而引發了家庭的意義變遷。這種家庭生活新秩序是一種建立在家庭分工、功能分化和關系調適基礎上的有機整合系統,其中伴隨著道德的實用化與價值的個體化。這啟示我們,必須以全新的視角來看待家庭生活領域正在經歷的各種“危機”,順應并保障家庭生活新秩序的建構。
關鍵詞:農民;家庭生活新秩序;家庭分工;家庭關系
一、導論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發揮著基礎性的作用。對于中國人尤其如此,中國社會是以家庭為本位的社會。農民的家庭生活秩序是農村社會秩序最重要的一個維度,也是一個根本的維度。
以往人們對于家庭的認識多是從感情、倫理和道德等層面展開的。古代的“三從四德”是對于婚姻內男女關系的規范,而“三綱五常”則由家庭關系的規范推演至政治制度和社會倫理。近代以來,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所推行的“婚姻自主”可謂是對家庭關系的重構,不過,婚姻自主強調的也是男女之間的感情。因為感情、倫理和道德的因素形成了人們對于家庭的認知,因而,人們對于家庭的印象多數要從感情倫理的因素和家庭整體的因素來考慮。不過,隨著打工經濟的擴展和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人們對于家庭的印象有了變化,現在的人們談論更多的是房子、車子、財產、權力關系、婆媳關系、當家權等,這些話題與倫理道德相關,不過卻更加凸顯了理性算計的因素。現實經驗的轉變要求我們必須重構對于家庭的認知。
學界對于這種轉變的關注并不多,近幾年來頗有影響的要數閻云翔對于私人生活變革及個體道德興起的研究。①閻云翔:《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里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系1949—1999》,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第239-243頁;閻云翔:《中國社會的個體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閻云翔對“私人生活”的分析更多的是指向中國農民的家庭生活,而家庭生活是私人生活最重要的部分,私人生活的變革催生出“無公德的個人”。于是,閻云翔的關注點隨即轉移到道德變革中來,并指出近些年來我國呈現出的一些道德困境與人們生活變革之間的關聯。閻云翔所觀察到的現象無疑是真實的,中國農民的家庭生活無疑正在發生著一場悄無聲息的革命,閻云翔的落腳點是個體道德的興起,還有沒有其他的解釋?
我們在最近幾年的社會調研中也深刻地感受到了農民家庭生活領域所發生的一些巨大變化,不少人從不同層面注意到了這場變革的某些片段。如,楊華①楊華:《從農民日常算計看稅改政治邏輯的得失》,《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1)。發現熟人社會陌生化,農民學會摒棄人情而專注于日常算計;賀雪峰②賀雪峰:《論農民理性化的表現與原因——以河南省汝南縣宋莊村的調查為例》,《湛江師范學院學報》,2008(2)。認為農民正在經歷理性化進程,由此引發了代際關系的重構。農村家庭核心化趨勢明顯,分家甚至父子分家都已經成為一種流行趨勢,農民的家庭由于打工的影響而半工半耕,從而影響到他們對于家庭生活的安排。③楊華:《中國農村的“半工半耕”結構》,《農業經濟問題》,2015(9)。代際之間的關系也已開始掙脫傳統文化的羈絆,婦女地位提高,父母則操心不斷。并且,人們還發現,農民家庭生活中的矛盾與糾紛日益減少,婆媳之間似乎更加親密了。④王德福:《角色預期、人生任務與生命周期:理解農村婆媳關系的框架》,《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11(1)。以上這些不同層面的變化都在向我們昭示著一種新的家庭生活秩序的建構;相應地,道德的效度和評價系統也已經悄悄地發生了變化。
不過,盡管學界已經敏銳地捕捉到了家庭生活領域的各種新變化,可是對此的理論解釋卻不足。有人認為是家庭關系的理性化和現代化,認為中國農民已經從傳統以道德倫理為主導的家庭生活中擺脫出來,日漸形成了更加理性化和工具化的家庭關系⑤賀雪峰:《論農民理性化的表現與原因——以河南省汝南縣宋莊村的調查為例》,《湛江師范學院學報》,2008(2)。;還有人認為是現代家庭制度的確立,尤其是家庭核心化⑥王躍生:《中國農村家庭核心化分析》,《中國人口科學》,2007(5)。的趨勢意味著農民的家庭制度已經現代化了;還有人認為這是私人生活和親密關系的變革,即家庭生活領域成了農民最主要的私人生活和親密關系的領地,家庭的意義是伴隨著私人生活的興起被建構。⑦閻云翔:《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里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系1949—1999》,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第239-243頁。
顯然,以上的觀點都能夠解釋農民家庭生活中的某些側面,不過卻各有不足之處。家庭是人類生活系統的最小單位,它培養并重構了人本身,也承擔著人類社會再生產的重任。因此,保衛家庭才成為一個有價值的社會命題。本文嘗試運用功能主義的視角來重新解讀農民家庭生活新秩序的建構。本文認為,近年來家庭生活領域發生的變化正朝著功能互補、意義互構的方向演進,家庭生活秩序建立在新的家庭分工、家庭關系和家庭價值依托之上。而今的農村正在經歷著家庭分工的轉變、家庭關系的重構和家庭價值系統的再生,這個過程中,農民家庭生活新秩序初現雛形。
雖然家庭關系既包括縱向的代際關系也包括橫向的夫妻關系,但在本文中,筆者將更多著墨于代際之間在家庭分工、家庭關系和家庭意義層面的變化,這是因為,農村夫妻之間的家庭分工因為打工經濟的影響日益同構,夫妻關系更加親密,家庭對于夫妻的意義也日益同化,因而,其變化邏輯較為明晰,論述較少。相比于夫妻關系,代際之間在家庭分工、家庭關系、家庭意義的層面呈現出復雜的樣態,其中的社會機制需要仔細分析,因而著墨較多。
劉莊村位于河南省中部W縣X鎮,現有人口1227人,下轄劉莊、高莊、謝莊3個自然村,5個村民組,耕地1739畝,人均1.3畝。劉莊村2009年被定為新農村建設示范村,是全國推動基層民主自治建設試點村。劉莊村距離X鎮鎮政府4公里,距離W縣城5公里,交通方便,地理條件優越。楊樓村是劉莊村的鄰村,現有人口1045人,6個村民組,1個自然村,270余戶。筆者于2015年7月10日至7月26日,在劉莊村和楊樓村進行了為期16天的社會學調研。
二、家庭分工重塑
從家庭形式上看,如今農民的家庭形態出現了一些既有的概念很難解釋的模糊現象,分家與否成了其中一個值得討論的話題。模糊的家庭形式背后,是其實質內涵的轉變,家庭分工從原本的夫妻橫向分工為主轉變為縱向的代際分工為主,這種轉變決定著家庭形式的相應變化。
(一)分家了還是沒有分家
打工經濟興起之后,農民往往對于分家不分家的問題感到疑惑。說是分家,小兩口打工回來依然吃住在父母家中;說是沒分家,小兩口的收入自己掌握,而父母的收入則往往負擔整個家庭的日常開支。有人稱這種家庭形式為“未分家式的分家”①陶自祥:《分裂與繼替:農村家庭延續機制的研究——兼論農村家庭的區域類型》,華中科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第223-245頁。,或者“新三代家庭結構”②張雪霖:《城市化背景下的新三代家庭結構——以江漢平原農村調查為基礎》,《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5)。。依照農民的習俗,往往將是否分灶吃飯作為分家與否的標志;而學者們將家庭理解為一個經濟核算單位,認為這是區分分家與否的關鍵。通常兩者并不沖突,分灶吃飯往往也意味著經濟核算單位的分化,不過,打工經濟和由此形成的農民家庭生活形態將問題復雜化,即有可能出現兩個經濟核算單位與“吃一鍋飯”共存的情況,即在主干家庭的基礎上,年輕一代的夫婦因為外出打工形成了他們自己獨有的經濟核算單位,可是生活形態和消費支出依然保持主干家庭的形式。如果說分灶吃飯是分家的形式,而經濟核算單位的分離是實質,現今農民的家庭生活多是名實分離。
家庭生活的名實分離以打工經濟的興起為背景,以特殊的家庭分工和代際關系模式為實質內涵。家庭生活的名實分離,使得通過家庭生活的形態(主干家庭、核心家庭、聯合家庭等)來認識農民的家庭成了一個偽命題;我們需要將討論問題的起點重新回歸到其實質內涵——家庭分工和代際關系模式之上。
(二)家庭分工的變化
狹義的家庭分工主要包括生產分工和家務分工,而廣義的家庭分工則加上收入構成與消費分配。以往的家庭分工主要是指以男主外女主內為主要表現形式的橫向夫妻分工。男人養家糊口,女人養兒育女。不同輩分男人的技能世代相傳,而不同輩份的女人共同生存于家庭生活的空間中。這種家庭分工主要是夫妻分工,代際之間主要是由于自然的身體衰減而形成的傳承關系,而非分工。而今的家庭分工很不同于以往的這種模式,具體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討論。
首先,生產分工可以用半工半耕來概括。打工經濟興起之后,農民的家庭形成了以代際分工為主要表現形式的生產分工:年輕的夫婦外出務工,而年老的父母在家種田帶孩子。當然,這種通行的模式會隨著具體情況而改變。比如,離縣城較近的農村,年輕人就近打工或者經商,居住在家,而尚有勞動能力的老年人也仍舊打些零工。再比如,筆者調查的某個地方,婦女都外出務工,男人則就近打工,農民的理由是家里種田需要重體力勞動,男人常年外出務工就不能照顧家。總之,農民家庭半工半耕模式成為必然,現今的農村能夠完全脫離農業生產的家庭并不多,而完全依靠農業勞動養家的情況也很不常見。
其次,生產分工也伴隨著家務分工的適時調整,這主要來自于撫育子代的任務。撫育子代的任務本是為人父母的責任,不過如今的農村社會將這個任務分配給了祖父母輩,尤其是年老的婦女。年輕的婦女生育之后,通常會有一段時間待在農村老家,過后她們會再次外出務工,將年幼的孩子留給爺奶撫養。然而,就算是年輕的婦女不外出,她們也并不承擔主要的養育職責,因為她們通常在孩子稍大的時候便就近找個合適的工作。筆者訪談過不少50—70歲之間的婆婆,幾乎無一例外,她們都在看管自家的孫子孫女,并且開玩笑說,現在的年輕人生個孩子都是給爺爺奶奶生的,父母照管很少。小時候喂奶換尿片,長大了接送孩子上學;從幾個月開始,孩子就與爺爺奶奶朝夕相處;一直到上中學甚至大學,都是爺爺奶奶負著主要的監管責任。這種全身心的隔代撫育引起了我們的關注,我們也曾多次反問那些老年婦女,你們年輕的時候婆婆不幫忙帶孩子嗎?答案是絕不會像現在這樣帶。她們年輕的時候往往兄弟較多,爺爺奶奶對好幾個孫子孫女照管不過來,并且往往是年輕人白天勞動的時候幫忙照管,晚上回家休息的時候就將孩子送回父母身邊。當孩子數量減少(1—2個孩子),并且子輩脫離了農業生產,家務勞動也基本上被老人承擔。父母做家務帶孩子,年輕人只管安心上班。這種家務分工將代際間的家庭責任重構。以往,男主外女主內,家務原本被建構為婦女的責任,而今,家務則成了父輩的責任。
再次,農民家庭的收入構成和消費分配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年輕人務工收入和老人務農收入是一個家庭收入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年輕人的收入往往是自己的,形成單獨的經濟核算單位;老人的種田收入和零工收入則往往要支付整個家庭日常運轉的支出,甚至如果有老人條件好的話還要接濟子輩。代際之間的消費觀也很不同,年輕人的消費傾向于發展性和享受型的消費,而老人則更加務實節約,以持家消費為本色。筆者在劉莊村訪談過10位40歲以下的年輕人,其中大部分都有買車的打算,車子成了年輕人在村莊中獲取面子最主要的表征;有的年輕人對現有住房(自家宅基地建房)不滿意,希望日后能夠在城市中再買套房子。年輕人也更愿意花費成本來打扮自己,穿名牌服裝,用時尚的電子產品。與此同時,老年人的消費則主要集中在家庭日常開支上,尤其是照顧孫子女所產生的消費。不論是收入構成還是消費分配,農村家庭都產生了代際間的分化。相對于原本農村家庭單一的收入來源和簡單的消費支出來說,這種分化意味著不同領域的收入來源和不同層次的消費支出,當然,這不同領域和不同層次是并行不悖的,他們共同構成了農村家庭的收入來源和消費開支。
在家庭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生產、家務、收入、消費等)都出現了明顯的代際分化,家庭內部形成了代際之間不同的分工與定位。從夫妻分工到代際分工,這是家庭分工重塑的重要表征,也是家庭生活新秩序建構的第一步。
三、家庭關系重構
隨著社會流動和社會轉型的加劇,家庭關系也變得更加復雜,和諧與對峙共存,親密與疏離共在。我們需要重新梳理家庭關系變遷的社會機理。
(一)家庭關系變好還是變壞
農民對于家庭關系的理解也出現了矛盾之處。一方面,不少村干部認為現在的家庭關系變好了,以往頻繁出現的婆媳不和、妯娌矛盾等家庭糾紛變少了;另一方面,農民覺得親人之間(尤其是代際之間)似乎也不像以往那么親密了,代際之間無條件的倫理責任愈來愈弱化,而有條件的倫理責任卻越來越明顯。賀雪峰①賀雪峰:《論農民理性化的表現與原因——以河南省汝南縣宋莊村的調查為例》,《湛江師范學院學報》,2008(2)。認為家庭關系越來越“理性化”,而閻云翔②閻云翔:《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里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系1949—1999》,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第99-126頁。的研究卻發現夫妻之間的私密化程度和親密感越來越強烈, 還有人認為這是一種交換型代際關系③孫新華:《交換型代際關系:農村家際代際關系的新動向》,《民俗研究》,2013(1)。, 是一種“協商式民主”④鐘曉慧、何式凝:《協商式親密關系:獨生子女父母對家庭關系和孝道的期待》,《開放時代》,2014(1)。。從家庭內部的子系統看, 縱向的代際關系越來越弱化,愈來愈多的代際之間分開居住,甚至獨子也分家;而橫向夫妻關系卻越來越親密,特別是年輕的夫妻共同外出務工變得越來越重要。家庭關系的這些變化都使得問題更加復雜化,其中家庭關系是理性化了還是親密化了?家庭關系是更加和諧了還是彼此疏離了?這是一個家庭本位的圖景還是個體本位的趨勢?
(二)家庭關系變遷的社會機理
家庭關系分為橫向的夫妻關系與縱向的代際關系。以往代際關系的重要性大于夫妻關系,而今夫妻關系則愈來愈大于代際關系。⑤王躍生:《中國當代家庭關系的變遷:形式、內容及功能》,《人民論壇》,2013(23)。
在上文論述的家庭分工中,因為共同外出務工,夫妻之間在經濟地位層面日益同構,這體現了男女平等的進一步的加強。夫妻關系也在這種分工體系中打破了傳統夫為妻綱和妻依附于夫的倫理模式,夫妻之間的溝通、協商、感情、親密感變得更為重要,夫妻關系的重要性上升,甚至,代際關系要依附于夫妻關系來定位自身。
代際關系的變化可以從婆媳關系來窺見一二。在“多年的媳婦熬成婆”的關系模式中,以往婆媳之間的關系是權力繼替式;而今婆媳之間因為家庭分工的重新規劃而形成了新的關系模式,體現為現在的婆婆更加會做“婆婆”了,媳婦也更加會做“媳婦”了,婆媳之間開始呈現出其樂融融的場景。農村的不少婆婆都說,媳婦自從進門,從來沒有做飯做家務,生個孩子是為婆婆生的。一個婆婆說: “媳婦有什么不滿意的?飯來張口衣來伸手,她出門之前早早地把飯準備好,回來之后家里干干凈凈的。想吃什么說一聲,立即買回來。我像以往討好婆婆一樣討好兒媳婦,生怕她有不開心與我兒子鬧矛盾過不好。”與此同時,媳婦也更加孝敬婆婆,不少婆婆向筆者談到,兒媳婦過年過節的時候都要為老兩口買些禮物,衣服、食物、保健品等。有年輕的媳婦告訴筆者,婆婆幫忙照看孩子、做家務,自己才能安心工作掙錢,過年過節的時候為公公婆婆買些禮物是應該的,“老人高興了,家才照看得有勁啊”。
婆媳之間原本被歸為同一個生活空間——家庭,而今婆媳之間,婆婆專司照管家庭,媳婦忙于參與工作,這不同的功能定位將她們彼此之間的主要生活空間分隔,她們要相互配合才能實現自身家庭利益的最大化,于是,婆媳之間相互配合、相互尊重、相互協商成了必然。
不過,以上的這種情況有賴于幾個基本條件,第一,婆婆身體尚好,能夠承擔起做家務帶孩子的任務;第二,婆婆只有一個兒子,或者多個孫子女的年齡差距較大,婆婆在較長一段時間內能夠全身心幫忙帶一個孫子,不能讓照看多個孫子的任務分散了婆婆的精力;第三,媳婦對于婆家的生活習慣和帶孩子方式能夠較好適應。以上任何一個條件的缺失都會使得婆媳之間的關系出現斷層。筆者曾遇見一個因為以往生過一場大病而身體不方便的婆婆,不能幫忙帶孫子。婆婆對此很是內疚,談起此事便以淚洗面。她覺得幫忙帶孫子就是自己的責任,如今責任沒法完成,婆婆產生了深深的自責。而且,因為過于想念孫子,婆婆精神上也產生了一定的問題。她的媳婦曾經過節時候給她買的衣服,婆婆都不愿意收下示人,因為她覺得自己沒盡義務。筆者也曾遇見另外一位婆婆,他有兩個兒子,大兒子早年離婚,留下一個孫女,一直是老兩口照看這個孫女,現今已經十多歲,上初一了。二兒子前幾年結婚,也生了一個孫女,老二兩口在城市中有固定工作,一直希望婆婆能夠長期居住一起幫忙他們照看家和帶孩子,可是婆婆卻總是掛念大孫女而不得安心照看小孫女,對此婆婆與二兒媳婦之間多有意見,婆媳之間的關系因而變得緊張。還有另外一個婆婆,她感到自己極其委屈,孫子出生時候兒媳婦便要求請月嫂,拒絕婆婆的照顧。月嫂走了之后,婆媳之間因為生活方式和養育孩子的問題矛盾不斷,婆婆用以往照顧兒子的土經驗,而媳婦卻認為不科學不衛生。婆媳關系因而變得緊張,婆婆覺得委屈,而媳婦更覺委屈。
總的來說,代際之間的關系已經完全不同于以往講求綱常倫理下的權威關系,代際(婆媳)之間的關系開始圍繞家庭分工和功能互補進行。當代際之間能夠達成家庭分工和功能互補的一致,并且客觀條件成行的情況下,代際關系就和諧穩定;反之,代際關系會出現斷裂。
家庭關系的重構以家庭分工的重塑為基礎,它延續了家庭分工領域的代際分化與功能互補,這是家庭生活新秩序形成的第二步。
四、家庭的意義變遷
家庭分工的變化、家庭關系的變遷,使得家庭對于個體的意義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
(一)家庭是社會的細胞還是個體的歸屬
農民的生產活動因為打工被帶入了工業化,而消費生活和家庭生活則多維持了農村的特性,有人用“半城市化”①王春光:《農村流動人口“半城市化”問題研究》,《社會學研究》,2006(5)。來描述農民工的兩棲生活。不過我們認為,其對于農民根本的影響在于,家庭對于個體農民的意義發生了變化。工業化的生產活動講求效率、程序和規范化,并且其結算方式是個體化的②宋麗娜、曹廣偉:《中國式農民工的社會性質——以農民工的身份轉換為切入點》,《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1)。,即打工經濟開發了農民作為“個體”(尤其是女性)的經濟價值。之前,農村女性要在帶孩子和家務勞動中獲得其對于家庭的價值,而現在她們更愿意與自己的丈夫一起為家庭做出經濟上的貢獻。因而,家庭的重心發生了數量上的變化,以經濟收入為主要標志,以往的農村家庭只有男主人一個重心,其余成員(妻子、老人、孩子)都處于從屬地位,而今女性也愈來愈成為家庭的重心,造成了整個家庭的失衡狀態,家庭的分工和結構也隨之發生相應的調整。
問題在于,當家庭中只有男人一個重心的時候,男人只有是家庭中的一員才能維系其重心位置,女人只能依附于男性才能獲得家庭生活的合法性,而老人和孩子也因為生理弱勢而依附于“家庭”,因而這種結構共同建構出強烈的“家庭”觀念,這時候的家庭是以整體面目出現的社會細胞。當家庭中的女人與男人共享家庭重心的時候,女人就不需要通過依附于男人而建構自身的合法性,而是通過經濟收入建構自身的家庭生活合法性,老人和孩子愈加弱勢而被徹底邊緣化,這種狀況下,家庭更多成了女性心靈上的歸屬,而老人和孩子的家庭觀念也深受打擊,尤其是老人對于家庭的離心傾向增強。
這個意義上看,家庭是社會的細胞還是個體的歸屬,確實是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二)家庭意義的建構
前些年,最后一代傳統婆婆①笑冬:《最后一代傳統婆婆?》,《社會學研究》,2002(3)。抱怨孝道衰落,她們聲嘶力竭地控訴兒子媳婦的不孝。可是,仔細辨析,我們會發現,最后一代傳統婆婆的控訴更多展現的是對自己的不尊重,是對自身地位的不確認,而很少有真正的給父母缺吃短喝的情況。隨著時間的推移,最后一代傳統婆婆相繼離世。新一代婆婆是原本對婆婆反抗的兒媳婦,現今自己也成了婆婆。這代人受過婆婆的苦,就更懂得如何做婆婆。對50—70歲之間婦女的訪談,我們發現,她們控訴婆婆的理由多是婆婆不通情理,不幫忙帶孩子,對其他兒子偏心,等等。她們的控訴顯然已經脫離了道德的制約,不再無理由地服從婆婆,而代之以實用的理由,即婆婆對于自己及自己小家庭的付出不夠,自己當然有理由“不孝順”。當她們再做婆婆的時候,她們便當牛做馬討好媳婦,按照她們的說法是,“我什么事都為他們考慮得一絲不茍,媳婦根本找不出我一點的毛病。”這其中變化彰顯了一個重要的趨勢——道德的實用化。
道德的實用化指的是在講道德的時候附帶實用性的理由,或者說,實用的社會交換是主體,道德成為依附于主體的外衣。這其中的一個關鍵是實用的社會交換。兒媳婦孝敬老人的前提是婆婆對自己好,并且能有助于小家庭的發展;并且,這時候孝敬的含義已不同于傳統上對于孝敬的社會映像。孝順是建立在地位不平等基礎上的人格不平等,而今婆媳之間關系的緩和不是地位不平等的孝順,而是建立在地位平等基礎之上的功能協調和功能互補,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親密感。
另外一個值得探討的趨勢是價值的個體化。老人的存在價值是被兒子媳婦需要,他們心甘情愿付出,兒子媳婦的存在價值卻要從家庭生活之外獲得。曾有一位帶孫子的老人這樣告訴我,“我們老兩口帶孫子看家種田。”我問他兒子是否會支付給他一定的生活費用。老人挺生氣,“還給生活費,我還得給他錢呢!”老人接著說,“我就一個兒子,不給他不是神經病嗎?老人就是民政所,哪個孩子難就接濟哪個。”與此同時,年輕人對于自身價值的定位卻很少在家庭成員上。我們訪談過一個30歲的年輕人,夫妻倆在縣郊的鴻福鞋廠工作,倆人工資加起來每月5000元左右。父母在家種田照顧家和帶兩個年幼的孫女。家庭條件一般,可是這個兒子如今卻準備買車。我們發現,夫妻倆上班距離家3公里左右,平時上下班電動車足夠。年輕人告訴我們,他前幾年打工共存了4萬元錢,說要買車后,父親將手里的4萬元全部給了他,而這些錢是父親早年通過打零工存下的。他就準備拿這8萬元錢買車。問他為何要買,利用率好像不高?他說買了車出去玩方便,而且下雨上班也方便。最后他也同意說,買車的利用率并不高,而且買車要耗盡他們父子所有的積蓄。盡管如此,他還是堅持要買車。我們問他為何不拿這個錢做本錢來做點生意,他說生意風險太大,萬一賠了就一無所有了,而買車還能得了東西。他們對于自身未來沒有太多規劃,只是說看將來有個工資更高的工作就換,對于兩個女兒似乎一點也不上心,只是說父母幫忙帶,需要學習資料告訴他買回來就是。年輕人對于“車子”的熱衷超越了孩子、家庭生活質量和未來的事業規劃,車子承載了他們人生價值的重要部分。這種價值便是年輕的夫妻極其迷戀車子帶給他們的面子、優越感和方便,顯然這種價值是個體的,與其他家庭成員和家庭整體利益并不相關。
道德的實用化和價值的個體化意味著家庭對于個人來說不再“神圣”,而是理性交換和功能互補的結果,它也為家庭生活新秩序提供了新的合法性理由,這是家庭生活新秩序建構的第三步。
五、家庭生活新秩序的建構
綜上所述,農民的家庭正在經歷著家庭分工、家庭關系和家庭意義的全方位重構,日益形成一種家庭生活的新秩序。這種家庭生活秩序機制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文化對于農民生活的建構。傳統的農民家庭生活是一種倫理的建構,農民的生活安排圍繞著道德和倫理文化進行,日常互助、關系建構與權力服從最終回應的是倫理秩序的問題。于是,傳統農民的家庭生活有家庭分工,沒有功能分化,更沒有功能調適,即如涂爾干所說的的“機械團結”,結構比較僵化,比較壓抑,但是秩序統一,道德有力。而今的家庭生活秩序是一種建立在家庭分工、功能分化和關系調適基礎上的有機整合系統,其中伴隨著道德的實用化與價值的個體化,結構松散,具流動性和權益性,也即“有機團結”①[法]埃米爾·涂爾干:《社會分工論》,渠東譯,北京:三聯書店,2013。。
家庭生活新秩序的建構意味著我們必須重視家庭內部的合理分工,在此基礎上形成一個能夠促使功能互補和功能協調的規則體系,進而將家庭重新建構成為家庭成員的生活港灣和價值歸屬。
家庭生活新秩序也意味著,我們并不能總是拿著道德和倫理的視野來討論婚姻家庭問題,將家庭問題道德化很可能只會讓家庭問題變得更加無解。從功能主義的視角來看,家庭問題的出現很可能只是家庭分工不合理而引發的功能失調,也可能是因為溝通不暢而引起的功能調適不足,更可能是個人的家庭貢獻與家庭角色錯位而產生的意義危機。
(責任編輯:狄金華)
Family Construction of Peasant Family Life’s New Order —From the Functional Perspective
SONG Li-na
Abstract:People usually analyze family from emotional, ethical and moral perspective, but practical experience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complic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ism, the peasants’ family life is being constructed. This article analyzed practice mechanism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order of peasant family life from the division of family, family relationship and family significance. The conclusion is that intergenerational labor division constitutes the core content of family division, causes the structural changes of family relations, and changes the meaning of family. The new order is a kind of organic integration system based on family labor division,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and family relationship adjustment, which is accompanied by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the value of individual morality. The implication is that we should analyze‘crisis’ in family life with new perspective and protect the construction of family life new order.
Key words:farmers; family life; new order; family labor division; family relationship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生代農民工的婚戀模式及其風險應對機制構建研究”(14CSH029)、河南省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優秀學者資助項目(2016-YXXZ-14)、河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2016-gh-148)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宋麗娜,河南農業大學文法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農村社會學。(鄭州,450046)